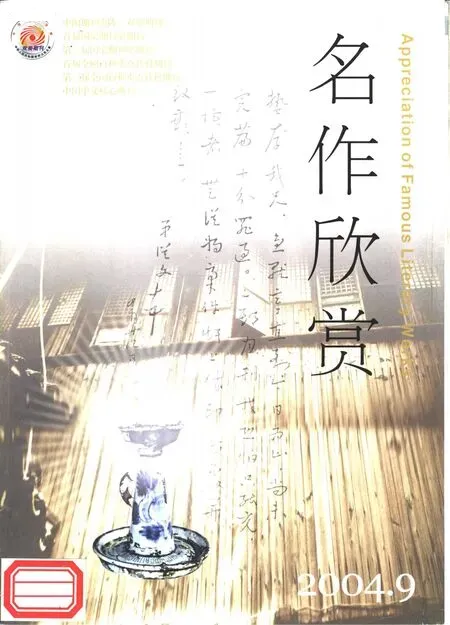袁枚選詩真講究
闕維杭
清代杭州籍詩人袁枚(1716—1797),是乾隆、嘉慶年間的“一代騷壇主”、詩壇“性靈派”旗手,他那本洋洋近60萬言的《隨園詩話》不乏自成一家的詩詞鑒賞、創作觀,足可供人揣摩,問世后一紙風行。“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記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許彥周詩話》)唐宋以降,詩詞創作繁榮興盛,詩話類的評析鑒賞文字也大行其道,至清代已然蔚為大觀。《隨園詩話》在采風、選錄大量當代各階層詩人性靈詩作之際,以隨筆筆法記事、點評,論證、彰顯其“性靈說”美學觀。在我看來,“隨園老人”袁枚的這部傳世之作,在大量采集詩壇乃至民間詩詞并做出點評方面有極大貢獻之外,也顯出他作為一個鑒賞家、詩論家兼編輯家出版的眼光與膽識。
袁枚身為名重一時的才子詩人,又長年累月地采編詩話,博聞多識,對如何選詩、選什么詩就相當講究,自有其標準。他在《隨園詩話》中稱:“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采取須嚴……嘗‘口號云‘:聲憑宮徵都須脆,味盡酸咸只要鮮。”(卷七之三十二)他當年編《隨園詩話》時,杭州、南京等地數百人爭先恐后獻上各自的詩篇(“爭以詩來,無慮百首”),以求入選為榮,哪怕僅一二摘句也心滿意足。袁枚則不以人取詩,而是看詩本身是否夠“脆”夠“鮮”。曾有人以某“巨公”之詩求入選《隨園詩話》,袁枚閱之昏昏欲睡,便直言相告:“詩甚清老,頗有功夫;然而非之無可非也,刺之無可刺也,摘之無可摘也。”(補遺卷二之七十二)。《隨園詩話》還記載一事,說是與袁枚“交好”之某太史送達詩集四十余卷,欲采數言入《隨園詩話》,袁枚“苦其太多,托門下士周午塘代勘之”。周勘閱后戲題詩回復道:“何苦老詞壇,篇篇別調彈。披沙三萬斛,檢得寸金難。”袁枚讀之“不覺大笑,戲和云:‘消夏閑無事,將人詩卷看。選詩如選色,總覺動心難”(補遺卷一之五十三)。
袁枚曾歸納“選家選近人之詩,有七病焉”,而他也坦言:“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七病也。末一條,余作《詩話》,亦不能免。”(卷十四之二)可見多少熟人乃至熟人之熟人相求選詩,有些“面子”還不能完全抹煞,然通觀整部《隨園詩話》,入選詩歌或摘句者以布衣、貧士詩人為多,并不以達官貴人為尊,甚至還有不少女子及販夫走卒之句獲其青睞而入選,這在當時文壇、社會極為難得,也與他身為詩壇“性靈派”盟主的詩歌觀與詩話編撰初衷相吻合。袁枚從不諱言“最愛言情之作”,“余每下蘇、杭,必采詩歸,以壯行色;性之所耽,老而愈篤”。凡有各方“投贈佳句,摘錄甚多”,當然入選詩句都要能是真性情之詩,概言之,無論言情狀物、記游抒懷還是詠史諷喻,總要不落俗套、各有特色才行,都是以其“性靈說”詩歌美學觀為根本,他的選詩之講究也即都落實于這根基之上。相較于某些巨公名士,袁枚稱贊“貧士詩有極妙者”,引用詩句如陳古漁:“雨昏陋巷燈無焰,風過貧家壁有聲。”“偶聞詩累吟懷減,偏到荒年飯量加。”楊思立:“家貧留客干妻惱,身病閑游惹母愁。”朱草衣:“床燒夜每借僧榻,糧盡妻常寄母家。”徐蘭圃:“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說鄰家午飯香。”皆貧語也。常州趙某云:“太窮常恐人防賊,久病都疑犬亦仙。”“短氣莫書賒酒券,索逋先長扣門聲。”袁枚稱這些詩句真情流瀉,盡顯各種窮而窘迫感。(卷三之十一)
因賞識詩作而鼓勵、提攜詩作者,在袁枚也是習以為常的舉動了。某年,他請人推薦一抄書人黃生,“人甚樸野”,一次袁枚偶爾路過黃生案頭,見黃生詠詩句云:“破庵僧賣臨街瓦,獨井人爭向晚泉。”
袁枚嘖嘖稱奇,即獎賞五斗米給黃生,獲得鼓勵的黃生從此更加努力作詩。《隨園詩話》選錄了黃生的不少佳詩妙句,五言句有:“云開日腳直,雨落水紋圓。”“竹銳穿泥壁,蠅酣落酒尊。”“釣久知魚性,樵多識樹名。”“筆殘蘆并用,墨盡指同磨。”七言云:“小窗近水寒偏覺,古木遮天曙不知。”“舊生萍處泥猶綠,新落花時水亦香。”“舊甓恐閑都貯水,破墻難補盡糊詩。”“有簾當檻云仍入,無客推門風自開。”(卷五之五)袁枚曾感慨道:“采詩如散賑也,寧濫毋遺。然其詩未刻稿者,寧失之濫。已刻稿者,不妨于遺。”(補遺卷八之二十五)他選詩始終抱有一種開放的態度,秉承以質取勝的標準之外,也盡量向沒有機會結集出詩歌的詩人傾斜,哪怕只是落第書生乃至被社會偏見鄙視的“賤工”即引車賣漿者。在袁枚幾十年的交游、采風、編撰生涯中,他接觸并意識到“詩往往有畸士賤工脫口而出者”(補遺卷十之三十八),因此《隨園詩話》也不吝篇幅,大量選錄落第秀才乃至各方社會底層人士的詩句,如收錄了“蘆墟縫人”(裁縫)吳鯤的詩:“小雨陰陰點石苔,見花零落意徘徊。徘徊且自掃花去,花掃不完雨又來。”杭州縫人鄭某詩句:“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不暖舊綿花。”又有漢西門袁某以賣面筋為業,其《詠雪和東坡》:“怪底六花難繡出,美人何處著針尖。”袁枚讀而悅目賞心,稱他們雖然“皆賤工也,而詩頗有生趣”。(補遺卷八之三十二)在《隨園詩話》卷八,隨園老人記錄道:“有箍桶匠老矣,其子時時凍餒之。子又生孫,老人愛孫,常抱于懷。人笑其癡。老人吟詩道:‘曾記當年養我兒,我兒今又養孫兒。我兒餓我憑他餓,莫遣孫兒餓我兒!”袁枚稱許此詩用意深厚。另記載家鄉一販鬻者(販賣販運之小販),不甚識字,而強學詞曲,作哭母詩云:“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袁枚點評說:“語雖俚,聞者動色。”
袁枚還對以家常語、口語入詩格外嘉許,譬如他說“家常語入詩最妙”,選錄了陳古漁《詠牡丹》詩句:“樓高自有紅云護,花好何須綠葉扶。”清初徐貫時《寄妾》詩句:“善保玉容休怨別,可憐無益又傷身。”皆為以家常俚語入詩而易于歌詠流傳者。(補遺卷一之二十五)又稱:“口頭話,說得出便是天籟。”例舉的選詩包括誦芬《冬暖》:“草痕回碧柳舒芽,眼底翻嫌歲序差。可惜輕寒重勒住,不然開遍小桃花。”黃蛟門《竹枝》:“自揀良辰去踏青,相邀女伴盡娉婷。關心生怕朝來雨,一夜東風側耳聽。”范瘦生有句云:“高手不從時尚體,好詩只說眼邊情。”又某有句云:“階前不種梧桐樹,何處飛來一葉風?”“貪著夜涼窗不掩,秋蟲飛上讀書燈。”這些詩句都是大白話,而又韻味十足。
《隨園詩話》中多次強調“詩有天籟最妙”,“童語終是真語”,對坊間各類兒童作詩也在藝術上予以肯定。有一天袁枚看兩個孩童放風箏,一童得順風大喜,另一童詠詩道:“勸君莫訝東風好,吹上還能吹下來。”袁枚聽見“深喜之”。(補遺卷七之二)又有戲村學究詩:“漆黑茅柴屋半間,豬窩牛圈浴鍋連。牧童八九縱橫坐,‘天地玄黃喊一年。”袁枚錄之,稱“末句趣極”。(卷八之三十七)又稱童子某嘲其師云:“褒衣大招方矩步,腐氣沖天天亦懼。”有太白《嘲魯儒》之意(。補遺卷六之八)《隨園詩話》補遺卷五之十記錄:“湘潭張紫峴九鉞年十三,登采石太白樓作歌,人呼‘太白后身。中有數聯云:‘乾坤浩蕩日月白,中有斯人容不得。空攜駿馬五花裘,調笑風塵二千石。自從大雅久沉淪,獨立寥寥今古春。待公不來我亦去,樓影蕭蕭愁殺人。果有青蓮風味。”
袁枚以為:“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好詩往往“妙在皆孩子語也”。長期頻繁地選詩、采風,袁枚雖然付出無數心血和時間,卻也得益不少,坦言“村童、牧豎,一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他在詩話中記錄隨園一擔糞者,某日在梅樹下欣喜報告說:“有一身花矣!”袁枚聽了后激起靈感,便吟成了一句詩:“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孕一身花。”(卷二之四)
正是采錄了大量社會低階人士乃至“賤工”之流的詩作,盡管《隨園詩話》印行前后,“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姚鼐:《袁隨園君墓志銘并序》),但也有人質疑“《詩話》收取太濫”,袁枚不理睬也不畏懼那些多來自士大夫階層的指責,坦蕩大方地回應:“然則《詩話》之作,集思廣益,顯微闡幽,寧濫毋遺:不亦可乎?”(補遺卷四之一十八)袁枚又強調:“自余作《詩話》,而四方以詩來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詩話,非選詩也。選則詩之佳者,選之而已,詩話必先有話,而后有詩。以詩來者千人萬人,而加話者,惟我一人。”說明所選之詩,都是依據他自己的鑒賞、評析而錄,即使寬泛些,也足以顯微闡幽。
選詩,能做到作品面前人人平等固然不易,但袁枚更懂得“君子不以人廢言”的道理,作為一個鑒賞力相當高的詩人,他對嚴嵩、阮大鋮等人的詩歌極為贊賞,也選取了他們的一些佳句評點,盡管他們是聲名狼藉的。在《隨園詩話·補遺》卷七之五十二節,他稱嚴嵩的《鈐山堂集》“頗有可觀,如:‘卷幔忽驚山霧入,近村長聽水禽啼。‘沙上柳松煙霽色,水邊樓閣雁歸聲。皆可愛也。”又引阮大鋮詩句道:“‘露涼集蟲語,風善定螢情。后五字頗耐想。”
袁枚,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生于錢塘(今浙江杭州),乾隆四年(1739年)考為進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步入仕途。三年后赴沭陽(今屬江蘇)、江寧(今江蘇南京)等地任知縣,由于為人正直善良,為官勤于治政,聲譽頗佳,但其詩人本色又怎能長期忍受封建官場約束羈絆,為官知縣六年后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冬天,無意仕途的袁枚即辭官歸里,離開了充滿是非和傾軋的官場。因喜愛古都金陵的山川秀色和人文氛圍,遂以“三百金”購下城內小倉山(今五臺山)麓江寧織造隋赫德的二百畝園墅“隋園”。相傳該園故址早先為明末文人吳應箕寓居金陵時的私家園墅“吳氏園”,后為曹雪芹的父親曹頫購得并改建;又因曹家后來獲罪,該園被雍正朝廷沒收,劃撥給繼任江寧織造隋赫德所用。袁枚買下隋園時,“園傾且頹弛,其室為酒肆,輿臺嚾呶,禽鳥厭之,不肯嫗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袁枚《:隨園記》),一派荒蕪雜亂景象。經他精心規劃整修,環境清幽雅致、悅目賞心,并更名“隨園”,寓意隨順自然、隨遇而安。《隨園詩話》中有不少筆墨狀寫隨園的風物環境,并說明:“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
袁枚退隱隨園近五十載,修身養性,勤于著述,怡然自樂于“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袁枚小倉山房楹聯)的金陵,除每年不定時出游神州好山好水之外,隨園就是他夢寐以求的詩意棲息地,是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書房”所在。平常歲月時有各地文人騷客造訪隨園,詩會雅集不斷,每逢四季佳日甚至對外開放,“因園中四時皆花,益以蟲鳥之音,雨雪之景,因之游人不斷,盛時年游人量達十余萬人……”(民國陳詒紱:《金陵園墅志》卷上)
袁枚畢生著述甚豐,《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新齊諧》《隨園食單》等皆為傳世之作,涵蓋文藝、評論、美學、飲食等諸多領域,影響深遠。這些成就使他與趙翼、蔣士銓并譽為以乾隆年間“江右三大家”。身為“性靈派”盟主、“一代騷壇主”,袁枚在清代詩壇四大派(另外三派為王士禛為代表的神韻派、以沈德潛為代表的格調派、以翁方綱為代表的肌理派)中獨樹一幟,開風氣之先,高舉“性靈說”大旗,橫掃沈德潛“格調說”的泥古之風與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陳腐之氣,風靡乾嘉詩壇。
《隨園詩話》博聞廣錄,所選之詩出自詩壇內外千家萬戶,不以名位取舍,不顧他者臧否。總體閱覽,袁枚呈現給世人的是帶有其個人品位和取向的作品,詩須雅致清通,更須鮮活生動,凸顯了真情、個性、詩才三方面的因素,這是“性靈說”美學詩論的主要觀點,因此縱觀整部《隨園詩話》,凸顯了袁枚獨有的審美視野以及作為一個詩人兼編輯家的眼光和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