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早上四點有雨
李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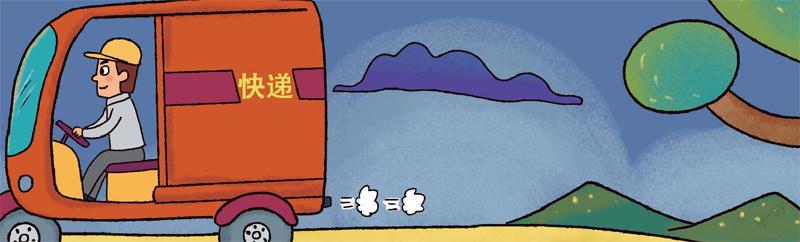

和世界失去聯(lián)系
時間確實有些趕,送完栗子街1巷和2巷客戶的包裹后,時間已經(jīng)來到了八點一刻。好吧,如果最后一位收件人接件順利的話,回程騎快點兒,一切還來得及。
我從車廂里拿出最后一個包裹,上面沒有具體的收件地址,只寫了栗子山。收件人的姓名寫著:白瑞德先生。我掏出手機,撥打白瑞德先生的電話。撥完后,電話里傳來:
對不起,您的電話已欠費,請續(xù)交話費。
隨之而來的是一條話費欠費的短信提醒。
我一開始并不以為意,心想交了話費再給白瑞德先生打電話。可是,后來,我發(fā)現(xiàn)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栗子山?jīng)]有手機充值營業(yè)廳;手機欠費連不上網(wǎng)絡(luò),就沒法在網(wǎng)上交話費;聯(lián)系不上收件人,無法得知收件人的更多信息;甚至無法刷快遞營業(yè)部的門禁卡、無法掃碼坐公交車回家。
空氣沉悶,舉目四望,我和這個世界失去了聯(lián)系。
土豆砂鍋店的老板是一只野豬
手中的包裹不沉,包裹外包裝袋印著一家雨篷布公司的名字,這里面裝的應(yīng)該是雨篷布吧,我立刻又想到了明天早上四點有雨。也許收件人就在附近,我發(fā)動車子。
遠遠地,我看見右邊小路上出現(xiàn)了三兩處燈光。我掉轉(zhuǎn)車頭開過去,燈光越來越亮。
“哈,土豆砂鍋店!”我喊了出來,把車子開向店門口。
一來確實餓了,二來想向店家打聽一下白瑞德先生,三來嘛,連上店家的無線網(wǎng)絡(luò),一切問題不就迎刃而解了嗎?
我吹著口哨,拔下車鑰匙,掀開簾子走進店內(nèi)。
兩排木頭長桌擺放整齊,一股燉菜的香味撲鼻而來。
“要吃什么?就要打烊了。”一只穿著圍裙的野豬拎著一麻袋土豆從廚房里走出來。
“你是……這家店的店主嗎?”我一臉驚愕。
“是。”野豬瞪了我一眼,遞給我一份菜單。
我瞟了一眼菜單,抬眼四處尋找寫有無線網(wǎng)密碼的單子。
“請問無線網(wǎng)絡(luò)的密碼是多少?”我找了一圈并沒有找到。
“要是餓了就坐下來吃飯。”野豬急躁地又鉆進廚房里。
“我的手機欠費了,連不上網(wǎng),沒有無線網(wǎng)絡(luò)的話我無法付賬,因為我沒有現(xiàn)金。”我把頭湊近廚房,只見灶臺的大砂鍋里正“咕嘟咕嘟”煮著一鍋食物,另一口鍋里正攤著煎餅。
“現(xiàn)在的年輕人就是不愛在家吃飯。”野豬只顧自言自語,“每次飯快做好了,臭小子就捎信來說不回家吃飯,就連下了大雨,自家地窖里的土豆被水泡了都不管。”
野豬從廚房出來,端著兩個大碗走到我跟前:“店里沒有無線網(wǎng)絡(luò),我也不用手機。這是我兒子的那份飯,他不回來,你吃吧。”
野豬把飯碗放到桌子上,自個兒端起另一碗吃起來。
既然吃了她兒子的飯,替她兒子把地窖里的土豆搬一搬也不算白吃。想到這兒,我心安理得地吃起了碗里的燉菜和煎餅。
吃飽喝足,開始干活。野豬把廚房后面地窖里的土豆搬出來,我負責把土豆運到大門口。嗬,足足二十袋土豆。
“要把土豆運到哪里去?”
“公交車上。”所有的土豆都搬出來了。
“現(xiàn)在還有公交車嗎?”我看了一下手機,都晚上十點了。
“栗子山的環(huán)山公交會過來。”野豬把用布包好的幾張煎餅也拿了出來。
趁著野豬歇下來,我問她:“你認識白瑞德先生嗎?我這里有個很重要的快遞要給他本人。”
“他的快遞?著急嗎?”野豬看著我。
“急,很急的。”
“出門沿大路直走,第三個路口左轉(zhuǎn)后的西紅柿菜地邊,他應(yīng)該會在那兒。”野豬把我領(lǐng)到店門口,給我指了方向。
告別了野豬,我騎上三輪電車直奔西紅柿菜地。
去玫瑰園找白瑞德先生
車燈前方的西紅柿菜地邊,我果然看到一個人影。
“喂,是白瑞德先生嗎?”我大喊。
人影回頭,竟然是一頭熊。
“你找誰?”對方甕聲甕氣地問。
“白瑞德先生,有他的快遞。”我朝熊揚了揚手中的包裹。
熊搖著腦袋:“我不認識你說的那位先生,不過你可以找飛毛松鼠,他是栗子山的信使,認識山上的所有住戶。”
說話的時候,熊不住地用他的小眼睛打量著我和我身后的三輪電車。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搭乘你的車回家嗎?我回家?guī)湍懵?lián)系飛毛松鼠。”熊搓著他那兩只胖乎乎的熊掌對我解釋說,“我剛剛下了皮特豬的公交車,太太急著讓我趕回家,要我在下雨前把一樓的東西都挪到二樓去。”
熊的家并不遠,我載著熊繞過西紅柿菜地,轉(zhuǎn)過一片樺樹林就到了。
“老婆子,我回來了。”車還沒停穩(wěn),熊就跳了下去。
“哦,親愛的,你終于回來了,明天早上四點有大雨。”熊太太上前輕輕抱住了熊。
熊的家像一個小型物流運轉(zhuǎn)中心,一件件裹著棉被、棉衣的家具和拔掉插頭的家用電器擠在一樓的桌子上、地板上,等待著熊這個搬運工搬到二樓去。
“親愛的,這里就交給我了,你休息會兒吧。”熊接過太太手里的兩杯茶,一杯遞給了我,“我現(xiàn)在就給飛毛松鼠寫信。”
熊放下茶杯,在一張紙上匆匆寫下幾行字,把信投進門口的信箱里。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今天晚上飛毛松鼠很忙,不過,最晚不會超過一個小時,我寫的是加急件。”熊對我說。
等待的時間,我也加入了搬運工行列。
大約半小時后,我見到了飛毛松鼠,他挎著腰包,手提著馬燈,一陣風似的出現(xiàn)在我面前。
“請問你要找白瑞德先生嗎?我們這里沒有白瑞德先生,能告訴我你找他具體有什么事嗎?”飛毛松鼠開門見山地問。說話的工夫,他的腰包“滴滴”叫了兩聲:您有兩封新的來信,請及時查收。
“白瑞德先生有個很重要的快遞,我要交給他。”我拿出那個包裹。
“是人類的網(wǎng)購包裹啊。栗子山只有他用人類的手機,會網(wǎng)購的也只有他了。沒記錯的話,他還給自己取過達西先生、羅切斯特先生這類奇奇怪怪的名字。”飛毛松鼠看了眼手表對我說,“你應(yīng)該去玫瑰園找他。”
“玫瑰園?”我立刻掏出手機想用地圖軟件搜索這個地名。
(當意識到手機欠費后,我佯裝看了下手機上的時間,現(xiàn)在是差十分鐘到十二點。)
“玫瑰園在栗子山的最東邊,還是有段距離的。”說著,飛毛松鼠的腰包又大叫起來:“您有一封特急來電,請立刻查收。”
一封信從腰包里跳到飛毛松鼠的手上。
“花貓?zhí)鷮殞毩耍毙枵堘t(yī)生,我現(xiàn)在要立刻去給河馬醫(yī)生送信。這是栗子山的地圖,你按照上面的路線走就能到玫瑰園。”飛毛松鼠遞給我一張地圖后,匆忙消失在夜色中。
轉(zhuǎn)送危房中的動物去玫瑰園
夜空仿佛被蒙上一塊厚布,看不到星星和月亮。即使騎電車行駛在山間小路上,我也絲毫感覺不到?jīng)隹臁?/p>
草叢里蟲鳴不斷,困意襲擾著我,我已經(jīng)騎了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夜間山路十分難走,還好地圖上有大路的標記,如果行進正確,拐過前面的這片林子就到玫瑰園了。
林子的一邊聲音嘈雜,在寂靜的半夜聽得尤為真切。轉(zhuǎn)過林子,我看到了一群動物:坐在小板凳上的駝背山貓、瘦骨嶙峋的鬣狗、皮毛雜亂的狐貍、拄著拐杖的黃鼠狼……
“不要停在這里,大家堅持一下,再往前走二百米就到玫瑰園了,皮特豬的公交車很快就到玫瑰園站了。”一只胖貓站在隊伍的最前頭。
聽到“玫瑰園”幾個字,我停下了車。
胖貓看見我和我的車,跑了過來,說:“你好,我是栗子山的動物警察。在大雨到來之前,我要把這些住在危房中的老年動物送到皮特豬的公交車上,可否借用一下你的車?他們實在走不動了。”
遠處的天邊劃過一道閃電。
“快上來吧!”我打開三輪車車廂門,幫著胖貓把老年動物們扶進車廂。我和胖貓決定分三批把這些動物送到玫瑰園外的空地。
車廂門就不關(guān)了,擠是擠了點,但路途不遠,我開得很慢,每趟大概兩三分鐘就到了。
皮特豬原來就是白瑞德先生
起風了,不遠處出現(xiàn)了兩道耀眼的光,原來是車發(fā)出的燈光。
“皮特豬來了,大家準備上車。”胖貓朝車駛來的方向揮舞手臂。
轉(zhuǎn)眼間,一個像巨大吐司面包的家伙停在我們面前,車頭上閃著幾個發(fā)光的字:栗子山環(huán)山公交。
車門打開,一只戴鴨舌帽的豬從車上跳下來。
“嗨,皮特豬。”胖貓同他打招呼。
這時,一滴雨珠落在我的鼻子上,開始下雨了。
皮特豬、胖貓、我和車上的熱心乘客,大家七手八腳把老年動物們攙扶上車。
公交車可真夠大的,簡直像個超級大市場。我看到了熊和他的太太、飛毛松鼠、懷里抱著三只小貓的花貓媽媽、河馬醫(yī)生……栗子山的動物們都在這里吧!車廂里堆著動物們家里沒地方放又怕被雨淋壞的家電、家具、衣服,我還看到幾十個大西瓜……
“你好,聽飛毛松鼠說,你在送我的包裹,我經(jīng)常跑車,也沒個確切地址,今晚又到處接人,讓你跑了這么遠的路,真不好意思。”皮特豬朝我走來,他脫下一只白手套和我握手。
“你就是白瑞德先生?”
“是的,在你們?nèi)祟惸抢锞W(wǎng)購總得取個像樣的人類名字,是我買的雨篷布。”
“終于找到你了!”我如釋重負地把包裹交給他。
“謝謝你,一起搭把手吧。”皮特豬和我把雨篷布牢牢地固定在公交車頂,然后他幫我把三輪車也推進了公交車。
“到車里來坐吧。”皮特豬給我找了個前排靠窗的座位。
接下來,公交車就飛馳起來了,比風還快。
早上四點下雨了
皮特豬的公交車離開玫瑰園后,在土豆砂鍋店門口停了車。
我再一次見到了野豬。
“臭小子,又是最后一個接你老媽!”野豬氣呼呼地把手里用布包著的煎餅扔給了皮特豬。
當野豬的最后一袋土豆被搬上車后,雨下大了。
雨像瀑布一樣從天而降,車廂里卻溫暖極了。皮特豬把車開到了一個安全的地方,無論下多大的雨,車廂都不會漏一滴雨。這里是栗子山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了一眼手機,現(xiàn)在是凌晨四點半。終于可以放心地睡會兒了,很快,我就靠著車窗睡著了。
- 課外生活(小學1-3年級)的其它文章
- 幽默的媽媽
- 書籍伴我成長
- 一次有趣的竹節(jié)人大戰(zhàn)
- 偏方
- 放學過三關(guān)
- 牽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