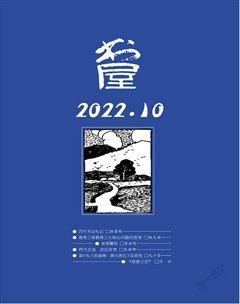兩代交誼 彌足珍貴
張昭卿
學長郭景德要我擔任《晚霞集》的編輯和校對,我欣然允諾。想起四十多年前,在文史樓聆聽錢谷融老師的現代文學課,如今在燈下閱讀他兒子錢震來的文章,不禁感慨歷史和命運交織的奇妙。其實,我只見過錢震來一面,還是在公共場合。1965新年,錢震來和他班上的幾個同學在上海中學大禮堂舞臺上表演小提琴合奏,他專注投入沉浸在樂曲中,拉琴的姿勢好像也比別人更加傳情。身邊的女同學指點著告訴我,領奏的那一個叫“錢震來”。
1977年,我進了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我們現代文學的是錢谷融教授。有人說他兒子也是上海中學的,會拉小提琴。我猜想他兒子一定是錢震來,因為兩人都姓錢,而且長得很像。我沒有當面問過錢老師,怕有套近乎之嫌。大學最后一年,我被允許旁聽研究生課,聽一位研究生說,錢教授與歷史系陳旭麓教授是親家,我想應該是錢震來娶了陳教授的女兒。
1987年,華東師大給章明分了房子,我們一家搬到了師大二村,錢谷融先生住在隔壁一幢樓。比鄰而居,見面的機會多了。早上送女兒上學,常常遇見錢先生與他的夫人從長風公園散步回來,“錢老師好!”“好!”他多半戴一頂貝雷帽,人總是客氣,笑臉相迎,回應著問候。但直到全家赴美離開師大二村,我都沒見過錢震來本人,他或許在“月黑風高夜”,“潛入細無聲”。
當我再“看見”他時,是在“北美上中群”,群里不少同學,包括他,都已邁入“耆耋”年齡。他依然很活躍,雖未聞琴聲悠揚,但時不時見他說東論西,天馬行空,有時也擺擂臺,針鋒相對,頗有見地。
后來,有了《北美上中人》期刊,我被邀請做編輯,這樣就不斷讀他的文章。很高興最近他的電子版的自選集出版,又把他的文章從頭到尾仔細讀了一遍,他的人生軌跡與文章脈絡逐漸清晰地展現在我的面前。
最先閱讀的是《在錢谷融先生追悼會上家屬答謝辭》。想起幾年前,郭秀君發給我一張照片,錢震來獨自一人推著父親的靈車前行,身上還斜挎著一個小包,我這才知道,錢谷融先生去世了。看著照片,我默默地坐著,感覺到了父與子之間那“靜靜,淌在血里的牽掛”。這篇答謝辭,我讀了好幾遍,這是一篇情辭并茂的悼念散文。錢先生的晚年,子女出國,但學校和他的弟子們對他的照顧無微不至:“父親是一名教師,他的學生就像他的孩子一樣,有他們的陪伴,晚年的父親從不寂寞。父親喜歡下棋,有人每周定時來陪老人下棋散心;父親愛到處走走看看,有人就常帶著父親去周邊轉轉,有人常來陪他談論《世說新語》,有人常陪他去長風公園散步。”“我想說,你們才是他真正的兒女。”敘述蘊情于事,細膩真切,肺腑之言,有禮得體。
面對父親,錢震來坦率真誠,告別時還不忘告訴大家“父與子”的區別。“我和逝者雖為父子,但處世為人不太相同,每代人似乎都會反叛上代人。如果說我父親相信的是‘人之初,性本善,那我看到更多的則是‘人之初,性本惡。面對惡,我父親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但仍守住了做人的底線。而我們這深感幻滅的一代則更可能會憤世嫉俗,看破紅塵,因別人作惡而自暴自棄地認為拿到了也做壞人的許可證。”
作者又說:“我想我只是自鳴得意地看到了笑臉后面的人性之惡,而我父親則再進一步在惡后面看到了善。所以,他活得比我平靜、灑脫、快樂。他雖然對別人的欺騙、出賣、惡意心知肚明,但他能理解、寬容,不求全責備,不斤斤計較。他深知人性之脆弱與無常,包括自己在內誰都不是圣人。”
文章寫父親的心態,自己的心態,舉重若輕,委婉至致,落筆看似輕簡,帶過的卻是一個老人的一生,兩代人的生命軌跡,一個時代的縮影。更令人欣慰的是,眾人也以此看到錢家家風、文風,薪火相傳。
1989年,錢震來赴密蘇里大學音樂系學習,三年后以全A成績獲得碩士學位。他縱身一躍,從文學評論轉向音樂評論。《肖邦的24與巴赫的48》寫于1991年,是他在密蘇里大學音樂系讀研時的習作,得到教授賞識與好評。這是一篇用英語寫的音樂評論,反映了作者良好的音樂理論修養和出色的英語水平。
錢震來喜歡歌劇,他說:“歌劇之所以那么有魅力,還不但是唱歌,這是集文學、戲劇、音樂、舞蹈、舞美、服裝于一身的全方位藝術,是燒金錢和燒天才的大制作。”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線上播放,不收費,他“只恨一天二十四小時太短”。他不僅自己看,還在微信群中推薦,文集中提到的歌劇就有二十多部。
從普及歌劇基本常識開始,他介紹說:“美國大都會歌劇院的海報上只并列了四位歌劇作曲家畫像:與巴赫同時代的同胞、在英國發跡的亨德爾(清唱劇),奧地利人莫扎特,意大利人威爾第,德國人瓦格納,代表了四個歌劇時代和風格。而以德語為母語的莫扎特居然有十三部歌劇用意大利語寫成,包括杰作《費加羅的婚禮》《唐·璜》《女人心》,與出名更早的同胞天才作曲家羅西尼(《塞爾維亞的理發師》等)惺惺相惜!威爾第最受歡迎的歌劇是《茶花女》《弄臣》和《阿依達》,但其他也均為上乘之作。”他推薦莫扎特的歌劇,“尤其是《費加羅的婚禮》《唐·璜》《魔笛》,更是古典音樂皇冠上的明珠”。
錢震來對歌劇的評論,最后還是落到了人與人性,編劇“對統治者也不是丑化或單純的鞭笞。而是挖掘到靈魂深處。Boris的所有唱段所表達的驚恐、悔恨、負罪感讓人看到了‘惡之后的更人性的一面”。
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是大手筆,美輪美奐,作者的文字介紹也是濃墨重彩,令人驚艷。“《指環》與冰島的神話故事聯系在一起。冰島是火與冰之地,有一種獨特的地貌,幾乎寸草不生,猶如天外星球,你可看到天氣怎樣在一天天醞釀,鬼使神差地造勢,你會直面世界原本不可見的力量,你會真相信有雷神和春之神。這里的大自然賦予視覺、聽覺及音樂創作無盡的想象力,這正是瓦格納劇本本身及勒佩杰團隊這次制作靈感之源泉”。“就如‘金木水火土,五行演變出萬物,這二十四塊枕木,猶如農歷二十四個節氣,變魔作法,在觀眾眼前不間斷地演變出四季交替,高山、大海、森林、河流,甚至戰馬、烈焰,不用落幕換景,一切連續發生,就如電影瞬時切換,就如無始無終的大自然本身,就如瓦格納永不間斷、延綿起伏的音樂”。
“反正我是極喜歡,連帶以前懶得去辨別的幾個動機都聽清楚了,還頗為享受瓦格納式龐大樂隊的寬厚豐富,起伏跌宕,一波又一波,如潮水般洶涌澎湃,讓你身如蕩漾在碧海藍天之間,演員之歌聲猶如馳過海面的海鷗,銀光點點,或如勇戰驚濤駭浪、狂風暴雨,天際盡頭,海燕如閃電般搏擊長空。總之,身臨其境,觀看了一場全景電影!”
錢震來對于群眾喜歡的節目也傾注同樣的熱情。他直言:“非常喜歡趙本山、宋丹丹的《昨天、今天、明天》及《不差錢》,起碼是讓底層農民真實地亮相了舞臺,老實又狡黠,可氣又可愛,知道這是真實,因為我們有幸上山下鄉,見過世面,要不是‘上調,本山大叔就會是咱們美麗的‘明天!”從趙本山又聯想到“阿Q”,然后比較兩者的共同點,及人物的延續性:“阿Q的形象之意義并非僅在于農民,而是某種普遍的國民性,我們至今還在阿Q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就像今天在趙本山身上也看到了我們自己的影子一般,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也不管是否傷了自視甚高者的自尊心。”
我也正巧也看過江蘇衛視的《新相親大會》。這是雙方父母都參與的大型代際相親節目,為相親家庭提供更加開放透明的“觀點碰撞空間”,也是透視現代婚姻的一個窗口。錢震來妙筆生花,挖掘出很多市井生活中的有趣元素:“有錢人飛來飛去,今朝巴黎,明日非洲,剛辭北冰洋,又赴南極洲。地球這么小,總有‘山重水復疑無路之日,與其拼死吃河豚,硬闖伊拉克,還不如聽聽財小氣不粗宅男‘柳暗花明又一村之道。最近趣味本不高的鄙人又再接再厲,更‘下一層樓,突然發現了江蘇臺的《新相親大會》,有幸見到各式家庭男女老少粉墨登場,熱鬧非凡。說實話,此節目遠勝于美國同類的相親節目,因為真實、土根,性格多樣,訴求各異,展現的不是豪華的海邊旅店、胸肌美腿,而是人的靈魂,不論多么渺小的‘你我他廬山真面目,更何況大媽們就是一本本迫不及待打開的書,一覽無余,要想讀不懂都難。此節目不但是喜劇、鬧劇、青春偶像劇,還是傷感劇。”
與錢震來同感,我在度過忙忙碌碌一天之后,晚上看看這檔相親節目,目睹蕓蕓眾生使出渾身力氣追求佳人的精彩博弈,不僅輕松有趣解乏,也通過這現代戀愛、婚姻的萬花筒,進一步讀懂社會。
2022年6月22日,同學發給我一篇文章,是華東師大毛尖教授在2015屆畢業典禮上的致辭,題目是《成為一個勇敢的人》。七年過去了,文字依然新鮮蓬勃。她有一段話說到錢谷融先生:“我的祖師爺錢谷融先生還在校園里散步,而九十六歲的錢先生還被學校里的很多百歲教授稱為‘young man。”那是2015年的華東師大校園一景。如今的錢震來確實也像一個“young man”,這是生命的傳承和呼應。
《晚霞集》給我的啟示,不僅僅是他寫了什么,更鼓舞我的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他有自己的愛好,自己青睞的園地,牽掛著,耕耘著。他關注著我們生活的世界,積極發表自己的看法,即使微不足道,也是一種個體的生命的體驗。陶淵明有“采菊東籬下”的悠然,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剛怒目”的時候。退休了,不需要再寫學術論文,不需再要交作業,但他選擇一種適合自己的寫作方法,選擇短小精悍一事一議的方法,以生動活潑的形式表達自己的看法。正如他在《怪圈》中寫道:“說不定人生真是個怪圈,遲早會回到原點。”他說自己年少時“對文學、戲劇、數學、物理、音樂、外語都先后有過興趣”,“不過父親對我一會兒學理科一會兒學音樂從來也不說什么,也不反對。我做的一切他都看不上眼,但對我寫的文章總稱贊有加”。錢先生睿智大度,尊重孩子的個性發展,包容他們愛好。也許冥冥之中確有一種命運的呼喚,相信錢先生看到他兒子的自選集,一定會笑逐顏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