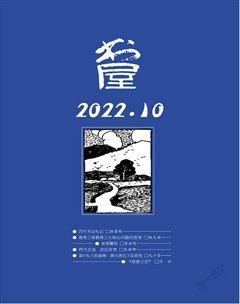略談幽閉型小說
孫旭誕
王小波寫過一篇名為《關于幽閉型小說》的文章,指斥張愛玲的小說大抵皆是此類,即小說里充溢著怨婦心理,“從早嘮叨到晚,說些尖酸刻薄的話——捕風捉影,指桑罵槐”,并直白地承認自己不喜歡:“看了以后不煩也要煩,煩了更要煩,而心煩這件事,正是多數中國人最大的苦難。”王小波還反感馬克·吐溫小說里的水手長,以為航海小說是幽閉型小說的一種。
王小波對“幽閉型小說”的定義是:“所謂幽閉類型的小說,有這么個特征:那就是把囚籠和噩夢當作一切來寫。或者當媳婦,被人煩;或者當婆婆,去煩人;或者自怨自艾;或者顧影自憐。總之,是在不幸之中品來品去。”王小波的想法很“陽光”:“我原是學理科的,學理科的不承認有牢不可破的囚籠,更不信有擺不脫的噩夢。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無能。”
王小波理念中的“幽閉”這一語詞,有著中國式的底色存在。在他的小說《紅拂夜奔》里,紅拂被囚在木制的籠子里,很能表征古代中國以纏足為象征的幽閉女性這一主題。
“幽閉”這一語詞的意涵,在中國歷史上非常不人道,是“對女犯施行的宮刑”,手法離奇多變。魯迅在《病后雜談》一文中道:“……對于女性就叫‘幽閉,向來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總之,是決非將她關起來,或者將它縫起來。近時好像被我查出一點大概來了,那辦法的兇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真使我不得不吃驚。”
在王小波眼里,船是一個幽閉之物。從張愛玲作品中,可以看出她非常喜愛小屋和船這些“幽閉”場所。在《談看書》一文里,她表達了對海盜生活的好奇與對庫克船長的偏愛。“在孩子對小屋和帳篷的迷戀上可發現這一點:把自己圈圍起來,待在里邊,這都是孩童和凡爾納心目中存在的理想狀態。”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在《“鸚鵡螺號”與“醉舟”》一文里揭示,其實這是一種對“完整性”的偏愛:“對船的喜愛總是意味著完全封閉本身充滿樂趣,手邊擁有盡可能豐盈的物品。可安排完全有限的空間:喜愛船,首先就是喜愛一所絕頂完美的房屋……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棲息地。”
羅蘭·巴特認為,大多數傳奇或小說當中的船都有點像“鸚鵡螺號”,含有令人珍愛的“幽閉”主題,因為將船呈現為人類的住所就足夠了,“讓人類在那兒即刻可安排這渾圓而光滑的天地產生的快樂”。
張愛玲在青少年時期因反抗父權而被勒令居家禁足一段時光。這一段人生經歷對她影響至深,早期長篇小說《十八春》里女主角顧曼楨遭囚禁這一情節就有張愛玲本人“幽閉”時期的個人體驗在里面。在晚期作品《小團圓》里,明顯可以看出她有著幽閉偏愛癥。在張愛玲的幸福之夢中,有“青山上紅棕色的小木屋”,有好幾個小孩,有之雍,“她醒來快樂了很久很久”。一家人,樂活在這渾圓而光滑的小木屋,就是幸福。
就小說而言,阿根廷作家胡里奧·科塔薩爾的《公共汽車》、張愛玲的《封鎖》、張大春的《懸蕩》這三篇小說,都可算是“幽閉型”小說。這里的“幽閉”一詞,更多地體現了現代心理學中的“幽閉恐懼癥”這一義項。小說家們將主角扔進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里,或者是一輛公共汽車,或者是一個索道纜車,從上車至下車,故事顯得有始有終。在這些“幽閉”的空間里,讀者仿如端坐在劇場的觀者,目視前方洞穴般的舞臺,大幕開合,戲如人生。古今中外眾多作家都將此型構作為練筆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