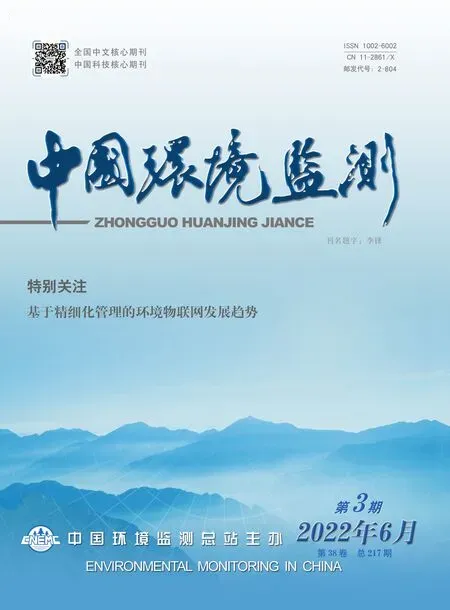瑞士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網(wǎng)絡(luò)構(gòu)建與運(yùn)行對(duì)中國的啟示
封 雪,李宗超,夏 新,李名升,姜曉旭
中國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總站,國家環(huán)境保護(hù)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質(zhì)量控制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北京 100012
為落實(shí)《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動(dòng)計(jì)劃》,中國建立了包含近8萬個(gè)點(diǎn)位的國家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網(wǎng),并于2016年開展監(jiān)測(cè)工作。與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相比,目前監(jiān)測(cè)網(wǎng)的監(jiān)測(cè)工作還處于起步階段,無論從經(jīng)驗(yàn)積累還是數(shù)據(jù)積累方面都有所欠缺。瑞士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網(wǎng)(Swiss Soil Monitoring Network,NABO)于1984年建網(wǎng),由瑞士農(nóng)業(yè)部門和環(huán)境部門主導(dǎo),瑞士農(nóng)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所具體負(fù)責(zé)網(wǎng)絡(luò)的建設(shè)和運(yùn)行。該網(wǎng)絡(luò)用于支撐瑞士國家層面土壤環(huán)境風(fēng)險(xiǎn)防控、土壤質(zhì)量保護(hù)等相關(guān)工作,經(jīng)過30余年的運(yùn)行,NABO建立了豐富和完備的指標(biāo)體系,從監(jiān)測(cè)技術(shù)、監(jiān)測(cè)網(wǎng)絡(luò)運(yùn)行、數(shù)據(jù)處理及評(píng)價(jià)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yàn)。筆者在回顧中國土壤監(jiān)測(cè)相關(guān)研究的基礎(chǔ)上,對(duì)NABO的建立背景、指標(biāo)選取、土壤監(jiān)測(cè)工作進(jìn)展等進(jìn)行分析和探討,以期為中國國家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網(wǎng)的建設(shè)工作提供參考。
1 NABO概況
1.1 NABO構(gòu)建目標(biāo)
NABO建立的主要目標(biāo)是長期在全國開展土壤監(jiān)測(cè),評(píng)估土壤物理、化學(xué)和生物性質(zhì),了解土壤環(huán)境現(xiàn)狀,開展長期變化趨勢(shì)分析,防范土壤性質(zhì)改變帶來的風(fēng)險(xiǎn)。通過監(jiān)測(cè)、模型計(jì)算等向國家和公眾提供可靠的土壤信息和服務(wù)[1]。
1.2 點(diǎn)位布設(shè)和樣品采集
1.2.1 點(diǎn)位布設(shè)
NABO綜合了土地利用類型、土壤類型和地理地質(zhì)等條件,于1984年在瑞士全境(面積為41 284 km2)設(shè)立100個(gè)監(jiān)測(cè)點(diǎn)位。點(diǎn)位土地利用類型包括集約化農(nóng)場(chǎng)、蔬菜地、果園、牧草場(chǎng)、森林和城市公園,其中以農(nóng)場(chǎng)、森林和牧草場(chǎng)點(diǎn)位居多,分別占總點(diǎn)位數(shù)的50%、33%和20%[1]。2012年,在100個(gè)點(diǎn)位的基礎(chǔ)上,新增了30個(gè)點(diǎn)位用于開展土壤生物的監(jiān)測(cè)和評(píng)價(jià)[2]。
1.2.2 樣品采集
NABO的監(jiān)測(cè)周期為5年,每年采集20%的點(diǎn)位土壤樣品。采樣時(shí)利用GPS定位目標(biāo)點(diǎn)位,在目標(biāo)點(diǎn)位周邊10 m×10 m范圍內(nèi),采集表層20 cm的土壤柱狀樣品。為保證采樣的均勻性,將10 m×10 m采樣范圍再分割為1 m×1 m的采樣方格,每4個(gè)相鄰方格進(jìn)行順序編號(hào)形成采樣序號(hào)(圖1),分別對(duì)每25個(gè)序號(hào)相同的方格采集柱狀樣品并混合為1個(gè)混合樣,共計(jì)4個(gè)混合樣。從2005年開始,除了采集表層土壤樣品外,同時(shí)采集深度為40 cm的深層樣品,而到2010年,深層樣品的采集深度從40 cm改為1 m。

圖1 10 m×10 m采樣范圍內(nèi)采樣序號(hào)示意圖[1]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ampling sequencein the sampling range of 10 m×10 m
1.3 監(jiān)測(cè)指標(biāo)
NABO在綜合評(píng)價(jià)土壤風(fēng)險(xiǎn)和質(zhì)量的基礎(chǔ)上,根據(jù)驅(qū)動(dòng)力-壓力-狀況-影響-響應(yīng)(DPSIR)模型構(gòu)建了包含物理、化學(xué)和生物指標(biāo)的綜合監(jiān)測(cè)指標(biāo)體系(表1)。

表1 土壤風(fēng)險(xiǎn)、關(guān)鍵問題與監(jiān)測(cè)指標(biāo)[1-4]Table 1 Soil risk,key issues and monitoring indicators
1.3.1 物理性質(zhì)監(jiān)測(cè)
受耕作等人類活動(dòng)的影響,土壤壓實(shí)問題在2000年以后逐漸得到關(guān)注,土壤壓實(shí)主要是由于土壤團(tuán)聚體被破壞,從而影響了土壤水、氣交換效率,最終導(dǎo)致土壤生物活性下降,嚴(yán)重影響土壤功能。從2015年開始,NABO選取部分點(diǎn)位,針對(duì)土壤壓實(shí)問題建立指標(biāo)體系,通過測(cè)定土壤物理指標(biāo)(如滲透阻力、含水量、容重和孔隙度等),衡量土壤壓實(shí)程度[3]。其中滲透阻力采用傳感器測(cè)定[1,3],測(cè)定深度為100 cm;含水量、容重及孔隙度的測(cè)定是采集深度為100 cm柱狀土樣,在觀察土樣的基礎(chǔ)上,對(duì)每5 cm土樣開展上述測(cè)定。
1.3.2 化學(xué)性質(zhì)指標(biāo)
NABO建網(wǎng)時(shí)最早關(guān)注的土壤性質(zhì)是化學(xué)性質(zhì),化學(xué)性質(zhì)的監(jiān)測(cè)從1984年至今每5年開展一次[1,4]。從監(jiān)測(cè)內(nèi)容來看,一方面是監(jiān)測(cè)土壤功能的可持續(xù)性,主要關(guān)注土壤的肥力和養(yǎng)分;另一方面是監(jiān)測(cè)土壤質(zhì)量和污染風(fēng)險(xiǎn),主要關(guān)注重金屬和有機(jī)污染物。
1.3.2.1 養(yǎng)分指標(biāo)
養(yǎng)分指標(biāo)包括土壤有機(jī)質(zhì)含量,有機(jī)碳含量,氮、磷和鉀含量等。土壤有機(jī)質(zhì)在土壤中起到貯存和緩沖作用,可以調(diào)節(jié)土壤養(yǎng)分循環(huán)與水分平衡,特別是在氣候變化條件下,土壤有機(jī)質(zhì)在保持土壤功能的長期可持續(xù)性方面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而土壤有機(jī)質(zhì)很大一部分是由碳組成,因此在監(jiān)測(cè)指標(biāo)中土壤有機(jī)質(zhì)和有機(jī)碳含量均可代表養(yǎng)分狀況。1985—2009年,監(jiān)測(cè)土壤有機(jī)質(zhì)時(shí)主要對(duì)表層土壤(0~20 cm)的土壤有機(jī)質(zhì)開展監(jiān)測(cè),2010年以后,為了進(jìn)一步測(cè)算土壤碳庫,不僅對(duì)表層土壤有機(jī)質(zhì)和有機(jī)碳含量進(jìn)行測(cè)定,同時(shí)選取深層土壤樣品進(jìn)行測(cè)定[4]。選取土壤有機(jī)質(zhì)和有機(jī)碳含量、氮、磷和鉀作為主要養(yǎng)分指標(biāo),一方面從養(yǎng)分可持續(xù)角度長期監(jiān)測(cè)土壤有機(jī)質(zhì)和有機(jī)碳含量,建立國家尺度土壤碳庫,另一方面對(duì)氮、磷元素(氮、磷等土壤養(yǎng)分流失會(huì)造成水環(huán)境污染風(fēng)險(xiǎn))進(jìn)行長期監(jiān)測(cè),進(jìn)一步說清土壤養(yǎng)分平衡和可持續(xù)性等問題。
1.3.2.2 污染物指標(biāo)
選取重金屬元素和有機(jī)污染物作為主要土壤污染觀測(cè)指標(biāo)。選取鎘、汞、鉛、鉻、銅、鋅和鎳等作為重金屬元素指標(biāo);選取多環(huán)芳烴、多氯聯(lián)苯和植物保護(hù)劑作為有機(jī)污染物指標(biāo)。
1.3.3 生物性質(zhì)指標(biāo)
為了進(jìn)一步探索土壤微生物及生物對(duì)土壤功能的影響,揭示土壤環(huán)境變化與土壤生物群落之間的關(guān)系,2012年,NABO構(gòu)建了包含動(dòng)物、微生物指標(biāo)的生物指標(biāo)體系,共同表征土壤的生物特性[2]。其中動(dòng)物指標(biāo)選取蚯蚓、小型生物生境情況作為主要觀測(cè)指標(biāo),微生物指標(biāo)包括生物量、微生物呼吸及生物活性等,選取真菌和細(xì)菌開展分子生物學(xué)測(cè)試工作,構(gòu)建土壤DNA庫。
1.4 數(shù)據(jù)、報(bào)告和信息發(fā)布
1.4.1 數(shù)據(jù)信息系統(tǒng)
2012年,NABO構(gòu)建了一整套全鏈條的數(shù)據(jù)信息系統(tǒng)(NABODAT),可廣泛收集土壤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并進(jìn)行數(shù)據(jù)處理與分析,支撐政府部門的管理決策[5]。NABODAT可實(shí)現(xiàn)對(duì)國家和各州土壤數(shù)據(jù)的更新和維護(hù)。除了政府部門的土壤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該系統(tǒng)還能收集其他機(jī)構(gòu)(如研究機(jī)構(gòu))的土壤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并在數(shù)據(jù)處理和分析中,將各來源的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與地理信息系統(tǒng)(GIS)相關(guān)聯(lián)開展綜合數(shù)據(jù)分析。聯(lián)邦政府和州政府用戶可根據(jù)權(quán)限,訪問數(shù)據(jù)庫中的原始數(shù)據(jù)和分析結(jié)果。
1.4.2 報(bào)告和數(shù)據(jù)共享
NABO在每一監(jiān)測(cè)周期結(jié)束后會(huì)編制監(jiān)測(cè)報(bào)告,由瑞士聯(lián)邦政府通過網(wǎng)站或正式出版物向公眾公開瑞士國家土壤環(huán)境狀況和變化趨勢(shì),其網(wǎng)站公開了2015年編寫完成的1984—2009年的國家土壤環(huán)境狀況。報(bào)告主要披露了環(huán)境狀況、變化趨勢(shì)和風(fēng)險(xiǎn)[1]。從數(shù)據(jù)表征方式來看,選用統(tǒng)計(jì)值描述狀態(tài),統(tǒng)計(jì)單元包括瑞士不同的土地利用類型(如草地、森林、耕地等),統(tǒng)計(jì)內(nèi)容包括各土地利用類型下土壤污染物、有機(jī)質(zhì)、pH等指標(biāo)的順序統(tǒng)計(jì)值(包含最小值、10%、50%、90%和最大值)、均值和95%置信區(qū)間;利用監(jiān)測(cè)結(jié)果與標(biāo)準(zhǔn)限值的比較反映污染風(fēng)險(xiǎn),其中標(biāo)準(zhǔn)限值選用1998年瑞士生態(tài)環(huán)境局發(fā)布的《土壤損害法令》(Osol)中的限值[6];在變化趨勢(shì)分析中,一是選用各監(jiān)測(cè)周期不同土地利用類型下的各指標(biāo)均值、95%置信區(qū)間及順序統(tǒng)計(jì)量通過圖表的形式表征變化趨勢(shì),二是將每個(gè)點(diǎn)位與《土壤損害法令》中的限制進(jìn)行比較,若2個(gè)監(jiān)測(cè)周期內(nèi)該點(diǎn)位某一監(jiān)測(cè)指標(biāo)含量變化幅度超過限值的±5%,則認(rèn)為有變化,否則認(rèn)為無變化,通過統(tǒng)計(jì)變化的點(diǎn)位數(shù),表征土壤變化趨勢(shì)。
1.4.3 數(shù)據(jù)綜合分析
NABO專門建立了數(shù)據(jù)分析模型[7],在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和評(píng)價(jià)的基礎(chǔ)上,通過模型開展數(shù)據(jù)時(shí)間和空間變化等分析,預(yù)估土壤污染風(fēng)險(xiǎn)。數(shù)據(jù)分析模型基于元素平衡進(jìn)行模型運(yùn)算,分為地表土壤模型和復(fù)雜模型,各模型均可以揭示農(nóng)業(yè)活動(dòng)對(duì)土壤功能、質(zhì)量和風(fēng)險(xiǎn)的長期影響,而復(fù)雜模型則可以分析和預(yù)測(cè)區(qū)域尺度或場(chǎng)地尺度的土壤管理、耕種對(duì)土壤特征和功能的影響。
目前,NABO主要開展4個(gè)方面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和分析(表2)[7-11]。一是利用元素平衡模型,開展各點(diǎn)位長期的元素平衡綜合分析,主要是對(duì)營養(yǎng)元素氮和磷、銅和鋅(基于農(nóng)業(yè)生態(tài)環(huán)境指標(biāo))等元素的平衡分析;二是研究人類活動(dòng)對(duì)土壤的影響,主要研究了植物保護(hù)劑和施肥等人類活動(dòng)對(duì)土壤重金屬元素和污染物累積的影響;三是利用同位素法開展土壤風(fēng)險(xiǎn)源分析;四是利用土壤過程模型,依據(jù)土壤動(dòng)力學(xué)原理,開展土壤風(fēng)險(xiǎn)預(yù)估等工作。

表2 NABO土壤數(shù)據(jù)綜合分析項(xiàng)目Table 2 Data analysis programs in NABO
1.4.4 主要監(jiān)測(cè)結(jié)果
綜合NABO各監(jiān)測(cè)周期的數(shù)據(jù)報(bào)告和相關(guān)文獻(xiàn)[1,9],1985—2009年,瑞士全國耕地、林地和草地土壤中重金屬元素鎘、鎳、鉻和鈷含量沒有顯著的變化,鉛和汞含量顯著下降,這可能與瑞士大氣環(huán)境保護(hù)政策中禁止使用含鉛汽油有關(guān)。在集約型放牧的草地土壤中銅和鋅含量顯著上升,在其他類型土地中銅和鋅的含量沒有顯著變化,可能與牛糞和豬糞有關(guān),而牛糞和豬糞中銅和鋅的來源與飼料添加物有關(guān)[10-11]。
對(duì)25個(gè)點(diǎn)位中土壤多環(huán)芳烴總量和各分量監(jiān)測(cè)發(fā)現(xiàn)[12],1985—2013年,土壤中多環(huán)芳烴的總量基本穩(wěn)定,但各分量變化情況略有不同,其中分子量小的多環(huán)芳烴(如萘和菲)含量有所下降,分子量較大的多環(huán)芳烴(如苯并[a]芘和苯并[ghi]苝),在大部分點(diǎn)位含量較為穩(wěn)定,只在零星點(diǎn)位有升高或降低趨勢(shì)。進(jìn)一步研究顯示,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與不同類型多環(huán)芳烴的物理化學(xué)特點(diǎn)及不同排放來源2個(gè)因素相互疊加有關(guān)。
NABO自2012年開展生物指標(biāo)監(jiān)測(cè),2018年瑞士聯(lián)邦政府和環(huán)境部門專門發(fā)布了此項(xiàng)監(jiān)測(cè)報(bào)告[2],5年間30個(gè)生物監(jiān)測(cè)點(diǎn)位的監(jiān)測(cè)結(jié)果顯示,耕地中生物量、微生物呼吸、DNA量要低于草地和林地,各點(diǎn)位微生物種群5年內(nèi)基本穩(wěn)定,未來將繼續(xù)開展生物指標(biāo)監(jiān)測(cè),并根據(jù)監(jiān)測(cè)結(jié)果不斷優(yōu)化監(jiān)測(cè)指標(biāo)。
2 瑞士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的特點(diǎn)和啟示
2.1 堅(jiān)持長期定位監(jiān)測(cè),關(guān)注土壤質(zhì)量趨勢(shì)變化
瑞士土壤監(jiān)測(cè)開始較早,積累了大量的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NABO在布點(diǎn)之初就建立了詳細(xì)的點(diǎn)位檔案,長期開展定位監(jiān)測(cè)工作,數(shù)據(jù)的歷史延續(xù)性較好,時(shí)間序列可比性強(qiáng)。除此之外,NABO的質(zhì)量評(píng)價(jià)工作更關(guān)注土壤質(zhì)量在時(shí)間序列上的分析,通過長期定位監(jiān)測(cè)和數(shù)據(jù)分析,判斷土壤質(zhì)量變化和環(huán)境保護(hù)措施的成效,預(yù)判土壤功能衰退風(fēng)險(xiǎn)。
與此相比,中國土壤質(zhì)量趨勢(shì)變化分析工作多數(shù)是以省、市為尺度,國家尺度較少,且鮮有長期定位監(jiān)測(cè)下的質(zhì)量變化趨勢(shì)分析[13-18],這主要是因?yàn)橹袊蚤L期定位監(jiān)測(cè)為目標(biāo)的土壤監(jiān)測(cè)工作起步較晚。回顧中國土壤監(jiān)測(cè)工作,國家尺度的土壤調(diào)查和監(jiān)測(cè)在20世紀(jì)50年代和80年代、“十一五”到“十三五”期間先后開展了土壤普查、背景值調(diào)查、土壤污染狀況調(diào)查、土壤質(zhì)量監(jiān)測(cè)及土壤詳查[19]。盡管土壤監(jiān)測(cè)和調(diào)查工作積累了大量數(shù)據(jù),但各類調(diào)查和監(jiān)測(cè)工作之間的延續(xù)性較差。一方面受限于對(duì)土壤監(jiān)測(cè)的目的認(rèn)識(shí)不足,早期主要關(guān)注肥力,近年來更關(guān)注土壤污染風(fēng)險(xiǎn),各調(diào)查和監(jiān)測(cè)工作布點(diǎn)方法、目的不盡相同,點(diǎn)位之間難以建立延續(xù)性;另一方面受到技術(shù)與土地利用方式快速發(fā)展和變化的限制,早期定位技術(shù)主要依賴羅盤和地圖,前期點(diǎn)位坐標(biāo)不精確,后期難以準(zhǔn)確定位開展延續(xù)性監(jiān)測(cè),此外隨著工業(yè)發(fā)展和城市化進(jìn)程的推進(jìn),部分點(diǎn)位土地利用方式發(fā)生改變,無法再次開展監(jiān)測(cè)工作。
“十三五”期間,由原環(huán)境保護(hù)部主導(dǎo)開展了國家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網(wǎng)(以下簡(jiǎn)稱國家網(wǎng))的監(jiān)測(cè)工作,依據(jù)網(wǎng)格化布點(diǎn)方法[20],綜合考慮歷史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點(diǎn)位的延續(xù)性,布設(shè)了國家網(wǎng)基礎(chǔ)點(diǎn),用以開展土壤質(zhì)量變化趨勢(shì)分析和評(píng)價(jià)工作,但由于起步較晚,數(shù)據(jù)積累較少,相關(guān)成果也較少。
區(qū)域尺度的質(zhì)量變化趨勢(shì)分析更多依據(jù)不同年份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而各年度數(shù)據(jù)很少來自同一點(diǎn)位。國內(nèi)部分長期觀測(cè)試驗(yàn)站或高校開展了長期定位土壤監(jiān)測(cè)工作[21-23],但空間尺度多為試驗(yàn)站或試驗(yàn)田,無法代表區(qū)域土壤變化趨勢(shì)。
2.2 以目標(biāo)和問題為導(dǎo)向建立綜合監(jiān)測(cè)指標(biāo)體系
NABO以土壤環(huán)境管理為目標(biāo),以土壤環(huán)境問題為導(dǎo)向,充分考慮土壤功能的可持續(xù)性和污染風(fēng)險(xiǎn),基于DPSIR模型理清了影響土壤質(zhì)量的各個(gè)因素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進(jìn)而篩選可以反映問題并支撐管理決策的監(jiān)測(cè)指標(biāo),最終建立了綜合土壤物理-化學(xué)-生物特性的指標(biāo)體系。
中國土壤調(diào)查和監(jiān)測(cè)工作中,早期調(diào)查關(guān)注土壤肥力[19,24-26],主要是土壤養(yǎng)分(如有機(jī)質(zhì)、氮、磷、鉀)等指標(biāo)。在“七五”背景值調(diào)查工作中共監(jiān)測(cè)了61種土壤無機(jī)元素的背景值[27-28],“十一五”以來在以環(huán)境部門為主導(dǎo)的土壤調(diào)查和監(jiān)測(cè)工作中逐步開展了土壤中重金屬污染物和部分有機(jī)污染物的調(diào)查,但農(nóng)業(yè)、環(huán)境和地質(zhì)部門開展的土壤監(jiān)測(cè)或調(diào)查工作仍以土壤化學(xué)指標(biāo)為主。近年來,在中國土壤質(zhì)量分析和評(píng)價(jià)研究中,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開始關(guān)注生物指標(biāo)和物理指標(biāo)[29-32]。生物指標(biāo)用來反映土壤生態(tài)環(huán)境和土壤的可持續(xù)性;物理指標(biāo)用來反映土壤結(jié)構(gòu)情況和水土流失風(fēng)險(xiǎn)等。在研究層面也逐步向綜合的監(jiān)測(cè)指標(biāo)體系發(fā)展,但在業(yè)務(wù)層面生物指標(biāo)和物理指標(biāo)還未構(gòu)建。一方面土壤環(huán)境管理的關(guān)注點(diǎn)還未從污染物向土壤生態(tài)及功能等方面轉(zhuǎn)移,另一方面評(píng)價(jià)方法和測(cè)試方法還存在制約,物理和生物指標(biāo)監(jiān)測(cè)還未建立系統(tǒng)的方法體系,評(píng)價(jià)方法和表征方式等也尚未明確。
2.3 充分利用監(jiān)測(cè)網(wǎng)絡(luò)和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開展統(tǒng)計(jì)分析
中國過去開展的研究項(xiàng)目存在一個(gè)普遍問題,即相互之間無法對(duì)接,數(shù)據(jù)不能共享,不同時(shí)期的研究成果由于精度、工作方法等多種原因不具有可比性[33]。地方性研究成果無法在國家層面應(yīng)用,同樣的工作在不同層面上進(jìn)行多次,造成資金、人力和物力的浪費(fèi)。
而在NABO的監(jiān)測(cè)工作中,為了最大限度利用原有監(jiān)測(cè)網(wǎng)絡(luò)和各部門數(shù)據(jù),在最初設(shè)計(jì)階段,布設(shè)點(diǎn)位時(shí)充分考慮到各個(gè)維度的分析需要,建立不同的指標(biāo)體系,并在監(jiān)測(cè)工作中,不斷豐富調(diào)查的指標(biāo)體系,提高效率。在一次采樣工作后,最大程度地開展測(cè)試和數(shù)據(jù)分析。除此之外,加強(qiáng)數(shù)據(jù)的互聯(lián)互通和共享,在數(shù)據(jù)分析中充分引入研究院所已有監(jiān)測(cè)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不斷擴(kuò)充分析數(shù)據(jù)集,開展多元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分析和土壤環(huán)境狀況評(píng)價(jià),深入挖掘土壤污染狀況原因,為土壤環(huán)境保護(hù)和污染防控工作提供有效支撐。
3 結(jié)論與建議
瑞士國家土壤監(jiān)測(cè)工作起步較早,以觀測(cè)土壤環(huán)境變化、探索人為活動(dòng)與土壤環(huán)境之間關(guān)系為目標(biāo)建立的長期定位觀測(cè)網(wǎng)絡(luò)NABO,在網(wǎng)絡(luò)建設(shè)目標(biāo)和方法上與中國國家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網(wǎng)基本一致,但NABO的監(jiān)測(cè)指標(biāo)體系較中國更為完備,突出了對(duì)土壤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關(guān)注。該網(wǎng)絡(luò)運(yùn)行30多年來,在監(jiān)測(cè)和數(shù)據(jù)共享等方面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體系,并在數(shù)據(jù)分析方面形成了豐富的成果,這些都值得中國借鑒。
中國國家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網(wǎng)絡(luò)在“十三五”時(shí)期已完成初步建設(shè),社會(huì)公眾對(duì)土壤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工作持續(xù)關(guān)注,可借鑒NABO的寶貴經(jīng)驗(yàn),進(jìn)一步做好中國土壤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工作。一是結(jié)合中國土壤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管理要求和主要問題,構(gòu)建適合的監(jiān)測(cè)指標(biāo)體系,逐步豐富監(jiān)測(cè)方法體系和評(píng)價(jià)體系;二是堅(jiān)持國家網(wǎng)長期開展定點(diǎn)監(jiān)測(cè),形成國家尺度長時(shí)間序列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庫;三是統(tǒng)籌國家網(wǎng)和地方網(wǎng)的監(jiān)測(cè)工作,建立土壤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平臺(tái),收集和維護(hù)國家、地方及相關(guān)科研機(jī)構(gòu)土壤監(jiān)測(cè)數(shù)據(jù),提升數(shù)據(jù)分析能力,為土壤環(huán)境管理和公眾提供可靠的數(shù)據(jù)產(chǎn)品。
- 中國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的其它文章
- 《中國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 第四屆編委會(huì)名單
- 邁進(jìn)前十!《中國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 學(xué)科排名再創(chuàng)新高
- 以嘉陵江鉈濃度異常事件為例探討《重特大突發(fā)水環(huán)境事件應(yīng)急監(jiān)測(cè)工作規(guī)程》在應(yīng)急監(jiān)測(cè)中的應(yīng)用
- 光污染管理政策與LED廣告屏干擾光限制標(biāo)準(zhǔn)分析
- 臭氧前驅(qū)體物監(jiān)測(cè)用氮?dú)庵卸嘟M分VOCs氣體標(biāo)準(zhǔn)物質(zhì)的研制
- 溶解性有機(jī)碳對(duì)微庫侖法測(cè)定水中可吸附有機(jī)鹵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