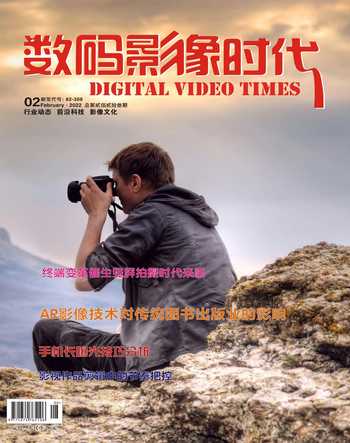智媒時代下播音主持面臨的挑戰及應對
王聰

我國電視事業相對于國際社會起步較晚,新中國成立后,直到1958年北京電視臺(1978年,改為中央電視臺)才成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從經濟領域到文化領域的改革逐漸拉開序幕,在這個階段,特別是在兩年后的1980年第十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的召開,這次會議上提出了“堅持自己走路”,充分尊重廣播電視媒介規律和傳播特征的思想得到確認并開始真正地推行。廣播電視也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折。在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之后,中央廣播事業局改組成了廣播電視部,電視才受到了重視,逐漸走進人們的生活,在我國廣播電視發展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回顧歷史,從廣播電視媒體誕生到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雖然沒有“主持人”這個稱謂,其實在這之前已經有了一些節目主持的事實。直到1980年7月12日,《觀察與思考》作為我國第一個新聞評論性的專欄節目在中央電視臺開播。節目片尾的職員表上打出了“主持人:龐嘯”的字樣, “主持人”這一稱呼第一次出現在我國電視史上。21世紀以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革新,媒體行業跨入了智能媒體時代,人工智能在人們生活各方面帶來影像的同時,給播音主持行業也帶來全新的變革,甚至影響到整個新聞傳播領域。在智能媒體時代,很多工作崗位由人工智能替代,導致從業者面臨全新的挑戰,大家都擔心是否在將來的某一天會被人工智能取代。
人工智能的優勢
工作效率增加
早在20年前,英國的一個網絡公司就已經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個虛擬主持人阿娜諾娃。雖然在21世紀初,中國的許多電視媒體都在嘗試虛擬主持人,但很多應用于廣播領域的人工智能產品都受到了傳播效果和成本的限制,并沒有變得更受歡迎。近幾年來,人工智能技術不斷成熟,人工智能技術在播音主持行業中的應用也日趨多樣化,智能語音播報、個性化語音合成、虛擬主播、AI合成主播等都能達到“以假亂真”的效果。
人工智能完全依靠技術的進行運作,可以隨時傳輸直播,設置必要的前期程序,然后給出指令,這樣就可以實現相關信息的實時傳輸。此外,還可以進一步提高信息傳播的效率,減少傳統信息傳遞過程中人力物力的投入。降低了信息處理的成本,利用這種技術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解放勞動力。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個人工智能機器人,它不僅可以節省大量的社會資源和成本,而且可以提高生產率,實時可靠地傳遞最新的信息。深夜、節假日和其他緊急情況時……如果無人被召回,就可以直接通過人工智能報告緊急事件。人工智能的靈活運用不僅可以迅速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降低成本。
信息處理穩定
人工智能由于受信息技術的局限,就像是一個播報機器沒有任何情感,與傳統的電視節目主持人相比較,人工智能在信息處理中有很大的優勢。一名方面,受外界因素的影響較小,保證了信息處理的客觀性,另一方面,因為它不受身體、情緒和緊急事件的影響,人工智能擁有更加穩定的處理信息能力。當面臨龐大雜糅的大數據時,人工智能比傳統節目主持人信息處理能力更強,精準度更高,同時各種數據信息的處理效率更快,質量也更高。與傳統播音員和主持人在技術完備的情況相比較來看,人工智能主持人的信息處理準確率更高,出錯概率更低。
例如,“AI合成主播”的功能是對新聞事件進行理性、客觀的簡單評論,解決了新聞行業評論中最大的“態度偏見”問題,這是我們沒有理由否認的。在數據庫的基礎上,通過語音識別、人臉識別等技術合成并建模出來的“AI合成主播”,說到底還是一個機器人,它也有一定的優勢,這種穩定的信息處理能力更能體現節目播出效果的穩定性。另外,在時事路況和股市預測方面,可以根據需要,在前期設置好強大的計算功能,這樣就可以極大地保證信息處理的準確性和穩定性。正是因為人工智能技術比起播音主持人能夠提供更加穩定的信息處理能力,所以它對信息技術的依賴至關重要。
經濟效能提高
人工智能技術合成的“AI主播”和“虛擬主持人”其實就可以被看作是播音主持人崗位上的另一種存在,跟節目主持人比起來,真人具有不可比擬的投產比和功能性,可以提高工作的整體經濟效益,這就是為什么在智能媒體時代下,人工智能技術在節目主持人行業爆發的原因。我們把“AI主播”可以看作是一種初始成本高、邊際成本低的媒介產品。因此,當“AI主播”“虛擬主持人”一旦被開發出來,那么就能依靠這個媒介產品增加內容的產出,從而獲得更高的利潤。
“AI主播”“虛擬主持人”工作的機會成本比實際的節目播音員、主持人要小得多,它是一個媒介資源優化配置的表現,讓人工智能技術造福人類。當這種技術運用一旦得到推廣時,就形成了播音主持工作的規模經濟效應和范圍經濟效應,實現了利潤矩陣。不出錯、清晰是播音主持人基本工作的標準,但是要達到這種標準要花費很長的時間成本,要進行系統的學習訓練、長年累月的業務實踐都是非常必要的,即使這樣,也很難保證每次播音主持都沒有差錯。如果運用了人工智能技術那就不一樣了,只要保證文本是準確的,AI主播就可以很容易的完成預定的播報,這兩個重要的標準得到了完美的實現。人工智能技術可以高效地完成全天候、多時空的連鎖任務,這是播音主持人無法達到的,因此,人工智能技術在播音主持行業的經濟效能也得到了大大提升。
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存在情感缺位
情感是播音主持創作的靈魂,正是由于情感的存在,創作主體才可以感知和理解原稿和畫面,并以外部技巧為支持,實現準確、清晰和動態的有聲語言表達。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缺乏情感和自由意志的理性基礎。事實上,人工智能的“思維”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復雜的算法操作,不能自由選擇,不會超過既定的算法,很難根據情感的價值做出選擇。播音主持的創作,主要通過滿足受眾的信息和情感需求來實現與受眾的溝通。
人工智能的傳播方式往往是單向傳播,溝通效果差,這一點在電視節目中訪談能力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人工智能只能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在數據庫中搜索答語,主動提問、挖掘信息的能力較低,無法自然流暢地與人溝通。例如,在中央電視臺2019年網絡春晚節目現場,主持人撒貝寧跟人工智能合成的“小小撒”對話中,撒貝寧的提問和“小小撒”的回答顯得呆板生硬,“小小撒”也不會根據撒貝寧的提問進行更多的情感交流,其實觀眾更期望在談話中看到“訪談嘉賓”與主持人之間形成情感交流和互動。跟專業的節目主持人比較起來,由人工智能打造的“虛擬主持人”由于受技術條件的限制,在節目進行過程中,往往只能替代簡單的信息溝通、交流互動,無法從嘉賓的視角來理解內容,導致傳播的方式相對單一,溝通效果差。一個優秀的節目主持人除了要具備扎實的專業素養,更應該具備人文關懷,讓傳播的內容不僅有廣度還要有溫度。人工智能只是一個冷冰冰的機器,無法進行情感上的交流,然而,節目中的情感互動往往是很重要的,可以讓觀眾感同身受,這恰恰是人工智能無法做到的。
不具代表性
人工智能技術合成的“AI主播”“虛擬主持人”沒有思想和溫度,在面對不同的事件和人物時跟真人比起來缺乏人文情懷。例如,2008年中央電視臺主播康輝在全國哀悼日的直播中不禁哽咽,試想,若換作人工智能,那么這些承載著傷痛的事件和死亡人數就僅僅只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而已。再比如在中央電視臺2020年的《回聲嘹亮》節目錄制中,節目主持人李思思在采訪已故英雄黃繼光的老戰友時,由于老人年紀大了,談到當年并肩作戰的戰友時幾度落淚,主持人李思思面對老英雄,跪地拭淚。讓觀眾無比動容,節目主持人李思思蹲身給老人擦拭淚水,體現了節目主持人在主持節目中不僅要有人文的尺度,更需要人文的溫度。但是假如這種情況換作AI主持人的話,是否也會有這種舉動呢。在電視節目中,節目主持人的言行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對丑惡現象的批判和行善往往能引領輿論風向,沒有人文關懷和責任感的人工智能是無法進入觀眾的心中的。
跟節目主持人比起來,人工智能不可能扮演有思想性的節目播音主持人,因為“它們”受到先導的程序的限制,“它們”沒有自由的意志,同樣沒有藝術創造力,不能去模仿人類的想法并把它和事件結合起來進行評估。由于不能理解文本的意思,所以無法實現真正的溝通和互動,也無法控制人物的感情,更不能把握節目的時間進程等等。目前來看,人工智能從事簡單的信息播報,并且由于技術條件的不成熟,人工智能技術合成的“AI主播”“虛擬主持人”沒有思想性,跟傳統節目主持人相比,無法形成自己的風格,獲得受眾的認可。因此,人工智能技術并不能代表真實的個人,代表的是更正式的立場還有傳聲的角色。
缺乏藝術創作
播音主持實際上是一種二次創作的過程,播音是以創作的基本要素為基礎,從創作的目的出發,通過有聲語言將準確、清晰、生動的稿件傳達給觀眾,從一種形式到另一種形式的變化是創作的核心。而人工智能只是把文字生產成聲音,不做二次創造,由此來看人工智能所做的工作只是機械地執行,并不能做出真正意義中的播音主持,也不能與觀眾產生共鳴。因此,人工智能無法與傳統的節目主持人進行思想上的比較,即使能夠準確無誤地傳遞信息,但是傳播方式相對單一,對作品無法進行二次的藝術創作。
從信息的編碼到解碼,這是在主持節目過程中主持人需要對信息進行二次創作,一個優秀的節目主持人除了向觀眾傳遞準確的信息以外,更重要的是能夠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專業素養以及思想內涵,對信息進行處理加工,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到節目當中去,讓觀眾能夠從節目中獲取更多的信息。人工智能正是因為缺乏生活的經驗,嚴格意義上來說并不能根據具體的事件和人物感情進行理解分析后對語音、語調進行調整,所以機械地播報并不能使觀眾產生情感上的認同,在播音主持的創作過程中缺少藝術上的創作,內容的主要主題和情感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表達,播出的節目對觀眾的吸引力也大大降低。
播音主持人的應對策略
加強風格
在當下的智能媒體時代,不管人工智能技術怎么發展,還是很難掌握播音主持創作過程中的內在情感的表現技巧,播音主持人完成了從原稿聲音表達到原稿個性表達的轉變。在此基礎上,播音主持人要根據自己的文化涵養和專業素質,在主持節目過程中,通過對“人性”的感知和控制,賦予互動行為以人文情懷,形成自己的主持風格,從而獲得受眾的認可與喜愛。對于廣電行業來說,播音主持人需要把更多的感情投入到節目中,在眾多同質化的節目內容中,根據自身的經驗和能力來主持節目,從而形成具有個性化和差異化的核心,打造自己的品牌風格,達到更多人的青睞。打造優秀的“個性化”作品,這恰恰是別人無法比擬的,人工智能更無法替代。
提高素養
在智能媒體時代,人工智能也許取代的是技能單一的播音主持人,只有具備多種精湛的專業知識,才能在職業道路上得到更好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在近年來,隨著短視頻時代的到來,在借助新媒體平臺的優勢下,很多播音主持人得到了更多的曝光率。雖然他們的生產的“內容”能在短時間內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但是產品本身的價值卻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一個專業播音主持人不僅要對自身專業具有敏感性,而且也應該電視節目播音主持創作中充分發揮自己專業優勢,在對一個新聞事件進行客觀的專業評論時,應該具有反思和剖析社會現實的能力。此外,對于播音主持行業來說,專業的復合型人才更受歡迎,這也是一種必要的趨勢。所以,這就要求播音主持人應該盡最大努力形成自身的專業壁壘,這樣在與另外的行業以及行業內的其他人不僅可以相互溝通,還能更加深入的溝通,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自身的獨特功能,在節目過程中與觀眾形成互動,達到情感上的共鳴,給節目帶來好的傳播效果。
正視機遇
如果說新媒體時代撼動了播音主持人的事業,那么,智能媒體的時代將對節目主持人的職業生涯帶來又一次影響。如今,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發展,“AI主播”“虛擬主持”以及“智能播報”等多種形式開始出現在播音主持領域。人工智能給我們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的想象力,所以,這是個挑戰,同時更應該看到的這是一個機遇,在智能媒體的挑戰下,播音主持人很可能陷入混亂的自我專業發展過程。盡管很難預測科學和技術的未來發展,但他們肯定是自由的,沒有自制力,沒有思維,只是作為一個“傳聲筒”存在的,播音主持人也許會等到被替代的那一天。對于勇于創新、進取的播音主持人來說,人工智能技術是錦上添花,它能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內容的創作質量,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
在智能媒體時代的傳播格局下,未來的電視節目也許AI主播和真實節目主持人將會共同存在,人機合作將改寫播音主持行業的傳播格局。在未來,我們可以轉變想法,把人工智能看作是播音主持人的隊友而不是對手,從而更加進一步的來探索人機合作的新模式。
結語
科技的發展,導致媒體不斷的推動新的創意產業,當人工智能延伸到播音主持領域時,媒體行業凝固的邊緣逐漸模糊,智能媒體融合的趨勢也會越來越明顯。人工智能技術給播音主持領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隨著“AI主播”“虛擬主持”以及“智能播報”的不斷出現,播音主持人的職業也面臨著發展危機,但現在受到了技術發展的制約,人工智能技術在播音主持行業的運用還存在一些缺陷。作為播音主持人,只有不斷學習和提高專業素養,順應時代的發展潮流,努力增強自身的發展實力,就能把挑戰變成機遇。
在如今的智能媒體時代,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沖擊,我們可以梳理從我國電視主持人誕生發展到如今的“AI主播”“智能播報”和“虛擬主持”,面對人工智能對節目主持人帶來的這種新挑戰,充實自身的內涵,讓自己的潛能得到挖掘,實現與人工智能技術的結合創新發展,這是在智能媒體時代下每個從業者必須思考的問題。將人工智能技術的便利性最大化,減少不必要的工作,提高思維能力,提高專業素養,利用人工智能的技術優勢,為播音主持積極創造更多的表現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