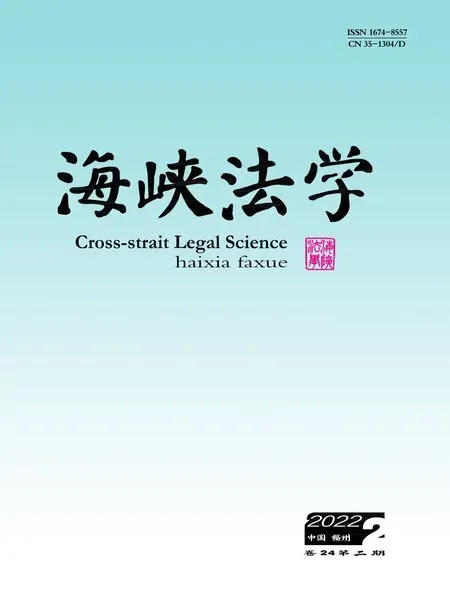對我國《海警法》質疑觀點的駁斥與對策
張琪悅
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以下簡稱為《海警法》)的頒布與實施是我國完善海上維權執法體系的重要里程碑。《海警法》首次明確了我國海警在維護海洋安全、開展海上執法、實施犯罪調查、深化國際合作等方面的作用,確立了授權使用警械和武器的范圍、方式、程序,將對規范我國海洋維權執法活動、維護國家主權與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產生積極影響,也對侵犯我國海洋權益的行為起到震懾作用。《海警法》的制定與實施引發相關國家強烈反響。本文在厘清各國主要法律質疑的基礎上,結合理論依據與國際實踐展開分析,為我國后續海上維權執法行動提供對策建議。
一、我國《海警法》面臨的外部質疑及影響
(一)使用武器的合法性
東盟國家普遍擔憂我國《海警法》賦予海警使用警械和武器的權利,將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可能構成“戰爭的威脅”。菲律賓外交部長特奧多羅·洛欽(Teodoro L.Locsin Jr.)提出外交抗議,①Hananeel Bordey,“LocsinProtestsChina’sNew CoastGuard Law”,https://tribune.net.ph/index.php/2021/01/28/locsin-protests-chinas-new-coast-guard-law/,下載日期:2022年5月29日。認為《海警法》允許開火的規則“非常值得警惕”,可能構成國家使用武器,特別是在管轄海域外使用武器將構成侵略,違反《聯合國憲章》(以下簡稱為《憲章》)規則,成為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②“China’sNew CoastGuard Law:Illegaland Escalatory”,https://www.iseas.edu.sg/media/commentaries/chinas-new-coast-guard-law-illegal-and-escalatory/,下載日期:2022年5月29日。印尼外交部長雷特諾·馬爾蘇迪(Retno Marsudi)、國防部長普拉博沃·蘇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對中國在爭議水域的行動與《海警法》的執行表達擔憂,強調維護國際法下航行自由的重要性。①“Int’l Public Opinion Concerned over China’sCoast Guard Law”,https://vietnamnet.vn/en/intl-public-opinion-concerned-over-chinas-Coast-gua rd-law-731539.html,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Ned·Price)擔憂,立法將加劇我國與周邊國家海洋爭端的緊張情勢,特別是使用武器條款將加劇東海和南海緊張態勢。②“USConcerned China’s New Coast Guard Law Could Escalate Maritime Disputes”,https://www.gmanetwork.com/news/topstories/world/776712/usconcerned-china-s-new-coast-guard-law-could-escalate-maritime-disputes/story/,下載日期:2022年5月29日。
(二)管轄海域范圍的模糊性
外界擔憂,由于我國周邊海域與鄰國存在大范圍重疊,當海洋劃界尚未解決時,在爭議海域執法使用警械和武器將引發嚴重沖突,增加在爭議水域發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③程智華:《海域執法武力行為國際法分析》,http://lawyer.110.com/14335053/article/show/type/1/aid/862673/,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日本防衛省將《海警法》適用地理范圍的模糊性、使用武器的規則視為《海警法》不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為《公約》)的原因。④“The Coast Guard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ttps://www.mod.go.jp/en/d_act/sec_env/ch_ocn/index.html,下載日期:202 2年5月30日。海洋法學家坂元茂樹(Shigeki Sakamoto)認為,《海警法》的管轄海域與《公約》不符:第一,基于對斷續線淵源的質疑與對南海仲裁案裁決結果的確認,否定我國在斷續線內享有歷史性權利。第二,在毗連區和專屬經濟區內劃定“海上臨時警戒區”有違《公約》適當顧及他國權利與公海自由的要求。⑤Shigeki Sakamoto,“China’s New Coast Guard Law and Implicationsfor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https://w ww.lawfareblog.com/chinas-new-coast-guard-law-and-implications-maritime-security-east-and-south-china-seas,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美國甚至惡意揣測我國以立法推行“非法”、“過度”海洋權利主張,加強對爭議海域的實際控制。
(三)對執法活動缺乏有效監督
從《海警法》的醞釀、頒布到實施,外界始終存在質疑認為,《海警法》存在執法權力定位不明確、權力邊界模糊、實施細則不明、執法協作機制不全等問題,為海上執法活動的監督管理造成阻礙。⑥段窮、曲亞囡:《中國海警海上行政執法權問題研究》,載《沈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第671~672頁。隨著我國與海上鄰國的海警船、政府船舶、漁船意外相遇的風險加劇,外界將更關注《海警法》第九章關于監督條款的規定能否有效實施,并要求我國履行防止南海地區緊張局勢加劇的義務。
(四)可能引發他國立法仿效
《海警法》將引發他國立法仿效。截至目前,美國與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均已頒布和實施海警法。我國《海警法》的頒布與實施勢必將為周邊國家造成壓力,容易引發尚未開展立法的國家進行立法仿效,激發他國為本國開展執法行動提供法律依據與規則保障。⑦Viet Anh,“An Act of War:Implications of China’s Coast Guard Law”,https://e.vnexpress.net/news/news/an-act-of-war-implications-ofchina-s-coast-guard-law-4227416.html,下載日期:2022年5月20日。各爭端國國內法適用范圍的重疊將成為海上危機管控與海洋爭端解決需要考量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五)導致爭端國海上執法沖突
印尼外交部擔憂我國主張的歷史性水域與他國在《公約》體系中有權主張的專屬經濟區存在重疊,從而引發執法沖突。海事安全局負責人巴卡姆拉(Bakamla)認為,立法將加劇兩國船舶在納土納群島水域發生沖突的風險。①“Can Bakamlabe at the Forefront of Indonesia’s Natuna Sea Strategy”,https://thediplomat.com/2022/01/can-bakamla-be-at-the-forefro nt-of-indonesias-natuna-sea-strategy/#:~:text=According%20to%20the%20law%2C%20the%20original%20purpose%20of,to%20dealing%20with%20other%20preexisting%20maritime%20security%20agencies,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日本已經正著手實施更廣泛的應對措施:將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心的情報聯絡室升級為官邸對策室,加強信息情報搜集能力;推動修改完善《自衛隊法》等法律,為海上執法行動提供更及時、更詳盡、更完善的規則依據;漁船做好使用武器的準備,應對可能與我國發生的海上執法沖突。②Shigeki Sakamoto,“China’s New Coast Guard Law and Implicationsfor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https://w ww.lawfareblog.com/chinas-new-coast-guard-law-and-implications-maritime-security-east-and-south-china-seas,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此外,美國承諾履行對日本和菲律賓的同盟條款,定期開展海上巡航,挑戰我國“過度的海洋權利主張”,將派遣海岸警衛隊與東南亞國家開展聯合執法,加強海洋能力建設。③“Philippines and USCoast Guards Conduct Joint Maritime Exercise”,https://www.navalnews.com/naval-news/2021/09/philippines-and-u s-coast-guards-conduct-joint-maritime-exercise/#:~:text=Philippines%20and%20US%20Coast%20Guards%20conduct%20Joint%20Mari time,03%20Sep%202021%20Philippine%20Coast%20Guard%20press%20release,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此舉將增強美國及其盟國對地區軍事活動的主導權,也將進一步加劇海上執法沖突。
(六)引發被訴諸國際司法機構的風險
越南外交學院副院長阮雄山(Nguyen Hung Son)強調,《海警法》的立法與執法應符合包括《公約》在內的海洋法規范。《海警法》可能導致爭端被訴諸國際司法機構。菲律賓離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奧·卡皮奧(Antonio Carpio)在《海警法》頒布后,慫恿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到國際司法機構宣布我國《海警法》無效,搜集我國執法行動可能構成侵權的依據。④JamesHuang,“China’sCoast Guard Law isa Threatof War”,https://usa.inquirer.net/66196/chinas-coast-guard-law-is-a-threat-of-war,下載日期:2022年5月29日。然而,此舉違反了國家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明顯違背“平等主體之間無管轄權”。
(七)對“南海行為準則”磋商造成阻礙
菲律賓大法官安東尼奧·卡皮奧提出,我國《海警法》的頒布實際上加速了“準則”的死亡,減損了各國制定區域規則的期待與信心。⑤Daphne Galvez,“Palace:Talks on SCSCodeof Conduct to go on Despite New China Coast Guard Law”,https://newsinfo.inquirer.net/1390653/palace-talks-on-scs-code-of-conduct-to-go-on-despite-new-china-coast-guard-law#:~:text=China%E2%80%99s%20new%20Coast%20Guard%20law%20authorizes%20the%20Chinese,upon%20by%20foreign%20organizations%20or%20individuals%20at%20sea.%E2%80%9D,下載日期:2022年5月29日。以印尼潘查西拉大學法學院院長埃迪·普拉托莫(Eddy Pratomo)為代表的海洋法學者認為,《海警法》的頒布將會干擾“準則”磋商的進程,違反了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義務,甚至違反了“準則”磋商的誠實信用原則。這一原因成為印尼對《海警法》提出反對意見的原因。⑥“Indonesian Expert:China’s New Coastguard Law Interrupts COC”,https://vovworld.vn/en-US/news/indonesian-expert-chinas-new-c oastguard-law-interrupts-coc-947157.vov,下載日期:2022年5月29日。綜上,反對觀點認為,《海警法》為我國周邊國家加重了風險管控的注意義務,增加了“準則”危機管控這一核心條款磋商的難度,為周邊海域帶來了不穩定因素。未來,我國在“準則”磋商與區域維穩方面恐將面臨來自他國更大的壓力。
二、對外部質疑的法律分析與回應
(一)海警使用武器的權力來源
判斷海警使用武器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其權力來源,具體包括:海警自身的性質、執法船舶的性質、行動的國內法依據、行使職權的性質等因素。
1.我國海警自身兼具海上行政執法與武裝力量的雙重屬性。①閆巖:《抹黑中國<海警法>無益海上安全合作》,載《環球時報》2021年2月10日,第014版。2018年海警隊伍轉隸武警部隊,組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海警總隊,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國海警局行使海上維權執法職權的決定》,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8/0623/c1011-30078248.html,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賦予海警武裝力量屬性。但海警使用武器與海軍使用武器的性質存在顯著區別。海軍使用武器屬于國家軍事行動,而海警難以做出同樣的界定。第一,在處置事項上,海警的主要職責在于海上救助、治安管理、維權執法,履行更廣泛的義務;③Patricia Jimenez Kwast,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Useof Force:Reflectionson the Categorization of Forcible Action at Seain the Light of the Guyana/Suriname Award,Journal of Conflict and Security Law,Vol.13,No.1,2008,p.74.海軍使用武器在于反對外來侵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第二,從人員構成來看,海警由現役軍人和非現役軍人組成,僅現役軍人編入武警部隊序列;而海警的人員構成更多樣化。根據海警自身的性質、處置的事項、人員的構成判斷,海警使用警械和武器更傾向于行政執法行為范疇而非海上軍事活動。
2.海警船從事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及海上執法行動且享有豁免權。美國參議員、著名法學家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認為,船舶的性質決定其權利范圍。根據《公約》第29條對“軍艦”的定義,“軍艦”是指隸屬于一國武裝部隊、具備辨別國籍的外部標志、由國家政府正式委任、名列相應現役名冊、有服從正規武裝部隊紀律的船員的船舶。④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e.pdf,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按照這一標準,我國海警船舶是否能擁有軍艦的法律地位和權利,取決于該船舶是否在武警部隊海警總隊系統中被登記為軍用性質的船舶,以及是否配備海警作為船員。但由于我國海警機構歷經改革,并且兼具維護海上安全與行政執法的屬性,應當根據具體國情綜合考慮。日本海洋法學家坂元茂樹提出另一種分析思路,認為判斷海警船舶的法律地位可以從《圣雷莫適用于海上武裝沖突的國際法手冊》(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to Armed Conflictsat Sea)中尋找標準。手冊第13條(g)與(h)項分別規定了“軍艦”與“輔助船舶”的定義,后者指“一國武裝部隊擁有或控制、暫時用來為政府開展非商業性服務的非軍艦類船只”。⑤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to Armed Conflictsat Sea,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因此,應當根據船舶的歸屬和管理,以及服務的臨時性或長期性,作為判斷船舶屬于“軍艦”或“輔助船舶”的依據。即使船舶未登記在軍用船舶序列中,如需將其改裝為軍艦,可參照1907年《海牙第七公約》(《關于商船改裝為軍艦公約》,Hague Convention VII Relating to the Conversion of Merchant Shipsinto War Ships,Hague VII)的要求,“應盡速宣布此項改裝,載入軍艦名單中”。⑥HagueConvention VIIRelatingtotheConversionof Merchant Shipsinto War Ships(HagueVII),https://www.warzone.cc/media/1907-Hague-Convention-VII-relating-to-the-Conversion-of-Merchant-Ships-into-War-Ships.pdf,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
海警船舶有權享有主權豁免。《公約》第298條第1款(b)項將“從事非商業服務的政府船只和飛機的軍事活動”排除在第十五部分強制爭端解決程序外。這一條款規定,關于軍事活動,包括從事非商業服務的政府船只和飛機的軍事活動的爭端,不屬于法院或法庭管轄的關于行使主權權利或管轄權的法律執行活動的爭端。況且,國際海洋法法庭在“烏克蘭訴俄羅斯扣押海軍艦船案”臨時措施的命令中強調,軍事活動與執法活動之間的區別不能僅基于船舶的性質做出判斷,因為二者的界限正變得模糊,并且各國同時使用這兩類船舶開展聯合行動的情況極為常見。因此,將使用船舶的性質作為判斷行為性質的參考意義有所減損。
3.賦予海警使用武器的權限在多國海警法立法中予以確認。美國《海岸警衛隊武力使用規則》規定,執法人員在自衛或保護他人、強制服從法律、阻止犯罪和執行司法逮捕時可以使用武力。①閆巖:《抹黑中國<海警法>無益海上安全合作》,載《環球時報》2021年2月10日,第014版。越南《海岸警衛隊法》第14條進一步規定了海警在履行職責時有權使用武力的各類情形,明確在嚴重威脅生命安全等情況下可以開火。②韋強譯:《越南海警法》,載《南洋資料譯叢》2019年第3期,第69~78頁。馬來西亞《海事執法局法》賦予執法官員在執行任務時可以攜帶武器的權利。③Pia Ranada,“PH,ASEANNationsCan Goto UNto Declare China Coast Guard Law Void”,https://www.rappler.com/nation/antonio-carpio-says-philippines-asean-nations-can-go-united-nations-declare-china-coast-guard-law-void/,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韓國《海警法》并無關于國家主權或主權權利的規定,但確實允許海警在國家安全受到危害時使用武力。④K.Lee,“The Korea Coast Guard’s Useof Force Against Chinese Fishing Vessels:A Note”,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The-Korea-Coast-Guard%27s-Use-of-Force-Against-A-Note-Lee/c2b03f02841f96926f0f5c3b58187326aee1035e,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亞洲海事透明倡議對于各國海警使用武力的情形做出統計,可以看出各國海警依據本國法律使用武器的情況較為普遍。

各國海警使用武力規則⑤資料來源:Force Majeure:China’s Coast Guard Law in Context,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March30,2021,https://amti.csis.org/forcemajeure-chinas-coast-guard-law-in-context/,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里所指的使用武力僅包括使用武器,而不包括登船、拖船、口頭警告等行動。各國立法幾乎都允許海警使用武器維護國家利益,保護本國船員和公民。在阻止涉嫌犯罪的船舶逃跑、登臨或拒捕時,也授權使用武力。但面臨更嚴重且廣泛的“維護國家主權或主權權利”時,情況就更復雜。各國通常不明確規定使用武力的合法性。
我國海警機構依照《國防法》和《人民武裝警察法》等有關法律、軍事法規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執行防衛作戰任務;在處理海上刑事案件時,應依照《刑事訴訟法》和《海警法》采取偵察和強制措施;對于阻礙海警機構執行公務的行為,應當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處罰;對于海警行政執法不服的,可依照《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追索。以上國內法成為證明海警行動合法性的事實與法理依據,反映出海警基于國內法開展執法,受到程序法的監督。
4.海警活動的性質和目的是重要的判斷依據。在性質上,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海警維權執法與海上軍事活動既存在聯系,又存在區別。聯系在于,海警在使用警械和武器的過程中應當更多地考慮國際因素。由于海上行政執法活動往往存在跨區域的特點,從國家主權范圍內的水域,到享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的海域,再到國際海域和空域,海警行動都應當符合國內法律與國際規則。但海警針對外國船舶的執法活動與國際法中的使用武器存在區別。⑥Patricia Jimenez Kwast,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Useof Force:Reflectionson the Categorization of Forcible Action at Seain the Light of the Guyana/Suriname Award,Journal of Conflict and Security Law,Vol.13,No.1,2008,p.58.日本海上自衛隊與保安廳也認為,當日本海岸警衛隊開展執法活動時,無論實際情況如何發展,都難以將其定性為武裝行動。①Tomohisa Takei,“How Japan Should Deal with China’s New Coast Guard Law”,http://thenationalpolicy.com/2021/04/10/how-japanshould-deal-with-chinas-new-coast-guard-law/,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海警處置海上突發事件,管控危機、打擊違法犯罪、保護海洋資源,具有更強的對內執法屬性。而海上軍事活動的目的在于應對外來侵略,二者的目的與性質存在區別。
軍事活動與執法活動的區別不能僅基于當事國對有關活動的界定,因為對于二者區別的描述是主觀且多變的,未必與真實情況相一致,特別是援引軍事活動例外具有更多解釋空間。國際海洋法法庭在審理烏克蘭訴俄羅斯案中稱,區分軍事活動和執法活動的主要依據要建立在對事件的客觀評價上,并應結合個案具體情況考慮相關情形。②ITLOS,Case Concerning the Detention of Three Ukrainian Naval Vessels,Ukrainev.Russian Federation,Request for the Prescription of Provisional Measures,Order,May 25,2019,paras.64-67.由此,國際司法實踐不能也不意在對軍事活動與執法活動確定統一標準。
由于海上執法行動與軍事活動間界限模糊,在不少情況下混合使用,因此應當根據海警的具體行動區分探討。海警在海上使用武器可大致分為三種情況:第一,因行使自衛權而使用武器,可定性為國家對外采取軍事行動,應當符合國際法上授權使用武器的標準。第二,因海上執法受阻使用武器。第三,在執法過程中使用武器。后兩種屬于國家行政執法的范疇。對于上述三類活動,應當區分行動性質分別探討。
(二)海警使用武器的國際法依據
根據國際案例,沿海國在海上執法過程中,依照國際法規范使用武力具有合法性。在1993年“孤獨號”案、1962年“紅十字軍號”案、1998年“漁業管轄權”案、1999年“塞加號”案、2008年“圭亞那訴蘇里南”案中,裁判機構認為,海上執法人員有權在合理限度內,依照國內法使用武力。例如在1998年西班牙訴加拿大“漁業管轄權”案中,國際法院認為,加拿大于1994年5月12日通過的C-8號法案與《刑法典》第25條的修訂都涉及執法問題。加拿大于1994年5月25日修訂的《沿海漁業保護條例》規定了“使用武力”的權限。國際法院認為,加拿大《刑法典》和《沿海漁業保護條例》授權使用武力屬于通常理解的執行養護和管理措施,根據“自然而合理”的解釋,包括為實現這一目的而采取登船、檢查、逮捕、最低限度使用武力。③ICJ,FisheriesJurisdiction Case,Spainv.Canada,Reportsof Judgments,Advisory Opinionsand Orders,Judgment,December4,1998,paras.81-84.
從上述國際司法判例可以總結以下基本規則。一是海警使用武器和訴諸武力應當符合必要性(necessity)、合理性(rationality)、成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原則,并作為可訴諸的最后途徑(the last resort)等實質性要求。
第一,使用武器應當符合必要性和合理性要求。必要性意味著僅在特定情況下作為一種需要。根據這一需要,交戰方有權采取武裝沖突法不禁止的任何必要措施獲取軍事行動勝利。合理性要求各方適用區分原則,區別對待平民和戰斗員、民用和軍事目標;采取預防措施,不傷及平民居民、平民個人、民用物體。④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to Armed Conflictsat Sea,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必要性和合理性原則在實踐中往往合并探討。“孤獨號”案裁決認為,美國可以按照《公約》規定,必要且合理地使用武器,登船、搜查、扣押。如因意外導致被追及的船舶沉沒,追及船為實現上述目的而必要地、合理地使用武器,可能完全不受指責。⑤Reports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S.S.“I’m Alone”,Canadav.United States,June30,1933,p.1615.在“紅十字軍號”案中,丹麥護航艦尼爾·艾伯遜號在英國漁船“紅十字軍號”涉嫌非法捕魚并企圖逃跑時對船體發出實彈射擊。裁判委員會認為,射擊在兩點超出合法使用武力的范疇:(1)在沒有收到實彈射擊警告的情況下開火;(2)在未被證明必要性的前提下開火,對“紅十字軍號”船上人的生命造成威脅。根據委員會意見,“紅十字軍號”逃跑是“公然違反接受和服從命令”,并拒絕停止。以上諸多情況不能成為丹麥暴力行動合法化的理由。委員會認為,丹麥船舶本應嘗試其他方法;如果堅持采取適當方法,就有可能說服英國船長停止射擊,恢復先前預期的操作程序。①Reports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Investigation of Certain Incidents Affecting the British Trawler Red Crusader,Report,March 23,1962,p.538.在“塞加號”案中,國際海洋法法庭認為,盡管《公約》并未對逮捕時使用武力的限度予以規定,但應當根據個案具體情況,遵守合理性和比例性原則。首先,必須盡可能避免使用武力;當不可避免地訴諸武力時,不能超出在當時情況下的合理和必要限度。法庭認為,幾內亞在登船前后過度使用武力,對生命造成威脅,明顯違反國際法規則。②ITLOS,The M/V“Saiga”(No.2)Case,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v.Guinea,Judgment,July 1,1999,pp.36-37.
第二,使用武器應當符合成比例性要求。在嚴格意義上,廣義的比例性包括適當性、必要性、狹義的比例性。比例性通常作為國際人道法規則,在諸多國際法和國內法領域中得到廣泛運用,成為國家為實現可允許的目標而合理、理智地適用的手段,避免不恰當地對他人或他國權利造成侵犯。《圣雷莫適用于海上武裝沖突的國際法手冊》中明確規定,各國從動用武力開始就受到國際人道法原則和規章的約束;人道法中的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則同樣適用于海上武裝沖突。例如在《日內瓦第二公約》中確立的海上武裝沖突的人道法規則,③《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第二公約》,https://www.icrc.org/zh/doc/resources/documents/misc/gc2.htm,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要求一國在實施海上軍事行動時,不得超出擊退武裝侵犯和恢復自身安全所需的、非武裝沖突法所禁止的使用武力的程度及種類,不得違背允許使用武器的標準和規則,禁止發動可能造成平民附帶傷亡、民用物體損害或造成上述后果的攻擊。
此外,《圣雷莫適用于海上武裝沖突的國際法手冊》還對海上執法規則做出明確規定,允許在專屬經濟區和外大陸架使用非致命武力,執行與資源相關的法律制度;允許在專屬經濟區和外大陸架使用武力,但應遵守有關法律制度;允許在毗連區使用非致命武力執行財政、移民、衛生和海關的法律制度;允許在毗連區使用武力,包括使用致命武力執行財政、移民、衛生和海關的法律制度;允許使用非致命武力緊追;允許使用武力,包括致命武力緊追;允許在領海內使用非致命武力制止非無害通過;允許在領海內使用武力,包括致命武力制止非無害通過等。④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to Armed Conflictsat Sea,https://ihl-databases.icrc.org/applic/ihl/ihl.nsf/,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盡管該手冊不具有強制約束力,僅反映出美、英、加、澳軍方人士的觀點,但由于制定主體具有權威性,能夠反映出實務部門的實踐經驗,可以被視為“公法學家學說”,作為《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的輔助淵源得以適用。
第三,使用武器應當作為各國訴諸的最后途徑。在“塞加號”案中,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稱,幾內亞使用大孔徑自動炮實彈射擊,在攔截和逮捕手無寸鐵的“塞加號”時,過度且不合理地使用武力。幾內亞辯稱,在“塞加號”拒絕聽從命令和信號后,幾內亞軍官只使用了極少幾聲槍響。在判斷這一爭議行動的合法性時,國際海洋法法庭重申了“孤獨號案”中闡明的“紅十字軍號”的習慣法標準,在海上對外國船只使用武力執法必須作為可以訴諸的最后手段,不得超過合理的和必要的范圍。⑤ITLOS,The M/V“Saiga”(No.2)Case,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v.Guinea,Judgment,July 1,1999,paras.155-156.
綜上,國際海洋法法庭對“使用武力”的標準提出三點具體要求:(a)在執法過程中盡量不對外國船舶使用武力,或將使用武力作為可以訴諸的最后手段;(b)當不可避免地使用武力時,不得超過合理、必要的限度;(c)使用武力不得危及人的生命。法庭認為,只有在采取一系列“適當行動”失敗后,才能將使用武力作為可以最后訴諸的強制性措施。即便如此,行為的實施者也應當發出適當警告,盡一切努力確保生命不受威脅。如果當事國不遵守以上規定,將加劇區域緊張局勢,有可能因非法、不合理、強制執法發生爭端,甚至引發武裝沖突。①Ivan Shearer,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Respect to the Law Enforcement Rolesof Naviesand Coast Guard in Peacetime,In ternational Law Studies,Vol.71,No.1,1998,p.430.
盡管上述案例已經確立了基本規則,但在實踐中仍存在一定靈活性。國家執法實踐始終存在差異和變化。有的國家傾向于盡快訴諸武力迫使對方投降,另一些國家傾向于耐心地使用和平方法解決,②William Fenrick,Legal Limitson the Useof Forceby Canadian Warships Engaged in Law Enforcement,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 l Law,Vol.18,1980,p.113,135-142.因此很難以統一的標準對各個國家做出同等的要求。各國應當避免墨守成規,將規則的原則性與實操的靈活性相結合,賦予一線人員以適度的處置權限與行動上的靈活性。
二是應當符合程序性要求。國際常設仲裁法院在圭亞那訴蘇里南案中援引“塞加號”案判決中確立的程序性規則,認為在海上攔截船只,特別是使用艦載和機載武器,應遵循通常的做法。首先,執法船舶應當發出國際公認的聽覺或視覺上的停止信號。如果發出信號仍未達到逼停目標船舶的效果,才可以采取進一步行動:發出警告,實施警告性射擊,向船頭開火。當采取以上行動失敗后,追及船才能使用武器作為最后手段,但也必須向被追及船發出警告,并盡一切努力確保生命不受威脅。如果使用手持武器,通常可省略請示程序直接開火。使用武器的程序性規則并非一成不變,而應根據實際情況做出調整。根據《海警法》第49條,海警機構工作人員依法使用武器,來不及警告或警告后可能導致更嚴重危害后果,可直接使用武器。
(三)海警管轄海域范圍的海洋法規則
根據《海警法》第3條規定,海警機構在我國管轄海域及其上空開展海上維權執法活動適用本法。由于《海警法》未對“管轄海域”做出明確界定而引發質疑,國際社會對于“管轄海域”的理解通常是基于以《公約》為基礎的現代海洋法體系對于海域的劃分。除我國外,其他各國在國內法中籠統規定執法范圍的情況始終存在。越南海警法規定,“越南海警在越南管轄海域開展執法活動”。菲律賓海警法也使用“管轄海域”來概括執法范圍。日本對管轄海域表述為“整個國家及沿岸水域”。韓國表述為“沿岸水域、離岸水域、開放水域”。我國《海警法》將具有執法權的海域籠統表述為“管轄海域”的方式并非首創,也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的一般規則。如果有關國家和媒體以此抹黑中國,構成“雙重標準”,不僅缺乏合理性,而且于法無據。③宗海合:《中國在南海執行海警法無可厚非》,載《環球時報》2021年3月19日,第014版。
然而,管轄海域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以及各聲索國之間海洋權利主張存在重疊的實際情況將為海警使用警械和武器的合法性與使用限度的解釋造成困難。我國執法部門也認識到,即使沿海國在特定海域對某一事項擁有特定的管轄權,也不能自動理解其為有權對外國船舶行使強制執行管轄權。對在不同管轄海域的行政執法權應當區別探討。
領海是沿海國全部主權向海洋的延伸,沿海國在領海理應享有執法權。毗連區作為沿海國享有安全利益的區域,能防止和懲治在其領土或領海內違反海關、財政、移民、衛生的法律和規章的行為。④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e.pdf,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一國在毗連區內的管轄權可以視為沿海國在領土和領海內執法權的延伸。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享有經濟權利而非軍事權利,但在專屬經濟區內涉及執法、海上治安的行動并不等同于軍事行動,⑤Patricia Jimenez Kwast,Maritime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Useof Force:Reflectionson the Categorization of Forcible Action at Seain the Light of the Guyana/Suriname Award,Journal of Conflict and Security Law,Vol.13,No.1,2008,p.55.而屬于國家基于主權權利行使行政執法活動,未被《公約》及海洋法規則所禁止。明晰我國在不同管轄海域享有的執法權的范疇,能避免非法、不公正、強制的執法行為引發爭端甚至是武裝沖突。
(四)海警執法行為的監督機制
我國《海警法》注重對執法行為的制約和監督,在操作層面對于不同武器的使用方法做出了詳細的程序性規定,增強了執法的規范性與可預見性,為實施監督提供了明確依據。《海警法》明確了執法行為應當依照法律中的條件、權限、程序,履行職責、行使職權,通過海警機構內部的監督機制、追責機制,確保執法活動合法實施,保障執法程序得到有效監督。《海警法》還設置了執法公開、執法過程記錄、執法過錯責任追責等制度,強化對使用武器的監督和追責。①宗海合:《中國在南海執行海警法無可厚非》,載《環球時報》2021年3月19日,第014版。對于執法過程中的違法與失當行為,被執行者可訴諸行政程序追責與索賠,獲得有效救濟。《海警法》的制定與實施將為執法行為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然而,由于立法本身具有概括性和模糊性特征,未來還需要依靠內部明確的政策性指導,②Shigeki Sakamoto,“China’s New Coast Guard Law and Implicationsfor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https://w ww.lawfareblog.com/chinas-new-coast-guard-law-and-implications-maritime-security-east-and-south-china-seas,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既能提供科學、合理、高效的行動方案,又能為監督提供明確標準和規則依據。此外,我國海警在執法實踐中也始終秉持專業精神與自我克制的態度。
三、對策建議
(一)區別對待相關國家質疑,警惕他國通過炒作實現政治目的
對于個別國家的合理疑問,我國應以恰當方式澄清海警使用武器的情形、限度,起到增信釋疑的作用。對于個別國家的污名化炒作、煽動國際輿論,打壓我國正當的海上維權活動,我國應當堅決予以回擊,強化國家行使權利和對管轄海域的實際控制。對于域外國家的強行干預,我國應當警惕他國通過對《海警法》的質疑介入南海爭端,通過構建區域規則與合作機制排除域外干預。
(二)加強對外宣傳,明確《海警法》立法與執法的合法性
我國應當通過恰當場合闡述《海警法》的頒布與實施屬于主權國家行使立法權的范疇,屬于對管轄海域行使行政權、管轄權、主權權利的正當行為;強調我國海警的行政執法與自衛行動遵守《憲章》對使用武器的規定,在執法過程中保持善意和克制,符合國際慣例與國家實踐中確立的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則。我國還應當加強執法信息公開,考慮由武警部隊海警總隊出具年度報告,通過對典型案例的處置與對海警執法行為的考評,向外界展示我國海警活動符合國際法規范,既有利于增強行政執法透明度,又能對外國的非法炒作、非理性質疑做出有力回應。
(三)明確海警執法詳細的程序性規范
《海警法》為執法行為提供了法律依據,但作為法律規則,在立法存在概括性和模糊性的特征,需要對一線人員提供更加詳細的內部性政策性指導意見。③Shigeki Sakamoto,“China’s New Coast Guard Law and Implications for Maritime Security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https://w ww.lawfareblog.com/chinas-new-coast-guard-law-and-implications-maritime-security-east-and-south-china-seas,下載日期:2022年5月30日。例如,確立海警的執法行為要先后包括警告、警告性射擊、船體射擊三個步驟,符合根據國際慣常標準設置的程序性規范,既能為海警的行動提供更加科學、合理、高效的方案,又能為對執法活動提供明確標準和依據。此外,為保障海警的執法合法、合理、高效,應當厘清兩類關系。第一,理順海警機構與其他涉海部門的職責分工和協作配合,特別是要明晰海軍與海警的職權劃分、指揮、協同,明確海警與地方政府部門對海洋管理的界限與協調機制,依法劃分海警與邊防支隊的管轄范圍。在明確海警機構的職能定位、權限措施和保障監督的基礎上,健全完善海上維權執法工作機制,為海上維權執法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第二,在執法過程中,做好不同法律間統籌銜接。明確《海警法》的上位政策、關聯政策、配套政策,處理好《海警法》與刑法、行政法、國防法、武裝警察法,與治安管理、海洋、漁業、海關等領域部門法間的銜接關系,維護法律體系內在協調統一。
(四)拓寬海警國際合作空間,共同維護海洋安全與秩序
我國遼闊的海域面積、復雜多樣的海域狀況、鄰國眾多的地緣環境,使我國成為受海上非傳統安全犯罪侵害較為嚴重的國家。①閻二鵬:《海上通道安全國際合作法律機制:模式選擇與制度構想》,載《海峽法學》2018年第4期,第54頁。海洋安全作為全球問題,亟需國際社會的通力合作,推動全面發展來妥善應對。②趙勇:《國際法發展新趨勢與非政府組織的參與》,載《海峽法學》2019年第4期,第49頁。推進海警機構國際合作將成為有效推進海洋治理與海洋安全的重要途徑,也是降低爭議海域敏感局勢、加強危機管控和建立互信的重要舉措。《海警法》規范了我國海警與外國海上執法機構和國際組織的合作機制,明確了各國在聯合打擊海上犯罪、保護海洋環境、維護海洋安全等領域合作方式。各國應以此為契機,加強雙多邊執法合作,攜手構建海洋合作與治理新秩序,共同應對各領域的風險挑戰,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建設,為國際社會的合作構建安全、穩定的海洋環境。③李衛海:《海警法:合力維護海洋和平安寧》,載《學習時報》2021年3月3日,第002版。
結論
《海警法》頒布實施以來,外界質疑集中在海警使用武器的合法性、管轄海域不明確、執法缺乏有效監督。海警基于自衛權使用武器可定性為國家對外采取軍事行動;在海上執法受阻或在執法過程中使用武器屬于國家行政執法范疇。實體層面應當符合必要性、合理性、成比例性原則,作為可以訴諸的最后途徑。程序層面應當符合國際通行的步驟與行為規范。海警有權在我國管轄海域及上空開展維權執法活動,除《公約》體系下的海洋區域外,還包括我國主張但尚未完成劃界的水域、歷史性權利的水域、海底區域。我國海警執法行為受到機構內部的監督、追責機制,能確保執法活動合法實施,保障執法程序得到有效監督。我國應當區別對待相關國家的質疑,警惕他國通過炒作實現政治目的;加強對外宣傳,明確立法與執法的合法性;明確海警執法的程序性規范;拓寬海警國際合作空間,共同維護海洋安全與秩序,為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承擔大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