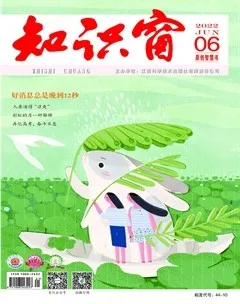情歌都去哪兒了
洛風

不知何時,我的音樂列表里只剩下20世紀的經典情歌,新的情歌在歌單里消失不見。這仿佛是一個不相信愛情的年代,這個年代的年輕人,已經沒有一首真正意義上的、屬于自己的經典情歌了。
人們都說,現在的流行音樂空洞、堆砌、程式化,像戀愛這樣真情實感的人間體驗,卻沒有歌手愿意用來創作。其實我們回頭看,二十年前,幾乎所有的流行歌都是情歌,甚至我們放眼海外,以“日記體”歌曲聞名的泰勒·斯威夫特為代表的歌手,一段時間內的作品就是一部她的“個人情史”。為何到了我們這一代,卻沒有新生代歌手愿意再創作出經典的情歌呢?
青年歌手毛不易,是屬于用歌詞來講故事的那一類人。
毛不易講深夜下班后從街邊攤借來的溫暖;講在外年輕人和家鄉親人之間的羈絆;講述東北經濟蕭條的宏大敘事感;講道理讓我們揣摩金錢的意義,甚至用揶揄的口吻講述每一個普通人的優秀……毛不易用小人物和平凡生活的碎片,聯結著生活與聽眾間的距離。
華語歌曲之所以一度風靡情歌,正是因為情歌被認為是獲得大眾共鳴的捷徑。于是在21世紀初,“樂壇情歌泛濫”成為無論是誰都能評上一嘴的萬能指摘。然而,二十年過去了,當現實再次牽動起我們的真實情感時,腦中回響起的,還是當年帶著溫度的曲調。
于是在21世紀初,我們看到了孫燕姿的《遇見》、周杰倫的《七里香》,林俊杰的《江南》、光良的《童話》、陳奕迅的《愛情轉移》,甚至在第一個年代接近尾聲時,回光返照般看到許嵩的《廬州月》。
但情歌的旋律仿佛永遠留在了21世紀初,不論是單戀、失戀、暗戀,還是動心、關心、痛心,好像只有在那個年代,才能讓每個人都找到屬于自己的情歌。
接下來的十年里,探索各類歌曲題材、語言和演唱方式的歌手層出不窮。無論是新一代音樂人,還是選秀節目出道的流量歌手們,都不是華語情歌的后繼者。
當然,作為藝術家本身,選擇自己想要表達、擅長表達的主題自然無可厚非。但當情歌成為這代歌手共同繞開的“危險話題”時,說明這背后一定有更廣泛的因素,正深刻影響著這個文化場域。
如果說創作歌手的風格化追求,讓他們放棄了對愛情的集中描寫,仍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商業化歌曲同樣主動避開了描繪真情實感的題材,則坐實了情歌沒落的現狀。
我們簡單瀏覽QQ音樂的年度流行歌曲排行榜就會發現,真正歌手發布的專輯歌曲占比不過三分之一,其余位置均被影視合作歌曲和抖音神曲強勢占領。影視綜藝卻漸漸成了歌手們的重要業務范圍,于是這些本該進一步渲染情感的音樂武器,處處顯得尷尬而落寞。
情歌瀕臨倒臺的另一個印證就是,這個時代再沒有新的情歌王子和情歌天后。
最為深入人心的情歌王子張信哲,在初入樂壇的時候,也曾經歷了定位尷尬的時期。恰逢此時,李宗盛作詞的《愛如潮水》因為過于展露男性柔軟的一面,風險較大,被一直壓在箱底。當李宗盛最終選擇把這首顛覆男人“有淚不輕彈”形象的細膩作品,交給年僅26歲的張信哲,打造癡情柔軟的傷心男人形象時,是一場名副其實的賭局。
因為李宗盛、張信哲和滾石唱片公司提供了一種大家羞于表達的情緒。他們在賭,賭的是飽滿真情的沖擊力,賭的是聽眾的敞開心扉。在那個年代,他們賭贏了,張信哲情歌王子的歌壇地位自此一戰成名。
然而到了當下,不論是歌手、詞曲作者,還是投資人,都早已拋棄了這種路徑,甚至歌手們由作品建構起來的自我形象,也在不斷地“去性別化”。
大家形容周深“一個人就是一個唱詩班”,空靈縹緲的歌聲從《大魚》唱到《鯨落》,其實唱的都是被投射的“我”;而毛不易更像是一個講述者,故事中的情感沖突再激烈,他的形象也永遠是站在第三人的視角……但和肩負著與歌迷“談戀愛”任務的上一代歌手相比,他們怎么看,都不會是對著你唱情歌的人。其實,歌手的形象和作品主題的變化,代表的是市場的選擇,也是作為受眾的我們,現實生活的倒影。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兩個“自己”之間的摩擦。愛情神話已經打動不了我們,那就更無須在情歌中寄托。可以說,“00后”對傳統愛情和婚姻模式沒有什么信心,但對“和紙片人談戀愛”“追星式戀愛”等新型關系有了更包容的心態。
猛然看來,情歌不再壟斷音樂市場,不見得是徹頭徹尾的壞事。因為其他更小眾的歌曲題材能因此獲得生長空間,且必將促進音樂市場和我們內心世界的多元繁茂。
但如果我們連最普通的情歌故事都說不好了,很難想象,被這樣的華語樂壇所映照著的我們,是否擁有比父輩們更加充沛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