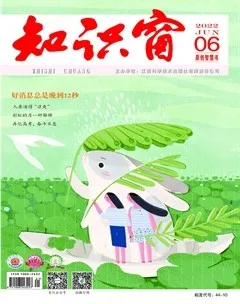現實主義的椰樹
寒石

坐飛機至三亞市,通過舷窗看到的第一抹綠蔭,一定是椰子樹。
在我印象中,椰樹跟竹、松、柏一樣,是詩意畫景里的常客。如果說竹、松、柏的比襯物是瘦石、巉巖,與椰樹為伍的則是碧海、金沙,是濃郁的熱帶風情。到了三亞市,這一切都眼見為實、觸手可及了。此外,在現實的這片美麗的中國海景里,我還讀到了有關椰樹在影像資料里所看不到的東西,即椰樹的現實圖像與生存環境。
在三亞市街頭,看到最多的行道樹是椰樹。事實上,椰樹在三亞擔當的是花的角色。雖然椰花看上去是黃瑩瑩的一團,盛開在高高的樹梢之上,甭說賞心悅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椰樹是以整樹的形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它那斑駁而高挑的樹身、闊大而青蔥的羽葉、渾圓而結實的果實,滄桑卻不顯老,當它一樹樹高舉綠色的旗幟,出沒在街道、人群與建筑物中間時,它就是花了,就是一樹樹巨大的、盛開的綠色花朵。
椰樹枝疏葉茂、高大俊朗,給人的整體形象是那樣青蔥勃發,那樣出類拔萃,呈現一種剛健的雄性美。椰樹,對土壤的要求不高,喜沙性土質,只適合長在陽光下,它對陽光的嗜好近乎苛刻:兩樹間距不能小于5米,不然它就長不好。從這個意義上說,椰樹其實并不適合做行道樹。它的遮陽面不夠大,它的習性與人們對行道樹的通常要求(遮陽)恰好相悖。三亞市本地人自然不懼陽光,而外地游客大多是沖著三亞市的海灘、陽光而來的。椰樹正好,雖不遮陽,卻把亞熱帶海景風情渲染得淋漓盡致。
漫步三亞市街頭、海灘、植物園,我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凡是具備熱帶海濱風情的樹種都長得跟椰樹差不多——細挑高瘦,像一截截電線桿,只在半空舉出一蓬綠蔭。比如檳榔、油棕、霸王棕、木瓜……聽導游說,別看這些樹長得高而細,但樹質大多疏松,沒多大實用價值。我明白了,這些樹只適合作為一種樹生長著,只有站著、生長著,它們的存在才有意義。它們長得高直細長,是為了爭取陽光、不招風,而樹本身無大用,就不招人,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無妨礙生長。在這里,物質生存法則竟體現得如此清晰、充分。
生長不分季節,這是包括椰子在內的許多熱帶植物的又一生存特征。即便江南已經入冬,但到了三亞市,我們看到的幾乎每一棵成年椰樹上都掛著碩大的椰子。仔細看,椰子的大小、色澤各有不同。再仔細看,椰果的上面還籠著一團粉白、一片粉黃,那就是椰花。邊開花邊結果,椰子惜時如金,分秒不浪費。
椰汁性涼,所以原始的椰汁要到陽光下喝,晚上或寒天最好少喝。午間,在亞龍灣海灘的椰林中,我買了一個椰子,讓刀斫個洞,插根吸管進去,捧著悠悠地吸著,邊享受著海風椰韻與碧浪青天,越發覺著椰子的可愛。椰樹真是造物主賜給熱帶地區人們的禮物啊!它自己不喝椰汁,卻長給人喝。
后來,在熱帶植物園,當我發現一棵棵椰苗從一摞摞用來裝飾的椰子上長出來時,我才意識到自己的幼稚和無知——椰汁并不是長給人類喝的。椰子首先是一枚種子,椰汁是用來哺育自己后代的,就像動物的母乳。椰樹生存的土壤大都是沙質土,沙質土壤最大的特征是存不住水,而椰苗在萌芽分蘗期是離不開水的,所以它預先為自己的后代存了一杯營養水,待椰苗喝光這杯“母乳”,它的根系已發育成熟,可以從土壤中汲取水分了……
現實的椰樹更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