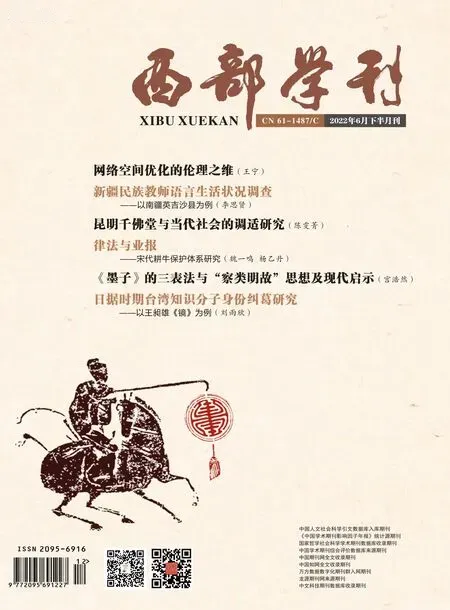文化適應性觀照下浙江山水詩英譯賞析
摘要:在翻譯過程中,文化適應性是一個重要現象。基于劉宓慶的文化適應性三原則,從特色文化詞匯、意象、詩形三個方面,對描繪浙江山水的古詩英譯本進行解讀和探討,提出適時運用各類修辭手法、兼顧交際目的與語義翻譯、注重受眾的審美認同是成功進行古詩翻譯的關鍵。
關鍵詞:文化適應性;浙江山水;山水詩;英譯
中圖分類號:H315;I04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12-0156-04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1]作為弘揚中國文化、陶冶情操的重要手段,山水詩以其豐富的內涵、美妙的意境以及綺麗的文體特性,在世界文壇獨具風采。它的有效對外傳播有助于增強我國優秀文化對外傳播與國際交往時的話語權。在“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譯者如何根據翻譯目的做出審美判斷,運用翻譯策略構建讀者接受環境,從而創作出文化適應度高的譯作,值得深入研究。
一、中國山水詩與浙江山水
中國詩詞在發展過程中衍生出了多種情景交融的方式,如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觸景生情、情景相生等。山水詩,作為中國詩詞的一個典例代表,以山和水作為描寫對象,實現了景與情、理、志的氣血貫通。根據景與情、理、志的聯系,山水詩可分為抒情山水詩、寓理山水詩和言志山水詩[2]。中國山水詩開創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說的浙江是山水詩的發源地。南朝謝靈運以五言詩體描繪浙東山水,創立了我國最早的山水詩派,是當之無愧的山水詩開山鼻祖。唐宋時涌現出眾多名家,其中以孟浩然、李白、蘇軾、楊萬里等為代表的詩人成就了浙江山水詩的繁榮興盛期。據統計,共有460多位詩人(其中浙江籍60余人)游歷棲居于由曹娥江水系和其周邊古道合圍而成的浙東唐詩之路①上,占收載于《全唐詩》2200余位詩人總數的1/5[3]。
二、文化翻譯與文化適應性原則
文化翻譯學派的領軍人物蘇姍·巴斯內特曾指出,“翻譯絕不是一個純語言的行為,它深深根植于語言所在的文化之中, 是為了滿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體的需要。”[4]在國內,劉宓慶構建了一套文化翻譯的理論新框架,提出了文化適應性原則,即:(1)準確的文化意義或含義把握;(2)良好的讀者接受;(3)適境的審美判斷[5]。正如有學者提出的:“與譯語觀眾相同文化環境的譯者通常有意無意都會擔當起文化調解者的角色,著眼于譯語觀眾的接受能力和文化心理,對原文采取變通手段,緩和文化沖突,朝著譯語觀眾的方向拉近文化距離。”[6]具體翻譯表現法的取舍通常需要進行語義考量(看哪一個對應式更切合原意)、語用考量(交流中合不合用)、審美考量(著眼于審美效果,實質也是一種語用考量),而最佳可讀性翻譯通常是譯者綜合考量的結果[7]。因此,我們可以歸納說,文化適應性原則包括三方面,即語義文化適應性、語用文化適應性和審美文化適應性。
三、文化適應性在《宿建德江》英譯本中的體現
《宿建德江》孟浩然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Spending the night on the Jiande River(Meng Haoran)
Mooring the boat among the mists-
Day wanes
A wanderer’s ache persists
In the vast wilds the sky descends to touch the trees
As brightening waters bear the moon to me(Tr. 張延琛 &Bruce M. Wilson)[8]
詩人孟浩然是唐代山水詩派的代表人物。《宿建德江》作為孟詩中的代表作,屬抒情山水詩。此詩為孟浩然于唐玄宗開元十八年(730)離鄉赴洛陽,再漫游吳越時所作,借以排遣仕途失意。這樣的漫游一方面是為了遍交天下名士,游覽名山大川;另一方面也是想將自己的詩文介紹給這些著名的人物。詩人無比思念天各一方的家鄉與親人,卻又不得不在外闖蕩,詩人的情緒由山水而生,也隱含在山水之間。
(一)適時運用各類修辭手法
原詩展現了詩人在船中間看到的自然景象,也是他情緒投射的某種意象,耐人尋味,印證了中國文化自古強調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中文對情感的表達內隱,而英文則往往外露。例如,原詩中本有“無我之境”,譯作為了保留這一特點,承句沒有用人稱代詞“I”來作主語,而用了“A wanderer”來表達,未破壞詩的原生態之美。詩人遠望,江天浩渺,在蒼茫天宇下,仿佛處在天空的懷抱里,近處的那些樹木反而顯得要高。坐于船中想念家鄉,扶手一看,一輪明月就在手邊。把手放在江水中,正好與明月融為一體,故江月親人的意境渾然天成。詩人以他對空間上一遠一近的敏感,揮筆一書,風格散淡。“低”與“近”兩字以動襯靜,畫面生動。如何用英文傳達出含蓄的情感,又經營出意境,需要譯者傾力用心,適當運用現代英文的寫作手法。英語的物稱傾向或無靈主語句式的廣泛使用,就是英語語言的優勢之一。若直譯“天低樹”為“sky was not higher than the tree tops”,則不能將詩人實際上在想家,需要溫暖的懷抱,以天所代表的大自然當作慰藉的感情表達出來。相比之下,此譯作接連通過三個意象的疊加,“vast wilds”,“brightening water”,將全詩詩眼“月近人”層層遞進襯托出來。空曠的原野與詩人的寂寥心境相符,天對樹的“俯身觸摸”(descends to touch)也是天對詩人的深情,江水通過對月亮的映射來關懷詩人,最后詩人俯視江中明月,與“天之俯身”動作相呼應,故轉合兩句相互依存與襯托。原野、天、樹、江水、月亮這些大自然的一分子此時渾然一體,“慷慨豁達”地給予了孟夫子安慰。“月近人”未用“the moon is close to man”直接譯出,而是由無靈主語waters加上有靈動詞bear,極大地提高了語言表達力,且增進了譯詩的美學效果。“一捧皎潔月光”似由周遭萬物“合掌獻出”,呈現于詩人眼前,照進詩人心房,也照亮了此刻落魄詩人的回程路。故后兩句點睛之譯touch與bear二詞,將天與江“人格化”,不僅體現了中國文化“萬物各得其養以成”,展現了大自然的包容與大度,也“撥動”了所有讀者的心弦。擬人化這一修辭手法的妙處,給譯文讀者留下想象的空間和回味的余地,并再現了中國古典詩所強調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意在言外”,“辭不盡意”。
(二)兼顧交際目的與語義翻譯
全詩語義解讀的關鍵還在于承句中的“客愁新”。何為客愁?是未及第的愁悶(grievance),是思念親人的鄉愁(nostalgia),是漫游者的愁思(wanderer’s melancholy),三者皆而有之。作者從長安一路漫游至江浙一帶,看到了江天日暮,孤舟獨橫,天低岸遠。他把自己欲說還休的愁緒附著在建德的江天月影之上,詩中一種淡淡“清愁”。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到的“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我之色彩”,就是對此種寓情于景手法的貼切展現。譯作巧妙地用ache一詞,表達了詩人身為異鄉客的鄉愁,身為旅客的孤獨寂寥,對京城中政壇、詩壇都頗為得意的王維等新交好友的艷羨,以及報國無門的惆悵等諸多情緒。《新牛津詞典》[9]里對該詞的定義主要有二,“1.figuratively,an emotion experienced with painful or bitter-sweet intensity,隱喻意思為一種惱人或苦樂參半的情感;2.a strong desire to do sth,渴望。”例句如:It makes my heart ache to see her suffer;I was aching for home。再如,賽珍珠在回憶狄更斯對其影響時也曾描繪:“An Englishman rendered an inestimable service to a small American child in China and the feeling of warm gratitude may ache until it is expressed”[10]。故ache一詞雖小,但地道貼切,準確地傳遞了原語信息。“新”又作何解?“新愁”不應單單理解為一縷新的愁緒,更指愁在眼前,無法回避。這首詩里,孟浩然的愁是一層層地疊加起來,在傍晚時分變得愈發深厚。這樣的心境,不獨孟浩然,其他的詩人也有,如東晉陶淵明的《飲酒》詩說:“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一路上的河流山川似乎能讓詩人短暫忘記憂傷,但其實郁積在心的愁一直都在,且在日落時分更加明顯。故persist一詞,乍看不“忠實”,其實是譯者真正地“洞察”了詩人的心境。英國紐馬克曾提出“語義翻譯”與“交際翻譯”兩個概念,前者適用于文學作品翻譯中,后者強調以讀者為中心,以歸化為主要翻譯策略[11]。persist譯法看似“大膽”,但展現了交際譯法的靈活性,且極大限度地傳遞了原語言的語義信息。
(三)詩形的適應性改造
詩體譯詩與散體譯詩這一爭論,歸根結底在于詩性與美感如何再現。綜觀譯詩,全詩行文流暢,開篇由-ing引導的狀語從句承接下句,后兩句又由連詞as自然勾連,思緒前后關照,概括之,語言平實,但卻言淺意深。兩位譯者使用了時興的自由體譯詩風,迎合了當代主流英語詩歌的潮流,雖省略了原詩的韻律韻腳,但也避免了“因韻害意”的風險[12]。通過綜合其個人情感,譯者最大程度地忠實于原詩的內容,也到位地譯出了原詩的精神。在翻譯過程中,作為文化調解者,兩譯者敏感地去探索詩人面對大自然時的文化心理,選擇并調整了相應的翻譯表現手法,使譯作順利地進入觀眾的期待視野。譯作既體現抒情山水詩的特點,又溝通了中西審美經驗,乃上佳譯作一枚。這次“中西合壁”的譯作,可移用呂叔湘點評賓納譯作的“出奇以制勝,雖盡可依循原作,亦不甘墨守”[13],許淵沖教授口中的“藝術譯法”[14]來評價。
四、文化適應性在《登飛來峰》英譯本中的體現
《登飛來峰》王安石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On the Winged Peak ?(Wang Anshi)
On the winged peak a sky-scraping pagoda towers.
Cock’s crows are heard to wake sunrise at early hours.
Fear not the floating clouds may veil the sun from sight.
For you have placed yourself at the top of the height.(Tr. 許淵沖)
詩人王安石最為人稱道的是推行“熙寧新法”,欲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當時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荊公學派”欲為“變法”找理論依據,認為人具有感覺和思維能力,能認識世界萬物。公元1050年夏天,詩人在浙江任滿回江西故里,宦游途中寫下此寓理山水詩。“唐詩言情,宋詩說理”,本詩就是一個典型代表。詩人從眼前景,身邊事說起,雖講理,但生動有趣,不死板。詩的一、二句寫景,三、四句于景闡發“站得高望得遠”的人生哲理。本詩之妙處,是其蘊含的理趣十分豐富。
(一)特色文化詞匯的語義適應
體現地域特點、民族風俗、文化典故等文化差異的專有詞令文化信息的傳遞難上加難,如詩中飛來峰、千尋塔的英文翻譯。起句中的飛來峰何在學術界向來有爭議,有兩說:一說在浙江紹興城外的寶林山,塔指應天塔。傳說此峰是從瑯即郡東武縣飛來的,故名飛來峰。另一說在今浙江杭州西湖靈隱寺前。許譯winged peak,意指“飛來之峰”,簡練地道。“千尋塔”中的“尋”本為古時長度單位,七或八尺為一尋,歷朝歷代的尺制不同,從戰國的23厘米一尺到現在的33厘米一尺不等。換算一下,約為2100米的高塔,連當代世界第一高樓800多米的哈利法塔都望塵莫及。詩人用這一夸張表述,借寫峰上古塔之高,寫出自己的立足點之高。sky-scraping pagoda意為“高聳入云,直沖云霄的寶塔”,譯者采用意象替換法,用詞老道、意思準確。
(二)意象處理過程中的語用適應
中國山水詩不僅用抒情的語言來抒情,也通過景物的畫面和豐富的意象來傳達內容。意象二字,以意為本質,以象為載體。翻譯過程中,意象的翻譯,應該采取以意為先的策略[15],如本詩承句的翻譯。此句用典《述異記》:“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則鳴,天下雞皆隨之鳴”。李白為浙江山水留下的著名大作《夢游天姥吟留別》中也曾云“腳著謝公木屐,身登青云梯。斗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本是“先日出,后天雞鳴”,但王安石不說“聞說日升聽雞鳴”,而是“先雞鳴,后日升”,用意頗深。詩人正值壯年,心懷抱負,欲借登飛來峰一抒胸臆。來看許淵沖教授如何準確把握詩人遣詞之意。譯文將“cock’s crows”作為意象,省略行為過程詞“hear”的感知者“I”,突出了天雞的響亮叫聲。原文本來用的是行為過程詞“見”字,但許譯采用“深化”類譯法中的“加詞”[15],即換用物質過程詞“wake”一詞,將天雞的動作描寫得惟妙惟肖,充分突出天雞的目的是“喚醒太陽”。原詩中天雞用以比喻遠大抱負的詩人自己;雞鳴旨在呼喚全新時代,喚醒統治階級;日升比喻盛世愿景。許譯為了突出無靈主語“天雞鳴叫”,即改革先鋒的吶喊,順勢變原語言的“主動”為“被動”,用限定嚴格的英文句法適應了西方人的邏輯思路。許教授運用深化法、創譯法,“從心所欲不逾矩”[14]地表現了詩人天雞般朝氣蓬勃、胸懷革新大志、對前途信心滿滿,重現了全詩的感情基調。
轉結二句,為絕妙名句,也是點睛之筆。心生畏懼(fear)本應是人類面對困難與生俱來的本能正常行為,許教授于行為過程詞fear后加上否定詞not形成強烈對比,傳神且簡練,從而表現了詩人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最后轉結二句譯文由連詞for自然勾連,思緒渾然一體。將“遮望眼”譯為“veil the sun from sight”,再次使用深化法,增譯太陽(the sun)這一意象,強調詩人心中的盛景氣象;“最高層”譯為“top of the height”,形象生動,再現“詩眼”。
(三)詩形審美的對等
原詩作為寓理山水詩的代表,詩歌風格爽利俊健,讀起來令人頗覺頓挫跌宕。英譯詩作以六音步抑揚格(iambic hexameter),12個音節構成的亞歷山大體(Alexandrine),“風神搖曳”地再現了中國寓理山水詩的特點。綜觀譯詩,詩句長短與原詩的形似,傳達出原詩的格律節奏美,實現了形式上的“對等”;亦以AABB韻式,傳達音韻美;內容上不是逐字的死譯,不僅傳達了原詩的意蘊,也譯出了原詩的神韻。簡言之,譯詩對仗工整,音韻優美,語言雋永,內容發人深省,真正做到了音美、形美、意美。譯詩適應與吸收了原詩語言和文化的活力,讀者結合自己的人生體驗和審美能力,能充分感受原作的意境美和精神。
結語
山水詩以山水景物作為獨立的審美對象,將自然景觀、人情風物以意象的形態展現在讀者面前,傳美感于文字和韻律之下。其翻譯應該既尊重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性,又體現其兼容性。詩的英譯與文化密切關聯,因此在翻譯過程中,文化適應性應該是不可或缺的衡量翻譯質量的評價標準。在充分理解原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的基礎上,既尊重原作當中所表達的意境和蘊藏的美感,又注重譯作受眾的文化接受和審美認同,努力使譯作受眾產生像讀原作一樣的閱讀感受,這就是文化適應性原則對詩詞譯者的要求。在中華詩詞譯介的漫漫長路上,我們應不忘初心,繼續堅持精益求精。
注釋:
①2018年1月25日,在浙江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時任省長的袁家軍提出要“積極打造浙東唐詩之路和錢塘江唐詩之路”;同年,浙江省委提出打造“四條詩路”,再加上大運河詩路與甌江山水詩路。目前,“四條詩路”文化帶建設正依照2021年發布的《三年行動計劃》穩步進行中。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N].文藝報,2014-01-03(01).
[2]黃驁騎.新語文教材里的山水詩[J].文科愛好者:教育教學版,2010(3).
[3]鄒志方.浙東唐詩之路[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84.
[4]BASSNETT S.Transplanting the Seed:poetry and translation[A]//BASSNETT S. & LEFEVERE A.(eds.).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58-66.
[5]劉宓慶.文化翻譯論綱(修訂本)[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7:62.
[6]韓琦敏.音樂劇《媽媽咪呀!》女主角形象在中文版翻譯中的文化適應[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3(4).
[7]王建國.劉宓慶文化翻譯理論簡評[J].外語研究,2010(2).
[8]張延琛,魏博思.唐詩一百首[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7:27.
[9]新牛津詞典[Z/OL].[2021-10-01].
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ache_1?q=ACHE.
[10]何兆熊.綜合教程1[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9:116.
[11]NEWMARK P.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Herfodshire:Prentice Hall,1986:212-217.
[12]朱斌.賓納與江亢虎英譯《唐詩三百首》研究[J].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19(2).
[13]呂叔湘.中詩英譯比錄[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0:12.
[14]許淵沖.譯學要敢為天下先[J].中國翻譯,1999(2).
[15]張智中.漢詩英譯美學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224-233.
作者簡介:胡麗艷(1985—),女,漢族,浙江永康人,浙江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翻譯研究。
(責任編輯: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