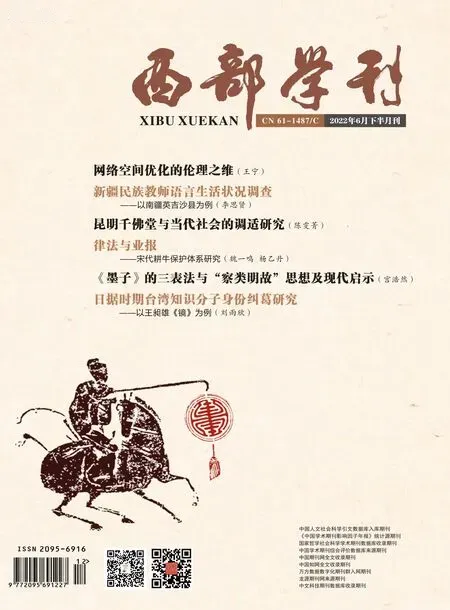《墨子》的三表法與“察類明故”思想及現代啟示
摘要:墨家與儒家并稱“顯學”,墨家之言在戰國時期一時盛極,對后世影響頗為深遠。墨子是中國最早自覺認識并總結提出科學方法論的思想家之一。墨子從民本主義的立場出發,構建出了“三表”的理論評價方法,并提出了“察類明故”的指導原則。墨子認為,為政者施政行事要運用“察類明故”的思想方法,從“考圣王事”“察民之實”“觀民之利”三個方面加以參照。這體現了墨家治國理政思想中尊重歷史經驗、以人民利益為本的基本立場。在現代視野下審視,可從《墨子》三表法所提倡的“本”“原”“用”三個重要方面了解和學習墨子“察類明故”的方法論思想。
關鍵詞:墨子;三表法;察類明故
中圖分類號:B2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12-0169-04
在先秦諸子中,墨子是繼孔子之后又一位極具盛名的思想家。墨子所創立的墨家學派在當時極具影響力,故孟子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1]5903,韓非子將儒、墨并稱為“世之顯學”[2]。作為“農與工肆之人”[3]67的代表,墨子胸懷著的是“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3]424的為民請命的理想信念,肩負著的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3]118的兼濟蒼生的使命擔當。即便是辟墨的孟子,亦不由感嘆:“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1]6025。
為了實現造福于天下生民的期愿,墨子率先意識到了科學原則和哲學方法論的重要性,認識到科學的方法論對于人們的實踐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所以,墨子從民本立場出發,構建出了包括“本”“原”“用”“三表”的理論評價體系,提出了“察類明故”的指導原則。墨子認為,為政者施政行事要從“考圣王事”“察民之實”“觀民之利”三個方面加以參照,依照“察類”“明故”的思想指引,以實現“愛利萬民”[3]77的價值目標。這些理論方法背后亦無不透顯著墨子殷切的民生關懷和篤實的民本精神。
一、三表法與“察類明故”思想的提出
“講民本”是墨家文化的重要核心理念之一。墨子從平民立場出發,提出了指導為政者民生建設的“三表法”。墨子言曰:
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連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3]400
在這里,墨子所述的“表”又稱為“法”“儀”或“法儀”,指的是標準或方法。“三表法”所指即是三種衡量標準和指導原則。墨子是中國最早總結出科學方法和哲學方法論的思想家之一,其原因就在于墨子最早意識到了樹立正確行為導向和價值指引方法的重要性。墨子認為,失去標準就無從辨別是非利害,一切也就難以謀求而不可明知其由。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無法做到“察類明故”,也就無法實現“愛利萬民”。如是,墨子正式提出了“三表法”: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3]400-401
墨子認為,衡量為政者的政治思想(理論)和作為是否可行,要從“本”“原”“用”三個方面來加以分析。所謂“本”“原”“用”,即“本源”“原因”“效用”。具體來說,也就是考究其本源,探索其原因,審查其效用。概言之,墨子所提出的三表法即為“考圣王事”“察民之實”“觀民之利”,其依據與目的在于“愛利萬民”,體現的是墨家以民為本的立場與兼濟天下的精神。歸結一處,墨子所追求的是為政者如何能夠更好地施政于民,為政者如何行事才能夠給民眾帶來最大的利益。
與三表法密切聯系,墨子在方法論意義上首先提出了“類”與“故”的概念,以此為明辨是非、審查異同而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在墨子看來,“類”是事物的類別與分類;“故”是事物發展的原因、根據或人們行動的目的,同時也是事物發展的一種結果。“察類明故”就是要求人們在認知事物時合理分類,找出各類事物的同異、因果及其演變依據,以探索前后的發展聯系,達成預期的行為目的。墨子強調,“察類”與“明故”密不可分,“明故”以“察類”為基礎,非“察類”則無以“明故”。因此,“明故”就意味著合理,就代表著持有正義的主張,站在正確的立場之上,也只有通過“察類”才能夠做到“明故”。故墨子云:“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3]220
可見,墨子所講的認知與辨別方法,不僅注重“類”的效果,也強調“故”的作用;只有“察言之類”,才能“明其故者”。其實,墨子作為廣大社會民眾的代言人,更希望的是為政者施政行事以“察類明故”作為指導思想。墨子主張的是為政者一切從民眾利益處著眼,站在平民角度之上,科學運用“察類”“明故”的指導思想,思索并解決民生問題,落實以民為本的基本原則。如是,為政者“察”諸多政“類”,“明”以民本為“故”,方可“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3]642。
綜上所論,三表法即“考圣王事”“察民之實”“觀民之利”,其依據與目的在于“愛利萬民”,這也是墨家民本精神內涵的外在體現和落實。為政者只有按照“察類明故”思想的要求,做到了“察”諸政之“類”,“明”民本之“故”,才能“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察名實之理”。由是可見,墨子的三表法與“察類明故”思想密不可分且一體相融。兩者既同為明辨是非、審查異同的理論方法,又同是體現以民為本、民生為重的思想主張。其實,墨子所提倡的,就是為政者“察”“本”“原”“用”三表,以“明”民為邦本、民為政基之“故”。
二、“察”圣王之“類”,“明”鑒史之“故”
在三表法中,墨子提到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這表明了為政者要善于將歷史上的成功經驗(圣王事跡)作為施政行事的參照。在墨子看來,“若昔者三代圣王,足以為法矣。若茍昔者三代圣王足以為法,然則姑嘗上觀圣王之事”,即上古三代的圣王足以作為效法的對象以樹立起辨別是非的標準,以此建立準則就要察看圣王的作為和事跡。這其實就是要求為政者首先做到對于“圣王之事”的“察類”。所以,墨子說:
然胡不嘗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明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3]414
墨子認為,只有圣王出現天下才能實現大治:為政者效仿圣王作為,依循圣王事跡,才能實現“古之圣王之治天下”[3]97的治世理想。故墨子對“圣王之事”推崇備至,在《墨子》中列舉了諸多的“圣王”事跡,為后世為政者施政行事以作參照。縱觀《墨子》全文,“圣王之事”涵蓋了墨子的“十論”思想,盡管其中的一些具體主張或已脫離時代,但這些思想中大多對于我們現代的社會生活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更何況墨子三表法所提倡的“考圣王事”具有的現代意義還在于其方法論的指導價值。概言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的“察類”所指的是,對歷史上依舊符合當今時代要求的成功案例的效仿和學習,對當今仍有益的以往治國理政的經驗的汲取與吸收。
所謂“本”,即為“故”,也就是“察”“圣王之事”此“類”的本源。“本”“故”其實所指的就是成功的歷史經驗,要求的是為政者決策前要對以往治國理政的成功案例加以深入考察,充分汲取間接經驗,以做到“以史為鑒”。換言之,這就是要求為政者施政時以歷史案例作一參照系,以歷史經驗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闡述治國理政新理念時大都體現了對歷史經驗的學習和運用,在講話中屢屢引用經典古語與歷史典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問題進行的第十八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創造的;對綿延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應該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對古代的成功經驗,我們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4]。“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5]
三、“察”民情之“類”,“明”愛民之“故”
在三表法中,墨子講到了“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這要求為政者要體察民情,聽取百姓對其執政施策的反饋意見,據此適時調整、不斷完善相應舉措以改善民生。具體來說,為政者要通過深入基層考察各項政策指導下人們的實踐活動,以了解人們實踐所取得的真正實際效果,在此基礎上對施行的政策加以堅持或改進。其實,這就是要求為政者做到對于“察民之實”的“察類”。所以,墨子說:
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3]337
可見,墨子主張以天下民眾的耳目之實作為判斷是非有無的重要基礎。在此事實基礎之上,墨子又告訴為政者,“察”“百姓耳目之實”之“類”所需“明”其中之“故”,即為“察民之實”背后所蘊藏之“原”。其實,三表法的“原”即為墨子一貫主張的愛民思想。為政者只有本著愛民之“原”才能獲得民心之所向,方可實現天下大同的治世理想。具體來說,即是要求為政者施政行事“察”“百姓耳目之實”之“類”,以“明”愛民之“故”。
以現代的視野來解讀,“察民之實”與我們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以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相背離。“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6],它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執政施策時,要始終堅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多聽取來自于群眾的聲音,著力解決群眾強烈反映的問題。為政者只有親身實地實踐、深入考察民生民情,才能做出最有利于人民群眾、最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正確決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把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深深植根于全黨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實到每個黨員行動上,下最大氣力解決黨內存在的問題特別是人民群眾不滿意的問題,使我們黨永遠贏得人民群眾信任和擁護[7]698。這種鮮明的人民立場所反映的就是墨子“察民之實”的愛民之“原”。所以,本于愛民之“原”,堅持群眾路線,就要真正讓人民來評判我們黨和政府的工作。所謂“知政失者在草野”“人心就是力量”,說的就是我們黨的執政水平和執政成效只能由人民來評判,人民才是我們黨的工作的最高裁決者和最終評判者。因此,出自于愛民之“原”,為政者要做到“察民之實”,了解各項政策在群眾當中的反響,讓人民來評價各種為政舉措。
四、“察”民利之“類”,“明”利民之“故”
在三表法中,墨子強調了“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這要求的是為政者要通過考察決策對于改善國計民生的實際效果,以判斷施策是否得當。正如《兼愛下》篇中所指出:“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3]176即如果施行的政策不能夠給民眾帶來好處,那就不能繼續采用;反之,如果政策是有利于民眾、能夠給民眾帶來實惠,那就要堅持執行。
接下來,圍繞著“觀民之利”的命題,墨子提出了“志功合一”的主張,即將動機與效果結合起來考察道德的評價機制。出于對同樣具有善的意義的效果卻可能來自完全相反動機的考量,墨子說:“合其志功而觀焉”[3]735,表達了對于“志”的重視,將其作為與“功”一同結合起來評判政治道德的重要標準,并認為為政者只有做到“利民”的“志功合一”才能是民生真正的托付者。同時,墨子又非常重視“功”,強調效果在道德評價中的作用。《墨經》上說:“功,利民也”[3]473,道出了“功”之所指就是為政者利民之舉的義理。《非攻》下篇亦提及了為政者利民之舉愈多則功勞愈大:“利人多,功故又大。”[3]218
可見,墨子十分重視功利的價值,其畢生其實都在致力于使為政者治理下“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飽食,便寧無憂”[3]304。特值一提的是,墨子提倡的功利價值觀與近代西方的功利主義價值觀相異趣,差別在于墨子是以利民為目的而不是為手段。這也充分反映了墨子政治倫理思想所具有的強烈人民性之要義。所以,所謂“志”就是“愛利萬民”的動機,“功”就是為民眾謀求利益的成就。“志功合一”中的“志”“功”,其實也就是“察”民利之“類”背后所蘊藏著的“故”。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黨和政府把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比之以墨子的“觀民之利”的利民思想,與“三個有利于”指導思想中的“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民生關切不無暗合之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一次會議上提出:“把是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否給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作為改革成效的評價標準。”這是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社會發展步入新階段、改革全面深化呈現新態勢的宏觀格局下,提出的關于改革成效評價的重要標準[8]。其實,“兩個是否”可以認為是對“三個有利于”的新發展,而這種發展又或與墨家“觀民之利”的利民思想不無關系。
我們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這與墨子所主張的“察民之利”的利民思想亦旨趣相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檢驗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終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實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利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7]698。這種鮮明的人民立場所反映的亦是墨子“觀民之利”的利民之“用”。
結語
墨子從民本主義立場出發,構建出了三表法的理論評價體系,提出了“察類明故”的方法論思想。他認為,為政者施政行事要從“考圣王事”“察民之實”“觀民之利”三個方面加以“察類”,以做到“明”其“本”“源”“用”之“故”,實現“愛利萬民”的政治理想信念。讀《墨子》不啻為了解墨家政治思想精粹,學習其心系民生以造福于民之優秀品格的一條重要捷徑。《墨子》中譬如三表法、“察類明故”思想在內的諸多真知灼見仍值得我們去挖掘和弘揚。經過現代視野下的重新認知和解讀,我們認為,當代治國理政要學習和借鑒墨子三表法的理論評價方法及“察類明故”的指導原則,把它們作為加強黨員干部政德修養的精神滋養。在現代視野下審視,我們可以從《墨子》三表法所提倡的“本”“原”“用”三個重要方面了解和學習墨子“察類明故”的方法論思想;以古照今,廣大黨員干部修身為國、勤政為民,亦可通過觀《墨子》以獲得有益鏡鑒。
參考文獻:
[1]阮元.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09.
[2]王先慎.韓非子集解[M].鐘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8:456.
[3]吳毓江.墨子校注[M].孫啟治,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
[4]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N].人民日報,2014-10-14(01).
[5]杜洪雷.習近平從歷史中借鑒了什么[N].齊魯晚報,2014-10-14(A05).
[6]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M]//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307-322.
[7]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M]//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8]吳毅君.改革評價標準:“兩個是否”對“三個有利于”的新發展[N].光明日報,2017-06-02(11).
作者簡介:宮浩然(1996—),男,漢族,山東棗莊人,單位為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方向為子學文化、儒家文化。
(責任編輯: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