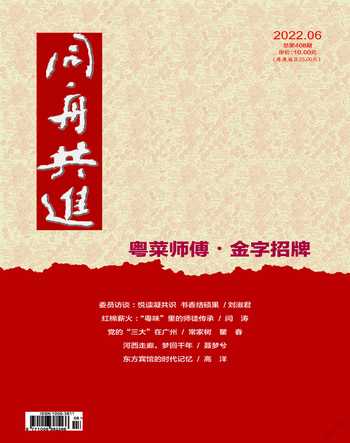都江堰的治水“密碼”
龔靜染
都江堰市過去叫灌縣,因灌江而名,即灌溉之意。《小腆紀傳》中說:“江從灌口來,夏秋水漲,闊盈里許。冬春水涸如帶,邦人或以‘河’名之。”但這個“灌”字不簡單,直接以“灌”作為地名可能在世界上都罕見。
我對“灌”的最早認識源于我父親,他曾在一個山區(qū)的水庫工作了十多年。那個水庫處于岷江水系三級支流上的鎮(zhèn)江河流域,離都江堰應(yīng)有足足200里的距離,但都江堰的水卻通過東風渠一路引流到水庫里,并用以灌溉附近的3萬畝農(nóng)田。小時候放暑假,我就會去父親的水庫玩耍。水庫有個百米長的庫壩,高達六七十米,頗為雄偉。洪水季節(jié),水庫有個泄洪口,水會通過泄洪口排出,形成一道懸瀑,壯觀之極。所以我從小就知道水庫的用處是為了灌溉,而那個水庫跟都江堰有很大關(guān)系,它是都江堰龐大灌溉體系中的一個分支。
“灌”是都江堰的魂,都江堰讓岷江為民所用,為萬頃土地所用。都江堰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而它的重要性也佐證了岷江絕非一般的江河,清人王人文在《歷代都江堰功小傳》的序中寫道:“中國言水利者,蜀最先。大禹,蜀人也;開明,蜀帝也;李冰,蜀守也。”都江堰這項古代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是中國早期對河流進行開發(fā)利用的實證,而它就在岷江上。
戰(zhàn)國時期,秦伐蜀,當時一般的謀士都反對,認為四川是蠻夷之地,沒有必要興師動眾,耗費錢財。但秦國將領(lǐng)司馬錯極力主張,認為“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他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呢?主要還是因為川西壩子的肥沃和岷江的灌溉、通航之利。后來的歷史印證,司馬錯的主張完全正確,秦惠文王采納了他的建議。
得蜀后,秦國又對都江堰進行開鑿和治理,同樣反映了秦國的政治軍事智慧,后來蜀郡守李冰治水雖然功勞很大,應(yīng)該說也只是貫徹了這一戰(zhàn)略思路,且深知治蜀必先治水的道理。著名學(xué)者姜蘊剛曾稱李冰是“世界上最古老、最聰明的水利專家”,他的功勞是“看定治水機要,在于萬山之下的灌縣地方,由岷江中流鑿開離堆以分散水勢,以內(nèi)外二江,然后再設(shè)都江堰操縱水力,使其灌溉整個成都平原,由水害轉(zhuǎn)為得水之利”。
“治水機要”四個字最為重要,也就是說,李冰的厲害之處,在于他非常準確地發(fā)現(xiàn)了岷江流域上這個最為重要的水利樞紐之地。清朝光緒年間,四川總督丁寶楨對都江堰水利進行修繕,就是隨意動了這個“治水機要”,從而引發(fā)了一場風波。
事情是這樣的,清光緒六年(1880),朝廷內(nèi)閣收到給事中吳鎮(zhèn)的一封奏折,說丁寶楨誤聽道員丁士彬之言,將灌縣離堆拆毀。此事非同小可,事關(guān)川西平原的水利和民生,所以接到奏折后,朝廷馬上派恩承、童華兩人前往調(diào)查,后又派成都將軍恒訓(xùn)督查此事,一時間讓地方緊張異常。
恒訓(xùn)督查后,在給朝廷的奏折中反映的問題主要有三點:一是在“分水大魚嘴,用石條當頭陡砌,加高一丈,一遇盛水,反致沖激漫溢”。二是“原修人字堤金剛墻(即現(xiàn)在的飛沙堰)一百三十丈……沖毀殘缺”。三是“離堆當水之沖,已有塌裂之處,設(shè)全行沖塌,省門恐為澤國”。
都江堰水利工程最重要的三個地方就是魚嘴、飛沙堰、寶瓶口,三者的主要功能分別是分水、泄水、排水。而恒訓(xùn)說丁寶楨在這三處都出了問題,這還了得,朝廷要求丁寶楨據(jù)實回奏。
丁寶楨(1820—1886),貴州平遠人,咸豐三年(1853)進士,擔任過岳州知府、長沙知府、山東巡撫、四川總督等職務(wù)。為官期間,頗具政聲,特別是他在當山東巡撫時,兩治黃河水患,攢下了足足的功德和口碑。所以光緒二年(1876),他到四川上任后被寄予厚望,剛一到任就干了幾件大事:嚴劾貪吏,建機器局,改革鹽法,修都江堰。但就在修都江堤堰一事上遇到了非議,被非議的關(guān)鍵就是把這個千年古堰給修壞了。
在都江堰的歷史上,歷代修堰都要遵循一個古老神秘的六字之法:深淘灘,低作堰。這句話如何理解?曾當過十年成都水利同知的強望泰,從道光七年(1827)起專門管理都江堰,他認為自己做的事是“矧都江堰千支萬派,溉十四州縣之田,活億萬生靈之命”,責任非常重大。強望泰是一位經(jīng)驗豐富的水利專家,在他的治理下,堤壩堅固,溝渠暢通,岷江暫無水潦之虞,下游灌區(qū)大大受益,而這都同他能深刻領(lǐng)會古法治堰的精妙之處有關(guān)。
他在《兩修都江堰工程紀略序》中是這樣理解“深淘灘,低作堰”的:
其云深淘灘者,所以防順流之沙石,不使淤入內(nèi)江也。低作堰者,所以使有余之渠水,便于泄入外江也。推明其義,因于是冬興工,即高加河防,廣作埂籠,深去河底之磧沙,低砌籠堤之層數(shù)。戊子春夏察看水勢,六字之法,覺更有驗,旋于各堰一律如前修治。
其實,這段文字看似簡單,實際操辦卻不容易。強望泰分析過歷史上的修堰經(jīng)驗和教訓(xùn),在“延訪紳耆,披閱志乘,細釋深思”的基礎(chǔ)上,才悟得古人六字之法的奧妙。但在實際修堰的過程中,還是疑竇叢生,如“深淘灘”要“深”到什么深度?“低作堰”要“低”到什么程度?因為從來就沒有一勞永逸的辦法,水情年年有變,而堰需年年修,在當時的條件下就得靈活掌握,對水情的拿捏十分不易。強望泰在擢升他地后,仍對都江堰充滿敬畏,認為自己多年的努力遠不能說是深謀遠慮,所以他寄望后賢能認真領(lǐng)悟六字古法,活學(xué)活用,用心管理好都江堰。
民國時期,吳江人沈兆奎曾寫過一首題為“都江堰”的詩,讀來頗有一番趣味。
深淘灘,低作堰,此理自深語自淺。
岷水分歧肺葉張,遂令千里成饒衍。
“岷水分歧肺葉張”一句非常之妙,在都江堰分水后,干支流散開,確如張開的肺葉,而分水的關(guān)鍵就是那六個字。丁寶楨所受到的責難其實就是說他沒有遵行六字古法,沒有找到治水機要,致使每年洪水來臨時沖毀河堤,貽害無窮。如吳鎮(zhèn)的奏折中說:“都江堰外江淤沙堆塞,地勢高于內(nèi)江丈余,丁寶楨復(fù)將內(nèi)江挖深一丈七八尺,水勢全注內(nèi)江,連年堰工沖塌,實由分水不勻所致。”所謂分水不勻,其實就是沒有掌握好“深淘灘,低作堰”的精要之處,讓內(nèi)外江失衡,河道受沖。
或許丁寶楨是真心想為百姓辦好事吧,畢竟他過去是朝野皆知的循吏,故他對恒訓(xùn)的“空言訾詆”感到很震驚,也很委屈,于是自辯道:“都江堰之壞,非壞自臣。臣之修堰,并非將河堰遷移而改置之也;亦就其自來形勢。為之疏其壅塞,培其堤埂,以順民之情,而救時之弊耳。”
后來丁寶楨寫了《覆陳都江堰工情形疏》一折,逐條應(yīng)答恒訓(xùn)的責難。他在回應(yīng)恒訓(xùn)關(guān)于“分水魚嘴”的指責時說,分水魚嘴每年都要修,工程卻常常偷工減料,裝卵石的竹籠一看就很“卑薄”。此處正當岷江正流的要沖,是截水的關(guān)鍵所在,建筑材料如果不堅厚高大,根本不能抵御洪水侵襲。他在魚嘴之前和兩側(cè)加了石籠外護數(shù)層,工程效果非常不錯,幾年來經(jīng)大水沖擊,至今屹立中流,絲毫沒有損壞。丁寶楨對恒訓(xùn)有些憤怒,不無譏諷地在奏折中寫道:“試問加高一丈,盛水猶且沖激漫溢,設(shè)再卑薄,則水將駕過魚嘴二丈以上,是一片汪洋,更何從藉以分水?其漫溢又將何如?”
丁寶楨又對恒訓(xùn)“離堆當水之沖,已有塌裂之處,設(shè)全行沖塌,省門恐為澤國”之語進行回應(yīng)。他說,都江堰的離堆正當江口上,李冰在開鑿內(nèi)江時,特意留了山石一角來對它進行屏障。由于上游山腳有石巖三道,將水一擋后,減少了沖擊力,使水不能直接沖擊離堆,這是李冰非常高妙的設(shè)計。但在同治三年(1864)修堰時,成綿道道員何咸宜誤將三道巖全部鑿去,致使離堆失去屏障,第二年洪水一來就把離堆沖塌了一角。后來該縣士民極為不安,多次想補砌,但因石頭是天然的,人工無能為力,所以他最怕補砌石頭后,效果會適得其反,假如一旦被水沖垮,石頭落下去就會堵塞堰口。
其實,丁寶楨修都江堰并非沒有用心用力,而恒訓(xùn)作為成都將軍,手握軍政大權(quán),還要參與川邊藏區(qū)的地方事務(wù),與他在權(quán)力上互相制衡,難免不故意挑刺。丁寶楨雖據(jù)理力爭,仍被朝廷認為有過錯。從中也可看出四川總督與成都將軍之間的矛盾之深。

《清實錄·光緒朝實錄》中記錄了此事的最終官方定論:
丁寶楨辦理堤工要務(wù),又值經(jīng)費支絀之時,宜如何盡心區(qū)畫,慎重興辦;乃僅憑丁士彬之言,并不詳細考察,率更成法,發(fā)帑興工,以致被水沖刷;又不據(jù)實奏陳,迨經(jīng)降旨詢問,仍以“人字堤毫無損折”等辭,粉飾覆奏,實屬辦事乖方。
處理辦法緊隨其后,首先是要求丁寶楨必須“仍守成法”,將分水魚嘴退修原處,再將外江淤沙淘平,內(nèi)江深漕平墊。按古法中的“內(nèi)六外四”來分水,并且“一俟水涸農(nóng)閑,即行辦理”。本來丁寶楨想在修堰上尋求更好的手段,但這樣一來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同時,他那幾年費盡苦心的治堰之舉被全部否定不說,相關(guān)人員也遭到處罰,成綿龍茂道員丁士彬、灌縣知縣陸葆德被革職,丁寶楨自己也被降為三品頂戴,只因皇帝念他過去的功勞,且此事只是好心辦壞事,所以還繼續(xù)讓他留任四川總督。
通過這件歷史陳案可以看出,丁寶楨之所以事與愿違,有一己固念、試圖僭越前賢的原因,也有歷史認知能力造成的局限。
1942年,老舍流寓四川,曾經(jīng)游覽都江堰,他在二王廟的墻上看到了“深淘灘,低作堰”六個字,也對這古法有所思考:
治水的訣竅只有一個字——“軟”。水本力猛,遇阻則激而決潰,所以應(yīng)低作堰,使之輕輕漫過,不至出險。水本急流而下,波濤洶涌,故中設(shè)魚嘴,使分為二,以減其力;分而又分,江乃成渠,力量分散,就有益而無損了。作堰的東西只是用竹編的籃子,盛上大石卵。竹有彈性,而石卵是活動的,都可以用“四兩破千斤”的勁兒對付那驚濤駭浪。用分化與軟化對付無情的急流,水便老實起來,乖乖地為人們灌田了。
老舍用一個“軟”字概述治理都江堰的方法,可謂道出了精髓所在。都江堰水利工程關(guān)系著億萬民生,歷代的治理都是謹小慎微,不敢貿(mào)然創(chuàng)新,這里面有著不少歷史經(jīng)驗和教訓(xùn),丁寶楨就是其中一例。都江堰有賴天地間的造化,是隱藏千年的水利密碼,要破譯它困難重重,而人們只能心領(lǐng)神會,相度形勢,對岷江水加以引導(dǎo),而不能憑一己想象行事。“深淘灘,低作堰”的核心是師法自然,人一定要順服于自然規(guī)律,否則就會招來禍患,正如強望泰所說:“余不敢諉之于天,不得不師之于古。”
但保守陳法,并不是指不作為。陸游在《禹廟賦》中說過:“溝澮可以殺人,濤瀾作于平地。”這絕非故作驚人之語,不管哪個朝代的統(tǒng)治者都要重視水利建設(shè),小心翼翼地對待大地上的每一條江河,才能“避其怒,導(dǎo)其駛”。
清道光四年(1824),四川布政使董純頒布了一張《防旱示》,他為了興修水利,特地制定了13條政策,勸諭四川各地筑堰開塘,以防災(zāi)害,并“將以水利廢興,定地方官之賢否,為舉劾之權(quán)衡”。將水利之興與仕途掛鉤,一條訓(xùn)令的產(chǎn)生背景和實施效果,都是與岷江水利密切相關(guān)的,它的利害程度是“以糧民身家計”的。所以,水利之興廢,牽連官吏之升貶,又必然會關(guān)系到庶民之禍福。
值得一提的是,有人曾認為六字古法最早是“深淘灘,低則堰”,而非“低作堰”,那個“作”字是后人改的。是否真有其事?清人彭遵泗在《蜀故》一書的“補遺”中有記載:
灌縣離堆斗雞臺之下,塹鑿石崖,尺為之畫,凡十有一,謂之水則。水及其九,則民喜,盡沒,則民困。傍有石刻八分書“深淘灘,低則堰”六字,皆蜀守李冰所為也。今《志》改“則堰”為“作堰”,便失其意,亦且不文。書以存古。
所謂“水則”,就是中國古代的水尺。宋代的水則是刻石十畫,兩畫相距一尺。設(shè)立水則的目的是觀察水位情況,以起到報汛的作用。“低則堰”的大意可能是水位低的時候便在堰上刻畫水則,確實與“低作堰”迥然有別,一個是記錄水情,一個是筑堤防洪。這樣說來,難道是人們理解錯了?一字之差卻是玄機重重,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如今,每次到都江堰游覽,我必在玉壘山的古建筑上眺望一番,那個位置正好可以把都江堰的全貌盡收眼底。悠悠江水流,歷史仿佛隨時都會從中突然站立而起,讓人們看到它還未消失的身影。杜甫當年曾在此處寫道:“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
(作者系文史學(xu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