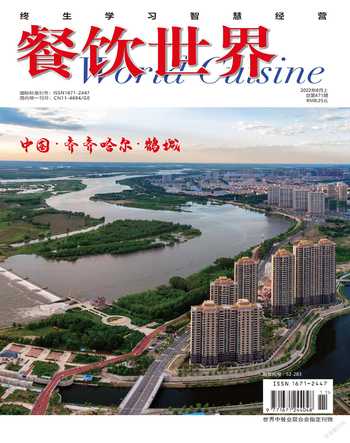中華飲食的文化自覺與飲食文明共同體的形成
白瑋
從中國的飲食結構上來說,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有四種飲食文明:以黃河中下游中原地區為中心的小麥文明,以長江中下游為中心的水稻文明,以西北塞外為中心的游牧飲食文明,以及以西北黃土高原為中心的小米文明。
中原飲食文明主要以麥面為主,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生活;江南飲食文明以魚米為主,過著飯稻羹魚的優渥生活;草原飲食文明以牛羊肉為主,過著刀馬游牧的生活;而小米,代表的則是黃河流域的黃土文明。
以農業文明為核心的中原飲食文明,由于土地肥沃,在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期內,都象征著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和繁華富庶。這為以后的戰事連綿埋下了不可避免的伏筆。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同飲食文明的交匯激蕩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從周朝開始,來自西北的西戎族群,由于向往中原的富庶,為了獲取中原的食物,就與中原的王朝不斷地發生著戰爭。周幽王時,為了博得美人褒姒一笑而烽火戲諸侯,最終釀成大禍。
公元前771年,申侯與犬戎聯絡,進攻周王朝,諸侯都不來救駕。犬戎與申侯迅速攻入鎬京,幽王急忙逃到驪山,被驪山之戎所殺。這時,關中地區大部分都被戎人占領。

到周平王時,又逢天災不斷。據史料載,從周宣王末年開始,西北關中一帶連年干旱,洛水、涇水和渭水三川都干涸了,農業生產遭到毀滅性破壞,所產的食物已不足以支撐一個強大的王庭運行。同時,岐山一帶又發生了地震和地崩災害,老百姓的飲食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周太史伯陽父根據陰陽五行學說,認為這是周將要滅亡的征兆。
當時,京師宮殿被焚毀,國庫虧空,而且西邊的很多土地都被犬戎占去,邊境烽火也是連年不息。于是,周平王不得不在秦國的幫助下將國都從鎬京東遷至洛陽,把對付西戎的臟活、累活都交給了秦襄公去打理。這為以后秦國的強大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以周平王東遷為分界,它標志著西戎的刀光正式開始閃爍進中原王朝上空,自此就再也沒有停止過。西北和東北的各個族群部落,包括匈奴、西羌、鮮卑、黨項、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型的各個族群,都先后向中原王朝的農業飲食文明不斷發生著沖擊。一個游牧族群被打跑,另一個新崛起的族群又襲來。兩千多年的歷史下來,來自北方的游牧族群像潮水一樣不斷沖擊著中原糧食文明的河灘。
歷史比較吊詭的是,當北方游牧文明的刀光在中原的農田里閃爍時,中原王朝的臣民們也向南方的魚米之地大規模地移民。在中國歷史上,前后發生的五次大規模移民像倒口袋一樣,把中原的人口和糧倉都倒往了南方。
對于中原農業文明下的漢族族群來說,如果說周平王的東遷,只是把王朝文明從墻外搬到了墻內的話。那么,后來發生的五次大規模移民,則是把王朝文明帶著飲食文明從故鄉搬到了異鄉。
在這五次大規模的移民歷史中,有兩次移民造成的影響最大:一次就是西晉時期五胡亂華造成的衣冠南渡;另一次則是北宋末年靖康之恥下的宋人南遷。兩次大型的移民都分別誕生了四個飲食文化帶:一個就是今天的客家菜文化帶,它相對完好地保留了中原飲食文化的余脈帶;一個就是東晉的國都建康,即今天的南京飲食文化帶;一個就是南宋的臨安,即今天的杭幫菜文化帶帶;一個就是今天的黃山,即徽菜文化帶。這四個地區的飲食風格都很好地延續發展了中華的飲食文明。
其間,加之隋煬帝開通的京杭大運河,將南北的飲食文化全面打通和連接,從而又創造了一個個運河沿岸的碼頭飲食文化。在此態勢下,食物的界線漸漸模糊,它們匯合在同一個王朝的餐桌上豐富著一個個后來的飲食民生,而淮揚菜無疑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我們先不討論歷史的成敗和悲歡,僅從飲食文明的傳續上來說,四種飲食文明的相互交織和融合發展構成了中華飲食文明的主體。如今,我們餐桌上擺放的食物,既有羊肉的鮮,也有魚米的甜,還有面食的暖。它們同時匯聚在我們的胃里,一如在我們肌體內流通的混合血液一樣,構成了我們今天所有的飲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