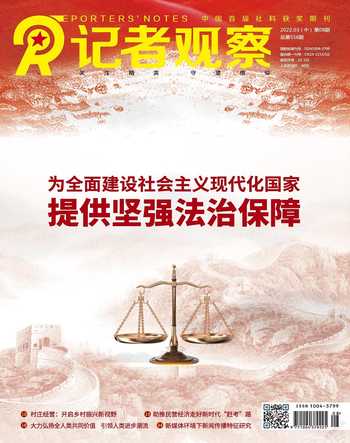淺議融媒體背景下數字出版的發展及編輯工作認識
薛慶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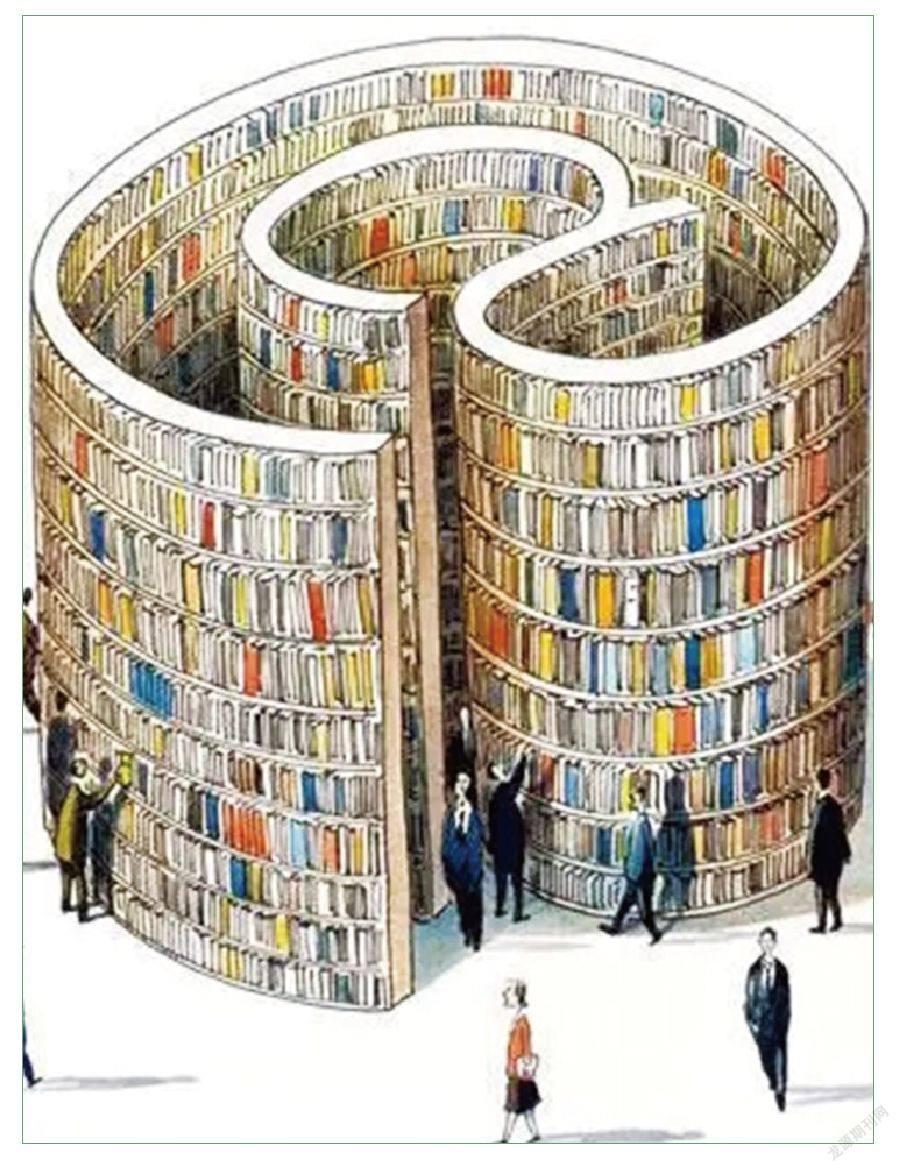
摘要:我國“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對于傳統出版產業來說,加快數字化轉型升級,促進傳統出版產業順應變革和融合發展,也是綱要應有之義。在融媒體背景下,做好數字出版的編輯工作,既是新時代對造就全能型出版人才的要求,也是編輯自身所應承擔的責任。
關鍵詞:融媒體;數字出版;編輯工作;認識
我國數字出版的發展進程
數字出版是近年來出現的一種新型出版形態,2018年即被列入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目錄。有學者這樣定義,數字出版是以數字化為本質特征、以數字技術為特有屬性、以數字技術賦能為產業鏈特征、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內容編輯加工,并通過互聯網發布數字內容產品的傳播方式,是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而形成規模的。數字出版從發端到成熟,也經歷了從初級階段到中級階段再到蓬勃發展階段的三個演進過程。
初級階段
電子出版被學界公認為是數字出版的第一階段,是隨著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的發展而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出版形式。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內存計算機只讀光盤和個人PC機的出現,使得電子出版載體CD-ROM應運而生;到90年代后期,CD-ROM逐漸被新的電子出版載體所取代。
早期的數字出版,只是簡單翻拍紙質圖書,即用數碼相機將出版物逐頁翻拍,然后掃入電腦,再上傳到互聯網。由于其缺少“內容生產數字化、管理過程數字化、產品形態數字化”等相應的數字出版流程,因此,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出版。
中級階段
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應用的普及,數字出版以互聯網出版為特征進入第二階段。與此同時,在手機的日益普及和功能不斷提高的背景下,互聯網出版又在無線網絡領域得到進一步發展。
互聯網出版顧名思義,是通過符合資質的互聯網信息提供者將自己創作或他人創作的作品,經過選擇和編輯加工,發布在互聯網上或者通過網絡發送到用戶端,供公眾瀏覽、閱讀。互聯網出版較電子出版最大的進步在于從載體形式、生產方式以及內容提供方式來看,互聯網出版周期短、成本低,在傳播上更加快速、便捷。
發展階段
數字技術的日臻完善,為數字出版帶來了巨大的成長空間。數字出版也以前所未有的動能而蓬勃發展。大數據是信息時代新的生產力,在大數據賦能下數字出版正逐步向數據出版迭代升級。相對于技術較為平庸的電子出版和互聯網出版,數據出版已成為一種科技含量更高的出版形式。“數據出版的最大特點是改變了出版創作的方式”。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智能出版、智能閱讀、智慧出版將會成為數字出版的更高階段。
疫情沖擊下數字出版的發展態勢
疫情期間,數字出版的產業現狀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兩年多來,我國全行業都受到了很大沖擊,傳統出版業更是按下暫停鍵。2020年前半期紙質圖書的銷售碼洋遭遇了斷崖式下跌。與紙質圖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數字出版在疫情期間卻逆勢上揚,令人振奮。據北京日報消息,第十一屆中國數字出版博覽會在國家會議中心開幕,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布了《2020—2021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報告顯示,2020年,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整體收入超萬億,比上年增加19.23%,呈現逆勢上揚態勢。數據說明,數字出版的產業優勢和巨大的商業價值在疫情期間充分顯現。
當下數字出版所面臨的問題
第一,內容開發。無論數字出版還是傳統出版,都非常重視內容開發。內容開發是數字出版產業鏈條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作為產業鏈上游,如果缺少有高度、有深度、有氣度、有溫度的內容做支撐,否則數字出版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從目前形勢來看,雖然疫情的暴發直接拉動了數字出版產品的消費需求,但我們還應當看到,除在線教育、網絡文學、有聲讀物、網絡游戲之外,從內容開發層面上看,一方面,品種仍較為單一,不能滿足廣大消費者對數字產品多樣化的需求。很多傳統出版資源中優秀的作品,并沒有開發成為數字出版產品,造成資源的浪費;有些數字出版產品一味追求閱讀流量和點擊率,對內容把關不嚴,開發出了一些迎合低俗趣味的內容,有些甚至打出色情暴力的“擦邊球”,導致低劣作品泛濫。另一方面,選題雷同,內容同質化現象嚴重。凡此種種皆損害了產業的良性發展,應引起有關部門足夠的重視。解決之道應是依托傳統出版中豐富的內容資源,整合優化數字出版全產業鏈,充分利用數字技術創新內容開發,以新時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導向,篩選出有夢想、有內涵、有價值的優質內容,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實現數字出版高質量發展。
第二,人才匱乏。眾所周知,數字出版無論從技術手段、產品形式、出版流程,還是市場營銷和傳播渠道等方面,都與傳統出版有很大不同。而數字出版的“數字化”特征,對從業人員較傳統出版在數字技術層面的要求更高。但是,從目前來看,傳統出版從業人員的教育背景均以文史專業居多,知識結構較為單一,重文輕理的情況較為普遍。對數字技術、信息技術、傳播技術知之甚少,知識儲備嚴重不足。掌握傳統出版運作流程的從業人員,不懂得數字出版技術和運營模式,對如何產生價值更是一頭霧水,簡單地認為數字出版不過是一種燒錢游戲,觀念較為陳舊;而有著一定數字技術的從業人員又不了解傳統出版的基本流程,對選題論證、三審三校制度頗有抵觸,二者缺乏融合。因而,加強數字出版復合型人才培養是當前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
第三,版權保護。長期以來,版權保護不力是制約數字出版發展的另一大因素,也是目前亟待解決的痛點和難點問題。相關法律法規的滯后,使得大量侵權、維權、再侵權、再維權形成的閉環無法破解,造成作者、出版機構因維權疲于奔命、收效甚微。因此,版權問題始終困擾著數字出版產業的健康發展。由于數字出版的特殊性,導致相關權利不像傳統出版那樣清晰可辨,權利邊際識別較為模糊,版權問題異常突出。新修訂的《著作權法》于2020年11月11日發布執行,其中有專門章節就圖書出版作出規定,但未明確區分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且條款規定缺乏強制性,給實際操作帶來困難。正是由于相關法律的滯后,使侵權變得更普遍、更隱蔽、更容易、成本也更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侵權案件頻發。據不完全統計,自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全國共發生著作權侵權糾紛案高達913451件,案發數量觸目驚心。如此高發的侵權行為無疑對行業造成了傷害。可以這樣斷言,沒有完善的版權保護機制,我國的數字出版很難做大做強。有鑒于此,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首先,完善立法。在《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以及《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的框架下,立法部門應盡快出臺適應數字版權保護的法律條款和規范,避免出現法律真空,形成有利于產業發展的法治環境。對侵權行為長期形成高壓態勢,以法律手段凈化數字出版的產業生態。
其次,加強監管。行業監管部門應切實履行職責,進一步完善監管體系、強化監管手段,完善網絡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建立間接第三人責任制度,對侵權行為進行全程監測,及時發現、高限處罰、加大懲罰力度;建立黑名單制度,對有侵權行為的單位和個人IP,運用多種技術手段重點監控,層層防范,推進監管體系和監管能力的現代化。
最后,技術保護。利用數字技術進行版權保護,是目前公認且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之一。目前較為成熟的數字版權保護技術稱為DRM。DRM技術是通過加密、數字水印、身份認證等方式保護數字資源不被非法傳播和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版權保護問題。早在2011年,我國就已啟動被列為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重大科技專項——“數字版權保護技術研發工程”。作為第一個正式啟動的新聞出版重大科技工程,標志著我國運用技術手段解決數字出版中的版權瓶頸成為現實。目前,該技術已在多家出版機構推廣使用。技術進步無止境。進入新時代,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的廣泛應用,保護程度更高、科技含量更高、技術也更為先進的數字指紋、哈希算法、非對稱加密、時間戳技術、鏈式數據結構以及節點間共識機制等高等級版權保護技術會不斷出現。版權保護將依托科技進步為產業發展營造健康有序的環境。
數字出版的編輯工作
突出政治引領
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的回信中指出:“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地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述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習近平總書記的回信高屋建瓶、內涵豐富、思想深邃,為數字出版的編輯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數字出版編輯工作必須始終堅持新聞出版的政治屬性,堅持新聞出版為意識形態服務的政治觀,堅持服務大局、統一思想、凝聚力量、增強文化自信的政治導向,把弘揚中國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編輯工作的必修課。加強編輯工作的政治引領,要做到以下三點:一是要把好選題的政治關。必須守住“黨管出版”這條底線,對有悖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階級性和政治性模糊不清的選題,堅決不予出版;二是把好內容的政治關。堅持“三審制”,對于內容存在政治導向、思想傾向、低級趣味等問題,嚴防死守,絕不放過;三是把好出版物的質量關。把傳統出版中對于質量把控的諸多措施和手段,嫁接、移植、復制、融合到數字出版中,為廣大消費者提供內容高尚、品味高雅、制作精良的數字出版產品。
加強能力建設
加強能力建設也是數字出版編輯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數字出版的不斷成熟,對于編輯的業務水平和技能要求層次更高。在數字環境下,編輯自身能力的高低,直接決定了數字出版產品質量的高低,加強編輯能力建設,也是推動數字出版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加強能力建設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轉變思想觀念。隨著信息技術和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加速融合。編輯工作作為一種專業性很強的精神生產活動,也要順應時代發展而作出改變。對于數字出版的挑戰,很多習慣于傳統出版工作模式的編輯大都選擇了漠視和“躺平”。對數字出版接受度不高,觀念老化,已經跟不上數字時代的節奏,更遑論主動提高自身能力了。只有徹底轉變思想觀念,把數字出版的發展作為自身職業進步的契機,才能激發編輯綜合能力的提高,才能在變革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實現職業和事業相互成就。二是學習賦能。當下很多出版機構的數字編輯均為傳統出版轉型而來,雖然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對數字編輯的需求,但較高的技術門檻使得其業務能力普遍不高。這些“半路出家”的編輯對數字語境下的加工手段和加工方式一知半解。所以主動參加學習和培訓,是補齊技術短板的有效方式之一,也是壯大專業人才隊伍的不二路徑。三是從單一技能向復合型人才轉變。掌握計算機應用技術,能熟練使用計算機及相應的操作系統也只是數字編輯的基本技能。從能力建設的角度來說,僅僅具備單一技能是遠遠不夠的。按照“編輯工作是整個出版工作的中心環節”這一總要求,數字編輯工作的質量和水平也與傳統出版一樣,必須全流程體現。因此,加強既懂數字和信息技術又懂傳統出版流程的復合型編輯人才隊伍建設,是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的重要努力方向。
提高版權保護意識
版權保護是近些年數字出版產業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深度掌握和運用著作權法也是編輯工作的重要方面。一是取得合法授權作為數字出版編輯工作的前置程序。最新修訂的著作權法中關于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定義為“即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使公眾可以在其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利”。可以說,取得信息網絡傳播權是數字出版編輯工作的前提,沒有授權,再優秀的選題都不能染指;二是樹立版權保護意識和維權意識。時刻保持“版權在我心中”的責任意識,把保護版權貫穿在數字出版編輯工作的各個環節,用法律武器保護作者、出版者的合法權益。
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這對數字出版產業來說無疑是國家層面的政策紅利,意義重大。因此,以國家數字化戰略為引領,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支撐,從而做強做優我國的數字出版是新時代所有出版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同時必須加強內容生產的編輯工作,提高編輯工作的質量和水平,著力推出“導向正確、內容優質、創新突出、雙效俱佳的數字出版產品和服務”,努力打造新時代數字出版產業發展新高地,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