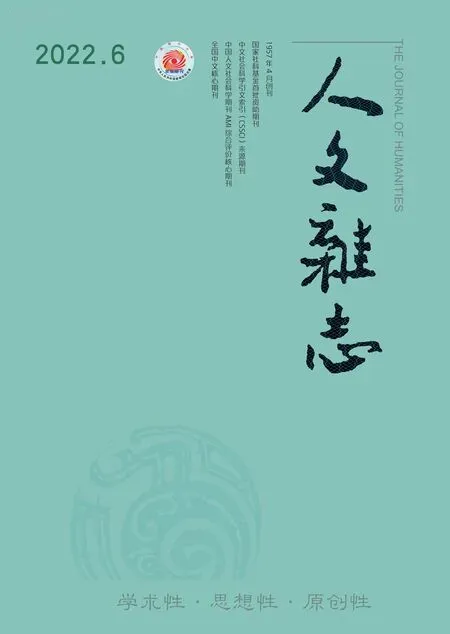文化的過渡與文學的新生
賀仲明 蔡楊淇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22)06-0059-08
1942年,茅盾和妻子孔德從香港、惠陽、老隆等地輾轉近兩個月來到桂林。此時的茅盾已經在抗戰事業上勞累多時,路途的艱辛給身體本來就不好的他造成不小的負擔,逃難的恐懼也一直籠罩在心頭,桂林給予茅盾一個身心得到暫時休憩的機會。正是在桂林期間,茅盾創作了長篇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第一部(以下簡稱《霜葉》)。《霜葉》是一部未竟之作。按照茅盾的寫作計劃,這是一部規模宏大的作品,某種程度上茅盾將其視作總結性的創作。①正因為如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文革”時期,《霜葉》也成為他唯一續寫的長篇小說。在茅盾的創作歷史中,《霜葉》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一部具有經典價值的作品。
作品問世之后,評論界和學術界展開過豐富而深入的討論。20世紀40年代的文學界更多是從階級斗爭和社會政治角度出發,關注《霜葉》的“新舊之間的斗爭”和作品的時代意義,卻未能深入探討作品新舊文化過渡的復雜內涵。②近年來,學界對《霜葉》有很多新的認識,尤其是充分肯定作品的民族形式和古典文學韻味、個體生命意識和女性意識、士紳文化和現代性等內涵。③一些學者還關注到《霜葉》在茅盾創作中的地位問題,指出《霜葉》在茅盾長篇小說譜系中的思想和藝術創新意義。① 更有學者指出“40年代初的中國文壇透過《霜葉紅似二月花》,似乎看到了一個藝術的茅盾的重生”。② 確實,《霜葉》在不同方面展現出一種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特征,從而深刻地折射出茅盾內心世界與藝術自我、傳統文化的復雜關聯。
茅盾大多數小說創作都非常注重反映社會現實,很多作品在刻畫中國近現代歷史變革和新舊文化沖突方面有突出的表現。像《子夜》前三章描寫吳老太爺從鄉下到上海,非常形象地以他的猝死寓意新舊文化之間的巨大沖突。相比《子夜》,《霜葉》對中國近現代新舊文化矛盾的刻畫,不在于以吳老太爺猝死這樣的事件做象征,而是將新舊文化的矛盾放置于一個江南小鎮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活動中,在從容的敘事結構中展現這些矛盾背后新舊文化的過渡性。
《霜葉》的新舊文化過渡,首先體現在個人從舊式封建家庭走向現代社會,即個人嘗試擺脫舊式家庭對其思想、行為上的束縛,走向更開闊的社會道路。《霜葉》花了不少力氣塑造了張府、黃府、王府、趙府和朱府等各自的家庭生活和人物關系,暴露幾輩人在生活習慣、思想觀念和社會意識上的沖突。不過,《霜葉》并非單純的家族小說,而是表現年輕一代想走出家庭、加入時代發展的新潮流。像張恂如在家時常感到百無聊賴、格格不入,連家族生意也不怎么關心,卻熟諳“外場”交際和熱心鎮上公益。他對房間里的家具擺放位置甚至都能發一番牢騷:“并不好看,也不舒服,可是你要是打算換一個式樣布置一下,那他們就要異口同聲來反對你了。”③這反映出他對舊式家庭專制獨斷的不滿和反叛,促使他在受挫中也想“早晚我得放它大大的一炮”。②錢良材更是大半時間不著家,熱衷于替鄉人朋友操辦各種事務。王伯申的兒子王民治不愿意接受包辦婚姻而想出國留學,也是為了掙脫封建家庭對自己人生大事的干涉。
這些故事內容所反映的文化過渡現象,既是時代文化的產物,也是時代變遷的真實折射。像茅盾這類出身于舊式家庭卻選擇積極擁抱現代社會發展潮流,從事社會革命的知識分子,對這些經歷自然有很深的感受。與茅盾同樣有著大家庭生活經驗的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也有相似的書寫,覺新、覺民和覺慧對家庭生活和人生道路的不同選擇,折射出青年從封建家庭走向社會的不同態度。所以,雖然《霜葉》開頭故事背景落腳于大家庭生活,但很快轉向鄉鎮社會,接續寫到地主、民族資產階級、新老鄉紳、公司職員和農民等。作品如果繼續深入,必然是家族/社會、知識分子成長/考驗兩類主題的結合。這一點,從茅盾個人創作來看,是對《蝕》三部曲和《虹》的拓展和深化;從文學史的角度看,《霜葉》是路翎《財主底兒女們》的先聲,可以被當作這一主題較早的開拓者。
《霜葉》對新舊文化的思索包含了社會階級的轉型,并在其中塑造有志青年知識分子,思考現代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局限性以及受傳統文化羈絆等現代文化問題。作品塑造的錢良材形象,可以看作是新興地主階級,也是革命知識分子的雛形。錢良材成長于傳統地主家庭,在喪偶之后熱心投身于社會,有志做一個有威望的鄉紳。盡管在《霜葉》中錢良材尚未投入革命工作,但他對社會的關注和熱心展現出典型的社會性人格。在農田遭到輪船損壞時,他為農民奔走協調、出謀劃策,領導他們修土堰,還想為混亂中被打死的孩子“小老虎”討公道。和一般地主不同的是,他并不把土地看成建構自身社會關系和社會地位最重要的東西,在抵擋“小火輪”而修建土堰的過程中不惜犧牲自家的桑田,甚至提出不需要全村農民的賠償。
茅盾對題名《霜葉紅似二月花》的解讀,體現出他對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問題的自覺思考:“我計劃寫‘五四’運動前到大革命失敗后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思想的大變動。書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于剝削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認不清方向。當革命的浪濤襲來時,他們投身風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們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了個人復仇,或消極沉淪。這也是我之所以把書名取作《霜葉紅似二月花》的原因,書中的主人公大多是霜葉,不是紅花。”①茅盾計劃在《霜葉》中表現錢良材等青年知識分子面對革命的困惑和軟弱、消極和沉淪,以暗示革命的艱難和復雜。不過在第一部中來不及深入表現這些內容,只是在后五章涉及錢良材嘗試調解農民階級與王伯申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最終失敗,而更復雜的階級斗爭和更深刻的社會革命主題還沒有充分展開。
《霜葉》對新舊文化過渡的表現還有現代文明對傳統農業文明的沖擊。茅盾在創作時顯然意識到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轉換的必然性。張家掌管著土地也經營著洋貨生意,少奶奶們經常使用洋貨并以此為時髦,出身地主階級的青年男女也能夠上洋學堂和出國,甚至“發霉的背時的紳縉”朱行健也在研究現代科學……整個鄉鎮從物質到精神上已經被現代文明所滲透。但茅盾對現代文明并非沒有批判性思考,例如對“小火輪”所代表的工業文明還是保持著一種天然的敵意。作品描寫輪船駛過河道時是“威嚴地占著河中心的航線”,它激起的水浪如“兩股雪鏈”“豁刺刺地直向兩岸沖擊,象兩條活龍”,錢良材因此擔憂“這黑色的野獸”會對兩岸的農田“怎樣作惡”。② 果然,趁著“秋潦”水漲船高,“小火輪”激起的水浪沖垮了岸邊的田地。“小火輪”的出現催生了王伯申這樣的鄉鎮民族資產階級,改變了當地傳統交通方式,也引發了小曹莊人和輪船公司的對峙。茅盾在回望20世紀初現代文明對傳統農業文明的沖擊時,一方面如實地表現這兩種文明的沖突和融合,另一方面也站在本土立場上去思考現代文明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霜葉》的新舊文化過渡還體現在對傳統婚戀觀的反思。茅盾特別注重刻畫青年知識分子在家庭中的壓抑狀態,以及思想上對新文化觀念,包括婚戀問題的接受和思考。作品寫了不少舊式婚姻和愛情的悲劇故事,例如張恂如和少奶奶寶珠沒有愛情的不幸婚姻,張婉卿與黃和光無法生育的苦悶,還有王民治難以反抗的包辦婚姻等。在舊式婚戀觀的拘束下,青年們并非麻木接受,而是在自身和周遭的婚戀悲劇中對愛情有了現代感悟。張恂如曾談到過愛情的“奇妙”:“今天你覺得不過如此,可東可西,然而將來你要后悔;這好比一種奇怪的丹藥,先時你原也不覺得肚子里有它,可是一到再吞下別的丹藥去,它那力量可就要發作了。”③錢良材對于“怎樣的一個女人”才“稱心滿意”的問題,不再秉持傳統觀念所認為的美貌、賢惠或聰明能干,而是認為沒有辦法判斷這些標準要達到何種程度,如果“遇到一個更好的”,這個問題就更無法回答。他們對愛情的理解更關注愛情的本質,而非傳統社會標準化的婚戀觀。這種理解超越了“五四”時期部分婚戀小說為了批判而批判的幼稚態度,而嘗試從現代愛情的角度反思自身的婚戀問題。
曹書文曾指出,《霜葉》的審美意蘊在于“對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歷史悲劇的真實再現,對封建家庭日趨衰落的命運的客觀描寫,對知識分子的彷徨苦悶心理的準確把握”。④ 這些審美意蘊的深刻性,得益于茅盾能忠實地表現新舊文化過渡中社會、文化和個人之間復雜的關系,尤其是能認識到這種過渡之間的承接性,沒有片面地割裂傳統文化社會與新興文化之間的聯系。他筆下的社會和個人始終徘徊于新舊文化的邊界,在不同文化的矛盾之中陷入困頓的處境。所以,盡管通過青年個體的婚戀、家庭難題和社會關系難以窺探那個時代變化的全貌,但茅盾能以時代浪潮更迭時期個體與家庭、社會的沖突和矛盾,反映出最典型的社會問題和文化特征,記錄下那些躁動不安的歷史時刻和難以準確表露的時代情緒,使得《霜葉》對新舊文化的表現具有多重審美意蘊的品格。
在藝術表現上,相比茅盾的代表作《蝕》三部曲和《子夜》,特別是同時期創作的《腐蝕》,《霜葉》顯然都有較大改變。李長之很早就評價過:“總之,這表現五四前夕的《霜葉紅似二月花》第一部,較之作者過去的《虹》,自然生動而不那樣沉悶了,較之《蝕》也更為深入,但卻遠不及《子夜》的堅實。”①雖然在社會價值上《霜葉》不如《子夜》“堅實”,但它也彌補了《子夜》不少藝術上的缺陷,并體現了茅盾自我的回歸,一方面是向小說藝術的回歸,另一方面是向自身成長經歷和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回歸。這些回歸看似是作家在創作上可以輕易達到的領域和境界,但對于從20世紀30年代就扛起左翼文學一面大旗、擅長“社會剖析”創作方法的茅盾,實屬非常重要的轉折和新生。
王曉明曾指出,茅盾在最初創作《幻滅》《動搖》時“雖然是在寫小說了,內心深處卻還沒有完成向小說家的轉變”。② 茅盾最初是帶著“政治家”“評論家”和“小說家”的多重身份步入創作的,他也一直在努力追求文學創作中藝術價值與社會、政治價值之間的平衡。但茅盾的這種努力仍產出不少失敗之作,例如小說集《野薔薇》和中篇小說《三人行》,都因為社會政治理念的介入太深,導致創作上的藝術性有所折損,甚至《子夜》這樣在藝術上用心經營的作品也存在這個問題。直到《霜葉》,茅盾才在個人經歷與傳統文化價值的回歸中避免了以往創作的一些弊病。
《霜葉》與茅盾早期左翼文學創作的重要區別就在于概念化、模式化痕跡的減弱。它不再以階級關系為構建故事的主要敘事邏輯,不再將階級性作為塑造人物、推動情節的主要依據,而將人物作為文學審美的個體進行塑造,真正回歸人與文學的純粹藝術關系,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子夜》在家庭生活和倫理關系表現上的不足。《霜葉》前半部分的感性色彩明顯超過理性色彩,尤其是在幾個家庭場景中都表現出濃郁的情感,塑造了不少生動的人物形象。即使第二章寫“外場”上張恂如、梁子安和朱行建等人在茶館的談話場景節奏也不拖沓,既有鎮里事宜的交流,也有各自性情的展現。相比茅盾早期的左翼文學作品,《霜葉》的審美風格更為含蓄婉轉,語言風格和敘事節奏都比較舒緩,并善于將人物心理與自然描寫充分地結合在一起,較好地改正了左翼文學概念化的毛病。
《霜葉》很好地融匯了中國古典小說和西方現代小說創作的特點,在文學本土化方面表現突出。在小說結構層面,如陳詠芹所認為的“在《子夜》的基礎上,《霜》似乎更多地吸收了《紅樓夢》的精髓,充分體現了中國古典小說‘可分可合、疏密相間、似斷實連’的結構特色,在結構藝術的民族化方面作出了新的貢獻”。③ 一方面,區別于《腐蝕》的日記體單線敘事,《霜葉》借鑒、融合了傳統章回體和西方現代長篇小說的敘事結構,采用與《子夜》類似的多章節結構,安排家庭“內場”和社會“外場”兩條主線索,每一章以其中一條線索大體按照時間順序進行敘述,但各章之間又互有勾連,逐步建構起整個社會的面貌和文化特征。相比于《子夜》中各類人物頻繁地輾轉于家庭、公債市場和信托公司,《霜葉》中人物和場景的流動沒有那么急促,即使作為主要人物之一的錢良材,也是在第九章才正式登場。
面對“五四”以來,新文學小說創作模式從中國古典小說的注重情節轉變為西方現代小說注重心理的傾向,《霜葉》比較好地兼顧到兩者之間的關系。從第十章到第十四章描寫小曹莊與輪船公司斗爭的線索時,《霜葉》采取了《子夜》式的寫法來突出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兩兩之間的斗爭,借鑒中國古典小說對復雜情節的結構和人物安排的經驗;同時學習西方現代長篇小說對中心人物的重視,以錢良材為中心,圍繞他的行動、思想和事跡,對幾組階級關系進行鋪敘,表現階級斗爭的線索和主題。但《霜葉》比《子夜》更進一步的是對錢良材心理的生動刻畫,超越了《子夜》的中心人物吳蓀甫。這得益于茅盾充分結合西方小說對人物心理刻畫的特點,在后五章著力表現錢良材的家庭生活及其對自身的靈魂拷問,從不同方面塑造這一新興地主階級形象。在第十二章中錢良材于深夜反思自己行為時,其心理描寫超越了一般古典小說對人物心理的刻畫程度,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俄羅斯文學心理分析式的描寫,有力地表現出這個周旋于“外場”而忽視家庭生活的青年豐富細膩的情感和充滿矛盾的思想。
《霜葉》最突出的藝術成就在于回歸中國傳統審美,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茅盾“企圖通過這本書的寫作,親自實踐一下如何在小說中體現‘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①的創作愿望。所以作品里最成功的人物,是那些具有中國古典韻味的傳統女性形象,在一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紅樓夢》的影響,特別是張婉卿。她與《紅樓夢》的王熙鳳有不少相似之處,她們都是舊式家庭婦女,非常能干且善于應酬,只不過張婉卿多了幾分善解人意的溫婉。在茅盾傳統與現代眼光的塑造下,張婉卿從形象、言語到人品等方面都有一種渾然天成的古典美,從穿著打扮、舉手投足到操持家務,每一樣都是那么得體和自然。面對離不開鴉片的丈夫,張婉卿沒有嫌棄或者鄙視,而是以一種母性光輝包容和鼓勵他戒煙,且親自操持家務,管理得井井有條,但其人格并未因依附傳統家庭而失去自身獨立意識。
《霜葉》在本土化方面的藝術成就,也得益于茅盾向自身成長經歷和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回歸。茅盾在《霜葉》中回溯“五四”前后的歷史、反思中國現代革命時,不忘調動自身的成長經歷進行敘述。他成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浙江烏鎮,而《霜葉》所著眼的江南鄉鎮和烏鎮就有非常多的相似性,包括水路發達、商業氣息濃厚、新舊文化雜糅。茅盾對近現代封建大家族生活也有深刻的感受,因為從小生活在傳統大家庭,對其中復雜的人際關系能夠感同身受,這為《霜葉》的家族敘事提供了很多素材和創作經驗。他曾回憶母親在外祖父家有靜心讀書的條件,連帶說到“不比在沈家,上面有一大輩的婆婆、嬸嬸,下面有一大堆的小叔、小姑,房屋小,擠在一處,亂哄哄地不得安寧,何論讀書”。② 有了在傳統大家庭生活的經歷,茅盾在《霜葉》里書寫的每個家庭場景都非常生動細膩,鮮少雕琢生疏之感,尤其是張婉卿主導的場景有不少地方流露出傳統家庭關系的溫情,與吳蓀甫和林佩瑤那種冷冰冰的現代都市家庭形成鮮明對比。此外,張婉卿人物形象的成功,也緣于她的性格、能力和母性光輝都帶有幾分茅盾母親的影子。茅盾兒子和兒媳稱:“祖母逝世兩年后,父親在桂林以長篇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的創作,來寄托對祖母的哀思。書中的女主人公張婉卿便是祖母形象的活生生的再現。”③可見茅盾在張婉卿身上投注了獨特的情感,這里面既有茅盾對1940年逝世的母親的一種懷念,也有他對這類女性比較深刻的理解。即使茅盾在《霜葉》中對傳統舊式家庭帶有批判審視的眼光,但他對于出身舊家庭的張婉卿更多的是欣賞。這種欣賞有別于茅盾早期小說中對現代女性的曖昧態度,而是反映他內心深處對傳統女性的尊敬,以及對現代女性獨立精神的肯定。
對于茅盾這樣經歷新舊交替文化的一代人來說,家族、特別是傳統文化的轉型,以及青年知識分子的新生,是他最深切的感受和最關心的問題。他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有太多青年在掙扎和出走,所以《霜葉》一寫到家庭生活和青年人物,總是帶有對舊式家庭和社會的反叛,同時夾雜著一種難以改變現狀的無力感。張恂如、黃和光和錢良材這類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識分子,事實上也或多或少透射著茅盾這種成長和思想經歷。茅盾對他們行動思想的揣摩,自然比通過觀察和采訪積累印象的民族資本家或農民更仔細。在他們幾個人身上,既包含著茅盾中年時期對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包括自身成長時代的審視和批判,也包含著對他們的包容和同情。張恂如的百無聊賴、黃和光的自甘墮落和錢良材行事的莽撞,在茅盾筆下都成為人物可以被理解的缺點。這也是茅盾對于自身成長和時代關系的一種深切體會。這種體會在茅盾創作《蝕》三部曲和《虹》時早有顯露,到了20世紀30年代茅盾的左翼文學創作已較少進行深刻反映。只有《霜葉》重拾這段歷史,才較為完整地完成了茅盾個人經歷與傳統文化價值觀的一次回歸。
《霜葉》在茅盾的創作道路上有著特別的意義,無論從藝術還是從情感上,它都表現出茅盾回歸自我的愿望,作為文學理論家、作家,他一直熱愛文學并積極投身于文學創作。他曾在1932年末回顧自己的創作,“所能自信的”一是“未嘗敢‘粗制濫造’”,二是“未嘗敢忘記了文學的社會的意義”,因此他總會“仔細地咀嚼我這失敗的經驗”而“生氣虎虎地再來動手做一篇新的”,他也做到了自己所說的“年復一年,創作不倦”。① 因此,盡管茅盾的創作始終很重視文學的社會意義,但他深知在創作藝術上應該精益求精。所以茅盾創作《霜葉》既是回歸藝術初心的體現,也是他不斷反思“失敗的經驗”的成果。
《霜葉》是否兼顧了藝術審美與文學社會意義的關系,實現了藝術自我的回歸呢?如果說在20世紀30年代初創作《子夜》時,茅盾是以一種復雜的心態接受時代感召,主動以文學承擔起社會剖析的責任,②那么創作于40年代初的《霜葉》則展現出作家試圖擺脫時代和自身創作慣性,以創造另一番藝術天地的努力。不過,茅盾不只是一個普通的作家個體,更是需要承擔更多責任和義務的革命文人。在茅盾“為人生”和馬克思主義創作觀的影響下,《霜葉》在茅盾回歸藝術自我方面也充滿了艱難和沖突。
在《霜葉》文本的藝術表現方面與其經典化過程中,茅盾回歸自我的愿望與時代要求存在一些錯位。某種程度上,茅盾在創作《霜葉》時有意不去迎合當時抗戰的主流文化和革命需求,而是通過描寫近20年的家族和鄉鎮生活變化去表現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此,茅盾當然很清楚這種題材與抗戰形勢之間的差距,于是他在創作中也試圖尋找一種自我與社會、個體與集體之間的平衡。這就形成了作品內容的變化——從家庭、個人、知識分子關懷角度走出來,轉向對社會革命、階級斗爭和知識分子的批判。但由于茅盾在《霜葉》中未能很好地處理這種變化,導致《霜葉》在處理個人與社會、舊文化向新文化的過渡過程中存在一些藝術上的問題。
最明顯的失衡即《霜葉》前九章與后五章故事線索的突然中斷和切換,使得作品的人物、結構和藝術感覺等并不協調。從第十章開始,茅盾以農民和輪船公司的對峙另起一條新線索,從前九章的家庭和鄉鎮生活轉向階級斗爭的內容,通過錢良材的出場和“外場”活動,把敘述視角從幾個大家庭轉向社會階級的斗爭。線索的突然切換反映作家急于把青年的時代苦悶從個人道路轉向更開闊的社會生活,雖然前面有適當鋪墊——王伯申和趙守義為了爭奪善堂積存而暗暗較勁,但后面他們的矛盾,成為錢良材領導農民對抗輪船公司的一個背景。
錢良材與困于舊式家庭的青年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本來就是可以自由游走在社會與家庭之間的人物,茅盾可以通過他展開社會活動和革命的線索。但從個人形象的塑造來看,他在社會中的表現不及在家庭關系中自然。例如在農民和輪船公司之間周旋時,他與農民的對話令人覺得他不太像是一位出身于地主階級、經常和農民打交道的人,遠不如第八章、第十二章和第十四章他在家庭場景中生動。哪怕被曹志誠和輪船公司聯合糊弄之后,錢良材的那份沮喪和生氣也有些奇怪,他對張恂如感慨:“鄉下人雖然愚笨,然而恩怨是能夠分明的,不像曹志誠他們,恩怨就是金錢。”“鄉下人容易上當,只因為曹志誠這班人太巧了又太毒辣!”連茅盾自己都覺得這種感慨過于生硬且難以評價,所以寫下“恂如瞠目看了良材一眼。良材這時的思想的線索,恂如顯然是無從捉摸的”。①
事實上,錢良材的出現并不能很好地接續《霜葉》前九章已經鋪墊好的內容,反而打亂了茅盾最早鋪設好的人物關系。張恂如、少奶奶和靜英之間的感情糾葛,黃和光與張婉卿對鴉片的復雜態度,以及王民治、靜英的求學之路等都不了了之。他們對舊家庭和舊社會的反叛只能全部寄托在一個錢良材身上,原來不同青年的處境、思想和命運的發展都變窄了。茅盾也努力想通過小曹莊和錢家莊的農民與地主群體斗爭的重要主題來彌補這種窄化,但原本豐富立體的個體形象和命運,很難在這種群體活動中得到對等的補償,原有依托舊式家庭和傳統文化所塑造出來的民族化風格,也在緊張的現實斗爭中被暫時打斷。
受到《霜葉》線索、人物和主題失衡的影響,批評界在很長時間內對《霜葉》中心人物和主題的理解、闡釋出現爭議,基本可以分為兩種觀點。一是以錢良材、王伯申和趙守義為中心人物,他們所代表的新舊勢力斗爭和階級斗爭是小說的主題。如丁爾綱指出“茅盾提煉的中心情節”是王、趙“斗法”和后半部分的農民社會悲劇,表現的主題依然是農民階級和地主資產階級的斗爭。② 這種觀點從《霜葉》問世后到20世紀80年代基本占據主導地位。二是以張婉卿、張恂如和錢良材等青年人為中心人物,他們的思想蛻變和命運發展是小說的主題。例如90年代后期吳福輝指出《霜葉》真正的主題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演化和中國女性的蛻變,兩者可以作為小說的雙主題,也可以合而為一共同作為主題。③ 這兩種看法到目前為止也無法分清誰主誰次,所以《霜葉》的中心人物和主題闡釋只能被選擇性地呈現,無法像《子夜》那樣主要圍繞吳蓀甫及其階級斗爭展開。茅盾本人對此也出現過選擇性闡釋的情況。他在1943年1月22日的《時事新報》副刊《青光》發表了《〈秋潦〉解題》一文來“說明以前的故事的梗概”,意在讓讀者“對這半部故事有點頭緒”,但茅盾對“以前的故事的梗概”只突出了王、趙的斗爭線索,省略了前九章的其他內容,不僅完全忽略了張、黃、錢等家庭的線索,張恂如、張婉卿與黃光等主要人物也絲毫沒有提到。④ 這種解題違背了茅盾最初以青年知識分子從“霜葉”到“紅花”的歷史境遇來反映時代的意愿。現有的《霜葉》無論是中心人物的失重,還是主題闡釋的失衡,都無法很好地承接茅盾原來的立意邏輯和思想深度。
茅盾創作《霜葉》的“回歸”心理,也在多年以后影響了他晚年續寫《霜葉》的選擇。茅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忙于各種政治事務,個人在創作上的計劃和野心也一再耽擱,他能夠在20世紀70年代的特殊環境下續寫《霜葉》,并不只是為了規避敏感的政治問題。按照韋韜和陳小曼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茅盾想通過續寫“找回了原來的自己———作家茅盾”的身份,進而在晚年“圓一個夢,一個多年的夢,他的創作夢”。⑤ 這從側面反映出,茅盾當年在流亡桂林時創作這部作品實現了“作家茅盾”的藝術追求,投注了“作家茅盾”真正的藝術見解和創作心力。
但在茅盾70年代續寫《霜葉》的文本上,能夠看出這種藝術回歸的艱難和沖突。即使續稿只有未完成的一些大綱片段和章節,但作家想要回歸藝術和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傾向很明顯,不僅采用文言文書寫續稿的大綱片段,而且寫得最完整最流暢的依然是張家、錢家他們的家庭生活場景。在第一部最有古典韻味的張婉卿在續稿中也明確成了中心人物,從“內場”走向了“外場”,多次施計救出身邊人,儼然一位熟諳社會規則和江湖的“女中豪杰”。另外,茅盾在續稿中安排青年從家庭走向革命的過程,一改第一部對青年人婚戀的悲劇書寫,而安排了“大團圓”的婚戀結局。第一部中無法生育的黃和光通過戒煙與就醫改善了夫妻感情,王民治在新婚之夜意外地與包辦妻子馮秋芳情投意合。青年們在第一部中的那些精神苦悶基本迎刃而解,個人命運和時代發展的沖突淡化了不少,看不出他們之前在新舊時代轉化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和困惑,在此過程中個體生命內涵的展示也沒有那么豐富和深刻。雖然不能只依據一部由大綱和片段組成的續稿就直接判定作家最終成稿藝術水平的高低,但茅盾最初想要呈現的從“霜葉”到“紅花”轉變過程中青年個人命運與內心世界的變化,在續稿中未能體現出來。盡管《霜葉》續稿在傳統文化和文學形式的回歸上做了不少努力,但是作品藝術水平上的回歸只能存疑。
茅盾創作《霜葉》的心態和作品命運可以與老舍晚年創作的《正紅旗下》類比,它們都體現出作家文學意識和自我意識的強烈自覺。在20世紀60年代初創作多部不成功的戲劇作品之后,老舍強烈希望回歸小說,回到他熟悉的舊北平生活,特別是記憶最深刻的童年生活。這是《正紅旗下》的創作初衷,也是老舍如此珍愛這部作品的原因。所以在1962年他把創作時間都給了這部小說,希望能夠找到創作《駱駝祥子》《四世同堂》時那種熟悉的藝術感覺。同樣,茅盾借《霜葉》重溫成長經歷中的家庭生活,直到晚年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下也愿意續寫這部作品,可以看出《霜葉》對于他有著非常獨特而親近的意義。兩部作品最后都成為未竟之作,一方面緣于作家創作環境的限制:老舍寫《正紅旗下》時,受到“一串又一串禁令接踵而來”“文藝政策上的不正常現象”的影響,最后“只好不寫,束之高閣”;①《霜葉》創作的中止,也受到茅盾抗戰時期顛沛流離的生活狀態和各種“急就章”創作任務的干擾。② 另一方面,作品的未完成也緣于作家個人藝術的回歸與時代創作要求的沖突,老舍想在《正紅旗下》表露旗人身份的文化內涵和經歷,茅盾則想借《霜葉》重拾自身豐富的藝術經驗。在特殊的創作環境下,作家們更現實的選擇是以創作回應社會和生活,而不是以創作回應內心與藝術。雖然前者也能創作出具有時代特色、緊密聯系時代的好作品,然而只有作家自己和讀者知道,這些作品是否達到或超過他們原有的藝術水平。不過從這些已有的“精美的殘簡”來看,茅盾和老舍能夠在種種沖突下努力尋找出路,進行艱難的小說創作,本身就已經證明他們自身文學意義的完成———雖然就文學史和讀者來說,可能更多是失望、無奈和遺憾。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中文系、廣州南方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責任編輯:魏策策 張翼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