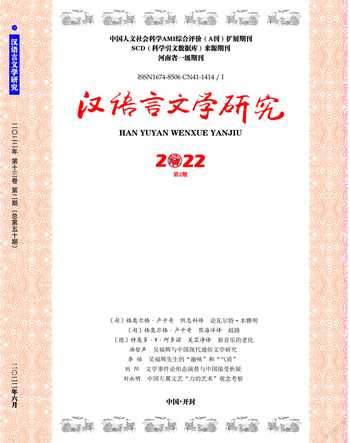文學(xué)事件論形態(tài)演替與中國接受析疑
摘? 要:正成為學(xué)術(shù)熱詞的“文學(xué)事件”,究竟是確實提出了此前未有的新問題,還是僅用新標(biāo)簽重復(fù)著已有研究論題,這取決于對其學(xué)理演替的深入考辨。在此過程中可以發(fā)現(xiàn),作為出處的、以阿特里奇為代表的英美文學(xué)事件論,是語言陌生化與讀者反應(yīng)批評理論的結(jié)合性翻版。結(jié)合阿特里奇的后理論文集編者身份與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主張分析,這一形態(tài)的出現(xiàn)與英美學(xué)界對理論的反思同步,它由此包含對理論的語言論盲點的批判,客觀上引出了超越語言論之后的兩種文學(xué)事件形態(tài),即文學(xué)事件在法國當(dāng)代理論中的差異形態(tài),以及淵源于本雅明等德國思想的晚近戲劇研究中的歷史形態(tài)。在推崇“不隔”的現(xiàn)代中國,接受“文學(xué)事件”時須構(gòu)造一個突破可能性范式的中介,才能化其完整形態(tài)入中國母體,這在抒情傳統(tǒng)與說書傳統(tǒng)強盛的我國語境中頗具難點。文學(xué)事件論的中國接受,因而提供了西方文論中國化的防范性標(biāo)本。
關(guān)鍵詞:文學(xué)事件;形態(tài)演替;中國接受
以伊格爾頓《文學(xué)事件》中譯本的出版為直接動力,“文學(xué)事件”之說開始在我國文學(xué)研究界流傳,時常可見這個詞在相關(guān)論文中的出場。但在這樣說著時,人們究竟要表達(dá)什么意圖,也每每引發(fā)我們類似于美國學(xué)者法蘭克福的懷疑,即說著這個新詞的人們往往似乎不意在“把事情說對”,而且“根本不打算嘗試去正確地說”而已。①這或許是迄今始終尚未出現(xiàn)《文學(xué)事件論》這樣的專題著作的原因?這本書能否建立在合法的論證基礎(chǔ)上而被寫出來?知識在這個新詞中果真得到了增殖嗎?還是它其實并沒有提出實質(zhì)性的新問題,而僅僅新瓶裝舊酒般對已有研究成果貼上個新標(biāo)簽、換了個新說法?
對此的回答,需要來深入考辨文學(xué)事件論在學(xué)理上的形態(tài)演替。這一考辨過程將表明,文學(xué)事件論不止于伊格爾頓等英美學(xué)者揭示出的形態(tài),它更為復(fù)雜的演替脈絡(luò),使我國學(xué)界對它的接受呈現(xiàn)出無法一蹴而就的耐人尋味之處。
一、英美形態(tài):陌生化與讀者反應(yīng)批評理論的結(jié)合
盡管“文學(xué)事件”看起來是個固定詞組,實際上在集中探討它的英美學(xué)界,它更多地是以“作為事件的文學(xué)”一語出現(xiàn)的,這方面的闡發(fā)主要源于伊格爾頓出版于2012年的著作:The event of literature。在這部迅速引起國際關(guān)注的近著中,伊格爾頓對自己1983年提出的問題——“什么是文學(xué)”,重新進(jìn)行了解答,聲明自己站在英美文學(xué)哲學(xué)派的立場上去探討這個問題。他選擇英美文學(xué)哲學(xué)路線,堅信文學(xué)邊界雖不斷變化,仍具有一些決定性的屬性,并通過分析實在論與唯名論之爭,來探討事物是否具有普遍本質(zhì),試圖證明“這并不能得出下列結(jié)論:文學(xué)沒有本質(zhì),故而這個范疇不具有絲毫合法性”②。因此,這部著作站在唯名論立場上,區(qū)別于費什等人的論證,借用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用一種非概括定義的方法闡釋了“發(fā)生或正在發(fā)生”的文學(xué)。全書主要涉及文學(xué)如何發(fā)生并起作用,沿此逐一研究了構(gòu)成文學(xué)性質(zhì)的五種屬性——虛構(gòu)性、道德性、語言性、非實用性與規(guī)范性。這至多從強調(diào)“發(fā)生”的角度,寬泛而廣義地肯定了文學(xué)是一種事件,尚談不上對文學(xué)事件論作出了正面強勢的論證。
在形成上述看法的同時,伊格爾頓研究了相應(yīng)的閱讀策略。依他之見,有兩種對待文本的態(tài)度,一種將其當(dāng)作客體對象,一種則將文本視為事件。前者以形式主義與布拉格學(xué)派為代表,后者則與結(jié)構(gòu)主義、部分符號學(xué)(如艾柯等人)的關(guān)系更為密切。將作品當(dāng)作事件,意味著讀者面對的并不是一個穩(wěn)定結(jié)構(gòu),而是一個結(jié)構(gòu)化過程,該過程通過讀者與文本互動來完成。伊格爾頓表示,這一觀點直接受到比自己這本書早八年出版、即正面研究了“文學(xué)事件”的英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理論家德里克·阿特里奇成果的影響。由此,伊格爾頓在《文學(xué)事件》第五章的注釋27中特意指出,對“將文學(xué)視為事件”這點,需要參見阿特里奇出版于2004年的《文學(xué)的獨異性》一書。這意味著,阿特里奇而非伊格爾頓,才是“文學(xué)事件”一詞的首度命名者。
阿特里奇以《文學(xué)的獨異性》一書榮獲歐洲英語研究協(xié)會圖書獎,2005年入選了英國科學(xué)院院士,主要研究英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后殖民文學(xué)批評等,尤其在文學(xué)語言等問題上用力甚深,迄今仍不斷有學(xué)術(shù)成果問世,是當(dāng)下英美學(xué)界具有國際影響的重要學(xué)者之一。他率先將事件思想與語言自覺聯(lián)系起來考察,探討了“作為事件的語言”:“整個文本提供無限的創(chuàng)新機會,需要顯著偏離一般慣例才能產(chǎn)生出強大的影響。……當(dāng)然,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可能性是無限的,因為每一條規(guī)則、每一個規(guī)范、每一個習(xí)慣、每一個涉及語言使用的期望都可以被拉伸、扭曲、引用、挫敗或夸大,并可以彼此進(jìn)行多種多樣的組合。它可以表現(xiàn)為對理解的一種顯著挑戰(zhàn),或是對熟悉事物的一點兒經(jīng)驗都沒有的、不熟悉的體驗。”①他緊接著指出,對規(guī)范的偏離還尚不足以導(dǎo)出他試圖解答的“作為事件的文學(xué)”問題:“只有當(dāng)這個偏離性事件被讀者(在第一種情況下,作者在文字出現(xiàn)時閱讀或表達(dá))‘作為一個事件’經(jīng)歷,作為一個打開了意義與感覺(被理解為動詞)的新的可能性的事件,或者更準(zhǔn)確地說,作為‘這種打開的’事件,我們才能談?wù)撐膶W(xué)。……這就是一部文學(xué)作品的‘本質(zhì)’。”②嚴(yán)格地說,這提供了“文學(xué)事件”一詞的出處語境。阿特里奇進(jìn)一步展開“獨異性的事件”論題,并在出版于2010年的《閱讀與責(zé)任:解構(gòu)的痕跡》與2015年的《文學(xué)作品》等著作中結(jié)合閱讀問題深化“文學(xué)作品只有在閱讀的情況下才產(chǎn)生”這一立場,③認(rèn)為讀者閱讀的有效性在于進(jìn)入文學(xué)事件,閱讀是行為(act)與事件(event)的結(jié)合體,由此引發(fā)的閱讀姿態(tài)主要是“解構(gòu)閱讀”④,這種閱讀展開了文學(xué)事件,文學(xué)作品包含著潛在而非現(xiàn)實的獨異性,被以適當(dāng)?shù)姆绞介喿x時才能釋放出經(jīng)驗。伊格爾頓從中受到的思想影響,于此清晰可尋。
這究竟是不是一種此前確未有過的新思想?細(xì)繹阿特里奇的理路,會發(fā)現(xiàn)他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種新的名義下重復(fù)已有的研究成果。首先,既然他所說的作為事件的語言,是指偏離規(guī)范與慣性后、在現(xiàn)有結(jié)構(gòu)組織上進(jìn)行加工改造的語言,這點看不出與什克洛夫斯基在二十世紀(jì)初即已提出的“陌生化”(一譯“奇異化”)理論有何原則性區(qū)別,從“拉伸、扭曲”等表述中,同樣不難見出兩者的接近。在此意義上,阿特里奇的說法只是重復(fù)了一下形式主義的語言觀,用“文學(xué)事件”重新命名了一下語言陌生化的過程。其次,雖然阿特里奇認(rèn)為,文學(xué)事件來自寫作行為(自然也即語言行為),離不開(甚至主要是針對)閱讀行為,擴展后者的同情心,深化其對細(xì)節(jié)的感知,祛除其意識形態(tài)遮蔽,但這顯然也是20世紀(jì)中后期以來的讀者反應(yīng)理論的基本要義,后者對讀者參與文學(xué)意義建構(gòu)的論說豐富而詳盡,被阿特里奇吸納進(jìn)了自身理路,當(dāng)然也以語言為閱讀的焦點。因此,可以初步得出一個結(jié)論:伊格爾頓與阿特里奇推出的文學(xué)事件論,是語言陌生化與讀者反應(yīng)批評理論的一種結(jié)合性翻版,代表了文學(xué)事件的形式形態(tài)。
這透露出文學(xué)事件論在英美學(xué)界的基本特色:重視語言與形式。但與此同時,我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事實,那就是,提出文學(xué)事件上述形式形態(tài)的伊格爾頓與阿特里奇,同時也都關(guān)心“后理論”。這一點似乎尚未被中外學(xué)界充分察覺與揭示。伊格爾頓固然在2003年,以《理論之后》一書拉開了晚近后理論研究的序幕,阿特里奇也于2011年與簡·艾略特合編出版了后理論文集《“理論”之后的理論》,匯集與展示新世紀(jì)前十年西方學(xué)界有關(guān)“理論之后”的思考,呼吁清除文化理論對神諭式人物、即當(dāng)紅理論家的作品的迷戀傾向,引起國際學(xué)界的廣泛關(guān)注,提供了后理論研究繞不過去的基本文獻(xiàn)。這僅僅是巧合嗎?還是于巧合中蘊含著某種必然呢?
筆者認(rèn)為,它蘊含著一種以可能性面目出現(xiàn)的必然邏輯:以語言為核心的英美文學(xué)事件形式形態(tài),內(nèi)含著對“語言作為形式”的突破可能和傾向,而不代表文學(xué)事件的全貌。因為,后理論承“理論之后”命題而來,是對20世紀(jì)以來源于歐陸哲學(xué)的理論運動的清算和超越,對準(zhǔn)的是理論的核心或基石——索緒爾語言論。正是語言作為任意性符號系統(tǒng)的性質(zhì)在20世紀(jì)索緒爾等語言學(xué)家手中的發(fā)現(xiàn),使知識對象不再自明,而有了被符號權(quán)力建構(gòu)、并沿此形成表層/深層結(jié)構(gòu)的二分問題,對這種二分結(jié)構(gòu)進(jìn)行揭示,成為理論的性質(zhì)。既然在經(jīng)歷了半個多世紀(jì)的輝煌之后,理論如伊格爾頓判斷的那樣,正逐漸呈露出衰退之跡;相應(yīng)地,那從根本上便離不開對構(gòu)成理論自身的語言論實質(zhì)的檢討。換言之,后理論必然內(nèi)含著調(diào)整語言的邏輯,理論之后,某種程度上就是語言之后,或更準(zhǔn)確地說:索緒爾語言論主流之后。阿特里奇在上述文集引言中,援引并肯定了后理論者勞倫特·迪布勒伊(Laurent Dubreuil)有關(guān)“將‘理論’的工作細(xì)化為對于語言必然失效的更為全面的分析”的主張,①便表明了這一立場。在此意義上,文學(xué)事件論譜系就不止于英美形式的一脈,而還需考慮超越語言論主流學(xué)理的其它形態(tài)可能,事實上它們在歐陸同樣客觀出現(xiàn)了。
二、法國形態(tài):反語言分叉與溢出的文學(xué)事件
處于形式形態(tài)中的文學(xué)事件,所遵循的語言論路線以符號區(qū)分形成的差異為基本性質(zhì)。但這種符號內(nèi)部相互吸引的區(qū)分活動所逐漸形成的差異,在當(dāng)代法國理論中的若干重要思想家看來,恰恰陷入了另一種形而上學(xué)因果實體,而消弭了真正的差異。因為當(dāng)索緒爾從根源上聲稱一個符號總要等下一個符號出來與之形成區(qū)分關(guān)系時才獲得意義時,這看似暫時充滿了未卜前景的風(fēng)險性處境,實際上從不改變另一個巋然存在著的客觀事實,即它總是能被下一個符號所區(qū)分,而獲得某種生命,這種存活的可能性是永久穩(wěn)定的。這是結(jié)構(gòu)主義之外的法國理論所不認(rèn)同的,后者認(rèn)為這種在同質(zhì)化前提下形成的差異,并非真正的、建立在異質(zhì)性上的差異。對此,利奧塔在較早時已提出反對意見,認(rèn)為索緒爾未發(fā)掘出“差別的根本意義”,卻把差別給有意無意地在觀念中凝固了起來,積極破壞這一語言學(xué)安排的暴力則是“事件”,事件應(yīng)“在認(rèn)識的無序中被發(fā)現(xiàn)”并伴隨“某種規(guī)則失常”②,差別的根本意義是產(chǎn)生事件,而使“一個人要注意差異:事件”③。利奧塔未及聯(lián)系文學(xué)來深入論證上述觀點,但他為法國理論從異質(zhì)性角度伸張差異、并沿此形成新的文學(xué)事件論,提供了出發(fā)點。在他之后不久,德勒茲與巴迪歐便分別從內(nèi)在性與超越性這兩大互補的角度,④論證了文學(xué)事件的差異形態(tài)。
德勒茲的事件哲學(xué)具有多重面相,就對文學(xué)的直接影響而言,其獨特的“逃逸”觀念,使人從字面上即已感到逃逸于同質(zhì)性差異之外的意義新生長點。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他對以索緒爾為代表的主流語言論的抵制態(tài)度。他雖然也認(rèn)為“事件本質(zhì)上屬于語言”;卻對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觀表現(xiàn)出微妙的態(tài)度,試圖“在語言表面上‘鉆孔’,以找出‘背后隱藏著什么’”①,這意味著語言無法再現(xiàn)事件,需要做的是“將結(jié)構(gòu)內(nèi)的歷史銘寫為一系列與結(jié)構(gòu)獨異性相關(guān)的事件”②,德勒茲由此主張“最小的實體單位不是詞語、觀念、概念或能指,而是裝置”,前者引出結(jié)構(gòu)。如果說“結(jié)構(gòu)關(guān)涉的是一種同質(zhì)化環(huán)境,而裝置則并不如此”③。通俗地說,德勒茲在此所言的“逃逸”,即在差異中不斷持續(xù)生發(fā)出進(jìn)一步的差異,讓某事件之果與另一個事件之因在一個序列中復(fù)雜并存,以消解總體性的各種頑固變體,實現(xiàn)分歧中的綜合。美國學(xué)者米歇爾·塞爾用“分叉”(branch)概括事件,著眼于事件對“大格式化程序”,即“以理性法則名義抹去偶然事件”的現(xiàn)狀的超越:“事件返回的格式,就像洪水過濾涓涓細(xì)流而流過堤防一樣”④,“分叉”便正是“逃逸”的形象描述。
在這一前提下,德勒茲如何立足于差異性視野談?wù)撌录c語言的關(guān)系呢?他對伊壁鳩魯學(xué)派與斯多噶學(xué)派作了一個區(qū)分,認(rèn)為前者的哲學(xué)側(cè)重對名詞與形容詞的使用與依賴,后者的哲學(xué)卻強調(diào)動詞性,注重“動詞與動詞的變位,以及非物質(zhì)事件之間的聯(lián)系。要知道語言中的名詞或動詞是主要的,因為動詞不代表動作,它表達(dá)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事件”⑤。緊緊抓住他在事件與意義邏輯的關(guān)系上所論述的核心——因果的異質(zhì)性及其在無限細(xì)分中形成的分歧性綜合效應(yīng),便容易對其抱以理解。該問題可以結(jié)合文學(xué)作品來稍加舉例。
例如,在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中,男主人公是個在車站錯過了換車機會的乘客,他進(jìn)書店買了本卡爾維諾剛出版的最新小說《寒冬夜行人》就津津有味讀起來,發(fā)現(xiàn)買到的這本小說只有開頭,于是他拿到原先那家書店調(diào)換,碰到女主人公也為同樣問題而來,兩人就這樣開始尋找《寒冬夜行人》的原書,一路找下去,只找到十部風(fēng)馬牛不相及的小說的十個不同開頭,故事走向尾聲,男女主角在這個過程中相愛并最終作出了結(jié)婚決定。把十個故事開頭嵌套插入,并沒有影響“男女主人公共同找書”這個總故事的自動運行,小說每章開頭都緊緊承接上一個套盒中的故事余音,各章和十個套盒是銜接自如的。相比之下,略薩的《胡利婭姨媽與作家》也分二十章,略薩與姨媽的故事主線貫穿單數(shù)章節(jié),雙數(shù)章節(jié)則一章一個短篇小說,嵌套起九個互不相干、各自獨立的社會故事,且都無明確結(jié)局,出現(xiàn)在這些彼此無關(guān)的短篇故事里的人物,僅在前后不同故事里偶爾被提及,卻不構(gòu)成主線。相比前者在差異中仍看護(hù)著的某種總體性走向,后者運用結(jié)構(gòu)現(xiàn)實主義寫法在差異中進(jìn)一步打破差異,才適合作為德勒茲上述事件論的闡釋對象。而對福柯文本的文學(xué)性揭示,則更集中代表了德勒茲這種以逃逸與分叉為特征的文學(xué)事件論:“他的句法閃出可見的反光和亮光,也像皮條一樣彎曲、對折和再對折。”⑥在“對折”中“再對折”,即在差異中再差異,與前文阿特里奇僅滿足于“扭曲”一次(或許在實際操作中也存在多次,但觀念上并未形成對“多次”的自覺意識)、從而逗留于穩(wěn)靠語言結(jié)構(gòu)實體中的形式性文學(xué)事件論,呈現(xiàn)出了異趣。
但德勒茲的這種文學(xué)事件論受制于內(nèi)在性立場,其對內(nèi)在平面性的相應(yīng)強調(diào)進(jìn)一步引起了巴迪歐的不滿。巴迪歐發(fā)現(xiàn),德勒茲以逃逸與分叉為本色的“褶子”概念“極具抗擴展性,似迷宮般直接且定性,以至于他根本無法解釋事件或破裂的獨異之處”①,仍忽視了“事件是連續(xù)性中的一種無法理解的斷裂,是與存在的一種分離,是一種無根無據(jù)的雜多,從中新事物之創(chuàng)造得以涌現(xiàn)”②。他因而選擇從更徹底的超越性角度闡釋文學(xué)事件,指出“真相總會碰到極限,由此證明此真相為獨異性的真相,它完全不會被整體所自我意識到”③,即避免一種存在于事件發(fā)生前的主體性,而將主體性維系于事件中的“空虛”對于真理的回應(yīng),事件的發(fā)生不依賴于先在的主體性意圖,而是在自身“空虛”(void)的過程中即時生成,這個過程成為真理的一部分,頗接近我國先秦道家所說的“虛其心”。換言之,事件在巴迪歐那里,外在于主體而類似于神跡,主體只能在稍縱即逝的事件發(fā)生后,才忠實于它并將它實現(xiàn)出來。這一核心看法影響了他對文學(xué)藝術(shù)的事件性闡釋。
藝術(shù)品以清晰的、結(jié)構(gòu)化的語言組織為表述目標(biāo),這是傳統(tǒng)藝術(shù)的一種慣見。巴迪歐不贊成這樣一種思路,認(rèn)為這種清晰性以消解事件、簡化(從而歪曲)真理內(nèi)部諸程序的復(fù)雜并存關(guān)系和“溢出”意向為代價,無法以某種現(xiàn)成的框架來直接表述藝術(shù)作品的意義,結(jié)構(gòu)組織的“溢出”——扭曲乃至晦澀,是作為事件的藝術(shù)的常態(tài)。在此意義上,語言注定將遭遇闡釋限度,這種限度成為事件的決定性要素。讓·雅克·勒塞克勒論證了巴迪歐上述事件思想對奇幻(fantastic)文學(xué)的獨特闡釋優(yōu)勢,以奇幻演繹真理程序作為事件的“溢出”,展示了事件與文學(xué)的關(guān)聯(lián)。
在他的考察中,德勒茲的事件論適合闡釋戰(zhàn)爭文學(xué),而巴迪歐的事件論則適合闡釋奇幻文學(xué),奇幻性文本“關(guān)注的是根本上全新的事件,而不是伴隨每一次事故的事件的虛幻本質(zhì)”④,它致力于各種不同的異質(zhì)性程序之間的隨時出乎意料、打破常規(guī)的共存。他繼續(xù)指出,“在巴迪歐所描述的情況下,當(dāng)一個事件發(fā)生時,由于它是不可辨別的、轉(zhuǎn)瞬即逝的、不可測量的,它只能在未來的前方被抓住,它就會發(fā)生,它將通過一個詢問的過程被回顧性地抓住。但是,敘述的特權(quán)在于將那些無法被立即感知的東西展示出來,并將其作為奇跡、頓悟來表現(xiàn)。”⑤他以奇幻小說《科學(xué)怪人》(Frankenstein)為例,通過分析其情節(jié),指出故事中事件發(fā)生的領(lǐng)域是科學(xué)領(lǐng)域,但能從情節(jié)中推斷出法國大革命這一政治事件的痕跡,同時在造物的過程中使人發(fā)現(xiàn)愛的勞動,這一切又都發(fā)生于帶有哥特式風(fēng)格的文學(xué)作品——小說中,這一來“對一個事件的出現(xiàn)、它留下的痕跡、它所引發(fā)的真理過程以及隨后的主觀性過程作一種情感敘述,這種過程會在勝利者的身上產(chǎn)生一個反應(yīng)性的主體”⑥,其文學(xué)后果尤其應(yīng)得到估計。
倘若承認(rèn)奇幻在廣義上是文學(xué)的根性,那么,能被如此運用于文學(xué)闡釋的巴迪歐事件論,即為一種文學(xué)事件論。從德勒茲的反語言分叉到巴迪歐更趨激進(jìn)的反語言溢出,當(dāng)代法國理論分明發(fā)展出了一種與索緒爾語言論主流相決裂的、差異形態(tài)的文學(xué)事件論,也醒目展示了與英美文學(xué)事件形態(tài)所不同的歐陸文學(xué)事件形態(tài)。這一新形態(tài)的特征,是用充滿差異的“隔”,超越了阿特里奇等英美學(xué)者在語言論思路中對“不隔”的持守信念,似乎還是第一次在思想史上讓人們看到了“隔”的同樣可取的一面。在此用“隔”描述差異,是受到布迪厄“區(qū)隔”(distinction)論的啟發(fā):“語言是不與事物存在必然符合關(guān)系的符號系統(tǒng)(替代品),始終替代(即重新說出而非傳達(dá))著事物,而去替代事物,即在符號的區(qū)分中創(chuàng)造(建構(gòu))新‘物’;符號的區(qū)分帶出著位置的差別(不等),說出著現(xiàn)實中的等級,此即符號權(quán)力(文化政治);替代的實質(zhì),因而是使作為深層結(jié)構(gòu)的符號權(quán)力不知不覺地實現(xiàn)為自明表象。布迪厄的符號權(quán)力理論,由此何嘗不可以看作是索緒爾語言論學(xué)理的自然發(fā)展?就此而言,當(dāng)布迪厄強調(diào),康德意義上的無利害的純粹審美鑒賞判斷背后,一樣存在著被說(建構(gòu))成這樣的符號權(quán)力背景時,他無疑承認(rèn)和吸收了索緒爾語言論的延伸性成果——作為表征(替代)的建構(gòu)主義。”①如果區(qū)隔植根于符號的區(qū)分,而符號的區(qū)分形成的正是差異原則,差異總是意味著“隔”,便屬于學(xué)理應(yīng)有之義。
我們的追問是:到這步就夠了嗎?差異似乎總在偶然性上發(fā)力,那么,歐陸文學(xué)事件論就不講“不隔”?還有沒有沿著差異更進(jìn)一步重建偶然中之必然的路徑呢?
三、德國形態(tài):震驚體驗中的文學(xué)事件
縱然法國理論被普遍視為事件思想的重鎮(zhèn),但其對偶然性的張揚,也使深沉的歷史感非其所長,及時補充注入后者而形成悲苦意識,是事件學(xué)譜系中需要接著差異講的下一環(huán),它尤其應(yīng)成為文學(xué)事件的動力,因為文學(xué)作為對存在的領(lǐng)悟,在廣義上處理的即是悲苦意識所植根于其中的深沉歷史。這一點在尼采對亞里士多德悲劇凈化說的批判中已露端倪。按尼采的觀點,悲劇及其渲染的苦難與困境,在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邏輯中無法成為事件。因為亞氏反復(fù)申述心理凈化的重要性,認(rèn)為一味沉溺于悲劇引發(fā)的憐憫與恐懼情緒中無助于領(lǐng)會其審美價值,這種明顯基于理性劃分意識的界限意識,隔開觀眾與事件,導(dǎo)致事件最終成為欣賞者從安全視點出發(fā)予以把握的認(rèn)識性對象:通過轉(zhuǎn)移與釋放悲劇性心理情緒而安全地觀賞悲劇,無異于理性地與悲劇展現(xiàn)的世界形成主客對立,即在理性中將悲劇對象化并去認(rèn)識它,哪怕主觀上是否自覺意識到。尼采由此指認(rèn)凈化說是一種“毫無美感的人”作出的、基于“病理學(xué)的宣泄”的“老生常談”,因為“憐憫和恐懼在每一個別場合因悲劇而得緩和與渲泄,但在總體上卻因悲劇的影響而強化”,由此他“一再指出亞里士多德的誤解”,認(rèn)定“假如他是對的,悲劇就是一種危及生命的藝術(shù)了:人們必須警惕它猶如警惕某種通常有害的和聲名狼藉的東西”②。比如可以研究,面對奧斯維辛這一浩劫,凈化之說果真切中了腠理嗎?沿著尼采開創(chuàng)的這一德國問題語境,阿多諾表示作為凈化實質(zhì)的“升華也包含意識形態(tài)成分,如此一來就會剝奪藝術(shù)的尊嚴(yán),所用方式就是滿足于真正滿意的代用品”,從而“凈化學(xué)說已在原則上開創(chuàng)了對藝術(shù)的操縱性支配”,以至于“亞里士多德的凈化觀念是一個過時的神話,在理解藝術(shù)產(chǎn)生的影響方面是那么無能為力”③。凈化說的實質(zhì),是認(rèn)為藝術(shù)與生活并無界限,實乃一體,不存在一個因所觀看的悲劇只處于藝術(shù)世界中、而減輕悲劇感的生活世界疏泄出口,悲劇就是讓人悲不自勝、難以釋懷的,這才是悲劇的真相。而懂得殘酷,也真正進(jìn)入了歷史。本雅明在同樣的意義上體察到,悲劇對生存困境的發(fā)現(xiàn)與開掘,又是一種基于震驚的現(xiàn)代生存體驗,它直接導(dǎo)致悲劇不止于文本對象的意義,而與人自身所處于其中的歷史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人由此進(jìn)入歷史的建構(gòu)過程。
基于上述觀念,觀看悲劇中上演的事件,是一個與現(xiàn)實生活發(fā)生間離的過程,此事件非彼事件。但當(dāng)代美學(xué)研究者們在本雅明等思想家的成果基礎(chǔ)上,試圖破除這種常識性理解,把對作為事件的悲劇的理解引向更深處,主張建構(gòu)“戲劇動態(tài)下的歷史的主體經(jīng)驗”④,使人們在對悲劇的觀看中,理解自己正處于其中的當(dāng)代歷史。如朗西埃借助政治與美學(xué)工具進(jìn)行的去主體化與再主體化研究,以及沿此對“美學(xué)政治”的工具與體制的重新配置,為思考戲劇事件對歷史的主體經(jīng)驗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參照。阿甘本也反對主體不去面對歷史性,即不去感知與把握主體自己的時間,認(rèn)為這將導(dǎo)致現(xiàn)存的歷史主體假定自己作為創(chuàng)造性的與政治的代理人的存在,相反主張在文學(xué)作品、比如曼德爾斯塔姆的詩歌作品中窺見與“自己的時間”——即當(dāng)代時間相關(guān)的美學(xué)模式,這種模式,在接近與距離、親密與分離之間維持一種視覺上的相互作用,從而在批判與創(chuàng)造的結(jié)合中有效地實現(xiàn)當(dāng)下的歷史化。從法國學(xué)者到意大利學(xué)者的這些思考成果,可以上溯至德國學(xué)術(shù)語境中作為震驚的獨異體驗。以法國與意大利為代表的當(dāng)代左翼理論的根子,實是德國理論。強調(diào)這一點的意義在于,一般談事件及其差異性,容易僅流于法國視界,這樣做不僅縮小了事件思想的譜系,更重要的是忽視了事件在差異中的建構(gòu)維度,這是事件在歷史深度上的必要保證。
也正是植根于這一點,2011年,蒙特利爾魁北克大學(xué)戲劇系教授約瑟特·費拉與畢業(yè)于多倫多大學(xué)并從事戲劇研究的萊斯利·威克斯發(fā)表了《從事件到極端現(xiàn)實:震驚的美學(xué)》一文,探究了幻覺與無中介事件之間的沖突。兩位學(xué)者認(rèn)為,這些場景將藝術(shù)、尤其是戲劇藝術(shù)帶出了戲劇框架,通過引出暴力的表演性行為以及與這種暴力面對面時所體驗到的極端臨場感,來創(chuàng)造出“一個真實的事件”①。他們借用保羅·阿登納(Paul ArdenneJs)出版于2006年的《極端:突破界限的美學(xué)》一書中的措辭,稱這種事件創(chuàng)造為“震驚美學(xué)”(aesthetic of shock),其核心內(nèi)容是:戲劇喚起的激烈的暴力,擁有超出戲劇本身的額外存在,沖破虛構(gòu)性而導(dǎo)致觀眾移出通常的舒適范圍,以其充滿震驚的敏感力量擊中了觀眾,消除審美距離而只留下事件,使事件現(xiàn)實化了;觀眾由此赤裸裸地面對暴力,面對凝視所進(jìn)入的吸引力,讓自身的動作獲得了與事件齊頭并進(jìn)的通透性,也使舞臺突然失去了幻覺性,改變其最初與觀眾的契約;這樣,在舞臺上創(chuàng)建事件,能克服戲劇幻覺而引發(fā)一種即時的存在,消除故事的介導(dǎo)與演員的對話。這開始將事件的獨異與震驚向人類歷史命運的深度空間拓展。視事件的瞬間為藝術(shù)品,在兩位學(xué)者看來是面對成千上萬的死亡保持沉默,是停留在強烈暴力的外面而變相羞辱受害者。唯有在事件超出戲劇表現(xiàn)形態(tài)意義的震驚層次上,被激怒并喚醒自己的感官,才能脫離幻想、虛構(gòu)與一度期望的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的舒適感,而在遭遇戲劇事件中重新排列感官與知覺的框架。
終極的悲劇感,就來自這份與歷史同呼吸共進(jìn)退的深沉感與惶惑。歷史作為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永恒聯(lián)結(jié),始終落實于當(dāng)下在場體驗,它既包含著唯恐虧欠過去的不安,也包含著面向未來籌劃的不確定感,因而總從廣義上滲透著悲劇因素。從悲劇中切身觀看到自己同樣置身于其中的歷史,人才會震驚,而震驚才是悲劇感的本真流露。從這一激發(fā)獨異性的事件角度理解悲劇,將之和主體在歷史進(jìn)程中的自我建構(gòu)結(jié)合起來,成為文學(xué)事件在德國語境中的代表形態(tài)。
四、中國接受的轉(zhuǎn)化樞紐:“不隔”論重估
從行文邏輯上順勢推出文學(xué)事件的中國形態(tài),會迸發(fā)圓滿的快感,卻也可能是輕率的。這種猶豫或許首先來自某種積淀于內(nèi)心的情感結(jié)構(gòu):一種以農(nóng)耕文明為特征的文化,合理的選項似乎是要“穩(wěn)定”而不要“事件”,如此則對“文學(xué)事件”的津津樂道從何談起?倘若不經(jīng)過必要的揚棄和轉(zhuǎn)換,文學(xué)事件論在中國語境中便可能成為缺乏實指的奢談。那么接受的中介在哪里呢?
英美的形式文學(xué)事件論建立于索緒爾語言論主流學(xué)理基礎(chǔ)上,這首先意味著文學(xué)事件論在西方有明確的動力,即對形而上學(xué)的批判與超越。這一問題意識卻不存乎中國文化語境。除外來的因明學(xué)以外,我國自古并無西方那種形而上學(xué)傳統(tǒng),不具備去掙脫形而上學(xué)的問題意識與原動力,不存在“形而上學(xué)是壞的”的堅定想法。這一背景下的文論,因而具有兩種性質(zhì)。其一是流露形而上學(xué)衷曲,安于做形而上學(xué)的變相同謀而不愿掙脫它。其表現(xiàn)為趣味主義:從語言上摩挲賞玩作品,臆造一個自足的審美結(jié)構(gòu),將自己框于其中享受此岸的樂趣,帶出士大夫趣味。其二認(rèn)為形而上學(xué)是沒有的,自己根本就不是形而上學(xué),而無從掙脫它。其表現(xiàn)為感悟隨想:散文式感悟品評不絕,這種語言游戲有鑒于語言作為符號不具實質(zhì)性、人類文化卻總得通過語言表達(dá)這一事實,而容易失去對人類文化絕對性的信任,導(dǎo)致“沒有誰相信任何東西”①,由此樂于用感悟隨想取代嚴(yán)整系統(tǒng)的理論話語建構(gòu),作為現(xiàn)代性張力結(jié)構(gòu)中反抗理性的、審美層面的用心,自有權(quán)得到理解,但有別于語言論所說的語言游戲,因為后者是針對自然語言觀或者說本質(zhì)主義語言觀而言的,語言不與世界發(fā)生一對一關(guān)系,只是一套不具實質(zhì)性的表征符號,人們從而不能借真理之名販賣私貨,反對形而上學(xué)的證據(jù)即在于此,這套證明本身卻是嚴(yán)格的學(xué)理思辨,其論證來自索緒爾與維特根斯坦這些最嚴(yán)謹(jǐn)?shù)恼Z言學(xué)家與哲學(xué)家。可見,我國古典感悟批評在語言層面上的活躍表現(xiàn),并不針對形而上學(xué)這一明確的靶子,與索緒爾語言論試圖自覺地通過語言擊中并走出形而上學(xué)區(qū)別鮮明。在此前提下,讓文學(xué)事件論在中國生根發(fā)芽便不是一件天經(jīng)地義的事。
不唯如此。也如前所述,不僅英美的形式文學(xué)事件論在某種程度上包含了對語言論主流范式的突破,而且法國的差異文學(xué)事件論從正面攻破了這點。德國的歷史文學(xué)事件論,同樣視索緒爾語言論為純粹語言的墮落。這種共同趨向,實際上是破除主流語言論以安穩(wěn)與同質(zhì)化為特征的“可能性”信念,代之以“不可能性”的刺激力量。這尤其構(gòu)成了引文學(xué)事件論融入中國語境的難點。
難點表面上體現(xiàn)在,新時期我國文學(xué)研究界對詩性民族文化本位的張揚,一大動因在于海德格爾哲學(xué)被大規(guī)模介紹進(jìn)來,鑒于文學(xué)自古被看成對抗平庸俗世人生的精神綠洲,它已被傳統(tǒng)眼光牢牢預(yù)設(shè)了美好的詩情畫意,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卻日漸暴露出現(xiàn)代人利欲、空虛的一面,海德格爾“詩意的思”的橫空著落,可謂適逢其時,它很快被文學(xué)界推舉為拯救商品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那種異化人格的強大力量。但學(xué)理的深入推進(jìn)已然證明這種做法里包藏的含混。按列維納斯的揭橥,海氏所說的存在是一種“未知”(unknown)而非“不可知”(unknowable)因素,②未知綻出本真的已知,總體結(jié)構(gòu)是肯定“可能性”的:主體作為事件的主人歡迎它,他者與主體處于田園牧歌式的和諧共存關(guān)系中。它在當(dāng)代中國受到的迎合與共振,反過來說明當(dāng)代中國簡單移植事件思維所可能落入的學(xué)理遮蔽。
而由表及里地繼續(xù)聯(lián)系漢語特性來考察,我們的詩性語言傳統(tǒng)從來以“可能性”為取徑,基本不在文論與美學(xué)研究序列中考慮“不可能性”的問題,典型表征即王國維在現(xiàn)代性發(fā)軔處提出的“不隔”優(yōu)于“隔”之論。王氏作為西學(xué)東漸的先驅(qū),對古老中國文學(xué)遺產(chǎn)的談?wù)撘验_始滲入西學(xué)思維方式,表現(xiàn)為用二元對立范疇提出一系列命題組,這些命題中有些被他平行對舉而不分軒輊,如造境/寫境、大境界/小境界,有些則被他從價值上作出了高下之分,如無我之境/有我之境以及不隔/隔,“不隔”優(yōu)于“隔”,“妙處唯在不隔”是其確切結(jié)論。③“隔”源自“不可能性”,對“不隔”的推崇,意味著對“可能性”境界的信賴與向往:總能透過阻隔而達(dá)成理想的狀態(tài)。尋根究源起來,不僅是注重心理調(diào)節(jié)與內(nèi)在超越的抒情傳統(tǒng)在對此起支撐作用,而且宋元以降的說書傳統(tǒng),同樣為此提供了動力。說書是調(diào)動一切精彩的敘述手段營造扣人心弦的現(xiàn)場效果,高度注重對于故事的“講”,為此而在敘述技巧層面上每每使出渾身解數(shù)來極盡巧思、吸引觀眾與讀者,從外部切入文學(xué)活動,將興奮點聚焦于文學(xué)對人的一系列外部關(guān)系的探討,而在深入開掘文學(xué)內(nèi)在精神方面的興趣方面相對顯得淡薄,與中國文化對待生活的某種逍遙的、莊子式的態(tài)度有關(guān)。這種逍遙來自 “一個世界”特征,其實質(zhì)是,由于并無在更高的力量面前的渺小感、有限感,而不滋生出相應(yīng)的不安全感,反而認(rèn)為自己可以自如操控眼前的局面,怎么來具體地操控它,都不妨礙自身所占據(jù)著的安全位置。這與西方文化在“兩個世界”特征上形成的、出于被拯救的訴求而滋生出的不安全感,是頗異其趣的。典型例證是,西方勇于坦承自身隱私的回憶錄與自傳作品發(fā)達(dá),相比之下中國卻甚少流傳下這類作品。說書傳統(tǒng)與抒情傳統(tǒng),因而實為同一個傳統(tǒng),兩者在夸揚自身主觀趣味與敘述這一點上殊途同歸,都面臨著如何寫出世界真實(客觀)性的嚴(yán)峻挑戰(zhàn)。
歸結(jié)地看,呈現(xiàn)為靜態(tài)的上述中國式“不隔”傳統(tǒng),在自我的主體預(yù)設(shè)與算計中,消弭了他者的異質(zhì)性暴力介入,將原本在事件意義上應(yīng)引入人性中充分差異、并揚棄偶然性而與歷史建立深刻主體心靈聯(lián)系的尖銳“不可能性”,以及其間值得深入開掘的大悲歡的沖突感,沖淡為憑意念的升華即可實現(xiàn)的“可能性”。西方語境中需經(jīng)“不可能性”(即“隔”)的轉(zhuǎn)換方能實現(xiàn)倫理訴求的事件思想,被處理成為中國語境中附會自我完善形象預(yù)設(shè)的添加物,以及相應(yīng)而來的“不隔”幻象。于是,在缺乏形而上學(xué)傳統(tǒng)及語言論學(xué)理自覺的當(dāng)下中國,關(guān)于“文學(xué)事件”的談?wù)摵捅砻婊惨疲尸F(xiàn)為一種得其形而未得其神的接受姿態(tài),須構(gòu)造一個突破語言論的可能性范式的中介,才有可能化文學(xué)事件論的完整形態(tài)入中國母體。能否順利構(gòu)造這樣的中介呢?這項任重道遠(yuǎn)的課題,難點不僅在于克服抒情傳統(tǒng)與說書傳統(tǒng)長期累積下來的思維定勢,還在于建立對漢語流利性及其隨筆寄生主義傾向的某種克制意識,懂得在漢語思維中卡一卡、頓一頓、隔一隔的必要,讓差異不再迅速流向新的“可能性”穩(wěn)靠變體,而嚴(yán)肅地張開異質(zhì)性空間,允諾進(jìn)一步差異,并在這一進(jìn)程中將偶然性與建構(gòu)性結(jié)合起來,走出看似“不隔”地融入、實則仍始終旁觀著或者說“隔”著的身份區(qū)域,將對象與自身主體歷史意識在事件的獨異體驗——震驚中深度貫通起來。文學(xué)事件論的中國接受,既取決于當(dāng)代中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在思想方式上的新探索與新突破,也取決于批評與理論研究在這一觀念調(diào)整與深化完善方面的相應(yīng)跟進(jìn),舍此便無從談起。這一個案由此提供了西方文論中國化的防范性標(biāo)本。
*?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項目“理論之后的寫作機理與漢語因緣研究”(項目批準(zhǔn)號:19FZWB021)的階段性成果。
①? [美]哈里·G·法蘭克福:《論扯淡》,南方朔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6頁。
②? [英]特里·伊格爾頓:《文學(xué)事件》,陰志科譯,鄭州: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頁。
①? Derek Attridge.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Routledge, 2004, pp.56-58.
②? Ibid, pp.58-59.
③? Derek Attridge. The Work of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5.
④? Derek Attridge. Reading and Responsibility: Deconstruction’s Trace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
①? Jane Elliott & Derek Attridge. Theory After “Theory”. Routledge, 2011. p.12.
②? [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話語,圖形》,謝晶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158頁。
③? Geoffrey Bennington. Lyotard: Writing the Even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73.
④? 當(dāng)代法國理論中觸及事件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者還有布朗肖與德里達(dá),但他們主要不在內(nèi)在性與超越性的互補這一典型整體角度上用力,需另題考慮。參見拙文《“文學(xué)事件”的緣起、命名、展開與跨語境演進(jìn)》(載《學(xué)習(xí)與探索》2022年第3期)與《作為寫作事件的后理論》(載《廣州大學(xué)學(xué)報》2020年第2期)。
①? Jean-Jacques Lecercle. Deleuze and Languag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6.
②? Ibid, p.106.
③? 白輕:《文字即垃圾:危機之后的文學(xué)》,重慶: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198頁。
④? Michel Serres. Branches: A Philosophy of Time, Event and Advent. Bloomsbury Academic, 2020. p.28.
⑤?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84.
⑥? [法]吉爾·德勒茲,劉漢全譯:《哲學(xué)與權(quán)力的談判——德勒茲訪談錄》,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1年版,第109頁。
①? Marian Fraser.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2006. p.131.
②? 汪民安、郭曉彥:《生產(chǎn)》第12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頁。
③? Alain Badiou. Handbook of Inaesthe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1.
④? Jean-Jacques Lecercle. Badiou and Deleuze Read Literatur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78.
⑤? Ibid, p.168.
⑥? Ibid, p.173.
①? 參見拙文《索緒爾語言論能否解釋藝術(shù)的言外之意?——一個通向當(dāng)代事件文論的考察》(載《人文雜志》2021年第9期)。
②? [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悲劇的誕生》,周國平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6年版,第97、201、382頁。
③? [德]西奧多·阿多諾:《美學(xué)理論》,王柯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51頁。
④? Adrian Kear. Theatre and Event: Staging the European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8.
①? Josette Feral & Leslie Wickes. From Event to Extreme Reality: The Aesthetic of Shock. TDR, Vol. 55, No. 4 (Winter 2011), pp.51-63.
①? [美]雅克·巴爾贊:《藝術(shù)的用途和濫用》,嚴(yán)忠志譯,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頁。
②? Emmanuel 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75.
③? 王國維:《王國維文學(xué)論著三種》,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1年版,第38頁。
作者簡介:劉陽,教育部青年長江學(xué)者,華東師范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文藝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