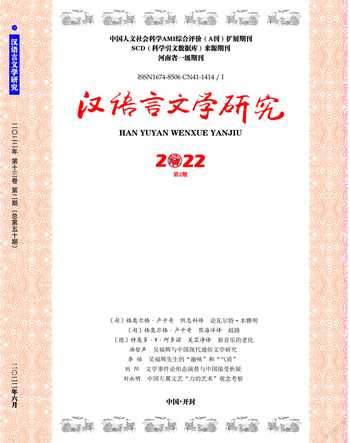主體生成的世界
張恩和先生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包括魯迅思想研究、魯迅舊詩研究、郭沫若研究、郁達夫研究等領域,其中又以魯迅研究的成績最為突出。在我看來,其治學中值得注意的特點是,關注魯迅反封建、魯迅與辛亥革命等問題,并且總結出自己的基本原則。他的學術研究在在體現著改革開放初期的學術風氣,體現出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與1980年代社會思想變化的共振性和同步性。在今天看來,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很值得重新檢討。
一
張恩和先生在研究中非常重視魯迅的反封建主義。他認為,魯迅到日本之后,認識到必須摧毀封建主義思想體系。封建社會的核心是專制,命脈是等級制度,要害是家族統治。他認為,魯迅反對帝國主義,但更看到封建主義的流毒對我們民族的發展和進步是最大的障礙,也就是強調對專制主義傳統思想的批判是最迫切的問題。張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反復強調這一觀點,甚至提出,與封建主義的斗爭,是魯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斗爭;對封建主義本質的揭露和批判,也是魯迅最重要的功績。①這構成了其魯迅研究的一個重要思想面向。
應該承認,張先生的觀點并不另類,代表著20世紀80年代魯迅研究的某種共識。然而,對于今天的青年學者而言,封建主義這個術語已經“去學術化”,基本上已經屬于失效的概念,很少有人再頻繁使用。但是,一個理論概念在學術市場上的身價漲跌,既可能與其自身的闡釋能力有關,也可能與這個學術市場的潮流、風向變化有關。這個概念本身在新時期之初是非常流行的、關鍵性的概念。今天的備受冷落,可能與其自身的理論局限有關,反過來,也可能反映了學術界的某種勢利和思維的受限。換言之,“封建主義”這個概念可能需要重新推敲和界定,但指出中國社會具有某種迥異于歐美社會的性質和文化,并且這種性質和文化仍在妨礙著中國的現代化、世界化的進程,這一判斷可能仍有其價值。
舉個例子。俞可平認為,“封建”一詞在漢語中自古有之。柳宗元《封建論》所說的“封建”特指春秋以前各國“封國土,建諸侯”的分封制度,秦朝以后這種封建就沒了,中國長期的歷史顯然不是柳宗元所說的“封建”。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封建主義源于歐洲中世紀的封地采邑制度,封建制度的實質是以領主或地主占有土地、剝削農民剩余勞動為基礎的社會制度。顯然,中國傳統社會也并不是嚴格意義上馬克思所說的封建社會。所以,用“封建主義”作為主要框架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并不合適。俞可平本人提出,能夠比較確切地反映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形態的概念是官本主義。②事實上,除了這兩個概念之外,學術界還提出了“宗法地主專制社會”“郡縣制社會”“選舉社會”“帝制農民社會”“君主專制和地主經濟形態”“皇權官僚專制社會”“帝制農商社會”等各種觀點。③這無疑說明,盡管“封建主義”這一概念/框架并不一定完全適合于分析中國傳統社會性質,但中國傳統社會的那種根深蒂固的、與歐美社會差別極大的特性是確實存在的。
因此,重新認識張恩和先生對魯迅反對封建主義問題的關注,就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面展開:首先,如上所言,封建主義概念自身的局限并不能取消或弱化我們對中國社會特殊性質的追問。在中國與世界關系面臨轉型和重新結構的今天,這一問題顯得格外緊迫。其次,“封建主義”這一概念是從19世紀歐洲橫向移植來的,是對19世紀歐洲狀況的重復,“但每一次重復同時也是置換——不僅是背景差異的產物,而且也是一種政治性的置換。這些概念重組了歷史敘述,也打破了舊敘述的統治地位,從而為新政治的展開鋪墊了道路。這并不是說這一時代的話語實踐不存在概念或范疇的誤植,而是說若無對這些概念或范疇的政治性展開過程的分析,我們根本不能理解它們的真正內涵、力量和局限,從而也就不能通過它們理解20世紀中國的獨特性”①。也就是說,封建主義這個概念本身的興衰成敗,就是魯迅研究史乃至新時期以來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課題。第三,張先生誠然是強調魯迅徹底的反封建主義的一面,但如果我們將封建主義替代為“中國傳統社會特殊性質”,那么魯迅本人顯然也是這一性質的基因攜帶者。那么,魯迅是否也具有某種“封建性”,魯迅的反封建與自身對封建性的超越是什么關系,就自然成為需要追問的問題。
二
值得思考的一個現象是,在第二代現代文學研究者身上,往往存在著內在的矛盾性,即他們在強調生命體驗和主觀投入的同時,又高度重視實證,堅持實事求是的治學原則。他們的“道”與“術”之間隱含著一種看起來矛盾緊張,但又奇特地彼此共存的關系,正是這種內在的張力催生了第二代現代文學學者富有中國學術特色的、兼具義理和考據,主體介入、現實批判和文獻辨正共存的研究風格。這一點在張恩和先生身上也有體現。
例如,張恩和先生素以對作家深入妥帖的情理辨析和理論評價見長,但他并不拒絕進行嚴肅細致的史實考證。他的《魯迅的初戀》和《魯迅為何提前離開廈門》,就是很典型、很有價值的考證文字,自成一家之言。他根據魯迅舊詩的研究狀況,借鑒古典學術傳統,采用“集解”的方式研究魯迅舊詩,并且提出這一工作其實可以當作“情報資料”來看,體現了他自覺的文獻意識:
我可以和古人的集解、集釋不同,不必將主要力量放在對詩句的研究上,逐字逐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給自己定下的任務是盡量完全地把別人的研究成果匯集起來,自然,在此基礎上,我可以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和“雙百”方針,也談點自己的看法,或者竟是提出問題。②
時至今日,他的《魯迅舊詩集解》仍是魯迅舊詩研究不可繞過的重要著作。在現代文學發生“文獻轉向”的今天,強調張先生的考證功夫,似乎是有意溢美,以塑造張先生文獻研究先驅的地位。但在我看來,張恩和這一代學人的史料考證之所以值得重視,正在于其歷史和時代賦予的特殊性,亦即“以考證為批判”。換言之,在他們的研究中,考證最初往往以方法論的面目出現,但最終卻是具有根本的價值論的意味。由于種種原因,在中國學術傳統中,考證有時并不僅僅意味著歷史事實的考訂,而是具有意識形態的顛覆力量,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實證主義常常具有批判性的意味,常常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先遣隊和助產士。這既是文化傳統的產物,也是魯迅研究傳統和現代史的產物,很值得注意和討論。張恩和先生等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二代學人,雖然多數也接受了正規的大學教育,但相對而言,20世紀中國壯闊激烈的革命歷史才是他們最重要的課堂,他們更多是從家國的動蕩和生命的顛沛中思考自我與研究對象。對他們而言,相較于思想,知識始終是第二位的。這就使他們的考證一定是服從于義理、史實,一定是服從于史識的。自然,這在今天很容易被詬病為不夠學院化、規范化,但這種“不夠學院化、規范化”自有它的優勢。至少在他這一代學者身上,多有心憂家國的情懷和與現實肉搏的勇氣,而少有饾饤腐儒的酸氣與蠅營狗茍的銅臭。隨著代際發展,學科逐漸正規化、體制化、專業化,不少青年學者受到更完整的學術訓練,更加技術主義,其考據和論證也變得精致化,計算機技術的引入更使文學研究具有了數字化的一面,但學科草創期的某些內在能量也在衰減、消散。長此以往,令人不禁憂慮,在學術研究日益強調客觀、實證、數據,日益排斥主觀、情感的今天,現代文學研究離被人工智能徹底取代還有多遠?數字人文是否最終會變得只有數字而無人文?
三
這其實涉及如何認識研究主體的問題。
張恩和先生并不諱言魯迅研究的特殊性,在世紀之交,他提出魯迅研究的三個基本原則:現實性、時代性和群眾性。我認為,他沒有明言但實際上堅持的還有一個主觀性原則,這個原則可能更具有決定性。他在《我的魯迅研究》中說:
我一向認為,研究魯迅不應簡單地將他當歷史、當作一般作家研究,而應該把他當作一種精神上的對話者或引領者,以他為精神偶像。研究魯迅不僅不同于研究自然科學,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社會科學研究。在那些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保持一定距離,保持客觀冷靜態度,研究者本身是不必要也不應該投入自己的熱情和主觀精神的。而在研究魯迅時,則應該有主觀精神的融入,用胡風的話說,簡直是應該表現出不能抑止的熱情,用全身心投入并擁抱他,并且應該表現出研究和學習相結合,即人們常的“知行合一”。對魯迅要有一種以之為范,“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情和態度。①
和當前“唯主觀而欲去之”、追求“價值中立”的學術正確完全不同的是,張恩和毫不隱諱、毫無保留地提出魯迅研究應該有主觀精神的融入,應該以“研究和學習相結合”的態度對待魯迅。這是令人驚訝的,因為這種觀點對學術研究客觀性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張恩和先生偏偏就堅持著這種看起來不能成立、初學者也不會堅持的觀點,毫不憂讒畏譏。
批評張先生是容易的,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分析他對主觀性的強調和堅持。他在文中所堅持的主觀性,其實就是主體性的表現,是主體性的另一種表述形式,也就是強調在魯迅研究中應該堅持主體性。張恩和先生把主體性表述為主觀性,又表述為以研究對象為學習對象,這種看法是否恰當可以討論,但其對研究者主體性的堅持是值得我們分析的。歷史地看,主體性這個概念其含義異常豐富,但簡單說就是“主體所潛在地具有并且能夠發揮出來的屬性”。②對我個人來說,張恩和先生對主體性的強調有以下幾點啟示:
首先,主體性思維要求以人為根本,反對將人視為工具。在研究作家時,就會將作家視為一個以人為基礎的主體,而不是空洞的、非人格化的符號。例如,在回答魯迅為何提前離開廈門這個具體的學術問題時,張恩和一方面承認原因的多元性,但另一方面又極為重視魯迅作為人的情感性,看到魯迅作為普通人的一面,進而提出魯迅的私人感情生活是他選擇提前離開廈門的主要因素:“種種原因,種種目的,都繞不開一個起主導作用(激化作用)的因素,就是希望盡快和許廣平在一起。這是魯迅作為普通人內心深處的主觀愿望和情感需要,我們不但不應回避,相反應該予以足夠的重視。”③張恩和先生自己解釋,這是為了呼應“魯迅是人不是神”、擺脫泛政治化的視角去觀察魯迅的學術思潮而作。將作家從政治幽靈的附體中解放出來,重新認識其主體的意志、情感、實踐,才能再現作家作為“人”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這是文學研究主體性思維的前提之一。
其次,主體性的特征之一就是為我性。馬克思曾說,“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④。當然,我們不能狹隘地去理解這個“我”,它既可以是個體,也是指整個人類。但在學術研究這種主客體關系中,這個“我”顯然是指研究者自身。所以,研究中的主體性思維,就要求以研究者為中心,研究不再是服務于客觀對象,不再被客觀對象所支配,而是從研究者自身需要出發,為研究者自身而服務,如此,研究者自身的存在價值才能得到確立,研究作為一種實踐活動才有其意義。對魯迅研究來說,從因果邏輯上看,當然是先有魯迅才有魯迅研究。但是從話語建構的角度看,魯迅又是魯迅研究所塑造的;從主體性角度看,魯迅研究又是為研究主體服務的,是研究主體獲得主體性的途徑,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研究并不從屬/依附于魯迅,而是平等、獨立于魯迅的。魯迅研究既是對客觀對象的探索,也是研究主體自我實現的方式。那么,無論其研究結果的性質、狀況如何,都應視為“這一個”研究主體的實踐行動的成果,都是“這一個”研究主體生成的方式,都應加以嚴肅的對待和充分的尊重。從這一意義上看,魯迅研究自身的歷史與魯迅文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最后,人的主體性不是單一的、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歷史的、實踐的,是在具體社會關系中,“社會歷史中行動的人”所具有的性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從不同的思想、觀點、方法去改造世界,表現出不同性質、不同方向的主體性,這就是不同代際研究者同中有異的原因。這也啟示我們,在魯迅研究中,盡管以張恩和先生為代表的第二代學者的學術影響多被第一代和第三代學者所遮蔽,隱而不彰,但其研究主體性仍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開掘。同時,新一代的學者也應在學術實踐的過程中堅持主體意識,在主體間的相互觀照、交互和斗爭中,追求并實現自身的主體性。也只有這樣,研究包括張恩和先生在內的魯迅學術史,才能不斷地成為一代又一代研究者主體性的重要源泉,因此不同代際、彼此影響和共在的主體,最終參與并決定了意義世界的生成。
①? 張恩和:《我的魯迅研究》,《上海魯迅研究》2019年第1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版。
②? 俞可平:《官本主義: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學分析》,法治政府網,http://fzzfyjy.cupl.edu.cn/info/1223/4300.htm
③? 詳見李振宏:《秦至清皇權專制社會說的經濟史論證》,《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
①? 汪暉:《作為思想對象的二十世紀中國(下)——空間革命、橫向時間與置換的政治》,《開放時代》2018年第6期。
②? 張恩和:《寫在前面》,《魯迅舊詩集解》,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頁。
①? 張恩和:《我的魯迅研究》,《上海魯迅研究》2019年第1期,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版。
②? 魏小萍:《“主體性”涵義辨析》,《哲學研究》1998年第2期。
③? 張恩和:《踏著魯迅的腳印——魯迅研究論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頁。
作者簡介:孟慶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新文化運動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