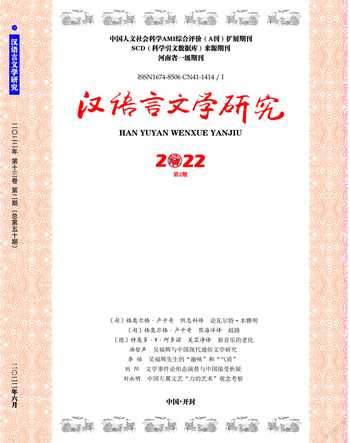中國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考察
摘? 要:左翼文藝豐富的“力”的藝術觀念,不僅是中國近現(xiàn)代尚力思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理論成果之一。學界對于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的研究一直比較零碎或者各有歸屬,并沒有統(tǒng)一共名到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體系下。建立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體系,有利于建構左翼文藝各種“力”的藝術觀念之間的整體性和普遍聯(lián)系,也有利于校正一些理論偏差,回答一些理論困惑。而以今日的理論視野,回望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體系的源起、本體論流變和體系性建構,學習其批評話語,可以促進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早期發(fā)展“中國性”問題的理解,也可以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批評的發(fā)展提供某種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力的文藝;力的文學;主觀力;人民力;藝術力;錢杏邨
20世紀是個新意識不斷(被)“發(fā)現(xiàn)”“自覺”的世紀。在中國近現(xiàn)代文藝思潮中,除了我們熟知的“審美”“個人”“階級”之外,還有其他發(fā)現(xiàn),比如“力的發(fā)現(xiàn)”。從嚴復“鼓民力”、梁啟超提倡小說“神力”(“熏浸刺提”),晚清開始出現(xiàn)尚力思潮,到左翼文藝運動各種“力”的藝術觀念,再到1943年經(jīng)典革命歌曲《團結就是力量》的誕生,從心力、個力到群力,力量意識綿延整個世紀,因此,20世紀也被稱為“力的世紀”。①而到了20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基于對“暴力”的反思,出現(xiàn)了對“力”的告別之論和對文學經(jīng)典“解毒”的思潮,②甚至出現(xiàn)了對于各種變異“力”(如“原始力”“生殖力”“錢力”等)的創(chuàng)作熱情和表現(xiàn)崇拜。③但不可否認的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歷史—社會性質的“力”的發(fā)現(xiàn)與自覺,對于20世紀我們民族和國家的覺醒與解放,產(chǎn)生過重大且偉大的作用。因此,有學者認為,從近代尚力思想中發(fā)展出來的現(xiàn)代尚力精神,已經(jīng)成為國家精神力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④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左翼文藝的各種“力”的藝術觀念無疑是發(fā)揮過重要作用的,如1930年代救亡背景下,左翼文藝界批判“閑適文學”“軟性電影”等,就借用了“力”的文學觀念。不僅如此,左翼文藝各種“力”的藝術觀念(以及在這個基礎上構建的“力的藝術”觀念體系⑤)在文藝理論系統(tǒng)內(nèi)有其理論價值和意義。因此,對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有進一步考察的必要。
一、“力”的藝術觀念的研究
相比其他藝術觀念,“力”的藝術觀念在中國藝術理論譜系中發(fā)育并不完全。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為對于“力”的本體論(作為詞根的“力”)闡釋特別薄弱,許多“力”的藝術觀念只是作為詞綴而存在的,比如氣力、骨力、筆力、人民力、他化力等,許多研究者并不區(qū)分詞根和詞綴的“力”的不同。二是和中國古代文論的特點有關。在傳統(tǒng)藝術理論史上,“力”的藝術觀念并不是一個熱點:從子不語“怪力亂神”到晚清,“力”一直不是中國傳統(tǒng)文論的一個重要范疇。這一方面和數(shù)千年來古人基本是將“力”和“德”相對立進行理解有關系,也和古人“發(fā)乎情,止乎禮義”“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溫柔敦厚”“主文而譎諫”的藝術中庸思想和“怨諷刺騷雅”美學理想有很大關系。這在主張社會性的古代文論中尚且如此,在形式主義文論或者審美主體性文論中就更為少見。三是“力”作為批評話語的批評效能相對較弱(比如相對于“真”),“力”本身很少作為一個獨立的批評話語被使用,也無法以其為中心構建一個批評話語體系,所以批評經(jīng)典之作鮮見。這與物理學對“力”的研究有著云泥之別。四是左翼文藝理論譜系中,還長期存在著對特定“力”的藝術觀念或本體論的批判和壓制,比如1940年代初期對堅持本體論“力”學觀念戰(zhàn)國策派的批判、中后期對胡風“主觀力”的批判等,一度抑制了“力”的藝術觀念的發(fā)展和研究。因此,對“力”的藝術觀念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不溫不火的一個論題。
但盡管如此,久久為功,數(shù)十年學界矚目所及,對“力”的藝術觀念的研究也是“草色遙看近卻無”一般,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些整體的氣象。綜合來看,目前,學界對于“力”的藝術觀念(這里更多地考慮到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的研究漸成規(guī)模并在客觀上呈現(xiàn)著三種類型或情況。
第一種是從古代到近現(xiàn)代,系統(tǒng)考察數(shù)千年中國“力”的藝術觀。這其中又可分為兩種亞類型:一是線性的梳理,比如胡傳吉《“力”之文學變道》(2010),李建中、李遠《放逐與重塑:論“力”與文學的關系》(2019)等;二是點狀的研究,比如孫敏強《“力”的文學——試論“建安風骨”》(1985)、李遠《從“不語力”到“論何力”:孔子“力”思想研究》(2020)等。李建中、李遠的兩篇文章主要是一種本體論的研究。
第二種是對于近現(xiàn)代中國啟蒙主義尚力思潮的研究。如對嚴復、梁啟超、魯迅、周作人等的“力”思想和藝術觀念的研究就很多;魯迅的《摩羅詩力說》(1907)、周作人的《人的文學》(1918)等一直是研究熱點。但這種類型較少涉及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如較早系統(tǒng)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尚力思潮的王本朝在《論近現(xiàn)代尚力美學思潮》(1993)等幾篇文章中就較少論及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后來他在《閑適與尚力:中國現(xiàn)代審美價值的裂變——20世紀30年代論語派與左翼文學論爭的美學意義》(2009)中作了專論。另外,一些現(xiàn)代尚力思潮的研究論及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如朱曉進《五四文學傳統(tǒng)與三十年代文學轉型》(2009)、楊姿《“尚力”精神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浪漫傳承》(2010)、張樂心《貝多芬在中國:西方古典音樂接受問題個案研究》(2013)等。當然,在后者,左翼文藝各種“力”的藝術觀往往是近現(xiàn)代尚力思潮線性研究中的一個點。
第三種是專論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也同樣存在著線性和點狀研究兩種亞類型。線性研究如王燁《20年代革命小說敘事成規(guī)的探尋與運用》(2008)、王智慧《論“革命文學”的藝術性追求》(2010)等,都是在某種邏輯下討論左翼文藝各種具體的“力”的藝術觀念;點狀研究的就非常多,如著名的斯洛伐克漢學家瑪利安·高利克在其專著《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發(fā)生史(1917—1930)》中的《錢杏邨:無產(chǎn)階級現(xiàn)實主義與“力的文藝”》專章、張清民《從“藝術力”概念看馮雪峰文學思想的精神實質——兼論胡風思想的影響》(2004)、孟麗娟碩士論文《丁玲創(chuàng)作與“力的文學”》(2005)等。其中錢杏邨、馮雪峰、胡風等的各種“力”的藝術觀更是大量研究的對象。
至于其他主題研究中涉及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的情況就更多更復雜,如溫儒敏《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1993)、黃曼君《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史》(2002)、朱曉進《政治文化與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學》(2006)等,自然少不了對于左翼文藝各種“力”的藝術觀念的討論。但整體來看,因為不是一個顯耀的存在,在一般現(xiàn)代文藝理論(批評)通史通論中,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都較少被提及。
從上可以看出,除了尚力思潮研究之外,鮮有一種體系性的概念范疇或研究路徑來統(tǒng)一安置左翼文藝各種“力”的藝術觀念。而構建一個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體系非常必要,它可以使我們在回望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的源起、本體論的流變和體系性建構過程中,能夠更為宏觀地看待左翼文藝各種“力”的藝術觀念之間的整體性和普遍聯(lián)系,也有利于校正一些理論偏差、回答一些理論困惑,比如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的本源性問題、1928—1929年期間與1940年代“力的藝術”觀念之間的聯(lián)系等。
二、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的源起
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指的是左翼文藝運動初期(1928—1930年前后),以魯迅、錢杏邨、馮乃超、郁達夫、李初梨等為代表的左翼文藝批評家所倡導的,在總結郭沫若、郁達夫和蔣光慈創(chuàng)作特色的基礎上,形成的有關“力”的藝術本體論、形式論、技巧論和批評論的一個新的藝術思潮和美學原則。其影響所及,不僅對當時的學衡派和京派評論家有影響,①對后來馮雪峰、胡風1940年代藝術理論的發(fā)展也產(chǎn)生過很大影響。
關于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的源起,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并非源自1920年代初中期就已經(jīng)形成的“力的文學”觀念。在1920年代初期,純文學觀念建立之后,在人們關于文學定義和分類的知識中,已經(jīng)普遍存在將文學區(qū)分為“力的文學”和“知(智)的文學”兩類的觀點。比如劉永濟著《文學概論》(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24年版)和日本本間久雄著、章錫琛譯《新文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等著作都持這種認識。②與影響周作人《人的文學》(1918)中的“力的文學”觀的英國18世紀詩人勃萊克(Blake)不同,一般認為,將文學區(qū)分為“力的文學”和“知的文學”始自19世紀初期英國文學家和批評家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年,舊譯“戴昆西”“德昆西”“臺昆雪”等)。如本間久雄《新文學概論》中說:“19世紀初英國著名文學者臺昆雪說道,‘先有知識的文學,其次有力的文學。前者的職能是教,后者的職能是動。’”③“知的文學”在于學識教化,“力的文學”在于感動化育。1934年,朱自清也指出:“‘純文學’、‘雜文學’是日本的名詞,大約從De Quincey的‘力的文學’與‘知的文學’而來,前者的作用在‘感’,后者的作用在‘教’。這種分法,將‘知’的作用看得太簡單(知與情往往不能相離),未必切合實際情性。”④但這里所說的“力的文學”的“動”和“感”,說的是情感活動,因此,從內(nèi)涵來看,早期“力的文學”觀念恰恰就是和左翼文藝“力的藝術”相對的“美的藝術”!但審美性質的“力的文學”如何在1920年代后期轉換成和審美性質文學相對的“力的文學”的邏輯進程,目前還不清楚。一種理解是認為二者之間沒有任何邏輯上的聯(lián)系,不存在轉換的問題,另一種理解是從審美主義的“力的文學”的審美之“感”“動”的力量之維過渡到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也未可知。對此暫且不論。
對于錢杏邨是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的首倡者和主要批評實踐者,⑤歷來研究者沒有太大的歧義,⑥但對于其思想源頭在何處,則普遍持“外源說”并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是以葛中俊為代表的認為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深受美國作家辛克萊影響的說法。辛克萊(Upton Sinclair,1878—1968)是20世紀初期美國的基督教現(xiàn)實主義作家,富有反抗精神,喜歡揭露社會黑暗。辛克萊和杰克·倫敦一樣,是深刻影響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美國作家,被認為是影響中國左翼文藝理論的美國源頭的代表。辛克萊對于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影響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創(chuàng)作(郭沫若翻譯的《屠場》與《石炭王》,易坎人翻譯的《煤油》等辛克萊作品對當時左翼作家有廣泛的影響),二是理論,三是批評(辛克萊對白璧德的批評文字被魯迅、郁達夫大量引用于與梁實秋的論爭之中)。理論方面的影響又有三個具體要點:一是強調(diào)文藝的階級性,這個成為左翼文藝理論家的主要理論武器;二是一切藝術都是宣傳的觀點,辛克萊的名言“一切的藝術是宣傳。普遍地、不可避免地它是宣傳;有時是無意識的,大底是故意的宣傳”曾經(jīng)被廣泛流傳,是造成中國左翼文藝運動早期錯誤思想的根源之一(這個觀點后來在左翼內(nèi)部陣營受到茅盾等的批判并成為引發(fā)革命文學論爭快速結束的原因之一);三是“力的藝術”觀念。葛中俊認為:“辛氏文藝觀的另一核心,在于對‘力的藝術’的提倡。在《拜金藝術》中,他套用了英國作家昆塞(Thomas Quincey)‘力的文學’這一術語,發(fā)明了‘力的藝術’并賦予其全新的涵義”,“20年代末,中國文壇對‘力的文學’的大力提倡并以此作為衡量作品的重要的審美標準,其內(nèi)在的動因,在于當時國內(nèi)革命的低潮所激發(fā)的作家內(nèi)心的激進情緒;而直接的、外在的動因,便是辛克萊關于‘力的藝術’的影響作用。”①葛中俊的這一觀點提出較早(1994),因此,影響深遠。
第二種是以杜運通為代表的主張錢杏邨“力的藝術”觀念源自俄蘇和日本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說法。杜運通認為:“太陽社的重要理論家錢杏邨,他倡導的‘無產(chǎn)階級現(xiàn)實主義’和‘力的文學’的理論依憑,一方面來自蘇聯(lián)‘拉普’派成員佐寧的《為了無產(chǎn)階級現(xiàn)實主義》一書;另一方面來自藏原惟人的《到新寫實主義之路》和《再論通往無產(chǎn)階級現(xiàn)實主義之路》等文章。”②杜運通的這一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錢杏邨《力的文藝》一書(包括同時期同主題的其他編譯評之作)就是對世界各國無產(chǎn)階級作家作品的一個評論集。同樣持這種觀點的張大明也認為“他(指藏原惟人——引注)的‘力學的寫實主義’,還被錢杏邨改造為‘力的文學’”。③
但相比之下,第一種說法似乎更有說服力,是因為支持者都會提到一個關鍵證據(jù):郁達夫在1928年2月24日日記中提及“Upton Sinclair 的主張”并說:“錢杏邨及孟超來談,與談新文學的革命性及革命文學的技巧問題。我以為革命文學之成立,在作品的力量上面,有力和沒有力,就是好的革命文學和壞的革命文學的區(qū)別。”④所以第一種說法就被固定下來并成為主流。
盡管如此,本文認為,錢杏邨的“力的藝術”觀念的源起,更多的是在對五四以來新文學和早期革命文學經(jīng)驗總結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一個本源性觀念,并不是一個外源性觀念。
首先,從文本上看,錢杏邨主要闡發(fā)“力的文學”觀念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第1卷)》完成于1928年上半年(錢杏邨“自序”中說“在材料方面大都是以一九二七為終止期”),《力的文藝》雖然成書時間是1929年上半年,但其中極力稱贊“力的文學”的文章卻是一年前的作品(如《德國文學漫評》載1928年3月《小說月報》第19卷第3號)。辛克萊是在《拜金藝術》一書中提出藝術分為“美的藝術”和“力的藝術”兩種。《拜金藝術》1925年在美國出版,1927年影響到日本,有木村生死的節(jié)譯本。1928年1月馮乃超節(jié)譯了該書主要論述藝術階級性和一切藝術都是宣傳的部分內(nèi)容,命名為《拜金藝術(藝術之經(jīng)濟學的研究)》,刊于《文化批判月刊》1928年第2號,馮乃超在前言中明確說明是節(jié)譯自英文。馮乃超的節(jié)譯部分沒有涉及“力的藝術”。與此同時,1928年年底到1929年年中,郁達夫根據(jù)日譯本的節(jié)譯又重新做了節(jié)譯(實際上也是選譯本),陸續(xù)刊發(fā)在《北新》第2卷第10期(1928年4月)至第3卷第14期(1929年8月),合計19章。根據(jù)郁達夫的每章譯后說明(大意是不能及時譯出、有譯出即發(fā)表),“力的藝術”的內(nèi)容出現(xiàn)在譯文的第16、17章。因此,根據(jù)文獻來判斷,辛克萊“力的藝術”觀念的譯出要比錢杏邨正式提出“力的文藝”觀念晚了至少一年。而考察錢杏邨1928年上半年同時期其他批評文本多處提到辛克萊的其他觀點(比如寫于1928年5月31日《藝術與經(jīng)濟》)卻沒有提到辛克萊的“力的藝術”觀;再考慮到同時期其他革命文學理論家文章情況,比如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寫于1928年1月),雖然有直接引用辛克萊一切藝術就是宣傳的觀念,但均不涉及“力的藝術”的觀念。因此,我們更傾向于認為,在提出“力的文藝”觀念時,錢杏邨沒直接受到辛克萊“力的藝術”觀念的影響。
其次,從《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第1卷)》和《力的文藝》的內(nèi)容可以明顯看出,錢杏邨是在總結五四以來新文學和早期革命文學成就的明確意圖上闡釋“力的藝術”觀的,二者的區(qū)別在于,前書是立論性質的、后書是借鑒性質的。
錢杏邨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第1卷)》《自序》第一段話中即說:“中國文壇已經(jīng)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過去十年的努力,只算建設了這新時代文藝的奠基石,在奠基時代,我們也曾有過不少的艱苦奮斗的歷史,也曾有過不少勇猛向前的斗士。艱苦奮斗的史事,當然是成了不可磨滅的往跡,可是當日的斗士,有的固然還是在邁步向前,有的卻因著抓不住時代而開始反動。這里,就想以這時代的眼把他們分別的研究一回,替過去的時代結一次總賬,于一般讀者不是無利的。”①總結過去和繼往開來的意味十足。盡管總結有許多失誤之處,但錢杏邨明確指出,“力的藝術”是未來文學的路。
書中在評價郭沫若的《詩人郭沫若》小節(jié)《女神與力的藝術》中,錢杏邨說:
是真的,從沫若開始了他的文藝生活一直到現(xiàn)在,在他的作品中確實的表現(xiàn)了一種毫無間斷的偉大的反抗的力。所以,沫若的創(chuàng)作的精神,給予青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一以貫之的反抗精神的表演。
《女神》實在有很多的好處,約略的說來,第一就是靈感的豐富。……。第二是詩里面所蘊藏的一種偉大的力,簡括的說,就是力的表現(xiàn),二十世紀的力的表現(xiàn),……。第三就是情緒的健全,……。第四是狂暴的表現(xiàn),……。
總結沫若已出版的詩歌集,……,我們可以找出里面所表現(xiàn)的是兩個方面,和三種的技巧。所謂兩個方面,是社會的與自然的;所謂三種技巧,一是力的技巧,二是沈著(按:即“沉著”)悲痛的調(diào)子,三是優(yōu)游自得的田園詩的技巧。當然,最能代表他的是第一種,表現(xiàn)了二十世紀的動的精神,舉一節(jié)最簡短的例:……(即《筆立山頭展望》,略——引注)。像這一類的詩,讀起來是很能感到震動,節(jié)奏,以及力的。②
在評價郁達夫的《“達夫代表作”后序》中,錢杏邨說:
這不過是概括的說明,便是我們自己也認為不能滿意,然而沒有方法可想。可是,在這里還要附帶的說明幾句,現(xiàn)在的文藝,已經(jīng)走到力的文藝的一條路了,我們的技巧也應該是力的技巧,出處要表現(xiàn)出力來,達夫在鴨綠江上讀后感里也已說過。達夫過去的創(chuàng)作,雖有了很大的成功,究竟還缺少了力的表現(xiàn)。我們希望達夫在今后的創(chuàng)制中,在技巧方面表現(xiàn)出偉大力量!……,表現(xiàn)出狂風暴雨時代的精神的力量!③
在批評郁達夫“軟弱”的同時,錢杏邨極其推崇蔣光慈“力的藝術”創(chuàng)作。在評價蔣光慈的《蔣光慈與革命文學》中,錢杏邨說:
(《短褲黨》)這一部小說,可以說是代表了過去的革命力量最高的表現(xiàn)。①
錢杏邨后來在《力的文藝·自序》(1928)中說:“這一集文藝批評的名稱,本來是題做‘力與爭斗’的。所以然題做這個名字的原因,是被批評的各部名著,不是代表了人間的偉大的力,就是描寫斗爭的”,“我們深切的知道這些偉大的作品對于無產(chǎn)階級文學的建設是有巨大力量的”,并且說:“我是一個力的崇拜者,力的謳歌者,這兩書(他指的是《強盜》和《尼伯龍根之歌》——引注)的特長是他們表現(xiàn)了最偉大的,最震動的,最咆哮的,最不肯妥協(xié)的,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偉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力!”②
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論》(1933)中,錢杏邨稱呼五四時期的郭沫若是“力的追求者”(《緒章》,寫于1930年),稱贊當時的穆時英“文字技術方面,作者是已經(jīng)有了很好的基礎,不僅從舊的小說中探求了新的比較大眾化的簡潔,明快,有力的形式,也熟悉了無產(chǎn)者大眾的、獨特的、為一般智識分子所不熟悉的語匯,以這樣的文字技術,去描寫正確的新的題材,是能以適應的,只要作者能艱苦的走上新的道路”(《1931年中國文壇的問題》,寫于1932年),并且由《力的文藝》中對英雄力的贊美已經(jīng)發(fā)展到對個人英雄主義(“流氓無產(chǎn)階級意識”)的批判了。③
可以看出,錢杏邨在總結五四新文學和早期革命文學成就的基礎上提出了“力的文藝”的概念,界定了“偉大的反抗”的“力的藝術”的本體論、“力的表現(xiàn)”的形式論和技巧論等的內(nèi)涵。所以說,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是革命文學理論家在總結五四新文學和早期革命文學經(jīng)驗和成就的基礎上,是在中國工農(nóng)力量已經(jīng)顯現(xiàn)的基礎上自覺形成的,④是一種民族性和本源性的理論成就。
而將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界定為“力的文學”,不僅在左翼文藝理論家如此,在非左翼文藝理論家也是如此。1940年,京派評論家李健吾(劉西渭)也說:“沒有比我們這個時代更其需要力的。假如中國新文學有什么高貴所在,假如藝術的價值有什么標志,我們相信力是五四運動以來最中心的表征。它從四面八方來,再奔四面八方去。它以種種面目出現(xiàn),反抗是它們共同的特點。”⑤這也佐證了這一認識的合理性。
這里需要辨析的是,黃曼君主編的《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史》將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學成就的一支排除在錢杏邨的“力的文藝”的范疇之外,似可商榷。該著作認為:“需要辨別的是,錢杏邨提倡‘力的文藝’,完全不同于五四時代浪漫狂飚詩人郭沫若一度崇尚的‘力的文藝’。郭沫若詩集《女神》篇什大量謳歌的高山、巨川、地球、太陽、宇宙……旨歸于對‘泛神’意志驅使下的自然、宇宙生命力的禮贊;郭沫若所贊美的‘女神’、‘天狗’、‘匪徒’……意在謳歌人類文化史上對現(xiàn)存秩序、既定規(guī)范的叛逆精神與文明創(chuàng)化力。錢杏邨提倡‘力的文藝’,直接體現(xiàn)的是現(xiàn)實社會中‘第四階級’的‘強烈的反抗心思’和‘偉大的意志’,是無產(chǎn)階級的革命、戰(zhàn)斗、反抗的力量。”⑥主張以錢杏邨主張無產(chǎn)階級性質的“力的文藝”來區(qū)隔五四新文學的民主革命性質的“力的文藝”。關于這一點,我們沒有在錢杏邨的文本中看到這種嚴格的界定;再者,郭沫若《女神·序詩》開篇即說“我是個無產(chǎn)階級者”“我愿意成個共產(chǎn)主義者”;何況,五四時期“郭沫若一度崇尚的‘力的文藝’”本身也是錢杏邨理論建構出來的。因此,很難將“郭沫若一度崇尚的‘力的文藝’”排除在錢杏邨的無產(chǎn)階級“力的文藝”范疇之外。
三、本體論流變和體系性建構
一般理解,本體指的是形成現(xiàn)象的根本實體。與啟蒙主義尚力思潮強調(diào)心力、個力的資產(chǎn)階級性質不同,①左翼文藝“力的藝術”是無產(chǎn)階級性質的,它強調(diào)的是階級之力、團結之力、集體之力、斗爭之力、非個人主義的英雄之力。就本質而言,“力的藝術”是左翼文藝倡導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的一個理論表征。因此,總體上可以認為,左翼文藝“力的藝術”是一種階級性本體論,但在左翼文藝譜系內(nèi)部,這種本體論并不具同一性,存在著一定的流變。
在辛克萊《拜金藝術》中,對于“力的藝術”的定義是很簡單的:“人類在世界藝術作品之內(nèi)自然表現(xiàn)在那里的氣質與態(tài)度有兩種不同的典型:就是美的藝術(the art of beauty)與力的藝術(the art of power)的兩種。”②美的藝術對應的是支配階級的藝術、力的藝術對應的是被治階級的藝術,按照辛克萊行文的內(nèi)容,被治階級上升為支配階級后,力的藝術就上升為美的藝術:“總之是那些本來是在創(chuàng)制力的藝術的人們,現(xiàn)在要開始創(chuàng)制起美的藝術來了。”③顯而易見,辛克萊的“力的藝術”是一種二元論的階級本體論藝術觀,而且這兩種藝術之間的轉化關系也略微讓人費解。
雖然錢杏邨沒有出現(xiàn)“力的藝術”和“美的藝術”的二元論論調(diào)(這也可以作為判定錢杏邨沒有受辛克萊影響的依據(jù)),但毫無疑問,錢杏邨“力的藝術”觀念在本體論上也是階級性的,是其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錢杏邨這種階級性本體論甚至達到了某種機械、庸俗的程度。比如他認為:“一般的創(chuàng)作家與批評家有一種極大的錯誤,就是沒有看清階級與技巧的關系,也可以說是技巧與題材的關系。”④將藝術技巧、題材泛階級化,這和認為語言是有階級性的錯誤是一樣的。因此說,在階級性本體論這點上,錢杏邨和辛克萊是一致的。
但在左翼文藝內(nèi)部,魯迅對于“力的藝術”的本體論認識卻不同,他將“力的藝術”歸之于“美”的范疇,沒有接受辛克萊的二元論,也沒有沿襲錢杏邨的階級本體論。李長之的《魯迅批判》(1936)在魯迅生前出版,曾受到魯迅的支持。魯迅閱讀了書稿、校定了書稿中的一些著作時日并提供了個人照片。李長之對魯迅“力的藝術”觀大加贊賞,他在書中說:“藝術之中,不錯,他也有所稱贊的,但卻就只限于‘力的表現(xiàn)’的木刻;魯迅對于優(yōu)美的,帶有女性的意味的藝術卻是不大熱心的。一如他在思想上之并不圓通一樣,在美的鑒賞上并不能兼容。”“強烈的情感和粗暴的力,才是魯迅所有的。”⑤
1929年,“力的藝術”觀念頻繁出現(xiàn)在魯迅的藝術批評中。在《近代木刻選集(2)·小引》(1929)中,魯迅說:“自然也可以逼真,也可以精細,然而這些之外有美,有力;仔細看去,雖在復制的畫幅上,總還可以看出一點‘有力之美’來”,“但這‘力之美’大約一時未必能和我們的眼睛相宜。流行的裝飾畫上,現(xiàn)在已經(jīng)多是削肩的美人,枯瘦的佛子,解散了的構成派繪畫了”,“有精力彌滿的作家和觀者,才會生出‘力’的藝術來。‘放筆直干’的圖畫,恐怕難以生存于頹唐,小巧的社會里的”⑥。在《我和〈語絲〉的始終》(1929)中,魯迅說:“雖然因為毀壞舊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舊物來的一種突擊之力,至今尚為舊的和自以為新的人們所憎惡,但這力是屬于往昔的了。”①從文字中可以看出,魯迅有個“力的藝術”的概念,但他“力”和“美”的概念是統(tǒng)一的,主張的是一種“力之美”,而不是二者的二元對立,從而將“力的藝術”從社會(科學)學的立場回歸到藝術美學的立場。
魯迅之外,追求“力之美”的“力的文學”也是1930年代左翼文藝批評和作家創(chuàng)作的“一種普遍的藝術追求”。②
到了“左聯(lián)”后期(1930年代的中后期),除了表現(xiàn)出主觀主義、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等弊端之外,傳統(tǒng)的左翼文藝理論在“文藝根源”和“創(chuàng)作動力”兩個根本性問題上開始出現(xiàn)分化。在解放區(qū),“文藝根源”和“創(chuàng)作動力”日漸生活化、政治化、大眾化,左翼文藝逐漸向普及和歌頌方向發(fā)展,而在胡風等主要生活在國統(tǒng)區(qū)的左翼文藝理論家那里,“文藝根源”和“創(chuàng)作動力”日漸主體化、精神化,繼續(xù)延續(xù)著五四新文學批判和暴露的方向發(fā)展。因此,在1935—1936年間,胡風把作者的精神狀態(tài)看作文藝根源和創(chuàng)作動力之一,開始注意到“主觀”以及“主觀力”這一類概念,其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軸心——主體理論基本形成,而1940年代“主觀戰(zhàn)斗精神”等理論只是在這個基礎上符合邏輯的發(fā)展。因此,胡風把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推動到主體性本體論階段。
1942年,胡風作為中華全國文藝家協(xié)會理事、研究部負責人,曾為文協(xié)理事會第六屆年會起草了《文藝工作底發(fā)展及其努力方向》的報告,提出了“主觀戰(zhàn)斗精神”這個概念。這個報告在當時就引發(fā)黃藥眠(《讀了〈文藝工作底發(fā)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茅盾等的異議。而與胡風思想較為接近,又與延安文藝有著緊密聯(lián)系、曾是魯迅與中共聯(lián)系人的馮雪峰,很清楚胡風理論的短板或者不適宜之處。因此1944年開始,馮雪峰為了糾正胡風主觀戰(zhàn)斗精神等理論的偏頗之處,在《論藝術力及其它》和《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等著作中提出了藝術力、主觀(戰(zhàn)斗)力、人民力等概念,以調(diào)和藝術主客觀立場的對立。
在《論藝術力及其它》中,馮雪峰正面界定了“藝術力”的概念:“藝術力——藝術的戰(zhàn)斗力”。在馮雪峰的理論中,所有藝術的功能都稱為“藝術力”,而藝術力的組成來自兩個方面——主觀力和人民力:
追求客觀真實和表現(xiàn)真實的力量;迫擊和深掘現(xiàn)實生活的意志;對于社會矛盾的認識與判決力,肯定與否定力;對于黑暗和一切壓迫勢力的憎惡;對于人民和一切光明力量的火一般的猛烈的愛,等等。從這里,反映著客觀的真理,反映著人民的新生,偉大的戰(zhàn)斗的姿態(tài),和英雄主義,反映著人類歷史的偉大的理想力和向上發(fā)展力。這就叫做藝術力。解釋地說,就是必須從藝術里表現(xiàn)出來的人民與作者的主觀戰(zhàn)斗力。(而客觀真理本身的力量,也自然在這主觀戰(zhàn)斗力中反映出來。)③
馮雪峰認為,藝術力或藝術戰(zhàn)斗力源自主觀力和人民力兩個方面,主觀力是藝術力的關鍵,但表現(xiàn)或者反映人民力是藝術力創(chuàng)作的本質和中心任務。將人民力論述成一個藝術批評術語,這是馮雪峰在歷史唯物主義把人民看作是主宰歷史的決定性力量這一信念支配下提出來的概念。④馮雪峰認為:“誰都認為反映全民族的人民的生活和現(xiàn)實的斗爭,特別反映在飛躍地發(fā)展著的人民的新生的力量,是我們革命現(xiàn)實主義文藝現(xiàn)在所追求的唯一根本的目標。”⑤
在《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中,馮雪峰指出:“人民的力量,對歷史和社會的客觀本身及其變動上的其他的客觀條件說,是人民的主觀的力量;但對作家或文藝的主觀說,它是客觀。人民的力量又是怎樣來的呢?來自歷史的現(xiàn)實的矛盾斗爭中。正惟這客觀的、人民的斗爭和力量,才是文藝的思想力,藝術力,作品或作者的一切主觀戰(zhàn)斗力的源泉。”馮雪峰更進一步指出:“因此,大家對文藝要求著思想力,藝術力,主觀的戰(zhàn)斗熱力,歸根結蒂,無非是要求文藝取得在歷史的現(xiàn)實的矛盾斗爭中的人民的力量,無非是要求文藝應該真實地在現(xiàn)實斗爭中而將人民力變成文藝的主觀的力量,于是文藝能在人民中起著強大的作用。這種主觀與客觀的關系以及具體的解決方向,是很明確的。”①
顯然,馮雪峰“這種主觀與客觀的關系以及具體的解決方向”中的“力的藝術”觀念又一定程度上位移回“藝術的力”的傳統(tǒng)范疇,也就是魯迅意義上的“力的藝術”,又同時在主體性和客體性本體論之外,建立了一種“藝術力”的間性本體論。輔以其他各方面(文藝與社會、生活、人民、主體、創(chuàng)作方法等)的論述,馮雪峰完成了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體系的建構:“力的藝術”和“藝術的力”的辯證統(tǒng)一。②
但這種體系性發(fā)展常常被忽視。因為無論錢杏邨還是魯迅,“力的藝術”觀念在1928—1929年之后就較為稀罕,而且辛克萊的藝術觀很快就受到批判。比如馮乃超在1930年《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文獻》中即說:“美國方面特別要舉出辛克萊的《拜金藝術》。這不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理論。因為有中文的譯本,不能不加以批評。”③對這種“斷裂”,研究者多認為主要是“力的藝術”觀被其他議題(比如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代替,從而沒有多維展開。④但其實從1928—1929年到1940年代,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的發(fā)展并沒有斷裂,在整個1930年代是客觀存在并且發(fā)展的。比如1933年,茅盾在《力的表現(xiàn)》中說“記得我們文壇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一個名詞:‘力的文學’”,似乎明確說“力的文學”(“力的藝術”)觀念已經(jīng)過時了,但茅盾在文章中以喝酒作比喻,說“真正有力的文藝作品應該是上口溫醇的酒”,“但并不是說上口極猛的文藝作品就要不得。不過作家應該不以‘上口猛’為滿足”,⑤顯然,茅盾是對錢杏邨曾經(jīng)主張過的粗暴、狂躁、粗糙的“力的文藝”美學風格加以發(fā)展、補充。同樣,1936年,有一篇署名為“秋”的文章提出《我們需要“力”的文學》(《民智月報》1936年第5卷第3期),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以“力的藝術”觀念對“消閑”“軟性”文學進行批判。更需要注意的是,1935年,有一篇署名為“獨”的文章《力的文學和文學的力》就呼吁將“力的文學”建立在“文學的力”的基礎上,力和文學不能分離。而這種“二統(tǒng)一”的“力的藝術”觀和馮雪峰1940年代的主體、客體、藝術“三統(tǒng)一”的“力的藝術”觀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構成了一種體系性的發(fā)展。⑥因此說,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是一種體系性存在,即使考慮到其發(fā)展并不充分,也至少應該認為是一種線性的存在。
四、回望的意義和必要性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展史上,左翼文藝運動是第一場大規(guī)模理論建設運動,文藝大眾化是這場理論運動成果的代表。相比文藝大眾化,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體系這類成就很容易被忽視或被遮蔽。我們討論的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的思源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過去由于長期禁錮在外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影響的敘述模式中,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與國際左翼文藝運動(如辛克萊)之間到底是怎樣一種影響關系和過程,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梳理和說明。通過前文我們認為,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主要是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理論家在總結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和早期革命文學創(chuàng)作成就的基礎上獨立起源的,是一種民族化的理論成果,并不是完全受到辛克萊理論的影響而產(chǎn)生的。所以說,相比文藝大眾化理論的日本起源,“力的藝術”觀念的源起和流變就更具有民族特性。
同樣的道理,過去我們只看到了點狀存在的左翼文藝各種“力”的藝術觀念,而沒有意識到其內(nèi)部本體論的流變和體系性的構成,也就忽視了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體系性存在的理論價值,甚至忽視了“力的藝術”觀念對包括文藝大眾化理論在內(nèi)的貢獻。1930年,魯迅在《文藝大眾化》中批評左翼批評家在文藝大眾化問題上一只眼看問題、一條腿走路,光說“動聽的話”“聊以自慰”,缺乏現(xiàn)實的可行性,但最后,魯迅并不否認文藝大眾化存在著大規(guī)模發(fā)展的可能,他認為需要某種“力”——也就是政治力的幫助才能實現(xiàn)真正的文藝大眾化:“若是大規(guī)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①認為只有在“政治之力的幫助”下,文藝大眾化才有可能真正、大規(guī)模地得以實踐。所以有研究者看到,政治力的變化在版畫和大眾關系的變遷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30年代魯迅推動新興版畫(包括木刻)這些藝術形式,就是借助了“政治力”這個因素。②
數(shù)十年來,不斷有研究者進行“力”的批評話語實踐,③但我們還是少有錢杏邨那樣經(jīng)典的批評成就。錢杏邨除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第1卷)》《力的文藝》,還編譯、撰寫了《作品論》(1929)、《文藝批評集》(1930)、《現(xiàn)代中國文學論》(1933)等,皆以“力”的藝術觀念為批評話語或標準收錄作品,對國內(nèi)外作家作品和文藝現(xiàn)象進行批評實踐。如《文藝批評集》中“從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新興創(chuàng)作與日俄文壇”等篇章,收錄了大量符合“力的藝術”觀念的“情緒至上”的“無產(chǎn)文學”。這些都是“力的藝術”批評實踐上的經(jīng)典之作,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和學習。
總而言之,這些既往被我們忽視的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體系的理論歷史與話語實踐(藝術批評),恰恰映射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早期發(fā)展的本源性特點和批評成就。因此,以今日的理論眼光回望左翼文藝“力的藝術”觀念,可以促進理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早期發(fā)展的中國性問題,可以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批評的發(fā)展提供借鑒和參考。
*? 本文系中國藝術研究院2020年基本科研業(yè)務費資助學術研究項目“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生學研究”(項目批準號:2020-1-20)的階段性成果。
①? 樊星:《尚力的世紀——五談告別20世紀》,《別了,20世紀》,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頁。
②? 劉永明:《顛覆抑或超越——2004年中國文學經(jīng)典“解毒”思潮回顧》,《美與時代(下)》2013年第11期。
③? 胡傳吉:《“力”之文學變道》,《小說評論》2010年第1期。
④? 白剛:《論近代尚力思想與現(xiàn)代尚力精神》,《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⑤? 本文把“力的文藝”“力的文學”等概念和左翼文藝各種“力”的藝術觀念都統(tǒng)括在“力的藝術”范疇。
①? 朱曉進《五四文學傳統(tǒng)與三十年代文學轉型》(《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曾是五四時期學衡派代表人物的吳宓,在30年代曾以激賞的眼光高度評價過茅盾的《子夜》等作品,是‘表現(xiàn)時代動搖之力,尤為深刻’。‘京派’主要批評家之一的劉西渭在評論葉紫的小說時,也曾以贊嘆的筆調(diào)稱其為:‘這是力,赤裸裸的力,一種堅韌的生命之力。’他甚至將‘力的文學’看作是‘中國新文學的高貴所在’和‘藝術價值’的‘標志’。”
②? 傅瑩:《中國現(xiàn)代文學理論發(fā)生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72、96頁。
③? [日]本間久雄:《新文學概論》,章錫琛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初版,第4頁。
④? 朱自清:《朱自清序跋書評集》,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版,第237頁。
⑤? 一些史料提到端木蕻良在南開中學讀書時(1928—1931)和老師合作撰寫了《力的文學宣言》一文(如孔海立《端木蕻良傳》,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頁),因未檢索到原文(2009年北京出版社《端木蕻良文集》第5卷《雜論篇》《文論篇》也未收錄該文),故不納入討論范圍。同樣情況的還有楊邨人(楊村人)編輯過《力的文學》作品集。
⑥? 如王智慧《論“革命文學”的藝術性追求》(《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革命文學’時期,悄然崛起了一種新的美學原則——即‘力的文藝’。錢杏邨是這一原則的最初提倡者與忠實執(zhí)行者。”
①? 葛中俊:《厄普敦·辛克萊對中國左翼文學的影響》,《中國比較文學》1994年第1期。
②? 杜運通:《我們社、太陽社比較論》,劉增杰、孫先科主編:《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轉捩點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頁。
③? 張大明:《中國左翼文學編年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0頁。
④? 郁達夫:《郁達夫全集·第5卷·日記》,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236頁。
①? 錢杏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第1卷)·自序》,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版,第1頁。
②? 錢杏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第1卷)》,第58、68、71頁。——引文中的粗字體為本文引者所加,下同。
③? 錢杏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第1卷)》,第136—137頁。
①? 錢杏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第1卷)》,第164頁。
②? 錢杏邨:《力的文藝》,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版,第4、6、118頁。
③? 錢杏邨:《現(xiàn)代中國文學論》,上海:合眾書店,1933年版,第18、96頁。
④? 錢杏邨《英蘭的一生》(1928年1月1日《太陽月刊》創(chuàng)刊號):“從五卅慘案發(fā)生后,中國民族有了一種極大的轉變,就是民眾的革命精神,尤其是工農(nóng)階級的反抗的偉大的革命精神,表現(xiàn)得一天比一天強烈,以這部小說寫作的時代說,完成已在香港十九個月的大罷工以后,中國工農(nóng)的力量是早已充分表現(xiàn)出來了,中國民族不單是為自己命運的不幸唱悲歌,哀喊,而能夠,進一步的站起來找出路了!”
⑤? 李健吾(劉西渭):《咀華集·咀華二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頁。
⑥? 黃曼君主編:《中國20世紀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289頁。
①? 晚清和五四時期的資產(chǎn)階級尚力思想有很大區(qū)別:晚清嚴復、梁啟超主張的“民力”是民族主義和國民主義的,也是集體性的;而1907—1908年時期魯迅的“心力”“立人”思想和五四時期的尚力思想是個人主義、自然主義的。
②? [美]辛克來:《拜金藝術》,《郁達夫譯文集》(上),郁達夫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84頁。
③? [美]辛克來:《拜金藝術》,《郁達夫譯文集》(上),郁達夫譯,第86頁。
④? 錢杏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家(第1卷)》,第169頁。
⑤? 李長之:《魯迅批判》,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版,第102頁。
⑥? 魯迅:《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0—351頁。
①? 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頁。
②? 朱曉進:《政治文化與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頁。
③? 馮雪峰:《論藝術力及其它——文藝風貌偶瞥之三》,《雪峰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238頁。
④? 溫儒敏:《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頁。
⑤? 馮雪峰:《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頁。
①? 馮雪峰:《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雪峰文集》第2卷,第166頁。
②? 馮雪峰“力”的藝術觀念非常龐雜,除了文中已經(jīng)提到的,還包括文化發(fā)展、文明交流等方面的“發(fā)展力”“同化力”“他化力”“創(chuàng)造力”等系列概念,其中一些概念和觀點還引起比較大的爭議、批評。
③? 馮乃超:《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文獻》(1930年4月1日《文藝講座》第1冊),《馮乃超文集(下)》,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頁。
④? 參見王燁《20年代革命小說敘事成規(guī)的探尋與運用》(《中國文學研究》2008年第4期)、孟麗娟碩士論文《丁玲創(chuàng)作與“力的文學”》(2005年四川大學)。
⑤? 茅盾:《力的表現(xiàn)》,《申報·自由談》(1933年12月1日)。
⑥? 經(jīng)查徐乃翔、欽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者筆名錄》(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未發(fā)現(xiàn)署“獨”“秋”筆名的作家。
①? 魯迅:《魯迅全集》第7卷,第368頁。
②? 張鵬:《解體與重建——論中國現(xiàn)代版畫與受眾之間的關系變遷》,《北方美術》2009年第3期。
③? 如劉暢《謝·維·拉赫瑪尼諾夫鋼琴創(chuàng)作中作為美學范疇的“力”》(《音樂創(chuàng)作》2013年第12期)、彭再生《“力”作為書法批評的范疇》(《中國美術報》2016年8月29日)。
作者簡介:劉永明,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