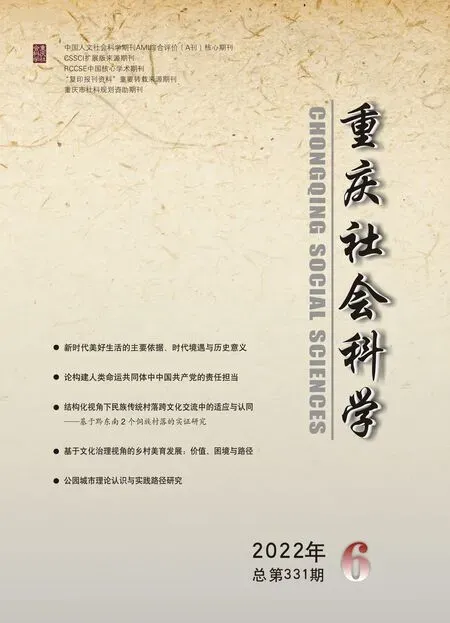基于文化治理視角的鄉村美育發展:價值、困境與路徑
胡楊
摘 要:鄉村美育是新時代我國鄉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內容和手段,具有激發鄉村文化內生活力、實現鄉村文化振興以及傳承民族文化基因的價值意義。鄉村社會轉型帶來鄉村社會結構和文化秩序的改變,導致我國鄉村美育面臨美育主體性危機、美育價值弱化、美育實踐碎片化以及現代性沖擊等現實困境。為此,從文化治理的角度,鄉村美育實踐應從培育鄉村文化主體成長、提升鄉村文化價值引領、注重鄉村美育場域打造、促進鄉村文化產業創新以及重塑鄉村文化治理格局等方面入手,實現以美治鄉、促進鄉村文化振興的目標愿景。
關鍵詞:鄉村美育;文化治理;鄉村文化振興
基金項目: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中特理論重點項目“新時代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數字化傳播研究”(2021ZTZD08);重慶市博士后科研項目特別資助。
[中圖分類號] C913 [文章編號] 1673-0186(2022)006-0047-012
[文獻標識碼] A ? ? [DOI編碼] 10.19631/j.cnki.css.2022.006.004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我國鄉村建設取得巨大成就,極大地推動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體目標前進。但同時,鄉村社會也面臨著經濟體制、價值觀念和文化形態的結構性變遷,在城市化與現代化進程中受到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沖擊,鄉村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拔根”危機[1]。在這種新的鄉村發展歷史境遇和文化建設語境中,鄉村審美實踐呈現出新的文化面向,鄉村文化振興迫切需要解決兩組矛盾:一是如何在鄉村現代化建設中既保護好原有的中國傳統“鄉土”文化精華,如具有傳承價值的鄉土倫理、文化生活樣式以及各類鄉村文化遺產等,又能摒棄落后、愚昧的鄉土文化糟粕;二是如何在鄉村現代化進程中既良好吸收譬如理性公平、現代契約精神以及法律意識等現代化精神理念,又保護其不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西方文化霸權的影響,既保持開放又堅定傳承,力求充分保持并展示自身特有的鄉土傳統文化精神。
自黨的十九大將鄉村振興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以來,鄉村文化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產業興旺、生態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方面緊密相連。《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強調,要“突出實效改進鄉村治理”,在鄉村文化治理方面要“加強農耕文化傳承保護,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和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利用”[2]。我國傳統農耕文化中蘊含的鄉村美育元素既是鄉村文化治理的手段,又是文化治理的內容,它既喚起村民內心對美的追求,又指導鄉村的物質建設和精神建設。因此,從鄉村文化治理的角度,重新審視鄉村美育在鄉村產業振興、文化振興和生態振興中的價值生產,梳理其面臨的現實困境并找準發展路徑,對于提升鄉村文化主體性、增強鄉村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美麗鄉村有著重要意義,同時也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使民族文化根脈“有土可依、有鄉可還”的重要路徑。
一、相關研究回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使每個社會細胞都健康活躍。”[3]在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如何通過鄉村文化治理實現鄉村文化振興成為學者們的研究熱點,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從審美和美育的角度關注鄉村文化治理和鄉村文化發展的研究卻相對較少。因此,基于鄉村美育和文化治理兩個角度,本文主要從理論基礎維度集中梳理現有的關于鄉村文化治理、審美符號與文化治理關系的研究,以及從實踐維度梳理人文藝術領域中對鄉村文化和鄉村美育的相關研究。
(一)文化治理中的審美符號
文化治理理論源于英國學者托尼·本尼特,他在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和葛蘭西的霸權主義基礎上提出了文化治理的概念,認為“應把文化看作一系列通過歷史特定的制度形成的治理關系,目標是為了轉變廣大人口的思想和行為,這部分是通過審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術和規則的社會體系實現的,文化就會更加讓人信服地加以構想”[4]210。他主張文化既是治理的對象又是治理的工具,既關涉社會生活的道德、禮儀和生活方式,又是對這些對象進行干預和調節的手段。正是在這種理論前提下,藝術活動、博物館、傳統文化等美育元素也被吸納進來成為文化治理的中介。
首先是關于我國鄉村文化治理的演化邏輯、現實困境和治理路徑的相關研究。有學者分析中國共產黨百年來的鄉村文化治理歷史,認為其經歷了從“有限治理”到“系統治理”再到“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邏輯演進[5];同時,研究者們對當下鄉村文化治理的現實困境關注較多,認為目前我國鄉村從文化環境到文化治理主體和客體等都受到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沖擊;鄉村傳統文化出現明顯的凋敝與異化[6],為本文探討鄉村美育的現狀與困境提供了現實參照。還有學者從文化治理策略的角度提出當前鄉村文化治理最為基礎的工作應首先對鄉村治理譜系進行圖譜繪制,“依據不同的鄉村屬性特質,編制和繪制鄉村治理的文化社會結構圖”[7]等。但從總量上看,以“鄉村文化治理”為主題的學術論文在CNKI中收錄還不到百篇,這樣的研究成果總量不論是從當前國家的戰略指向還是鄉村文化治理現狀看,都是與之不相匹配的。
其次是關于美育或審美活動在文化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的相關研究。西方早期美育思想家康德、席勒主張審美無功利思想,力求通過審美超越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帶來的現實弊病,從而實現人的精神自由。而后福柯和本尼特等人都對康德的審美無功利進行了批判,認為其思想割裂了個體和社會文化、政治之間的關系,這種“文化區隔”僅是一種幻想。就我國而言,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文化治理的概念,但審美文化治理邏輯卻貫穿幾千年中華文明。從古代儒家思想中的“禮樂詩書教化”,到近現代梁啟超的“新民”美育思想、蔡元培的“以美代宗教”思想以及朱光潛主張“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的“人生論”美學等等,美育一直在國家社會治理領域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當代的美育研究中,學者們也十分重視對美育社會功能的研究。有學者認為,“人文理想”和“文化治理”是構成美育思想和實踐的兩個維度,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了美育在文化史中的不同人文面相和演變線索[8]。同時,美育因其“實踐性”而對我國現代社會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有不可低估的作用[9]。對于當代社會中的個人發展而言,美育更是“感性教育、培養整體人格的教育以及創造教育”[10],人的全面發展是其最終目的。而關于當代美育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是審美教育超越傳統美學向哲學意義上的“日常生活”轉向,認為“必須在諸如日常生活、政治、經濟、生態、倫理和科學領域里,來尋找今日的審美方式”[11],這就為審美符號在文化治理中的運用提供了現實合法性和理論依據,其中的生態審美、自然審美、技術審美等領域的開拓也為新時代鄉村文化振興研究提供了新的視域。
(二)人文藝術視野下的鄉村文化與鄉村美育
從實踐層面,我國學者從文化藝術領域關注鄉村文化與鄉村美育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路徑。
一種是從藝術介入鄉村的角度,將現代自律藝術的理念和手段與傳統非自律鄉村藝術的生產相結合,以藝術鄉建為美麗鄉村建設賦能。近年來涌現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藝術介入鄉村的案例,如山西許村計劃、廣東青田范式等等。這些藝術鄉建嘗試,更多是藝術家自身“尋求一種精神的復興之路,重塑信仰和價值”[12],因此,它的問題也非常明顯:大多從外來者和藝術家的角度觀照鄉村的發展,更多是在尋求城市人和藝術家心目中的“鄉村和鄉愁”,這種天然的局限性導致鄉村文化建設和鄉村美育主體的錯位和缺失。有學者因此提出藝術鄉建要考慮各個主體在鄉建場域中的多樣化張力和互動關系[13],采用“鄉村型藝術集聚”的方式,推動前工業文明向后工業文明的轉型[14],并開始關注國外尤其是日本的藝術鄉建經驗[15],希望能為我國藝術介入鄉村建設提供借鑒。
另一種是從文藝民俗學和藝術人類學的角度,對鄉村傳統的民族民間文化內容進行研究,尋求鄉村文化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并從客觀上促進鄉村美育發展。文藝民俗學者主要關注我國各種民間傳統文化習俗,包括音樂、舞蹈、美術及戲劇,等等[16],在歷史積淀中尋求當代傳承與轉換的路徑;有學者認為,人類學家的主要作用是“幫助鄉村重建文化記憶和文化知識體系”[17];藝術人類學則從更宏大的視野觀照鄉村建設,關注藝術在鄉村政治空間、娛樂空間、歷史空間和教育空間等中的作用,關注鄉村建設的主體全面發展,以及關注鄉村發展過程的價值傳統延續創新以及生態發展等。
面對新時代社會轉型期我國鄉村的復雜環境,鄉村文化振興也應是多維度多層次的。雖然現階段我國專家學者們對當代鄉村文化振興中的文化治理和文化發展已經積累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從理論上看,鄉村文化治理中審美治理的作用機理還需進一步闡釋;從實踐上看,還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對鄉村建設主體審美意識、審美能力提升的關注,缺乏對鄉村審美環境建設的長期和系統規劃,與當下藝術鄉建活動開展如火如荼的現狀形成強烈反差。因此,將鄉村美育作為鄉村文化治理的方向之一,探討鄉村美育內涵以及在鄉村文化振興中的價值,以鄉村美育推動鄉村主體發展、鄉村文化生態系統建設和鄉村文化自信提升等相關內容,應該成為當下藝術鄉建乃至鄉村文化振興的新的思考方向。
二、鄉村美育的內涵及價值生產
在鄉村振興和鄉村文化治理語境中關注鄉村美育的意義和方法,不僅是對“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等戰略目標的踐行,也是對現代文化治理和社會美育的理論拓展。因此,要進一步探討何種藝術類型和審美維度能夠被引入鄉村文化治理范疇、藝術和審美應在何種標準下對鄉村文化建設發揮作用,以及如何保證鄉村美育與鄉村發展形成長期有效的積極促進關系等問題,需要首先明確鄉村美育的內涵及其在鄉村文化治理中的價值生產。
(一)鄉村美育的內涵
美育即審美教育。從教育的形式和對象上進行劃分,可以分為學校美育、家庭美育以及社會美育。學校美育與家庭美育較好理解,而社會美育則是前兩者之外的、伴隨人終生的、貫穿于各類社會活動、人與自然關系中的社會美育文化[18]。鄉村美育則可以進一步理解為是一個從屬于社會美育的概念,指在鄉村場域中的、鄉村社會活動實踐和各類關系中的美育文化。鄉村美育應至少包含兩個對象層次:村民個體的審美成長和鄉村美育生態的整體建構。當把我國鄉村文明看作是由千百年來我國農耕文明沉淀出的一套完整的社會文明關系體系時,其美育內核就體現在鄉村社會的方方面面:從內容上看,既包含有鄉村社會精神文明、倫理道德、鄉風民俗,也包含鄉村流行時尚與消費行為,還包含民間文化藝術和自然生態美育等。同時,由于我國傳統鄉村“家庭主義”文化內核和“家庭本位”的生活秩序[1],鄉村美育與家庭美育在手段和內容上又有貫穿和重疊。
(二)鄉村美育在鄉村文化治理中的價值生產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強調:“中華文明根植于農耕文化,鄉村是中華文明的基本載體。”鄉村美育以中華耕讀文明為依托,同時又承接現代文明發展,是鄉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內容和手段,對留住和傳承鄉村文化根脈、促進鄉村文化振興有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第一,有助于激發文化內生活力,提升農民精神風貌。如馬克思所說,“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19]。鄉村文化從鄉村泥土里生長出來,在鄉村勞作、鄉村社會生活實踐中慢慢形成、發展和再生產。換句話說,鄉村日常生活的實踐邏輯就是鄉村文化的生產邏輯,具有鮮明的內生性特征。同時,鄉村文化的內生性又體現為文化主體的內生,只有當農民對自身文化形成一種“文化自覺”,明白其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鄉村文化才會具有不竭的內生活力。鄉村美育以鄉村社會精神文明、倫理道德、鄉風民俗以及民間文化藝術為內容,有助于喚醒農民的審美意識、用與鄉村社會生產生活實踐緊密相連的各類審美活動提升農民的精神風貌,有助于將中國農民從晏陽初所說的傳統的“愚窮弱私”的固有形象中解放出來,形成新時代中國農民的文明、昂揚、奮發的風貌。
第二,有助于實現鄉村文化振興,建設美麗鄉村格局。2022年2月,自21世紀以來連續第19個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出臺,再次對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做出部署,鄉村美育對于鄉村文化振興有著重要意義。一是鄉村美育本質與美育的本質一致,是一種人格教育、感性教育和創造力教育,有助于提高鄉村文化振興主體的整體人才水平;二是鄉村美育目標與鄉村文化振興目標一致,強調對鄉村思想道德的建設、對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提升,有助于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和淳樸民風;三是鄉村美育實踐路徑與鄉村社會生活實踐路徑一致,都融會于鄉村日常生活,有助于村民以審美的態度對待自然、對待社會以及自身,有助于農民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提升。因此,鄉村美育的實施是以一種系統綜合的力量推動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生態振興尤其是文化振興,從而進一步推動“望得見山、看得見水、留得住鄉愁”的美麗鄉村格局建設。
第三,有助于傳承民族文化基因,增強社會文化認同。中國文化的根在鄉土,費孝通說:“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20]從這個意義上講,新時代的鄉村振興,不僅關乎鄉村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關乎整個中國社會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禮失求諸野”,中華文明延綿幾千年,在傳統鄉村社會中一直存在一套相對穩定又被廣泛接受的價值系統,因其包含中華文明中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的生命存在意義的深刻理解而成為整個中國社會重建的價值來源[21]。但隨著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來自鄉村的價值基礎與現代社會價值間正面臨“文化斷裂”。鄉村美育從民間藝術、鄉風民俗、鄉村景觀、鄉村文化遺產等多重維度入手,挖掘蘊含在農耕文化中的審美元素,提取并傳承民族文化基因,讓鄉村文明繼續輻射整個中國的現代文明,留住中華文明的根脈,凝聚人心、增強社會文化認同。
三、新時代鄉村美育的現實困境
如前文所說,鄉村美育是一項系統的、整體的鄉村文化治理路徑。鄉村人口的流動、新農村建設對鄉村居住環境和地理環境的改變以及社會現代化進程對鄉村傳統文化的沖擊等等,都直接影響著鄉村美育的實施。具體而言,新時代我國鄉村美育面臨的現實困境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鄉村美育的主體性危機
鄉村社會的主體性問題一直是鄉村振興研究者關注的熱點。在費孝通先生看來,“文化主體性”是文化自覺的目的,體現為對現代化的一種“自主的適應”[22]。具體到鄉村美育上,其主體性體現為對當下鄉村建設和文化轉型中的審美元素進行自主適應、選擇批判和包容創新。從美育的角度看,這種主體性特征也是社會美育的主要特征。社會美育與學校美育間最大區別在于前者具有社會性、內生性和自發性。然而當前鄉村美育主體的內生性和自發性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甚至遭遇主體性危機。
首先,鄉村美育的多重主體帶來主體性危機。從美育誕生之初,藝術便是其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美育不完全是藝術,但藝術天然屬于美育的內容,因此,藝術介入鄉村行動既是鄉村文化振興和美麗鄉村建設的重要渠道,也是鄉村美育的重要舉措之一。但這些轟轟烈烈的藝術行動卻并不都是成功的。藝術介入涉及藝術家、村民、鄉村管理者等多重主體,藝術家希望能在藝術鄉建活動中體現自己的藝術主張、尋找內心“遺失的鄉愁”,鄉村管理者則希望通過藝術鄉建活動拉動鄉村經濟活力、提升治理效果,而村民則希望能夠進一步增加收入、改變生活現狀。因此,藝術鄉建的多重主體之間出現“相互拉扯、掙扎、妥協、合作的關系”[13],這種多重主體間的張力或者“主體間性”沖淡和弱化了村民作為鄉村建設主體的地位。當鄉村文化成為市場商品,鄉村本身成為外來審美元素的容器而不是鄉村審美元素的生產和創造主體時,其主體性也就不復存在。
其次,“他者”視角造成鄉村美育的主體性危機。實際上,已經有學者對“藝術介入”一詞提出異議,認為“介入”本身含有“外來者”的含義[23],更多的學者傾向使用“藝術鄉建”一詞,以弱化藝術介入的強硬入侵感。鄉村美育的實踐邏輯建立在鄉村日常生活實踐中,美育的審美要素也應來自鄉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以外來者的眼光和審美展開行動。許村計劃的主要策劃人和實施者渠巖在訪談中談到,藝術介入鄉村行動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取得村民的信任與參與,其實這就是對鄉村美育主體性的尊重和確認。與藝術介入存有同樣“他者”視角的還有實施了多年的送文化下鄉行動。許多農村書屋中的書閑置無人翻閱、電影下鄉無人觀看,其原因在于對鄉村的“他者視角的想象”和將其視為“被拯救、被教化”的對象[24],而鄉村美育真正主體的自身訴求卻被忽略了。
(二)鄉村美育的價值弱化
在我國的文化語境中,審美從來都是飽含價值引導的思想活動。所謂“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26],“樂”與“和”之間、“禮”與“節”之間,便體現出我國古代社會的審美教化與價值引導。托尼·本尼特從文化治理的角度說,“給藝術設計一種手段連接外部世界,從而使其可以有效地作用于世界”[4]481,這里的“作用于世界”也充分說明了藝術審美活動的社會價值功能。當下我國鄉村美育面臨的正是審美價值弱化的困境。
一是內部審美文化根脈的價值萎縮。鄉村以一個天然共同體的形式,蘊含了我國鄉土社會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的獨特文化[6]。家庭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倫理審美更是我國鄉村社會倫理審美價值體系的基礎,鄉村普通家庭的生存日常與生活空間、鄉村社會民間生活的本真狀態等,提供了來自哲學意義上的“日常生活”的審美維度。這種文化審美價值從家庭倫理審美活動中外溢和輻射,從而促進村莊日常生活的倫理化[1]。因此本文認為,家庭倫理審美價值是個體內部審美文化根脈的土壤。但當下鄉村社會由于青壯年階層流失而造成嚴重空心化,破壞了家庭日常倫理美育實踐,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的家庭日常組織模式,使家庭倫理行動實踐基礎減弱,以血緣和地緣形成的鄉村日常文化生產實踐也逐漸衰退,導致關于個體、家庭和宗族之間的文化記憶和審美符號被淡化,個體內部的審美文化根脈的價值遭遇萎縮。
二是外部審美活動的價值減弱。從文化治理的角度,傳統鄉村中的天地祭祀、宗祠祭祖、節日慶祝等民間藝術活動和象征儀式,以其特有的藝術展現形式和精神感化力量,成為保障傳統鄉村社會生存繁衍和社會穩定的倫理價值秩序。這些傳統的美育活動中,既有生命支撐價值、審美價值、宗教象征價值,也有娛樂價值、經濟價值,鄉村社會發展所需的民間倫理、價值觀念、生活邏輯和社會基礎規范秩序都蘊含在這些審美元素中。鄉村社會結構中傳統文化活動組織體制機制的弱化和生活節奏的加快,使許多傳統文化事項的美育價值也開始減弱,有的因其具有經濟價值和旅游價值而被市場不斷單一強化,有的則因為考慮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被弱化。但不論是強化還是弱化,都存在忽略文化事項背后的鄉土習俗、禮儀制度、層級秩序、社會結構、情感鏈條等問題,破壞了其原本的意義和張力,使其作為審美活動的價值被減弱。
(三)鄉村美育的碎片化實踐
理想的鄉村美育是由村民個體的審美意識、審美能力,以及鄉村社會的審美文化、審美空間等共同構建的系統的、整體的審美文化生態圈。但由于鄉村文化區隔、社會分化以及農村非組織化等的影響,形成了當下鄉村美育的碎片化審美實踐。
首先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中美育實踐的碎片化。一直以來,我國針對鄉村開展了多項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如圖書下鄉、農村電影放映工程、家電下鄉等等,力求豐富鄉村文化和美育內容和形式。尤其農家書屋和文化禮堂等文化空間的建設,其初衷是既帶動鄉村群眾的文化提升,又豐富鄉村文化景觀,但實際情況卻是這些公共文化服務措施大多遭到冷遇,農家書屋書沒人看、文化禮堂成為麻將館[24]。這種“頭痛醫頭”的散點式美育實踐策略,既沒有充分回應村民的文化生活實踐需求,也沒有契合鄉村生活實踐,最終無法形成完整的鄉村美育生態鏈。
其次,市場化導致鄉村美育實踐活動的碎片化提取。傳統的鄉村文化活動根植于鄉村社會實踐,目的是滿足鄉村日常生活需要。但當鄉村文化按照市場規律尋求產業化道路時,卻需要按照市場喜好對鄉村文化活動進行各類元素提取和舍棄,許多鄉村旅游的文化體驗項目都是從趣味性和代表性的角度呈現出碎片化的文化側面,從而破壞了其中原有的審美價值鏈條和審美文化張力。
再次,媒介技術導致鄉村審美趣味的個人化和碎片化。2022年2月25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正式發布了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2.84億,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7.6%[25]。媒介信息的易獲得以及媒介技術的平民化,使村民按照個人審美興趣選擇文化內容成為可能,將審美文化內容進一步個人化和碎片化,從而形成個體之間的文化區隔,也使得鄉村美育公共文化的生產和創新面臨新的挑戰。最后,農村非組織化的分化格局導致鄉村審美精神分化。當下部分鄉村由于鄉村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其基層組織的整合能力非常薄弱,這種鄉村社會凝聚力的喪失讓村民抵御外界風險能力變弱,同時也使其精神變得貧困[21],在文化審美活動中各自為政,很難從公共美育的角度形成具有整體特色和獨特地域風格的審美文化。
(四)鄉村美育的現代性沖擊
從社會發展實際來看,我國與世界大范圍的人類社會發展轉型階段步調并不完全一致。法國哲學家利奧塔認為,隨著20世紀50年代末期知識經濟和大眾文化的崛起,世界上許多社會已經進入后工業時代,許多文化進入后現代時期[27]。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呈現出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等經濟社會文化現象同時并存的現狀[28]。我國鄉村的情況則更為復雜:現代社會的科學、理性精神與農村封建文化之間的對抗,大眾文化、網絡文化、消費文化等潮流對鄉村文化形成的沖擊,以及后現代社會對創造本性及和諧共生的追求等等,都對鄉村美育實踐提出新的挑戰,形成新的審美語境。
一方面是鄉村社會多元價值觀的形成。正如德國現代社會理論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所說,現代社會對傳統社會的“祛魅”和權威消解形成了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但同時也導致了多種價值觀間的“諸神之爭”[29],這是當代中國社會無論城市鄉村都正經歷的社會背景。如前文論述,我國鄉村社會結構變遷導致家庭倫理和鄉村社會秩序的變遷以及鄉村權威的消解,傳統鄉村的價值體系正逐漸走向解體。如何引導轉型期的鄉村社會形成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價值體系,是當代鄉村美育和鄉村文化治理面臨的實際問題。
另一方面是現代消費文化對鄉村審美的沖擊。波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告誡我們,消費時代需要警惕一種“商品被文化”的陷阱,即我們以為自己在享受文化,但其實卻陷入了符號的消費泥淖[30]。在鄉村社會陷入現代消費文化的同時,還面臨日常生活的審美轉向以及大眾文化的娛樂狂歡。三者的結合對鄉村審美文化形成巨大沖擊,使鄉村審美習慣和審美范式出現對城市文化的盲目追捧和對符號消費的跟風。當前鄉村社會中對住房、汽車以及各種生活儀式排場的追求愈加泛濫:登上網絡熱搜的福建農村歐洲城堡式住房建筑,被網友驚嘆有錢攀比的背后卻是福建傳統民居建筑文化的消逝;紅白喜事中不顧傳統民俗和情感,強行加入不合時宜的流行文化元素等等。由鄉村符號消費帶來的文化虛假繁榮反而導致鄉村文化的荒漠化。鄉村美育將面臨對抗大眾媒介時代的娛樂狂歡現象、擺脫消費文化的物欲裹挾等多重困境和挑戰。
四、文化治理下的鄉村美育發展實現路徑
從文化治理的視角觀照鄉村美育的發展,應以系統化和整體化的思維對鄉村美育的主體成長、價值提升、空間構建、產業發展以及體制機制等方面進行探索,力圖形成一個良性發展的鄉村美育文化生態圈。
(一)以美化人,培育鄉村文化主體成長
無論是鄉村文化振興戰略,還是鄉村文化治理策略,以及本文主要論述的鄉村美育行動,雖然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都涉及村民、政府以及外來的社會和市場力量等多個參與者,但其最根本最核心的目標仍然是通過這些文化行動推動鄉村社會發展、滿足村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村民仍然是鄉村文化與鄉村美育的核心主體。要讓村民能夠用審美的態度對待生活、社會、他人、自身以及自然,其個體審美素質的提高是鄉村美育的關鍵。一方面是主體審美意識的形成。審美意識是指村民對美的主動的、自發的追求。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莊嚴宣告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推進鄉村振興的道路上,要讓對美好家園和美好生活的建設成為村民社會生活的自覺,引導村民對原來鄉村文化中的愚昧、落后現象予以摒棄,自覺尋求符合時代發展的美的思想、美的事物以及美的行為,自覺尋求所在鄉村傳統文化中美的元素并發揚光大。另一方面是主體審美創造力的培育。美育本身即是一種審美創造力的培育,強調了主體自發涌現的對美的創造欲望和動力以及自覺的創新意識。鄉村美育應注重激活村民的文化創新創造活力,以此豐富村民的個體文化生命;培育和保護村民審美創造的直覺性,以保證美育行動擁有土生土長的鄉土元素,而不是遠離鄉土實踐的空中樓閣;注重發展村民的審美獨創性,以此抵御消費社會“跟風”式審美,也將為鄉村文化治理提供重要文化理念支持。
(二)以美聚神,提升鄉村文化價值引領
進入新時代以來,“弘揚中華美育精神”成為我國美育建設的重大時代命題。鄉村美育應以多種形式、方法和手段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三者融入鄉村美育實踐中,開闊鄉村審美視野并促進審美思想的解放,力圖在鄉村文化振興中以美聚神,實現美育的價值引領作用。傳承中華民族幾千年農耕文明中特有的審美情趣和生活理想,提取“禮樂教化”“耕讀傳家”“天人合一”等傳統精神文化中的審美元素;踐行革命文化中堅韌不拔、艱苦奮斗、舍我成仁等不屈奮斗的精神;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鮮明的科學精神和時代精神,用科學的、前瞻的、實踐的眼光發展鄉村美育。培養高尚的審美趣味,摒棄愚昧、低俗,用崇高、偉大以及理想、榮譽等具有高尚意義的價值觀念作為鄉村美育的價值追求,通過文化藝術作品、文藝演出、文化活動組織等行動促成價值觀念的內化,促進鄉村精神文明的建構,使鄉村建設主體能夠形成中華美育精神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自覺抵御全球化、市場化、娛樂化對個體審美造成的強烈沖擊,提高鄉村建設主體的審美素養、陶冶高尚的審美情操、塑造高尚的審美趣味。
(三)以美建新,注重鄉村美育場域打造
傳統的美育場域既是承載美育實施的物理空間載體,也是一種外在的、有形的美育內容資源。新時代的鄉村美育場域則應該力圖超越單一的物理空間場域打造,追求社會與自然、生產生活方式與社會組織、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現實與虛擬等多元一體、相互作用的完整審美生態系統構建。已有的一些農家書屋、鄉村文化館等設施沒有發揮其作用,最大的原因是不接地氣,遠離了鄉村文化生活實踐,本文認為鄉村美育場域打造關鍵在于立足“在地”與“本土”。首先,是結合鄉村原有的文物古跡、宗祠建筑、傳統村落布局以及各類農業遺跡等進行美育文化空間的設計和打造,以空間建設承載文化生產;其次,是充分結合當下的鄉村生活實踐,在日常生活中進行鄉村美育空間場域構建,既體現其實用功能的有效性,又凸顯其審美性。例如在新農村的舊房改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行動中加入傳統審美元素,讓村民在日復一日的鄉村生活中受到美育的滋養和浸潤。再次,應注重自然生態美育,將生態環境保護作為鄉村美育物理場域構建的重要原則。自然哲學家羅爾斯頓說:“我們的人性并非在我們自身內部,而是在于我們與世界的對話中。”[31]要用綠水青山、天人合一的自然審美理念指導鄉村建設中的自然改造,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榮共生的美育生態場域。最后,充分利用現代媒介技術,完成傳統鄉村美育元素的數字轉化,例如制作傳統藝術和文化遺產的數字化展示、講解甚至數字再造小游戲等,形成線上與線下、虛擬與現實相結合的美育場域。
(四)以美賦能,促進鄉村文化產業創新
在鄉村文化治理過程中,通過鄉村美育激發鄉村文化產業活力、促進產業創新是促進鄉村社會良性發展的重要舉措。一是利用美育元素促進鄉村傳統文化產業的現代創新。例如農村手工藝產業的發展,應在依托傳統手工藝技術的基礎上,廣泛關注和吸收當代的社會流行審美元素,形成傳統手工藝的“內核+現代”審美外觀的模式,豐富制作題材和品種,以適應現代市場需求,也推動傳統文化藝術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二是應充分利用獨特的在地審美元素形成品牌,增加產品的文化和情感附加值,進一步拓展鄉村農產品和文化工藝產品等的銷售渠道,從而促進產業發展。嗶哩嗶哩網站UP主李子柒便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她以短視頻的方式充分展現鄉村生活的田園詩意和古樸自然,契合了現代人對我國鄉村生活的美好想象,從而推動自有品牌的產業發展,有數據顯示李子柒品牌相關產品在2020年的銷售額已達16億元[32]。三是鄉村美育促進鄉村旅游業的發展。旅游產業規劃本身便是一項大的產業布局,鄉村美育的發展既有助于硬性的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也有助于軟性的在地文化推廣。在審美眼光的指導下提取和發揚鄉村社會獨特的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充分利用當地的歷史、人文和自然景觀,注重因地制宜,走一條生態的、文化的鄉村旅游產業發展之路。
(五)以美促治,重塑鄉村文化治理格局
鄉村美育是鄉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內容,應通過審美活動塑造主體的文化規范以達到審美治理的作用。首先,鄉村社會日常生活結構是鄉村美育實踐的基本框架,要將鄉村美育內容納入鄉村均衡文化內容體系的構建,以美的意識、美的精神和美的行為串聯起鄉村社會的風土人情、傳統文化、歷史底蘊和特色產業,強調文化內容建構中審美性、倫理性、公共性和實用性的統一,形成均衡的鄉村文化內容體系,促進鄉村社會的文化秩序重建。其次,要構建鄉村美育共同體,鄉村美育涉及各級政府、村民、各類文化藝術民間組織以及企業等主體,政府應充分發揮行政治理作用,鼓勵和引導民間社會力量和企業參與到鄉村美育的內容和場域建構中來,同時充分調動村民的主體內生動力和審美自覺,對市場行為進行有效監管,協調各方在鄉村美育實踐中的融合。最后,是健全鄉村美育的體制機制,政府部門應依據鄉村本地實際做好鄉村美育實踐的總體規劃,將審美治理統籌進鄉村產業振興、文化振興和生態振興的各項規劃布局中,探索形成行政引導約束監管、社會充分參與及村民自覺自治的三位一體的審美文化治理格局,以促進鄉村美育的制度化和規范化。
參考文獻
[1] ?杜鵬.轉型期鄉村文化治理的行動邏輯[J].求實,2021(2):79-97+112.
[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EB/OL].[2022-02-22].http://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
[3] ?光明網.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EB/OL].[2020-09-18].https://news.gmw.cn/2020-09/18/lontent_34197905.htm.
[4] ?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與社會——托尼·本尼特自選集[M].王杰,強東紅,等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
[5] ?張海榮.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文化治理的邏輯演進[J].人民論壇,2021(10):72-75.
[6] ?文豐安.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推進之理性審視[J].重慶社會科學,2018(4):16-24.
[7] ?胡惠林.鄉村文化治理:鄉村振興中的治理文明變革[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10):62-75.
[8] ?孔新苗.再論美育的兩個維度:人文理想與文化治理[J].美育學刊,2016(6):5-9.
[9] ?錢曉芳.談美育實踐與文化發展的關系[J].新美術,2019(3):114-118.
[10] ?杜衛.美育三義[J].文藝研究,2016(11):9-21.
[11] ?沃爾夫岡·韋爾施.重構美學[M].陸揚,張巖冰,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110.
[12] ?鄧小南,渠敬東,渠巖,等.當代鄉村建設中的藝術實踐[J].學術研究,2016(10):51-78.
[13] ?劉姝曼.鄉村振興戰略下藝術鄉建的“多重主體性”——以“青田范式”為例[J].民族藝術,2020(6):135-143.
[14] ?榮潔,胡惠林.文明轉型與權力轉換:藝術集聚的文化空間再造[J].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21(4):136-143.
[15] ?張穎.異質與共生:日本當代藝術鄉建諸模式[J].民族藝術,2020(3):20-28+37.
[16] ?孫曉霞.對當代中國鄉村藝術活動的理論反思[J].文藝理論與批評,2013(6):115-118.
[17] ?李修建.方李莉:藝術鄉建的人類學視野、方法與觀念[J].美術觀察,2019(1):18-21.
[18] ?孔新苗.“社會美育”三題:含義、實踐、功能[J].美術,2021(2):10-14.
[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20]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21] ?錢理群,劉鐵芳.鄉土中國與鄉村教育[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17.
[22] ?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第14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66.
[23] ?王孟圖.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藝術介入鄉村建設的再思考——基于福建屏南古村落發展實踐的啟示[J].民族藝術研究,2019(6):145-153.
[24] ?沙垚.鄉村文化傳播的內生性視角:“文化下鄉”的困境與出路[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6(6):20-24+30.
[25] ?十三經注疏(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530.
[26] ?CNNIC發布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2022-02-25)[2022-03-01].http://cnnic.cn/gywm/xwzx/rdxw/20172017_7086/202202/t20220225_71725.htm.
[27]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M].島子,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34.
[28] ?曾繁仁.美育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259.
[29] ?劉擎.西方現代思想講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21:36.
[30] ?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31] ?霍爾姆斯·羅爾斯頓Ⅲ.哲學走向荒野[M].劉耳,葉平,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11.
[32] ?字節跳動投資李子柒,“第一網紅”背后的豪華股東陣營曝光[EB/OL].(2021-07-05)[2022-03-01].https://new.qq.com/rain/a/20210705A0CCUE00.
Development of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value, dilemma and path
Hu Yang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means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has the value significance of stimulating the living ability of rural culture, realiz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inheriting national cultural genes.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s brought about the change of rural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order, leading to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facing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subjectivity crisi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weakening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fragment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and the impact of modernity.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overnance, the practice of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should cultivate the growth of rural cultural subjects, enhance the rural cultural value guidance,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field, promote rural cultural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reshape the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patter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culture governance ;cultur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