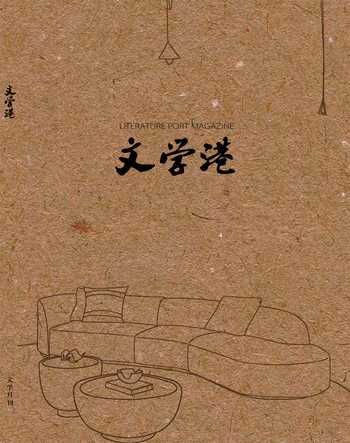墓畔回聲(外一題)
帕提古麗,筆名:帕蒂古麗,女,維吾爾族,中國作協(xié)會員,已出版散文集《跟羊兒分享的秘密》《混血的村莊》《思念的重量》《水乳交融的村莊秘境》《模仿者的生活》《蘊情的土地》。散文《模仿者的生活》獲2012年度《民族文學(xué)》獎,2012年度最佳華文散文獎,2012年度在場主義散文獎新銳獎,散文《思念的重量》獲全國散文大賽一等獎。散文《被語言爭奪的舌頭》獲得2014年度人民文學(xué)獎。
長篇小說《柯卡之戀》獲得北京市優(yōu)秀出版物獎,長篇小說《百年血脈》獲得“第六屆中華優(yōu)秀出版物獎提名獎”、“第三屆向全國推薦百種優(yōu)秀民族圖書”、北京市優(yōu)秀長篇小說獎,并被中譯出版社翻譯成英文出版發(fā)行。
在山東德州北郊北營村,仲春的晨光灑在蘇祿國東王墓高大的墳堆上,墳土刨得很松,幾株小草正從蓬松的黃土里探出綠芽。同行者在墓地的圍墻外急急地喊:
“走,我們該回去了!”
這句話的回聲在墓地四周撞擊。我驀然發(fā)現(xiàn)自己繞著水泥護(hù)圍和墓地磚墻恰巧踱出一個“回”。來墓地的每個人,都有意無意間用腳步在墓地周圍回旋轉(zhuǎn)繞。
“回”字中間躺著的是蘇祿王。惶惑間,我一時難以分清,這個“回”究竟是在喚我回去,還是在喚地下的蘇祿王回去。我第一次驚心于這個平平常常的“回”,內(nèi)心有一種倏然的警醒。
明朝永樂十五年(1417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巴哈剌與西王、峒王,率340人的大型使團(tuán)訪問中國,那年蘇祿三位王爺在北京愉快地逗留了二十余天,受到朱棣皇帝的盛情款待。使團(tuán)離京后,乘船沿京杭大運河南下回國,到達(dá)德州時,東王突患急癥,1417年9 月13日殞歿于德州以北安陵鎮(zhèn)驛館。
蘇祿國東王長眠德州,他枕著運河的堤岸,聽著黃河的水聲,不管溫度和濕度是否適宜,這里成了他永世的歸宿。
東王下葬后,其長子都馬含隨西王、峒王等人回國繼承王位,王妃葛木寧、次子溫哈剌(塔拉)(譯音)、三子安都魯及侍從十余人則留在德州守墓三年。永樂二十二年(1424 年),明朝政府派人護(hù)送王妃葛木寧回國,王妃葛木寧眷戀東王,次年她再次返回德州,從此再未離開,與兩位王子長期留居德州,直到去世。
現(xiàn)蘇祿王墓東南側(cè),有三個比王墓略小的土堆,便是王妃葛木寧及東王次子溫哈剌(塔拉)、三子安都魯之墓。這個村子里的很多居民,應(yīng)該就是他們的后代。蘇祿國東王墓不是中國唯一的外國國王陵墓,卻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帶有守陵村落的異邦王陵。
蘇祿國東王的葬身之地最早并無村落,居民除王妃、王子及侍從十余人外,就是明王朝從山東歷城遷來的三戶回民: 馬丑斯、陳咬柱、夏乃馬。因蘇祿國習(xí)俗與回族相似,由三戶回民負(fù)責(zé)王墓祭祀、耕種祭田及家務(wù)雜役,所有人同住墓側(cè)。
大約在萬歷至天啟年間(1573—1627 年),在東王墓西南立清真寺一座,于安、溫兩姓中各選掌教一人,負(fù)責(zé)宗教事務(wù)。每逢回教大典,掌教率領(lǐng)安、溫全體族人誦經(jīng)祭墓,成為定例。雖然生活習(xí)俗與當(dāng)?shù)厝私咏诩漓霒|王時,后裔還是按照伊斯蘭教習(xí)俗紀(jì)念,并沒有仿效當(dāng)?shù)氐募漓雰x式。
墓畔長滿守墓者的后人
故國王土,變成不可企及之地,彌留之際,東王對陪自己同去京城、同奔?xì)w途的蘇祿王子說的,少不了這一個“回”字。不能回去的父王,只有以王子回去的形式,完成自己回去的心愿。上一代回鄉(xiāng)的意愿,可以讓下一代承接完成,血脈就像一條河流,哪怕一條分支到達(dá)了源頭,也代表這根血脈的回歸。只是回憶起這一段失去了父親的路途,不知道這位王子回國后,會在怎樣的思念和祈禱中度過一生。
按照大明禮制,守孝三年期滿后,王子等守墓人員都可以歸國,但他們放棄了。東王的第八世孫蘇祿國王通述,請求清朝廷將德州守墓人員的后裔入籍中華。后經(jīng)朝廷禮部查明,準(zhǔn)予入籍。東王后裔正式“以溫、安為姓入籍德州”,成為清朝編戶齊民,并逐漸融入回族,結(jié)束了“客居”身份。史料記載,兩位王子和仆人隨從學(xué)會了當(dāng)?shù)卦挘钭兊酶轮萑撕芟嘞瘢?dāng)?shù)厝艘矊晌粸楦甘匦⒌耐鈬踝泳粗赜屑印?/p>
德州當(dāng)?shù)氐募易逦幕饾u影響著這個新興的王室家族。安、溫家族的孩童在清真寺接受伊斯蘭教基礎(chǔ)普及教育后,也學(xué)習(xí)漢字以及《三字經(jīng)》《百家姓》等。家族中出了十幾位秀才,清初,溫泮還成為家族第一位舉人,官至廣東按察司知事。溫憲則通過科舉入仕,累官至知府、道臺。民國時期,安、溫家族還在西北軍中出了一位“不侍二主”的名將安樹德。
東王后裔迄今已傳至第21代。今天的北營村已經(jīng)擁有七百多戶居民,其中安、溫兩姓占到四成以上,余下的以馬、劉姓居多。全村光屠宰戶就占了八成,并以溫姓最多。據(jù)當(dāng)?shù)厝私榻B,從古至今,安、溫兩氏修建的房子都分布在王墓的周圍,表現(xiàn)了一種對先祖的尊敬。
本是些回不去的人,卻成了回族,這幾近語言學(xué)意義上的一個悖論。東王的隨從及其后人,在墓畔堅守,回去的想法,最終也只凝固在他們作為“回族”的命名里,如今他們與當(dāng)?shù)氐拿褡迦跒橐惑w。新中國成立前只允許族內(nèi)通婚,如今隨著觀念開放,越來越多的王室后裔去外省發(fā)展,通婚不再只限于族內(nèi)。
在北營村蘇祿王御園里,遇到作為管理員的“80后”王室后裔安靜。她笑著說,這里的王族后裔,早已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了,沒有王族的感受,也沒有總想著那塊重洋遠(yuǎn)隔的“故土”,現(xiàn)在因守墓而發(fā)展起來的北營村,每家每戶都可以用“安靜”兩個字來形容。
近些年,菲律賓蘇祿王王室后裔訪華祭祖越發(fā)頻繁,北營村的安、溫家族也有更多機(jī)會聽到來自家鄉(xiāng)的聲音。菲律賓的親人們來祭奠蘇祿東王墓的照片,掛滿了蘇祿東王墓旁展覽廳的墻面,人們坐在墓的周圍誦經(jīng),說著早已遺忘了的從前,久遠(yuǎn)的歲月匯聚在墓前,他們與先祖在墓地旁完成了隔世的團(tuán)聚。
看著眼前這一切,心中莫名地哀婉。我懷疑自己對“回”字的破譯,只是一己的想象。面對偶然的文化轉(zhuǎn)向,蘇祿東王后人和隨從,他們當(dāng)時是哀婉嘆息,還是一心如鐵扎根他鄉(xiāng),選擇在異地上崛起和重建?
人類在大的文化轉(zhuǎn)向面前,難以平衡自己,往往是太在乎失去的東西。沒人能將失卻忽略不計而去論得到。面對失卻,應(yīng)有哀婉。哀婉也許能讓人得到一種精神安慰和心理上的滿足,卻無法彌補和挽回巨大的失去。有時候,在突如其來的生存環(huán)境大轉(zhuǎn)換之際,只怕連哀婉和嘆息都來不及。
有故鄉(xiāng)而不能抵達(dá),蘇祿東王被埋葬在一個大大的“回”字中間。穿過久遠(yuǎn)的時間向后看,歷史上一批把自己模仿成當(dāng)?shù)鼗孛竦姆坡少e人,他們身上幾乎濃縮了外來者在另一方土地上生命漸漸演進(jìn)的過程。
墓地周圍古老的松柏,像是一個個隱喻。逝者,可以以一座墓的形式落地生根,守望回不去的故國家園;生者,也可以像樹一樣移植異國他鄉(xiāng),守望一座經(jīng)世之墓。一眼望去,墓葬周圍,谷子一樣一茬一茬長滿了守墓者的后人。
生活在另一塊土地上重新打開
在蘇祿東王的墓地,我突然覺得漢字的“問”字與“回”字是這么形似,“回”字是被包圍的,“問”字像是打開了一堵圍墻和一側(cè)的門鎖。走向墓地一側(cè)的門,我仿佛從“回”字,走到了“問”字。
墓中的蘇祿東王似乎在對我言語:回不去了,就像我一樣,躺在陌生的土地上,曬曬異鄉(xiāng)的太陽。像丟掉累人的行囊一樣,丟下屬于你的一切,學(xué)習(xí)當(dāng)?shù)厝说纳睿屪訉O后代在另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身為王者尚且如此,何況普天之下的蒼生呢?
蘇祿東王及其隨從的后人,是一群特殊的回族,他們從自己的文化偶然闖入了別人的文化。在六百年的歲月磨損里,他們漸漸褪掉了身上所有菲律賓人的印記,隨著一代代與當(dāng)?shù)鼐用竦娜诤希麄兊墓?jié)日,他們的服飾,甚至他們的長相,都完全回族化了。這個墓地里,沒有任何能代表蘇祿國的文字,東王亡故后,留下的守墓者和他們的后人,漸漸扔掉了原有的文化,他們的語言、他們的習(xí)俗都已湮滅。
當(dāng)一個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被埋在這片土地上的時候,根似乎被無聲地挪移了,墓地成了他們永遠(yuǎn)的故鄉(xiāng),生活在另一塊土地上重新打開。他們完全融進(jìn)了這片土地,他們頑強(qiáng)地生存下來,在遼闊的齊魯大地上耕種、收獲,這片寬厚而蘊情的土地喂養(yǎng)了他們。他們將清真寺建在墓旁,墓前還有皇帝題的墓碑,墓碑由一種龍頭、龜身、蛇尾的動物馱著,這種人間不存在的動物叫赑屃。
赑屃這種在漢文化傳說里具有神力的動物,沒能在活的時候馱著蘇祿東王漂洋過海,回到他遠(yuǎn)隔重洋的國度。在他死了以后的六百年里,赑屃馱著墓碑,高昂著頭,似乎一直在行進(jìn)中。它穿過層層的歲月,漂浮在時間的河流之上。這讓人想起這位菲律賓的王,從大運河坐著船一路自京城漂流下來的路程。這塊墓碑將一直被這只不知疲倦的赑屃馱著遠(yuǎn)行,從他鄉(xiāng)永遠(yuǎn)地往回走,一直走到時間的盡頭。
幸好還有一個“回”字可守
大地上的人們在不斷地遷徙,每個人的命運都在無奈地搬遷和無奈地挪移中變幻莫測。很多情形下,也許我們能夠堅守的就是一個親人的墓,甚至有時候,連親人的墓都被我們拋到了千里之外。瞬息萬變中,我們不知道會在哪一刻喪失家園、喪失語言、喪失文化、喪失生命的原點和能量。
從大地的這一頭遷徙到那一頭,尊貴為王者,尚且命運難卜,半途葬身,難以料想我們的墓,最終會修在哪一段來路和去途中,甚至將來世界的某一處,會不會有一座為我們預(yù)備的墓,用來掩埋我們的遺骨。如果我們有碑,碑上會刻什么樣的痕跡,來講述我們在接連不斷的失卻中完結(jié)的一生。
我們從世界的這一處行往那一處,不知道會碰上什么樣的風(fēng)浪,遭遇什么樣的險阻,然后就會徹底地改變我們回歸的方向。我們會在哪里安身,會守住一個什么樣的根?我們會在途中遺落什么?我們又能夠堅守住一些什么?
命運這個聽起來那么厚重的詞語,在一場偶然面前,竟然顯得那么輕、那么薄。甚至不需要戰(zhàn)爭,不需要瘟疫。蘇祿東王路途中的一場風(fēng)寒,就足以使他的后裔命運轉(zhuǎn)向、民族變更、文化盡失。這一群喪失了一切的人,代代更迭,如果到了最后,連出發(fā)的原點和初心都已忘記,一旦根系枯死,就真的再也沒有還魂的可能了。幸好還有一個“回”字可守,只要守住了一部分,那一部分就成為種子和根,人就可以在那微小的一部分里存活著,繁衍生息。
蘇祿東王巨大的墓,以死亡的形式,向人們昭示著一種生,那是一個用一代代守護(hù)者的盼望澆灌的生,而這所有的生命的原動力,就是與墓地建筑形意相同的一個“回”字!他們的根系陰差陽錯地扎在了異國的土地上,回族這個身份和名稱于他們,儼然成為一種心愿的象征。六百年夢回,內(nèi)心還是聽從著墓畔響徹的“回”聲。
只要“回”這個愿望一息尚存,它就是有生命的一個字!這座墓也就是有生命象征意義的一座墓,因為它的盼望沒有死,它的守護(hù)者依然守護(hù)著與墓主人相同的盼望,雖然那盼望就如石碑上的刻痕,由于年代久遠(yuǎn),已經(jīng)變得模糊不清,而守望者以不變的初心守望一座墓的姿態(tài),已經(jīng)成為這個墓旁強(qiáng)大的文化注解。
關(guān)于根與歸根,關(guān)于歸人與過客,關(guān)于回去和現(xiàn)在,關(guān)于我們該回到哪里和我們能夠回到哪里,回不去以后,我們的生活最終會變成怎樣,蘇祿王的墓,將關(guān)于文化的宿命昭示世人。
現(xiàn)在,一切靜靜地化為一座墓的形象,回到歷史深處。蘇祿東王的隨從和后人們,六百年來化作大大小小的墳?zāi)梗谶M(jìn)腳下的泥土。他們活著的子孫,有的生活在墓地周圍,有的從墓地周圍遷徙四散,扎根別處,這些外來者不外乎這樣兩種宿命。
在墓地門口,我看到一位賣鞋墊的中年女人和一位賣茶葉蛋的老年婦女,她們用當(dāng)?shù)乜谝暨汉戎D沟氐膰鷫Ω拢铱吹皆S多與泥土打交道的莊稼漢,我看不出他們是不是跟這座墓有關(guān)系。我問,你們知道這墓里是什么人嗎?
一個農(nóng)民模樣的中年男人回答:“我爺爺知道,聽他說是一個外國人,我們祖先守過這個墓。我們早就改種地了,現(xiàn)在這里是景點,不管墓里頭埋著啥人,時間過去太久了,跟我們也沒有啥關(guān)系了。”
守著守著,恐怕最后連守墓的人自己都忘記守的是誰了。
我看到有一家人聚集在墓地前的清真寺門口合影,一名年輕人推著輪椅,輪椅上坐著一個白胡子的老者,后面站著一對中年夫婦,男的戴著白帽子,女人頭上戴著蓋頭。
中年女人指著墓地旁邊的白房子說,她的家過去就在墓地附近,她的祖先就是守這座墓的。他們從很遠(yuǎn)的地方回來,為的是帶孩子來看看自己的根。言語間,他們已把這里當(dāng)成了自己的根。我看著那一家人推著輪椅上的老者進(jìn)了清真寺的門。對于外來客漂泊的靈魂,也許只有他們認(rèn)同這里是他們的根,才不至于在漂泊的命運中遺失自己。
回去可一定要趁早啊
這世界上,還有很多像蘇祿東王的后人和隨從一樣的人,雖然沒有把“回”字寫在他們民族的命名里,但作為回不到故鄉(xiāng)的人,他們到死念著一個“回”字。當(dāng)故土無法回歸,我們將何去何從?我突然擔(dān)心自己也像蘇祿東王一樣,成了一個走到半路回不去的人,我更害怕成為一半回去、另一半回不去的人。
從浙江支邊寧夏的我公公,死后躺進(jìn)寧夏河套平原的黃土里,他的眼睛到死也沒有閉上。他回不去了,跟他同祖籍的妻子守著他的墓,也回不去了。我能聽見他喊著一個無聲的“回”字。他沒有喊出來的那個字,是一曲無法唱出的歸鄉(xiāng)哀歌,只有我這個幾十年來跟他一樣患著嚴(yán)重的思鄉(xiāng)病的人能夠聽懂。
我的母親是回族,我不知道她曾祖父以上那些久遠(yuǎn)的歷史。我至少知道在半個多世紀(jì)前,黃眼珠、棕紅胡子的回族太外公帶著我漢族的外公、回族的外婆和后來成為我母親的那個人,從甘肅天水張家川逃荒出來,到了新疆的北疆以后,就再也沒有回去過。饑餓相逼,活命成了第一法則,整個家族倉皇遷徙,故園反而成為一個亟待逃離的噩夢。直到晚年,回去道別或走墳故園,才開始成為他們生命里生長出來的迫切念想,而漫長的歲月中,念想延伸的根或慢慢枯干,或被無常的命運斬斷。他們那幾代人直到死去,沒有任何一個再返回過故鄉(xiāng)。
帶著一半的回族血統(tǒng),現(xiàn)在生活在江南的我,一直想去母血的源頭,認(rèn)領(lǐng)我的另一個故鄉(xiāng)。我沿著來路一代代上溯,順著原初的根脈去探看,去撫摸,我不知道這樣做,算不算替他們回去。
我身體內(nèi)的另一半維吾爾族的血脈,渴望著與父親的血脈靠近。父親在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初,從喀什來到了北疆,直到生命終結(jié),也沒有再回過自己的故鄉(xiāng)。父親的墓就在離村莊不遠(yuǎn)的地方,我?guī)е氐礁赣H身邊一樣的喜悅,在我的出生地老沙灣大梁坡蓋了房子。衰老來臨之前,我要做好一切回歸的準(zhǔn)備,這算不算另一種形式的守墓?墓地是我生命的原點,也會是我生命的終點,我只是一直流浪在路上的那一個,一直游動在兩者之間。我們不想成為既不能到達(dá),也無法返回的那一個。我的還鄉(xiāng),就是返回對生命原點的無限接近中。
現(xiàn)在我是另一塊土地上的那個我,我精通寧波這個地方的方言,那是我父親認(rèn)為世上最難懂的語言。我諳熟南方人的生活習(xí)性,依照他們的習(xí)慣行事,除了盡最大的努力遵循能遵循的傳統(tǒng)規(guī)則,我按這里的生活方式生活。每天走在路上一片悵惘,腳下的青石板上的苔蘚,都擺出一副不認(rèn)識我的吃驚模樣,仿佛提醒我,為何煞有介事地錯踏在南方的青苔上。
我半邊腦子在想,死后也許我會葬在寧波東錢湖畔的穆斯林公墓,或許我會滿世界走,最終連自己也找不到自己;半邊腦子又在想,我要在死去之前,回到生養(yǎng)我的大梁坡,好在死后把自己埋進(jìn)那片鹽堿灘,去暖一暖父親冰冷的白骨。人們還能從我雙眼里看出什么?一只寫著南方,一只寫著北方嗎?抑或是一種分裂?站在生活一側(cè)旁觀的那個北方的我,猜不透生活在南方的我在想什么,就像我一半的血脈,猜不透我另一半的血脈。
我要尋回父親的血脈,母親的子宮。我要在所有孕育過他們的地方重新誕生一遍,重新掩埋一遍,重新復(fù)活一遍,活成我應(yīng)該活成的樣子。一年一次親近新疆那塊熟悉的土地,成了我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回去可一定要趁早啊,晚了,途中被什么事情一耽擱,恐怕連喊一聲“回”字都要啞了,就像那個客死異國他鄉(xiāng)的蘇祿王一樣。蘇祿王患病他鄉(xiāng)時,回不去了的醒悟是那么可怕!
看到我彌留他鄉(xiāng)的樣子。
我努力使自己在蘇祿王墳?zāi)古孕阎碾S從和后人們六百年來在他墓畔演繹的,是另一方水土上的生生不息。突如其來的死亡,讓他眼前的一切變得黑暗,他只能抗拒著走向生命的終點。遇到這客死的王陵,似乎遇到了一個可以讓我入戲的角色,一段為我而寫的獨白。我恨不能借這座墓冢,伴著他鄉(xiāng)的墓畔哀歌,美美地哭上一回。
從遇見這座墓的那一刻起,內(nèi)心的不安感和安慰感,就化成兩股繩索,向兩個不同的方向拉扯我的心。不安,是看見墓里面那些別人看不見的東西,安慰是因為幾十年來懷鄉(xiāng)的情感,暫時借助一個客死他鄉(xiāng)者的墳冢得以釋放。
在遇到這座墓之前,我的一些意識是沉睡著的,在這座墓旁,我遇見了另一個我。我的心猛然收緊,她原來一直在那里冷眼看著我在異鄉(xiāng)生活、想念和撕裂,只是我平時一直故意沉浸、奔波在另一些事情當(dāng)中。她是能夠帶我回到原鄉(xiāng)的靈,我只是她在現(xiàn)實當(dāng)中的空殼。她很從容,時間、心跳和喘息,都因她的從容變得很緩慢。我就那樣看著她在墓旁踱步,繞著水泥護(hù)圍轉(zhuǎn)圈,踱出一個又一個“回”字。一些意識從我的心底新生出來,很強(qiáng)大,我無力制止,無法抗拒。
這座墓在恍惚中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多年后彌留他鄉(xiāng)的樣子。人是不是在惶惑中,才更容易接近和抵達(dá)自己?我突然想到,一個民族最終能留下的是什么?某個民族引以為榮的服裝,最終可能成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時裝秀,說明服飾肯定不是。許多人以為可能是語言,蘇祿王的后裔主動放棄了語言,說明他們意識到在與其他民族的融合中,語言可能會是障礙。而宗教信仰從文化學(xué)視野下屬于一種文化形態(tài),在社會學(xué)視野下宗教乃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那么最終能留下的可能就是一種精神氣 質(zhì)吧。
佇立蘇祿王墓畔,兩邊是蒼松翠柏、青柳白楊,我躬身撿起一片被風(fēng)吹落的葉子,撫摸上面的葉脈。蘇祿王,曾經(jīng)作為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存在,這里居住過蘇祿王的一個王妃和兩個王子,王族的血脈衍生出的枝丫也曾在這里延續(xù)。我沒法比對植物的葉脈與人的血脈到底有什么不同。六百年過去,蘇祿王的血脈從這里漸漸擴(kuò)散到越來越遠(yuǎn)的地方,消融在齊魯大地上,那些細(xì)若游絲的脈絡(luò),已經(jīng)融合在更大的群體中。
墓地的圍墻外,一幢接一幢守墓者和他們子孫的白房子,遠(yuǎn)看一片縞素,一重一重朝遠(yuǎn)處延展,像一個套一個的“回”字,似乎千萬張口在重復(fù)一個字:回!回!回!這個有形的聲音,以王的墓為原點,一層一層的回聲在五月的風(fēng)中回蕩,在空空的墓地上空像漣漪一般不斷回旋、擴(kuò)展,自近處的層樓和人群擴(kuò)散到遠(yuǎn)方,直到風(fēng)流云散,再也聽不到一絲回音……
七 日
第一日 死訊
那幾天我們正在籌錢買新房子,公公的死訊就在新年的前一天到來,似乎存心和誰過不去。買房的事只好先停下來,活人的事可以等等再說,新年的頭等大事變成了買墓地和棺材,籌辦喪事。
丈夫在電話里向居住在南方的親戚們傳播公公的死訊,像是在傳死者的壞話那般不自然,似乎心懷歉意又不得不傳,措辭中盛滿不知所措的恐慌。聽不到電話那頭的對答,只看到他說話的樣子十分古怪,全然不像是在說一件令他哀慟的事,倒像是在說一件令他尷尬的事。而且他用的不是很肯定的語氣,仿佛在傳播一條不怎么體面的小道消息,苦笑中還夾雜著對自己作為傳話者這一角色的懷疑和嘲弄。
電話那頭,親戚們正忙著給他奶奶過百天忌日,也許公公死亡時間與奶奶百天忌日巧合地撞上,令正在吃忌日飯的親戚們格外吃驚,他們在電話那頭的質(zhì)疑口氣,令丈夫也懷疑起自己父親該不該在這個時候死去。他的表情和語氣中夾雜著推卸責(zé)任的意味,好像不用這語氣說話,別人就會把公公死亡的責(zé)任推給他似的。
丈夫很快找到了辦法來抵抗這個令他恐懼的事實:集聚所有的親人,共赴中衛(wèi)老家奔喪。丈夫打電話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大,充滿自信和號召力,似乎親戚們?nèi)サ枚嘈芨淖児呀?jīng)死亡這個事實。我知道,他害怕,他需要給自己壯膽。
第二日 奔喪
每天不斷地接電話,深夜不眠地等電話,只為等一個確切的死訊,公公沒有咽氣,我們即使去了,還是要趕回來上班。聽著很殘酷,但事實就是這樣,我們?nèi)サ哪康乃坪鹾苊鞔_,就是去為他送葬。
站在公公的靈棚前,第一個念頭是懺悔,我奪了他們的兒子后,就把后面的歲月扔給了兩位離鄉(xiāng)背井的老人。借口有姐姐和弟弟在那邊,平時我們很少打電話過問父母晚年的生活,似乎他們都是鋼鑄鐵打的,不會生病,不會寂寞,不會鬧情緒,不會抱怨,不會想念。作為一兒一女的母親,我懂得,一個孩子的孝心,是另一個孩子無法替代的。正如此時我的愧疚,也是別人無法替代的。
若不是公公,我和丈夫恐怕不會走到現(xiàn)在。與丈夫戀愛時,他母親嫌我是異族,且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喜歡筆墨的公公知道我是個搞文字的,對兒子的眼光很滿意。
我相信平時陪伴和盡孝的機(jī)會多,對公公去世的內(nèi)疚和恐懼也就沒有那么深了。丈夫的恐懼或許來自沒能讓公公回鄉(xiāng)養(yǎng)老,也沒能在其身邊替他送終,巨大的內(nèi)疚在公公的死亡面前轉(zhuǎn)化成巨大的恐懼,讓他無法心安。
這種恐懼在他的夢里展露無遺。那天他在樓下臨時搭的靈棚里守了一夜的靈,天亮?xí)r才上樓休息。躺在公公病逝的那張單人床上,丈夫夢見公公伸手拍他的肩膀,他推搡過去,那只手又拉住他的胳臂不放,他在夢里向四叔呼救。
也許他的潛意識里,是四叔支持我們在南方扎根的,只有他可以向公公解釋和求情。在夢里四叔并不理他。當(dāng)他從夢里醒來,向四叔和眾親戚敘述完這個夢,大家都默然了。
四叔似乎并不介意公公的遺體在樓下停著,他在樓上高聲跟親戚們說笑:“老太太看二哥可憐,剛過了百天就叫二哥去陰間做伴了,二哥現(xiàn)在又來拉自己的大兒子。”
四叔兩口子也是年輕時雙雙去內(nèi)蒙古支邊的浙江余姚知青,后來回鄉(xiāng)安了家。言語間有著身在故鄉(xiāng)生死無憂的優(yōu)越感,雖說樂觀豁達(dá)的勁頭倒跟平常并無二致,在這個時候卻讓我感覺有些異樣。也許作為許家家族的力量核心,在眾人傷心時,四叔刻意擔(dān)當(dāng)了為大家寬心的角色。
無論四叔怎么寬心,暗地里我和丈夫都在擔(dān)心公公會責(zé)怪我們,沒能在余姚為他養(yǎng)老送終。雖然在中衛(wèi)也有一兒一女陪伴著他,他沒有正式要求過回余姚定居,可我知道他做過打算,想回老家陪老母親。
那年春節(jié),他到出生地慈溪天元鎮(zhèn)走親戚,回來跟我們說,天元的老房子收拾收拾還可以住人。我們只推說舊房子靠著臭水溝,夏天蚊子多,這話題就以環(huán)境惡化,小時候可以下去洗澡的小河變成了臭水溝為終結(jié)。公公還寫了一個關(guān)于治理臭水溝的建議,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公公跟我們說起這事的時候,丈夫也許沒往心里去,可我往心里去了。當(dāng)時剛到異鄉(xiāng)異地,生活中諸多不適應(yīng),對還鄉(xiāng)這個話題比較敏感,我格外能體會一個離鄉(xiāng)者的心緒。
當(dāng)時我和孩子還寄住在四叔家,丈夫在外面跑銷售,一家人尚無安身之處。后來我們買了套不大的二手房,公公和婆婆帶著小孫女來,都要住在附近的親戚家里。我們買了新房子后,公婆每次來帶著大姑子當(dāng)廚師,公公親自去菜場采購,恨不得把在中衛(wèi)吃不到的泥螺和小黃魚都買回來吃進(jìn)肚子里再回去。只是住不了多久,他們就牽掛著那邊的孫子,趕回中衛(wèi)去了。
在中衛(wèi)的七天,我們一大堆從南方過來奔喪的人都特別怕冷,整日躲在暖氣屋子里,只有大姑子跑上跑下忙著買菜做飯,下樓守靈,上樓招呼客人,感覺她在天上地界地跑。
零下二十?dāng)z氏度的氣溫,躺在靈棚里的人恐怕已經(jīng)凍得硬邦邦的了。下樓到靈棚里,點根香,凍得吸溜吸溜,被刺骨的寒風(fēng)逼到樓上,上來該吃的照吃,該喝的照喝,一頓也沒有省。
第三日 棺木
公公的去世,讓過去一直排斥參加異族死者葬禮的我,想起五十年前,我爹爹不避民族和宗教忌諱,在麥田里看守了一個自殺的漢族人的遺體三天三夜。我突然明白,死亡擺在那里,民族、政治、宗教甚至罪孽的概念頓時消亡了,唯有一具遺體橫亙在活人眼前。
從樓上看下去,小叔子從中寧運來的那口雕花柏木棺材,就像一艘船泊在院子里。也許不該用這樣的比喻,似乎將那口棺材比喻成船,就能使這個客死他鄉(xiāng)者的靈魂得到超度。死亡就是死亡,棺材就是棺材,不存在隱喻,它甚至連一個死亡的容器都算不上,超度只是活人隱秘的意愿。
看了中衛(wèi)的那塊陵墓,面積很大,沿途都是棗樹和蘋果樹,夏天應(yīng)該一路上都飄散著花香果香。墓是雙穴的,右邊的位置給婆婆留著。
無端地聯(lián)想到跟丈夫去看過的樣板房,從講價買房聯(lián)想到討價還價買墓地,從棺木裝飾無端地想到房屋裝修,從拱形的建筑裝飾想到墓碑,活人和死者的境況相差無幾,生與死的居所何其相似。
或許丈夫也有類似的感覺,他說,這次買了新房,他也不一定會住,他想回去陪母親和姐弟,他甚至心思迫切到想提前退休,我聽了只覺得茫然。他想了想又說,如果他退休了母親還在,他就回中衛(wèi)生活。
我知道,剩下寡母和離異多年的姐姐在家里,他放心不下。公公的去世,讓他覺得家里位置空了出來,等著他填補。或許潛意識里,他想替代公公這個缺失的角色。或許丈夫言下還隱含著想離躺進(jìn)異鄉(xiāng)黃土中的公公近一些的意味。
第四日 墓地
公公喜歡喝兩杯,他的每一盤下酒菜都是自己做的。幾位老鄉(xiāng)跟婆婆說,除了抽煙,家里做菜的人患肺癌的概率比較高,婆婆聽完大概,血壓瞬間升高了,臉紅得像蒙了塊紅布。
公公從西安做完手術(shù)回來后不久,病情就開始惡化,去世前兩個月,婆婆根本不敢去碰這個全身發(fā)黑、只剩下細(xì)長的幾根骨頭攤在被子里的丈夫,所有的護(hù)理工作由大姑子承擔(dān)。公公臨死前的一個月,婆婆干脆待在院門口的門衛(wèi)室里不上樓,夜里也睡在里面,說是替大姑子做門衛(wèi)。
大姑子說她在樓下忙完上來,看見公公眼睛圓睜著,摸摸人已經(jīng)涼了。她開始給公公穿衣服穿鞋,慌亂中她發(fā)現(xiàn)鞋子好像變得小了,費了很大勁都穿不進(jìn)去,她擔(dān)心公公有話要說,不肯穿了鞋子上路。
死的時候身邊一個人也沒有,自然是死不瞑目,靈堂里公公的眼睛圓睜著,小叔子使勁往下揉了揉眼皮,隨著他的手離開眼簾,公公的眼又睜開了。回來跟婆婆說,婆婆張圓了嘴巴,神情顯得很慌張。
等到眾人掃棺時,公公骷髏一樣的顴骨上面深陷的眼睛,比先前靈堂里睜得更圓了,只是那眼里沒有光。
小叔子的女兒媛媛偷偷對我說:“爺爺去世,最后悔、最怕的應(yīng)該是奶奶。奶奶沒有好好照顧爺爺,每天住在樓下的門衛(wèi)室,從來不回家睡覺。喝水吃飯,都由姑姑燒好了送下去。”
婆婆是跟公公一起插隊的余姚女人,不大會照顧人,但至少讓公公可以幻想有朝一日跟她一起還鄉(xiāng),這個夢一直做到死前,他還說胡話要回余姚,讓婆婆快點收拾東西。
婆婆因為從小被家里人擠兌,至今記恨在心,一直不想回南方。聽大姑子說,公公被查出患肺癌之前,買好了兩張火車票,要拉著婆婆一起回來看看,婆婆死活不依,躺在地上打滾,抗拒公公的決定。結(jié)果公公嘆著氣讓大姑子退了火車票。那時離他去世不到兩年。
婆婆每次來都不肯在余姚久待,喜歡打麻將的她,回余姚最不習(xí)慣的是,雖從小在余姚城里長大,如今回來居然叫不齊人陪她打一桌麻將。她的牌友都在中衛(wèi),那里有和她一起下鄉(xiāng)的幾十個兄弟姐妹,操持公公葬禮的人,多半就是這幫余姚老鄉(xiāng)。
在中衛(wèi)那天,婆婆搬出了一本相冊給我看。前幾年余姚知青搞了個聚會,相片上合影的有四十多個人,她數(shù)了數(shù)說,已經(jīng)有十幾個不在人世了。這些活著沒能還鄉(xiāng)的江南人,死了都埋在中衛(wèi)的那片黃土里。
第五日 悼詞
公公是個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一手毛筆字寫得很清雅。中衛(wèi)的家里正堂上懸掛的,是我給他從一位老書法家那里求來的“人生七十不稀奇”,而他卻在七十出頭時走了。恐怕他南方的肺,生來就不該承受北方的塵沙。
我熟悉公公的筆跡,當(dāng)年我跟丈夫戀愛遇到婆婆阻攔,他寫過一封長信給我,意思是不要計較婆婆的封建思想,說自己的女兒離異后也是孤身一人,這并不代表她不賢惠。
大概從那個特殊時代過來的人,都有動輒寫信向上級反映問題的習(xí)慣。那年過年,公公來我家,給政府寫了一封在我看來很不合時宜的信,信中那種以建設(shè)大西北的功臣自居,要求政府照顧后代的乞憐口吻讓我羞愧。我假托已經(jīng)交給了政府,將信偷偷塞進(jìn)了抽屜。這次在葬禮上,碰到為公公操辦喪事的余姚知青的頭兒,問起公公的那封信政府有沒有作答,看我遲疑地?fù)u頭,他很遺憾地說:“我告訴過他,那封信應(yīng)該交給信訪辦,那里專門有人受理。”
本來公公的悼詞是交給我來寫的,我想了好幾天,不知道如何總結(jié)公公的一生,最后還是由那個余姚知青的頭兒代勞。丈夫在眾親友面前念了那份悼詞,其中少不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之類的話。有幾句話讓我眼睛發(fā)熱:躺在大家面前的這個人,把自己寶貴的一生獻(xiàn)給了第二故鄉(xiāng),最終將遺體埋進(jìn)了黃河邊的這片黃土。
第六日 入殮
在靈堂里,我撕心裂肺地喊著要帶公公回余姚。或許在公公的葬禮上,我從頭到尾都在哭我自己吧,哭那個想象中多年以后客死他鄉(xiāng)的自己。
丈夫是個不會落淚的人,我從來沒有見他哭過。那幾天,他只是胸悶氣短,長吁短嘆,即使在公公入殮時,他要哭出來依然很困難,偶爾干號兩聲,那兩聲在一群哭喪聲中,只有我辨認(rèn)得出來,顯得很不自然。他一跪下就站不起來,每次都由我在一旁連攙帶扶把他拉起來,全身的筋骨似乎被抽掉了,在公公的遺體前他顯得軟弱無力。
我給靈堂里的公公送了六天的飯,那些飯每次倒在一個陶盆里,入殮前,陰陽師把盆子里結(jié)了冰的飯菜,用釘棺材的鐵釘撬碎,裝進(jìn)一個小瓦罐,那只沒有蓋子的瓦罐最后用饅頭封口,用紅底碎花的紙包起來。陰陽師讓我用紅線幫他捧住包了花紙的罐子,在罐口打了幾個活結(jié),說口不能扎太緊,吃的時候不方便。我知道那個被打扮得像一件藝術(shù)品一樣的瓦罐,第二天出殯是要被帶到墳前砸爛的,聽他這么一說,心跟著一熱,仿佛那罐子里冰凍的吃食也讓這句話化開了。
入殮時,丈夫用酒精給公公擦完臉后,悄悄跟我說,紗布從臉上擦過去,像擦在冰疙瘩上。我安慰說,凍實了好,無菌,入土后可以保存得完好些。心里忍不住猜測丈夫那一刻的感受。
我跟丈夫說,人不是怕死人,人怕的是看見了自己的死亡。這話像是在安慰自己。我不知道丈夫怕不怕,他有事沒事會喊我一聲,一有空就擠到我身邊來,看著我干這干那,或者叫我陪他出去走走,看看小時候玩耍的地方。他還喜歡走路緊緊扣住我的手指,扣得我手指發(fā)痛。這些細(xì)微的動作是過去少有的,我明顯感覺出,他想用這種生命的親近,把一些占據(jù)了內(nèi)心的對死亡的恐懼?jǐn)D壓出去。
第七日 遺像
料理完喪事,我將公公的遺像抱回余姚來了。那幅遺像我在靈堂整整看了六天,公公入殮后,大姑子的兒子馬駿還讓我把遺像抱在胸前,好讓他把兩側(cè)的黑飄帶和小白花用透明膠粘住,以防第二天出喪時在靈車上被北風(fēng)吹落。
不知為什么,一開始我就認(rèn)定了那張遺像只適合放在靈堂。丈夫卻把它擺在了客房的櫥柜上,遺像正對著我們的臥室門,與屋子里棕紅的色調(diào)很不協(xié)調(diào)。這讓我總覺得從那天起,另一個人接管了這間屋子,每次進(jìn)臥室,都覺得有個人在門口看著,做什么都不自在。
丈夫知道我們穆斯林是不擺遺像的,我父母從來就沒有照過相。過去我看到漢族人家擺著遺像,目光總是回避。
自從遺像占據(jù)了那間客房,丈夫也不再去那邊看電視或者休息,他的活動空間轉(zhuǎn)移到了客廳和書房,有時干脆就睡在客廳或書房里。他還找了各種理由,說那間屋子睡著有嗚嗚的風(fēng)聲,在書房和客廳就沒有這種聲音。那間客房靠樓最西邊,窗戶邊上就是巷子,有風(fēng)聲是難免的,只是住了幾年了,也沒那么在意過。客房反正沒人住,干脆就讓給遺像吧。
我忌憚著那幅黑白照片,本能地將自己的日子與那張遺像拉開距離。大概是受我的感染,丈夫偶爾去客房敬敬香,象征性地去看一眼遺像,客房里一天到晚不開空調(diào),冷冰冰的,沒有人氣。
兒子回來,我和他躲在書房里說說笑笑,這時候我也會想到在西邊客房里的公公,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聽見了我們說笑。這又讓我想起公公蓋了薄薄的被子,凍得硬邦邦地躺在靈棚里,我們一大堆人在中衛(wèi)暖氣很足的熱房子里吃吃喝喝、說說笑笑的場景,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跟兒子說,我們?nèi)ソo爺爺上炷香吧。爺爺活著的時候不能來,現(xiàn)在終于可以住在我們家了。
兒子說,我們?nèi)ヅ銧敔斂磿弘娨暋?/p>
從小到大,兒子沒見過爺爺幾面,兒子以前總是抱怨,爺爺只照顧媛媛和馬駿,從來沒有照顧過他。現(xiàn)在爺爺死了,他原諒他了。
我和兒子都接受了這個老人以遺像的形式跟我們住在一起。遺像只占了柜子的一個格子,丈夫在像前放了一盒煙,斟了一杯酒。丈夫仿佛把父親接到了家里生活一般,買了幾刀冥幣,說是等到五七焚化。我看了看,有美元、歐元和人民幣。我說,看樣子你要送老爺子出國旅游了。丈夫不置可否地說,老爺子現(xiàn)在出國,護(hù)照都免了。
活人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來揣度死者。逝者已去,活人還要將日子過下去。我每次進(jìn)客房拿東西,看公公一眼,公公也看我一眼,他像一面鏡子,每天照見我早出晚歸的不同神情。公公的眼神在鏡片后面不斷變換著,眼睛里有時是滿意,有時是責(zé)備,有時是疑惑,有時是安慰。
忙完了,累了,我就去給公公上炷香,在他面前站著,什么也不說,他似乎什么都看見了,也聽見了我的一兩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