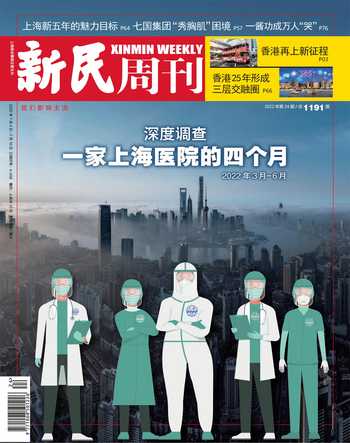仁濟急診:生命守夜人
王煜

仁濟東院急診重癥監護室,醫護人員查看監測儀。攝影/ 李強
過去的三個月,上海的夜晚不少地方靜悄悄。然而,有一個地方永遠燈火通明、忙碌不已,人們為挽救生命奔跑、堅守、拼搏,永無停息。
這里是仁濟醫院的急診。這里的醫護,是疫情洶涌之時,民眾的生命守夜人。
“外面有病人快不行了!”2022年3月下旬的一個晚上,一個小伙沖進仁濟東院急診大廳。急診搶救室小組長、護士胡秋穎馬上跟著他飛奔到樓外廣場上的一輛私家車旁。此時,后座的女士已經呼之無應、頸動脈搏動消失。她當即與家屬一起把患者平放到車外的地上。胡秋穎一邊跪著為患者做心肺復蘇,一邊詢問病史、通過對講機通知搶救室的同事做好準備。
仁濟急診醫護團隊隨后對患者實施氣管插管接呼吸機,使用心肺復蘇儀,搶救過程持續了2個多小時。胡秋穎當天接了40多輛救護車,這個患者讓她印象深刻;后來她得知,這是家屬當晚求助的第三家醫院,之前的兩家醫院都沒能接診。
她的這次救治,是仁濟急診在本輪上海疫情中的縮影。在全域靜態管理的日子里,上海一些醫院的急診曾經暫時關閉,而仁濟急診從3月23日起一刻也沒有停下。
“夜里常常是救護車來得最集中的時候。”仁濟醫院急診科護士長范穎向《新民周刊》記者展示了她拍攝的一張相片:4月的某天晚上,仁濟東院急診樓前同時停進了七八輛救護車,幾乎將小廣場塞滿。
仁濟醫院東院是浦東地區最大的三甲醫院,平時的急診接診量就比較大。3月28日浦東開始全域封控后,來到仁濟東院急診的患者人數開始急劇飆升。平日里一天接救護車五六十輛,疫情封控期間,最高值一天達到170余輛。
應收盡收,急診很快嚴重超載。平時收治七八十名患者的空間,封控期間最多住進超過200 名患者,加上他們的陪同家屬和急診的醫護、工作人員,四五百人將有限的空間擠占殆盡。
對于患者和家屬,仁濟急診“來者不拒”。有核酸報告的直接進去;沒有核酸報告的現場采樣后進入緩沖區先開始治療,不用等核酸結果出來;對危急患者是一邊搶救一邊采樣。甚至有的患者來時就是明確的新冠陽性,仁濟急診也照收不誤。
“不可能因為他們是新冠感染者我們就不救,救人是我們的天職。”仁濟醫院護理部主任奚慧琴說,“封控期間來我們這里的,大多都是真的撐不住的病人。”
應收盡收,急診很快嚴重超載。平時收治七八十名患者的空間,封控期間最多住進超過200名患者,加上他們的陪同家屬和急診的醫護、工作人員,四五百人將有限的空間擠占殆盡。

醫護人員在緩沖區為急診病人測體溫。
急診醫護把原先候診區的椅子全都拆掉,為患者和家屬騰出空間。護士臺邊、付款處旁、電梯廳里、過道的兩旁……每一個空間都擺滿了病床,勉強留下可供人穿過的一條通道。有的“病床”其實只是一張輪椅,有人甚至在地上鋪開硬紙板當作“床位”。
原有的床號早已不夠,護士用數字牌掛在患者的輸液架上,就算新增了個床位。
“急診難就難在情況復雜,沒法預料下一個患者是什么情況,醫護時刻都要緊繃著神經。”仁濟醫院急診科副主任劉黎說。
那段特殊的時期,急診醫護既要救治患者、防控疫情,還要照顧患者和家屬的生活,工作量成倍上升;全程二級防護之下連續高壓工作好幾個小時,每說一句話都覺得特別累。“一直隔著面屏和裹著薄膜的手機盯著屏幕看,我們不少醫護的視力都明顯下降了。”劉黎說。但她不能不看,在十幾個群里,隨時都可能出現和救治患者有關的重要消息,“連把手機設置成振動都不敢,生怕錯過,一定要把提示音調到最大聲”。
浦東開始全域靜態管理的前一天晚上,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時,仁濟急診的醫護沒有一個推脫,全都連夜拉著行李箱趕來集合。在任務最重的時候,也沒有一個醫護說“不干了”;有位護士累病了,對范穎說:“讓我休息一下,好了再上。任務太重,我知道你找不到替班的人了。”
急診就是一個微縮的社會,世間百態顯露無遺。生活中的離別、糾結、感傷,在這里都可以看到;平時如此,封控期間人們的情緒更容易爆發。仁濟醫護的一個重要職責,就是勸解、安慰這里的患者和家屬。
急診科里的患者和家屬越來越多,吃飯就成了大問題。封控前期,外賣完全停擺;后來雖然恢復,但外賣取餐會增大感染風險。

深夜,120 救護車送來急診病人。攝影/ 李強
在了解到病人和家屬來院就診的飲食需求后,仁濟醫院副院長李勁立即召集后勤保障處討論急診大樓外盒飯供應點的選址、菜品的選擇等,做好做足預案。“看病是剛需,吃飯同樣是剛需。疫情期間大家總是討論著‘搶菜’、‘團購’,‘吃’是老百姓關注度很高的一件事。我們要讓老百姓來仁濟看好病,也不能讓他們餓肚子。”
按照防疫規定,陽性感染者和陰性人員是不能共處的;然而急診室中的現實是,不少患者和家屬出現了“一陰一陽”,此時只能靠醫護對他們耐心地做工作。
4月12日,劉黎收到了急診病房11床的來信。患者是一位71歲的老先生,信是陪伴他的老伴寫的。
老太太在信里說:眼看病房里不時有陽性感染者被轉運走,不知哪天會輪到他們。于是,她和老先生商量決定,無論夫妻雙方誰成了陽性,希望可以待在一起,永遠不分開。并且,為了感謝醫護人員的照顧,兩人決定把遺體捐獻給醫院,“如果這事辦妥了,我也不害怕了,隨時隨地做好準備”。
老太太手寫的字跡,密密麻麻鋪滿了好幾張紙。看到這封信,劉黎哭了一場,但她心里清楚,老夫妻倆的心愿很難實現。該如何勸說他們呢?
最終,她并沒有面對這個難題,新冠病毒也并沒有打擾這對老人。4月23日夜里,老先生因為基礎疾病,平靜地走了。
醫護何嘗不是同樣經歷著分離與焦慮。“一名護士的丈夫3月27日腦溢血住院,家里還有今年要參加中考的孩子。我知道這個情況后,跟她說照顧好家人,不用來了。結果第二天我還是在醫院見到了她。她把自己的父母連夜從崇明接過來在家里照顧孩子。”奚慧琴告訴《新民周刊》記者,這次堅守急診的護士團隊,像這樣家里只有老人照看孩子的,還有很多。
“年輕的小姑娘,誰在自己家里又不是個寶貝呢?”這些“寶貝”在特殊時期都化身全能的戰士。平時看起來文弱的小姑娘,運病人、扛物資、搞衛生每一樣都自己上,因為每個人都任務艱巨,只能自己盡力多分擔。
急診一個班6小時,因為工作太多,醫護實際常常工作8小時以上。兩點一線的閉環管理,醫護人員的臨時宿舍在20多公里外的浦江鎮,車程需45分鐘,下班后回到宿舍真正能休息的時間非常少。
反復電除顫、心肺復蘇、心臟血管成功開通,當最后一臺急診手術結束時,導管手術室窗外天已經亮了。這是上海全域封控期間,仁濟心內科最忙碌的一夜,連續五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得到急診手術成功救治。
深夜跟車轉運陽性感染者時,120救護車上往往只有一名司機。推病床、搬東西,急診科的醫生護士都得干。有時候,救護車從仁濟東院把陽性感染者轉運到仁濟南院后并不馬上返回,而是去其他地方收集醫廢,醫生只能跟在車上。“回來后,這個跟車的小姑娘直接累哭了。”劉黎說。
“累哭了、委屈哭了,在這段時間真的是人之常情。”奚慧琴感慨,“有的護士長跟我打電話時哽咽了,我跟她說:哭沒有關系,但你確認一下是自己一個人在房間里。哭好了,出去還是接著要給大家鼓勁。”
反復電除顫、心肺復蘇、心臟血管成功開通,當最后一臺急診手術結束時,導管手術室窗外天已經亮了。這是上海全域封控期間,仁濟心內科最忙碌的一夜,連續五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得到急診手術成功救治。“對于急性心梗患者而言,時間就是生命。”仁濟醫院心內科主任卜軍說,“多耽誤一刻,危險就多一分。所有急診心臟病患者都在第一時間救治,從未因等核酸結果而延誤。”
在疫情期間被救治的急診心臟病患者里,有11名患者后來被確認為新冠陽性感染者。很多急性心梗發生在夜間,卜軍和同事們一直駐扎在醫院,成為心臟病患者們的“守夜人”。
在3月疫情之初,仁濟醫院各部門通力合作,在科學防疫的基礎上,打通急診大廳到導管手術室的綠色通道。“快速抗原檢測先行”、“邊等核酸邊救治”、“三區兩通道”、“急診一人一手術一消殺”等,心內科在各部門的幫助下,制定了“仁濟醫院現階段疫情防控下的心血管急癥救治流程”。這套流程來自于心內科急診團隊在現實救治需求中的點點滴滴,細致到救治環節的每個細節。其中有一條寫著:“接診新病人時,將防護面屏上撕下的塑料薄膜包裹在接診Call機上,方便消殺。”
心導管手術在X射線成像之下開展,急救團隊的醫護人員需要穿著重達十幾斤的鉛衣。一場手術下來,脫去防護服,脫下隔離衣和鉛衣,渾身已經濕透。
疫情期間有不少心臟驟停、竇性停搏的急診患者。仁濟心內科已經退休的毛家亮教授,了解到科室人員在各處奮戰在防疫前線,主動要求披掛上陣,第一時間趕到導管手術室,疫情期間完成了18例急診安裝起搏器手術。
上海全域封控期間,心內科團隊24小時駐扎在醫院,總共救治了108名急性心梗患者,其中最小的29歲,最大的90歲。
在急診科的病房,仁濟醫護同樣時刻守護著每一位患者。
有一位特殊的患者君君(化名)是急診科的老病人,當年因為一場意外導致高位截癱,脖子以下無法動彈,要靠呼吸機維持生命。多年來,他的父母都在病床邊照顧。
然而,在這輪疫情中,他的父母雙雙感染,需要去方艙醫院隔離。離開父母照顧的君君該怎么辦?護士們告訴他的父母:你們放心去,我們會像對親人一樣照顧好他。
醫護定時讓君君與父母視頻交流,讓老人了解兒子的情況。“當我看到護士們為了給他翻身,汗水濕透衣服時,我的眼淚一下子出來了,她們太累了!我真是感動!”君君母親說,在方艙唯一擔心牽掛的就是兒子,看到醫護人員用心付出,她終于可以安心治療。
劉黎記得:在當“臨時家長”的時間里,大家交班時,都會特別提醒“要記得給君君打開電腦”。他的電腦很特別,有一個眼動儀可以讓他控制電腦。他喜歡看體育賽事,也會通過電腦微信與人聊天,這是他與外界接觸的方式,也是他的生機所在。
最終,君君父母新冠治愈出院、解除醫學隔離,一家三口再次團聚。“你們是人間的天使,你們又給了我們一個完整的家!”君君母親寫下這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