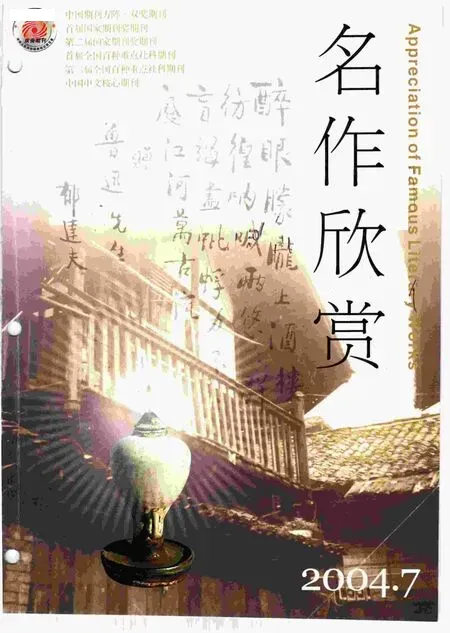《察今》如何察今?
劉偉生
關鍵詞:《察今》 《呂氏春秋》 認識方法
《察今》是《呂氏春秋》中的代表性篇章,又選入中學語文教材,不乏各類解讀文章,但都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到底應該怎樣來考察當今社會形勢以擬定法令制度。我們不妨結合文章的中心意旨與論證方法,來分析《察今》如何察今,并借此了解《呂氏春秋》及其編撰時代人們的認識方法與思維方式。
《察今》的中心意旨與論證方法
關于《察今》的主題,有“察今”“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先王之法不可法”“察今而定法”等說法。
高中語文教參即認為《察今》一文的中心論點為標題本身,而更多的人則認為“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才是文章的主旨a。主張中心論點是“先王之法不可法”的,認為《察今》的議論對象即中心話題是“要不要法先王之法”,全文的論據也都或直接或間接地指向“先王之法不可法”,而不是“察今”。b 其實“察今”的目的是為了定法,而“先王之法不可法”與“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既是一體兩面的不同表述方式,也可以互為論證依據。這幾個觀點雖有側重,但不矛盾,應該綜合起來理解:明察當今,因時變法,而非死守故法。徐曉鴻“察今而定法”之說,庶幾近之。
《察今》篇本系法家言論,與韓非子《五蠹》篇“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的觀點相似。《五蠹》篇中著名寓言“守株待兔”,即用以論證韓非的這一主張,認為“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先秦諸子中,儒、墨、道諸家都主張效法先王,法家尤其韓非,則“力圖把世人尤其是儒家學者從渺遠的先王拉回到現實之中,力圖啟示人們關注現實,并從現實中尋求治理國家百姓的有效辦法”d。“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察今》篇無疑也具備這樣講求實效的精神實質。
就論證方法而言,《察今》善用正反結合以類比推理,好以一意數喻而反復論證。為了論證因時變法這一核心觀點,文章先從反面論述“先王之法不可法”,即否定拘泥古法的做法,再正面強調“世易時移,變法宜矣”的主張。其間有直接的論議,說“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人可益之,人或損之”,說“先王之法,有要于時也,時不與法俱至”,說“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有事實的引證,說“天下有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尤以比喻和寓言居多,前言“堂下之陰”“瓶水之冰”“嘗一臠肉”,中譬良醫、良劍、良馬,再穿插“循表夜涉”“刻舟求劍”“引嬰投江”三則寓言,真可謂反復甚至繁復。或許比喻與寓言比直接的論議更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察今》如何察今以定法
論證的方法雖然繁復多樣,《察今》中也有難解難通的地方,就是從“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時也”到“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這一段。李彥明稱其為“斷裂的論證”,理由有四:一是在“察已”與“察今”之間沒有過渡,出現了論證思路上的斷點;二是“察今則可以知古”之說,沒有闡明察今的真正目的;三是說“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若不加限定,其語義與全文論證難以統一;四則認為“有道之士”至“一鼎之調”一組句子與文章中心論點及分論點無關。e 這段話涉及人我古今,確實有含糊不清與循環論證的味道,李彥明先生不可謂不敏銳。但人我古今之間也并非單向度的傳播,一方面今從古來,是先有古后有今,另一方面我們今天所了解到的“古”已然不是本初的“古”,而是經由選擇乃至再造的古,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古從今來,我們對古代情事包括立法情況的考察便是從今人的角度來進行的,然后再從這種考察中吸取包括通用方法在內的有益成分,所以說“觀今能鑒古,無古不成今”,“古今一也”。人我關系也是一樣,只是因語言的簡省而造成了文意的斷裂與歧義。
議論文講引論、本論、結論,要提出問題、分析問題,還要解決問題。其實這一段就是要回答“怎么辦”即如何察今以定法的問題。
那到底該如何“察今”呢?我們可以從原理、途徑、方法等維度來考察《察今》中的這一段文字。
這段文字在回答“怎么辦”的問題時,首先說到的是“釋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放棄先王成法難在理念而非操作,“法其所以為法”則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為法方法,二是法其方法。“法其所以為法”之所以可能,其實是因為人我古今的立法精神、立法原則、立法方式是相通甚至相同的,即“因時變法”,在這一點上,“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這是大的前提,也是基本原理。這基本原理甚至可以上升到“道”與“德”的高度。《去私》篇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貴信》篇說“春之德風”“夏之德暑”“秋之德雨”“冬之德寒”,講的是自然規律。《察今》篇說“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講的是社會規律。
除了崇高而籠統的普遍規律外,還有類同原則,類可推原則。所謂“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召類》),在類同的前提下,可以由已知推知未知,即“以所見知所不見”。《長見》篇也有近似的說法:“今之于古也,猶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猶今之于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
再說“人”,今天我們講立法要以人為本,要滿足人的需求,要有人來考察人的各種需求。古代立法當然也圍繞“人”,但“人”的范圍可能沒這么大,或者說分工有所不同,權利與責任不那么對等。《察今》篇的后面說:“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可見上段文字中的“人”“我”主要是就因時變法的人君而言的。當然,也不妨礙我們理解為更廣義與廣泛的包含“民”的“人”,因為即便在古代,君民之間也是既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的。
既然人我古今“因時變法”的立法精神、立法原則、立法方式是相通的,甚至上通于道、上通于德,那就要因應時勢,以道察今,即一面悟道、存道、據道、證道,一面察今、察時、察人、察事。具體來說,就是要根據類同原則“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前面說過,“以今知古”與“以古知今”是雙向互動的,就閱讀習慣而言,不妨用“以古知今”代替“以今知古”。從字面意思來看,“以近知遠”涉及空間關系,“以古知今”指向時間維度,“以所見知所不見”關乎部分與整體、現象與本質問題,也是考察與認識過程由已知到未知的共性。
為了更進一步解釋如何根據類同原則“以所見知所不見”,《察今》接下來還用了三種生活常識來做比擬:“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大致說來,這三事三喻對應著上文三句所言時間上已知與未知、空間上已知與未知,以及部分與整體、現象與本質的關系問題。結合因時變法的觀點來理解,就是要通過考察古今、遠近、人我等各種情事來歸納立法的通用之道,再根據這通用之道,結合當今具體形勢,用類推方法制定法令。
因為時間、空間原本難解難分,部分與整體更關乎空間屬性,再加比擬的方式預存有諸多闡釋的可能,對這三事三喻的理解自然會多元多貌。比如“堂下之陰”與“日月之行”,既涉時間,也關空間,又何嘗不蘊含現象與本質的關系?而“瓶水之冰”與“天下之寒”,雖側重于空間關系,又何嘗不涉及時間維度,乃至如徐曉鴻所言之虛實、因果、彼此關系?(徐說:“第二喻講的是由實見虛,由果知因,由此知彼。”) 可再怎么復雜,無非還是講要利用一般與個別的關系,使用歸類與類推的方法,進行從已知到未知的考察。
到此為止,文章已完成了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三部曲般的論說,余下的段落不過是觀點的正面提煉與比喻寓言式論據的多重鋪陳。就邏輯性而言,這些段落也未必嚴謹,從接受效果來看,比喻與喻言卻比純粹的說理更引人注目。三則寓言甚至可以脫離文本也具有獨立的價值。這就說明認識與表達、邏輯與感悟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與張力。
《呂氏春秋》的道法觀念及認識思想
從更大范圍與背景上了解《呂氏春秋》的道法觀念與認識思想或許有助于理解《察今》篇未能詳述的“察今”方法。
因時變法是法家一貫的主張與做法,《商君書》開篇即名《更法》,內中商鞅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其實五霸爭雄都離不開變法圖強,戰國七雄也沒有固守藩籬舊制。韓非子作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更強調“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呂氏春秋》因時變法的思想可以說淵源有自,但《呂氏春秋》也罕見關于立法程序與方式的具體論述,更多的是認識目標、過程、方法等方面的言論。
《呂氏春秋》認為,認識的根本任務在于“知一”。“一”即“太一”,“太一”即“道”。
《大樂》篇說:“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名,謂之太一。”又說:“萬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陰陽。”《論人》篇更直說:
凡彼萬形,得一后成。故知(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故知知一,則復歸于樸,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顯而易見,這“知一”便是“知道”“得道”。“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惑之也。”(《有度》)知道、有道,并執道,便能辨明萬物、治理萬物。所以《察今》篇稱“察今”者是“有道之士”。
要想更快更好地知道識道,還得去除成見,免受思維局限。用《呂氏春秋》的話來說,就是要“去宥”“去尤”:
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后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去宥》)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去尤》)
“宥”同于“囿”,意指局限;“尤”同于“疣”,義含缺陷。因為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認識的過程難免有局限與缺陷,“去宥”“去尤”就是要盡可能消除主觀偏見,彌補客觀不足。
關于認識的過程,《察今》篇已提到由近及遠、由古及今(由今及古)、由己及人、由所見知所未見的路線,并舉三事為喻。《貴因》篇也有近似的比擬:“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因循天地運行的規律,就可以審察、推論四時與晦朔。《論人》篇也講到由己及人:“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強者,失之彌遠。”認識他人與外物之前,先要“反諸己”,什么叫“反諸己”呢?《論人》篇繼續說:“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還是說要消除各種主觀好惡,即“去宥”“去尤”,“去宥”“去尤”才能“得一”即“得道”。《觀表》篇與《察傳》篇還用到“征表”與“熟論”這樣的語詞:
圣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征表,無征表而欲先知,堯舜與眾人同等。(《觀表》)
凡聞言必熟論,其于人必驗之以理。(《察傳》)即便是先知先覺的圣人,也要審察征兆與表象,而聽到傳聞一定要深入考察并加以驗證。“征表”與“熟論”分屬兩篇,合在一處正好可以說明認識是一個由表及里的過程。
至于認識方法,主要還是類推,在識類、別類的基礎上比類、推類,識類推類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察傳察疑。
“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圓道》)“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疑似》)因為事物的復雜性與迷惑性,需要知類、識類,知類、識類的手段與方法是別類、察類。“別類者,謂凡事必分別類居而尋求其所以然,否則必致理論與事實相違戾。”f 別類不僅為了事物的分類,更以“尋求其所以然”為宗旨。《別類》篇專舉別類的案例,通過批評以偏概全、籠統比類的做法,來闡述“類不必固”“因而興制”的思想。按蔣開天的統計:“在《呂氏春秋》中,‘察類’的具體表現形式有五:‘察微’‘察疑似’‘察傳言’‘察其所以’‘察不疑’。”g 其實近似的說法還有“加慮”“察疑”“熟論”“驗理”等。歸納起來應該是耳目直觀、邏輯推理、實情檢驗等方式方法。
耳目直觀是感性認識。“目不失其明,而見黑白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執一》)耳目原本具有感知事物的功能。《論人》更提出“八觀”之說:“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八觀所述都有特定的情景,這其實也是檢驗,所以“八觀”之后,還有“六驗”:“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察傳》篇也講到以實情來檢驗的方法:“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圣人這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察傳》)根據物情與人情來考察,也是驗證。邏輯推理即前文所講類推,其所依據的是類同原則,就方向言,有人我、古今、遠近之別;就方法言,有歸納與演繹之別;就表達方式言,有直陳有比擬有寓言。
總言之,從根本目標,到大致過程,再到具體方法,《呂氏春秋》中有著豐富的認識思想,了解《呂氏春秋》的道法觀念與認識思想,對解讀《察今》終究如何察今以定法的問題不無幫助。
余論
作為雜家代表作的《呂氏春秋》,匯集了先秦各家學說的精華。其所承繼的因時變法思想,成為我國古代重要的立法原則。其所蘊含的類推方法與認識思想,在中國古代,也具有典范意義。研讀《察今》及《呂氏春秋》,有助于了解古人的立法思想與認識方法。同時也要看到,包括《呂氏春秋》在內的古代認識與表達的局限,整體直觀思維與類比推導的方式,“只是關于現象整體性質的模糊性知識,而不是關于現象局部的清晰的、確切的真實知識。它只強調現象的已然狀況,而不強調現象所以然的原因”h。古代漢語有簡練省凈的優長,但簡省的語言也容易導致如《察言》篇所說的“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的是非不分的結果。以致兩千年后,我們讀《察今》篇中如何察今這一段時,會產生如此多的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