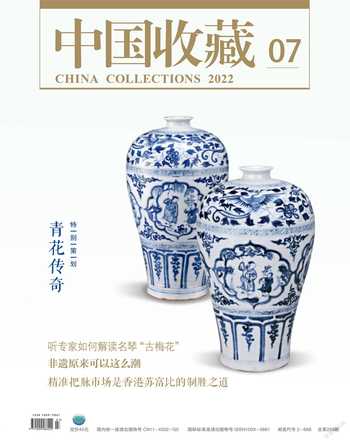數字化讓非遺玩法“潮”起來
陳曦

點開手機屏幕體驗線上“云游非遺”,足不出戶就能遍覽全國各地的非遺技藝、表演;到“非遺購物節”逛一圈,身懷絕技的非遺傳承人搖身一變成為主播,玩轉直播帶貨??近日,全國各地正持續火熱上演著非遺的精彩活動。不難發現,這一個個原本古老而傳統的技藝通過數字化技術的發展,變得愈發“潮”了起來。
不久前,在我國第17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期間,文化和旅游部組織、發動各地開展了豐富多彩的非遺宣傳展示活動,重點打造了“云游非遺·影像展”“非遺購物節”兩大品牌活動。而各地舉辦的多項非遺宣傳展示活動在促進非遺資源數字化轉化利用和全民共享的同時,也滿足了公眾認識非遺、學習非遺、研習技藝的需求。特別是在線上各大平臺努力貼近年輕群體、以年輕人樂于參與的方式進行傳播推廣。
其中,“云游非遺·影像展”在線展播2300多部非遺傳承紀錄影像、非遺題材紀錄片,同步開展各類非遺短視頻話題、主題直播、話題討論等活動;還打造了“非遺購物節”,組織7500多家非遺店鋪參與,涉及非遺項目4000多項。
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子項和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均位列全國第一的浙江省為例——為迎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浙江省期間開展了形式多樣的非遺活動。而“非遺購物節·浙江消費季”也在線上線下均獲得了不錯的反響。有數據顯示,僅一周時間內,浙江省全省銷售非遺產品及相關衍生品(文創產品)981萬余件,銷售額達35624.95萬元,覆蓋老字號網絡直播531場,銷售39萬余件產品,銷售金額超過2335萬元,共有1227萬人次觀看直播。
在此期間,除了“云演出”“云逛展”以及直播購物外,全國各地的非遺保護機構、專家學者推出的線上非遺課堂、論壇還為公眾輸送了寶貴的非遺文化知識,讓非遺在數字化時代的背景下更貼近生活、深入人心。比如我國首座國家級工藝美術和非遺展示博物館——中國工藝美術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館,就在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當天舉辦了首屆“非遺館里話非遺”論壇,邀請行業領導和專家學者共同探討“文化數字化背景下非遺保護與教育”的議題。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司長王晨陽在論壇上表示:“文化數字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活起來、火起來的重要途徑。近年來,我們大力推進非遺保護領域的數字技術應用與推廣工作。2013年起,累計支持對1636名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開展記錄,用數字多媒體手段記錄和留存代表性傳承人所承載的獨到技藝和文化記憶,逐步推動優秀記錄成果的研究利用、社會共享和大眾傳播。”
中國工藝美術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館館長韓子勇則指出,我們每個人在今天實際上都是“數字移民”,我們既生活在一個現實的世界里,同時又和數字世界、信息社會發生深刻的聯系。“數字技術在各種文化類型中都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不光是保護、傳承、記載、交流、傳播的作用,它在新的知識生成、經驗傳遞上都會起到作用。由于非遺形態多樣、綜合繁雜,又是活態的,因此對信息技術、數字技術的需求迫切程度更高,數字化、信息化對非遺的傳承、創新、發展的幫助也是最大、最突出的。”
當數字化時代的關鍵詞與非遺發生了不小的“化學反應”時,會對這一傳統文化帶來怎樣的發展機遇?又會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問題?針對非遺在數字化時代的傳承與保護、教育與發展事業,不少業內人士在“非遺館里話非遺”論壇中各抒己見,干貨滿滿。
郭藝(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館)主任、研究館員):
數字化提高了非遺資源的保存效率。以浙江省為例,2011年浙江省開始建立非遺數據庫,至今已形成了“一臺五庫”的框架,即非遺工作管理平臺與非遺項目庫、傳承人庫、非遺影像庫、普查庫以及文獻庫。然而這些功能尚不能滿足當前非遺保護的需求,數據庫也沒有發揮與社會互動的作用——一方面無法吸納社會的數字資源,另一方面也不能為社會提供更好的數字資源服務,因此我們想通過數字化改革解決現存的問題。
我們接下來的工作主要涵蓋幾個方面:一是要建立非遺數據采集的標準;二是社會各個方面都在參與非遺研究,包括非遺相關的藝術創作等都是非常豐富的資源,我們可以通過有償或無償的方式向社會征集非遺資源;三是向社會公眾提供非遺的查詢平臺,也為非遺的傳承、教育、研究提供服務,為全社會共同參與非遺的傳承發展提供支持。
陳岸瑛(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主任、教授):
非遺館是非遺保護中一個傳播環節,銜接了文化的創造者和接收者。從場館空間角度來說,非遺館采取的是一種“再現”模式,對非遺項目的歷史進行靜態或活態的展示,都是對已經消亡歷史的展示;第二,國家這些年比較注重對非遺館的建設,從中國非遺館到各省市縣級的非遺館都是代表各地的一扇窗口,游客可以通過這一窗口去獲得一份“非遺地圖”和指南。當然,這不僅僅是在實體空間發生的,在數字化時代也可以變成“掌上非遺地圖”等形式。從這兩個方面看,非遺館與民俗館的展陳空間功能非常接近。
但非遺不同于民俗,非遺館也不同于民俗館,它們之間是有差異的。非遺館里會開展各種節慶活動和體驗活動,這種展示模式是“再現+參與”的模式,以臨時性展覽為核心。這種“參與”模式比較接近當代藝術的策展機制,是基于非遺保護中的主體,比如非遺傳承人和參與非遺保護的保護者、研究者等在當代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群,定期從不同的主題策劃展覽,展現他們的當代創新成果。在這個意義上使得非遺館不同于民俗館,這也構成了非遺館帶有自身特色的一種核心功能。
范周(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導,北京京和文旅發展研究院院長):
非遺保護與教育的數字化發展應避免重技術形式而輕文化內涵,對元宇宙、NFT等發展模式一定要冷靜地對待。NFT數字藏品開發也是當前非遺數字化領域中的一個熱點,相關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數字藏品發行平臺多達38家,中國各個非遺產品發售數量約456萬份,總發行價值超過1.5億元。其中,針對國潮非遺等類型在發售當中經常出現秒空的現象,體現出年輕人對非遺數字產品的喜愛。
我們在發展當中不能拒絕這種嘗試,但仍需注意數字藏品的有限發售與非遺要實現最大化傳播在理念層面存在的沖突,以及真正的數字藏品知識產權的認定和管理目前還存在一定的監管盲區,這些都加大了非遺數字化建設當中的風險。因此,對于這些新的概念和新的發展模式,我們仍然要冷靜地看待,不要盲目入局。
易介中(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文化和旅游工作委員會會長):
當以95后為主體的Z世代這些互聯網“原住民”遇到非遺,他們會認為是有趣、有藝還是有術?這是我很關注的現象。通過在年輕人中比較時髦的字眼,比如“擴列”“破圈”“出圈”“融圈”等可以將二者的關系建立起來。
對非遺進行時尚傳播,讓其具備很高的美譽度和關注度,目標就是讓人們主動保護非遺、接受非遺教育。以前的時尚傳播是在不停地將非遺進行藝術化包裝,而我覺得應該往創意化思維轉變。要采用更生動、鮮活、更“萌”的語言和年輕人對話,體現非遺的“療愈型”產業特征。非遺傳播必須持續吸引新一代的關注,需要“討好”新一代。他們會“為美好而戰”,去關注兢兢業業的匠心、匠人,為非遺的“顏值”站臺。
楊瀾(資深媒體人、陽光媒體集團董事長、北京陽光未來藝術教育基金會理事長):
對于非遺的傳播價值或其在社會文化構建當中的地位,我們的認知是在不斷地升級和擴展的。2018年,我們的電視節目《匠心傳奇》將焦點從“物”本身轉到“人”的故事,關注他們的經歷、情感、技藝、夢想,讓觀眾更好地貼近非遺、貼近傳統文化;對非遺傳承人的定義也從匠人轉化為藝匠,許多傳承人不僅僅是完成了技藝本身的傳承或是達到了極其精湛的水平,他們也在不斷地進行藝術性創造和突破。通過體驗性、過程性和即時性相結合,我們用節目記錄下鮮活的人物和活態的技藝。
在之后將推出的《萬物新生》節目中,我們將聚焦非遺的“守、破、離”,即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非遺作品、產品在空間中兼具展示、表演、體驗、設計、手作、教育等多重功能,打造新的人、物、場的生態關系;使得觀眾對非遺從“仰視”到“平視”,讓每一個人都成為新的創造者、分享者。
意娜(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會秘書長):
這些年我們看到與非遺相關的新聞報道時,經常能看到一個形容詞:活色生香。
“活”即活態。我們要保護的不是非遺的表現形式,而是它背后的人,以及它生動、活態的一套系統。“色”,即非遺豐富的表現形式。比如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圍繞新年等傳統節日都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表現形式,文化表現形式是非遺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一個根本,這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非遺寶庫;“生”指生命力,即非遺的“存續力”。如今我們有了新技術以及像中國非遺館這樣的專業機構,便可以把過去難以傳承的非遺項目通過音頻、檔案等資料進行集中展示,甚至可以用沉浸式、虛擬現實的方式完全還原非遺場景;“香”則是指非遺的傳播。數字化新時代帶來的不光是傳播手段的革新,更是一種結構性的革新。隨著數字平臺的崛起,文化產業鏈的創意、生產、傳播、獲得等每一個節點都會承擔更多的功能,文化生產不再是一個線性的鏈條,而是形成了網狀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