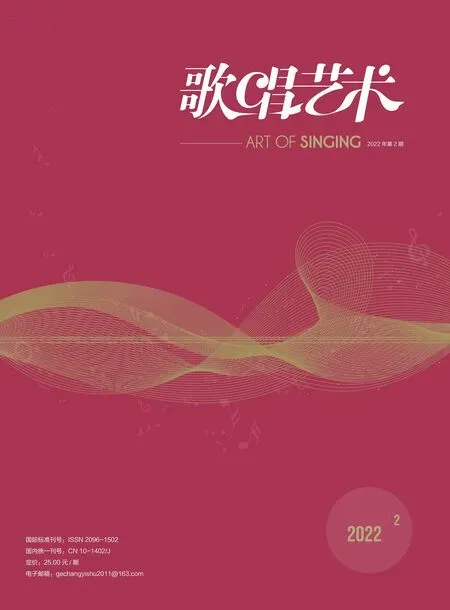做經典的衛道士,還是時代的弄潮兒?
—— 論荷蘭國家歌劇院2016年版《黑桃皇后》的解構思維
孫兆潤

自2012年1月在俄羅斯通過《19——21世紀杰出歌唱家對柴科夫斯基〈黑桃皇后〉中角色蓋爾曼的表演詮釋研究》的博士論文答辯后,筆者一直沒再萌生過聆賞新版《黑桃皇后》整劇的沖動,不是因為審美疲勞,而是源自“乾坤大挪移”時空倒錯的銳意改編和新生代演員們在聲樂與表演實力上的頹弱而衍生的審美抗拒。
但是,最近偶然間卻被一版新編《黑桃皇后》的視頻所吸引,竟一氣呵成,將目光梭巡到演出班底列表結束。這是2016年由荷蘭國家歌劇舞劇院和英國科文特花園皇家歌劇院聯合制作,由斯捷番·赫爾黑姆 (Stefan Herheim)執導、馬里斯·楊松斯(Mariss Ivars Georgs Jansons)指揮的版本。演員陣容:米沙·狄杜科 (Миша Дидык)飾蓋爾曼;斯維塔拉娜·阿克謝諾娃(Светлана Аксёнова)飾麗薩;拉麗薩·加吉科娃(Лариса Дядькова)飾伯爵夫人;烏拉基米爾·斯托亞諾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оянов)飾葉列茨基(兼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阿列克賽·馬爾科夫(Алексей Марков)飾托姆斯基。
雖然有悖傳統,但是該版歌劇在執導思想上極富想象力,深刻揭示了戲劇內涵。作為當今國際上最有才華的歌劇導演之一,挪威人斯捷番·赫爾黑姆無疑是在深入研究并參透作曲家創作意圖的原則上展開執導的,該版本是建立在史考和音樂學考據結論基礎之上對原作進行的創新性解構。不得不欽佩斯捷番·赫爾黑姆深厚的音樂和戲劇學養,以及建立在豐厚修養基礎上謀篇布局的宏觀把控能力,精妙、細致的戲劇構思能力,關系繁復卻符合邏輯的劇情鉤織和人物關聯能力。在經典歌劇的傳承,當代歌劇藝術發展的宏大命題和與時俱進的當代審美潮流之間的碰撞中尋找突破,始終是當代歌劇編導們的重大使命。當然,筆者認為,在這個天才的戲劇解構中也不免摻雜了迎合當代觀眾的低品元素。
一、寓意深刻的序幕和序曲
大幕開啟,舞臺上是一個大廳的場景,左側擺著一臺放著燭臺的鋼琴,燭光搖曳。
右側躺椅上是反枕著胳膊只穿著背心躺著的主人公蓋爾曼,他打了個哈欠。趴在蓋爾曼懷里的是一位西裝革履的男士,他站起身來離開了蓋爾曼,系上扣子。這段舞臺活動采用的是啞劇式的表演方式,沒有任何背景音樂襯托。
經過一番心理活動之后,西裝男又回到熟睡的蓋爾曼身邊,單膝跪地,親吻他的手背。蓋爾曼驚醒,穿上軍服,轉回身,向正裝男伸出手,正裝男從口袋里掏出了一摞鈔票遞了過去。
蓋爾曼俯身擰開鳥籠狀八音盒(內有一只鸚鵡)的開關,在錚錚淙淙的音響中,蓋爾曼得意地笑著推門而去。
窘迫的正裝男趕忙跟過去,掩上房門,回身急忙關上鳴響的八音盒……
此版序幕在歌劇原作中并不存在,而是斯捷番制作團隊解讀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私生活的寫照。西裝男就是曲作者柴科夫斯基。柴科夫斯基的性取向在今天已經不再是秘密,導演顯然是要強化這個結論。這個看似斧鑿的序幕部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柴科夫斯基悲劇命運的終結與序幕寓意的鋪陳有著直接的勾連。而序幕中的重要道具鋼琴、會唱歌的鳥籠都被導演賦予了深刻的含義(下文將逐一釋疑)。
序曲用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對作曲家死亡情境進行了再現,既交代了現實中作曲家的悲劇命運,揭示了其死亡真相,又奠定了歌劇的悲劇基調。這種用高度濃縮富含寓意的無聲表演來詮釋序曲的方式在21世紀歌劇排演中非常流行。
西裝男(這顯然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本人)走向鋼琴,拿起譜紙,序曲響起。
隨著音樂主題的發展,燈光直射在高懸于舞臺右側墻面上的被稱為“莫斯科的維納斯”的伯爵夫人的巨幅畫像上。作曲家驚恐地抬頭凝視著她。
音樂進入快速段落,作曲家靈感乍現,迅速返回鋼琴前,撫琴投入創作。
這時候,所有的門都洞開,一群與作曲家同樣著裝、同樣發式的人闖了進來。他們每人手里拿著一杯水圍住了作曲家。
作曲家奪過一杯水,仰頭一飲而盡。隨后捏住脖子,陷入痛苦的掙扎中。此時樂隊奏響的正是蓋爾曼熾熱的“愛情主題”。
長著羽翼的麗薩(天使或靈魂)從黑暗處浮現,眾人皆散。
作曲家和麗薩四目相對,遂在麗薩憐惜而安詳的目光中倒地而亡。
麗薩遁地而去,燈光全息,僅剩一絲微光灑在柴科夫斯基的尸體和那個水杯上。
那,是杯毒水!
在原歌劇的戲劇敘事中,所有的矛盾都將在終場主人公的死亡中得到解決。蓋爾曼和麗薩之間愛情的糾葛,將蓋爾曼和伯爵夫人的生死捆綁在一起的神秘紐帶,蓋爾曼本人在愛情和金錢上的權衡,蓋爾曼本人的欲望和良心的掙扎,蓋爾曼涉險的生死考量,蓋爾曼瞬間暴富的夢想和對神秘玄學的迷醉之間的隱秘聯系等,都在男主人公呼吸停止的瞬間得以平息。但是,在斯捷番·赫爾黑姆的解構中,當為蓋爾曼亡靈祈禱的眾人散開,才發現橫在臺上的卻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尸體!這讓本該在安詳的樂聲和觀眾的唏噓聲中煞尾的敘事再添沖擊力,驚詫之余,讓人不得不在慨嘆主人公悲劇命運的同時,去探求柴科夫斯基的命運和死亡真相。
如果你是一位柴科夫斯基音樂學研究領域的關注者,就能體味導演的良苦用心——他是作曲家“服毒自殺說”的堅定支持者。劇中蓋爾曼的死,就是現實中作曲家的死,他們都是在社會的威壓下自殺的。作曲家現實中的所有矛盾也都在歌劇終場以本我死亡的方式得到了解決。
蘇聯著名音樂學家鮑里斯·阿薩費耶夫(Борис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Асафьев,1884——1949)稱《黑桃皇后》在柴科夫斯基的創作中扮演了“類似于莫扎特《安魂曲》那樣的角色”。柴科夫斯基在1890年1月30日給格拉祖諾夫的信中寫道:“我在經歷一段通往墳墓的謎一般的路徑。內心究竟承受了什么,我自己都不明白。是某種對生命的厭倦,是一種悲觀失望。有時極度地憂郁,但在這憂郁的深處又突然涌現出對生的留戀,突然又是絕望的、臨終的那個一貫平庸的結局。我就是帶著這種可怕的心緒創作的。一方面,我感到我已經好景不長了;另一方面,又難以遏制對茍延此生的渴望……”這就是柴科夫斯基凄涼的人生晚境。這種心境直接影響了他晚期兩部最重要的作品《黑桃皇后》(1890)、《第六交響曲》(1893)的創作。這兩部作品折射出其對死亡命題的好奇與恐懼,同時還有對宿命論的全盤接受。一直畏懼和逃避死亡話題的作曲家,不但開始正視死亡,而且還用音樂對死亡進行了令人膽寒的描述。
導演和制作團隊顯然在柴科夫斯基的性取向和死亡之謎的結論上達成了共識,并將作曲家同性戀和被謀殺中毒死亡的結論通過序幕和序曲中演員的無聲表演進行了毫無保留的揭示。

1893年《每日新聞》報第3720號刊登柴科夫斯基死亡的新聞
柴科夫斯基卒于1893年11月6日(舊俄歷10月25日凌晨3點)。當年官方發布的消息稱,柴科夫斯基因為在圣彼得堡的霍亂時期喝了一杯生水,導致染病不治而亡。1980年11月在美國的僑民報紙《新美國人》上,刊登了1979年移居美國的蘇聯音樂學家、柴科夫斯基專著作者亞歷山德拉·奧爾洛娃(Alexandra Anatolyevna Orlova,1911——?)的文章,文中首次披露了柴科夫斯基死亡的歷史真相。原來,作曲家死于“霍亂說”是欲蓋彌彰的謊言,其實是其同性戀行為導致的被迫自殺之惡果。柴科夫斯基早年就讀法律學院的同窗、時任元老院上訴庭檢察長的尼古拉·鮑利索維奇·雅科比糾結其他七名同窗畢業生私設“榮譽法庭”對其同性戀“惡癖”進行“名譽審判”,以其同意自殺為條件,換取不向沙皇遞交控告信的結果。柴科夫斯基被迫服毒自殺。這個新說由蘇聯研究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學家公開發布,在西方世界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出現大批擁躉者。但是,因為奧爾洛娃除了耳聞的口述信息外,并未提供其他有力的實證,在俄羅斯境內,持反對意見和懷疑態度者居多。
俄羅斯著名音樂學家阿爾諾德·阿里施萬科(Арнольд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льшванг,1898——1960)稱蓋爾曼是柴科夫斯基時代的產物,同時還認為,“作曲家為自己最喜愛的人物形象注入了許多個人的、隱秘的心靈特點:周圍環境的壓抑、對幸福求而不得的痛苦等”。我們是否可以把這一段話看作是一種暗示?毋庸置疑,作曲家的生活經歷、情感世界對其創作會產生深刻的影響。柴科夫斯基是社會成見的犧牲品,是貴族階層偽善、殘忍、專橫的犧牲品。那么,令人費解的是,序幕中用毫無掩飾的交易把兩位男性媾合在一起有何深意?作曲家的性取向與劇情發展有何深度關聯呢?的確,柴科夫斯基在創作過程中對主人公蓋爾曼抱著深深的憐憫和同情,以至于在寫完蓋爾曼之死時竟然失聲慟哭!難道除了掬淚一抔,他還對主人公抱有性幻想?
如果真相確如奧爾洛娃所言,那么,作曲家本人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難道還不夠嗎?也許我們沒有義務為古人披上遮羞的罩衣,但作曲家自己刻意隱藏起來的創傷,我們非要殘忍地撕開,血淋淋地展現給大家看嗎?我們該不該尊重作曲家的創作意圖,給逝者留以足夠的尊嚴呢?
筆者記起自己的聲樂老師、俄羅斯男高音歌唱家阿列克賽·斯捷波連科列舉的一個真實案例:在歐洲某歌劇院舞臺上,為把懷念死去的姑娘這一橋段演繹得真實可信,男一號竟然從市場上買回新鮮的牛心臟,把它拿到舞臺上欲當作逝去愛人的心臟收藏在錦匣中。結果,當這位男演員把鮮血淋漓的牛心臟端在手中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時候,觀眾席上一陣騷亂,遭到觀眾們的譴責,演出失敗了。第二場演出時,這位男演員換回道具心臟,主人公的悲劇命運和真摯愛情立刻博得了觀眾們的同情,引來滿場熱烈的掌聲和喝彩。斯捷波連科認為:“真實的、血淋淋的心臟扼殺了演員表演全部的浪漫、詩意和抒情性,毀壞了戲劇的氣氛。這種現象同樣出現在當今歌劇舞臺上,那些渴望成功但品位不高的導演們,把歌劇舞臺變為廚房、肉鋪,把當今歌劇引向荒唐、無品的窘境。”藝術來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就連超現實主義歌劇都不能把真實生活原樣搬上舞臺。藝術的真實,永遠不同于現實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沒有提煉和升華,真實主義在歌劇藝術中毫無價值可言。夏里亞賓對戲劇表演中人物詮釋“是,還是不是”的命題的認知應該是:好像是,但是要合適的、合身的“是”!“好像是”,是一種高境界的欺騙。觀眾恰恰需要這種“欺騙”。
這個精心設計的序幕從形式感上來說,做到了首尾呼應,從作曲家和歌劇主人公命運高度融合的悲劇性上來說,也是吻合的;但是,強加在作曲家和主人公身上牽強附會的性關系,完全是一種低劣的意淫,是一種惡俗的欺騙,不僅嚴重違背了19世紀浪漫主義音樂藝術的美學傳統,更違背了作曲家的創作意圖,拉低了觀眾的審美品位。其與第二幕第一場劇中劇《牧羊女的坦白》作曲家被迫為“兩只媾和的鸚鵡”蓋上大氅的橋段一起,都屬于執導上的敗筆。鳥類無羞恥,何須遮羞布?美國某歌劇院對柴科夫斯基的另一部歌劇《葉甫根尼·奧涅金》做出了顛覆性的改編,他們賦予男主角奧涅金全新的性取向,他拒絕塔姬亞娜求愛的直接原因,是因為他愛上了他的朋友、詩人連斯基,而且在舞臺上竟然有兩人同性相親的場面。而導演演繹的借口,正是作曲家本人的同性戀取向。這明顯是博庸人眼球,討低級趣味者歡心的噱頭。在馬林斯基劇院與美國大都會歌劇院共同打造的歌劇《戰爭與和平》的演出現場,為體現拿破侖大軍入侵俄國燒殺擄掠的惡行,竟然真的用一個裸體女性在舞臺上表演被強暴的情節。這與為觀眾們奉上血淋淋地牛心臟有何區別?歌劇場景不等同于電影鏡頭,可以吸取電影元素,但是不應該把暴力美學搬上歌劇舞臺。
二、精妙細致的戲劇解構
在筆者看來,該版創作最大的成功之處,也是最吸引筆者的構思,就是把作曲家搬上舞臺,把他創作《黑桃皇后》的心路歷程巧妙地與戲劇本身的進程糅合在一起,把戲劇主人公蓋爾曼的悲劇命運和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悲劇人生用戲劇手法重疊在一起,在道德層面上把柴科夫斯基和劇中人葉列茨基公爵做了合體。斯捷番·赫爾黑姆團隊對柴科夫斯基的原作進行了精妙解構,將現實和戲劇有效結合,成功詮釋了“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戲劇信條。
阿薩費耶夫曾指出:《黑桃皇后》創作的心理過程極具吸引力。導演團隊顯然是在研究了大量關于柴科夫斯基的文獻的基礎之上做出改編的。至少,其對作曲家創作這部歌劇的心路歷程是有研究的,對包括筆者的博士論文(著作)在內的《黑桃皇后》的創作排演的新的音樂學研究成果是了解的。筆者在博士論文的第二章“柴科夫斯基,蓋爾曼形象的首位詮釋者”(П. И.Чайковский как интерпретатор образа германа)即對柴科夫斯基歌劇創作的心路歷程,以及對蓋爾曼人物的態度作了翔實的考證和論述。
從柴科夫斯基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發現《黑桃皇后》這部從1890年1月18日至3月15日共用了44天的歌劇的創作過程并不順暢,有時甚至可以說是備受煎熬。部分摘錄列表如下:

表1

續表
在歌劇的創作進程中,伴隨著作曲家內心巨大的起伏、難抑的淚水、沸騰的創作熱情和飽脹的自我滿足感,同時還伴隨著對作品完美性的模糊預感。有時創作過程顯然受到作曲家心情和健康狀況的影響,甚至暴露出精神世界的惶恐不安。2月16至18日,作曲家的心情甚至達到憤怒的程度。在日記中清楚地記錄著歌劇煞尾前三天里作曲家的創作狀態。
俄羅斯學者塔基亞娜·瑪爾施科娃(Татьяна Ивановна Маршкова)認為:“柴科夫斯基以自己全部痛苦、憂郁的靈魂同情自己的主人公,那實際上就是他第二個自己。”從這個角度上,作曲家柴科夫斯基與劇中人蓋爾曼已經做到了某種精神上的契合。在戲劇中,兩個人物都在社會的威壓下掙扎并最終走向毀滅。
在該版歌劇中,演員烏拉基米爾·斯托亞諾夫一人分飾作曲家柴科夫斯基和葉列茨基公爵兩個角色。在第一幕第一場中,一直在舞臺上呈現創作狀態的作曲家轉換角色成為劇中這位剛訂婚的“幸運的”公爵,向朋友們驕傲地介紹自己的未婚妻。在即將結束本場舞臺使命時,葉列茨基被妒火中燒的情敵蓋爾曼強壯的胳膊奮力一拽,重新帶回作曲家角色的創作現實中。在第二幕第一場,作曲家化身葉列茨基對自己的未婚妻表白:“我愛您,我如此地愛您,沒有您我一天都過不下去,我胸中涌動著無窮的力量準備馬上奉獻給您!”在第三幕第三場,作曲家化身葉列茨基在牌桌上與情敵蓋爾曼決戰,以正義者的身份對蓋爾曼迷失的靈魂進行宣判。如此,現實中的作曲家和劇中人葉列茨基公爵得以合體。筆者以為,葉列茨基是道德的化身,他身上沒有污點,甚至在濫賭成風的年代,他從來沒進過賭場(他最終進入賭場是帶著終結蓋爾曼迷失自我的使命)。本來,葉列茨基與麗薩是門當戶對最為般配的一對,怎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麗薩的心許給了鬼迷心竅的蓋爾曼。柴科夫斯基的心靈無疑也是高潔的,這當然與性取向無關。葉列茨基充滿憐惜地擁著將死的情敵蓋爾曼,正傳達了柴科夫斯基對待蓋爾曼的態度:“蓋爾曼甚至是可愛的……蓋爾曼咽氣的一瞬間,我哭得一塌糊涂。”
除此之外,在該版三幕七場的戲劇進程中,柴科夫斯基作為戲劇的締造者始終在舞臺上占據重要的位置,他時而奮筆疾書,時而手舞足蹈,時而慨然試奏,時而亢奮指揮,時而掩面悲泣,時而昏厥倒地……柴科夫斯基的創作過程、創作狀態和創作心路歷程與戲劇進程緊密糅合在一起,作曲家在舞臺上既是看客,也是戲中人,是悲劇的締造者,更是悲劇的主人公。
伯爵夫人是“黑桃皇后”的化身,“黑桃皇后”的牌語就代表著厄運和死亡。這也是普希金小說原作命名的緣由。在普希金的原作中,除了伯爵夫人之外,麗薩和蓋爾曼都沒有死,麗薩嫁了別人,蓋爾曼進了瘋人院。《黑桃皇后》的劇本作者、作曲家的弟弟莫杰斯特·柴科夫斯基曾就歌劇結局和主人公的命運問題和作曲家產生過一場爭論:莫杰斯特贊同保留原作蓋爾曼瘋癲的下場,但是彼得·柴科夫斯基卻固執地堅持讓蓋爾曼和麗薩必須死亡。彼得·柴科夫斯基認為,如果蓋爾曼不死,他就不會意識到自己的墮落,他的靈魂就不會得到澄清,歌劇的主旨就得不到升華,要知道瘋癲之人是不會有悔過之意的。而麗薩之死加深了悲劇性和強化了戲劇沖突,從道德高度升華了這位俄羅斯女性的悲劇形象。所以,這場三人(麗莎、蓋爾曼、伯爵夫人)殞命的悲劇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一手締造的,這就能夠理解,作為劇中人和看客,作曲家要頻頻阻止事態發展。作為這場悲劇的導演,唯有他是知道結局的,作曲家眼見事態在因果中朝惡性方向發展,三個人物逐步滑向命運的深淵,雖然充滿著憐憫,卻無力拯救他們。而眼前人物命運的發展,也正是柴科夫斯基本人死亡預見的自我感知,作曲家幾次精疲力竭的倒地,都是這種矛盾心態的反映。讓蓋爾曼和麗薩、蓋爾曼和伯爵夫人三人交織凝結的矛盾潛藏、激化、碰撞、毀滅,恰恰印證了“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魯迅語)的悲劇本質,只是作曲家自導自演的悲劇從頭至尾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自己看!而該版歌劇的導演則是把作曲家導演的悲劇和他自身的人生悲劇,塑造成有價值的藝術品毀滅給別人看!
三、含義雋永的道具
斯捷番·赫爾黑姆團隊將舞臺道具的寓意運用到了極致,幾乎每一件舞臺上出現的道具都是含義雋永的。比如,八音盒鳥籠子就是一個被賦予深層使命的重要道具,它其實暗示著當時俄羅斯封建制度的禁錮,這個“會唱歌的鳥籠子”隱喻的是貌似歌舞升平的沙俄封建帝制。正是這個“鳥籠子”導致了階級分化,造成了求而不得的痛苦,造成了個體與制度的碰撞和個體的灰飛煙滅,是造成蓋爾曼和作曲家柴科夫斯基悲劇的終極原因。無論是劇中人蓋爾曼,還是現實中的作曲家,他們都是籠中之鳥,他們渴望飛出鳥籠、脫離桎梏,但是獲得自由的代價就是自我毀滅,是被人制成一把羽毛扇。第二幕第一場,蓋爾曼偽裝的“女皇”被作曲家扯下了華麗的罩衣,正是揭開統治者的偽善面具,揭露他們貪婪本質的歌劇創作主旨的體現。

作為道具,水杯在這版歌劇中處于重要的地位。水杯之水淹沒了麗薩,毒死了伯爵夫人,毒死了作曲家本人,它是殺死柴科夫斯基的元兇。無論官方的“生水致病說”,還是奧爾洛娃的“服毒自殺說”,都離不開這杯水。“上善若水”,但卻被賦予殺人的使命,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反諷性。仆人們手中端著的不是水,是公堂的飛沫、偽善的眼淚和唾棄的口水。第三幕第一場,三位身上插著羽毛筆鮮血淋漓的作曲家的幽靈出現,把另一個寓意深刻的道具的寓意提升起來——羽毛筆,它既是作曲家手中的創作工具,又是誅人于無形的可畏人言。而搖晃著的噴著霧的吊燈在視覺上產生的不穩定感和音樂張力所營造出的恐懼氛圍,為伯爵夫人幽靈的出現堆積氣氛,其形似東正教牧師手中的法器,也暗喻宗教信仰在蓋爾曼精神世界中地位的動搖和坍塌。而從頭至尾在舞臺上擺放的鋼琴,既是作曲家創作的工具,又是現世的我及其主宰的三位主人公的生命歸宿——棺材。三張紙牌和作曲家的三份樂譜合體的含義,筆者忖度,意喻牌賭是蓋爾曼的宿命,作曲則是作曲家的天職。
結 語
蓋爾曼在彌留之際向葉列茨基公爵虔誠懺悔,化身天使的麗薩溫柔地俯視著她的愛人……歌劇精神主旨最終在懺悔和寬恕的宗教氛圍中得到升華,一切矛盾仿佛都和解了。但是蓋爾曼在歌劇中向眾人投擲出的問題,仿佛還在回蕩:“Что наша жизнь?”(我們的人生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Игра!”(賭博!) 終場,葉列茨基公爵拔搶和托姆斯基公爵玩起了輪盤賭,其實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正如蓋爾曼的“獲獎”感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誰不是在玩一場死亡的游戲?俄語“Игра”的釋義寬泛,有“賭博、游戲、表演、演奏、比賽、手段”的含義。我們不禁捫心自問:“我們的人生究竟是什么?”這是擲給全人類的永恒的哲學命題!在“Игра”的多重釋義中,可以單選,可以多選,當然也可以棄選。
2003年6月23日法國報紙《行板》刊出一則消息:圣彼得堡愛樂樂團藝術總監、著名指揮家尤里·杰米爾卡諾夫因為不堪忍受法國里昂歌劇院篡改得面目全非的《黑桃皇后》而憤然棄棒離去,在訪談中他發出了“歌劇這一藝術體裁正在走向滅亡”的哀嘆!“導演們擯棄他們以為公式化的演出(自以為是好事),試圖以劇情討好觀眾,復興歌劇,顧盼戲劇舞臺和電影藝術,卻不知丟掉了感覺的標尺,給歌劇混入其他體裁的血液,最終結果混亂不堪,給歌劇質量和聲樂層面的水準帶來災難性的影響……毀滅了音樂中承載的精神和思想。這種現象和力量,使得歌劇的面貌變得丑陋不堪,給歌劇藝術判了極刑。”作為在歐洲歌劇舞臺上征戰十余年的馬林斯基劇院劇院歌劇藝術家,阿列克賽·斯捷波連科憂心忡忡,卻一語中地,直指要害。
做經典歌劇的衛道士,還是做時代審美的弄潮兒?其實抉擇不是非黑即白,只選一極。保持經典的本真面目,將會失去大部分新生代觀眾,顛覆性的解構改編則有悖傳統,違背原作的創作意圖,讓經典不再。如果說蓋爾曼擲出的是“我們的人生是什么?”的命題,那么,導演斯捷番·赫爾黑姆向我們擲出的卻是“我們的歌劇藝術如何發展”的嚴肅命題。筆者以為,這種建立在史考和音樂學考據結論基礎之上對原作進行的創新性解構,尚可行!
(作者附言:本文系2020年度黑龍江省教育科學規劃重點課題本科高校項目“俄羅斯歌劇藝術的發展及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示”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GJB1422662。)
注 釋
①(Игорь Глебов). Чайковский. Опыт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Пг.: Светозар, 1921. С. 35.
②Неизвестный Чайковский.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Сост., комм., вст. ст. Т. И. Маршкова. М.: Эксмо, 2010. С.152-153.
③,Чайковский П. И., О музыке, о жизни, о себе,Л.1976 г. 272 с.
④Альшванг А. А. П. И.Чайковский. Изд. 3-е. М.: Музыка, 1970. С.625.
⑤〔俄〕阿列克賽·阿列克賽維奇·斯捷波連科著,孫兆潤譯《歌劇歌唱藝術:意大利聲樂學派(三)——聲音“陛下”》,《歌唱藝術》2021年第5期。
⑥Сунь Чжаожунь. Герман П. И. Чайковского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выдающихся певцов XIX-XXI веков. Монография.-СП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ГПУ им. А. И. Герцена, 2013. -180 с.
⑦摘自:Чайковский. П.И. Дневники. 1873-1891. М.; Пг.: Музгиз,1923. СПб.: Эго, Северный олень, 1993. С. 251-258.
⑧Маршкова Т. И. 《Я всегда полон тоски по идеал》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Чайковский.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Указ. изд. С. 9.
⑨Чайковский М. И. Жизнь Петра Ильича Чайковского (1885-1893) Т. 3. М.: Алгоритм, 1997. С. 341.
⑩同注⑤,第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