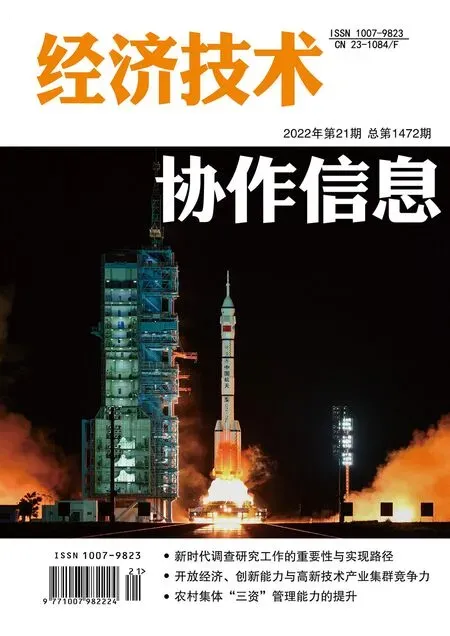開放經濟、創新能力與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競爭力
——基于中介效應的檢驗
◎孫治宇 劉思杰 余曉攀
一、引言
世界許多發展實踐都已證明高新技術產業集群是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增強國家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自1988 年第一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立后,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集群也依托高新區的建設而快速發展起來。2020 年末,我國已建成國家級高新區169 家,聚集了近10 萬家高新技術企業,出口額達到6484.4 億美元,占全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例超過80%,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但與美國硅谷、英國劍橋科技園等世界知名產業集群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集群仍然存在創新能力不強、技術水平不高、價值鏈分工地位偏低等問題。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擴大開放,立足國內大循環,協同推進強大國內市場和貿易強國建設,形成全球資源要素強大引力場,加快培育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在更廣范圍更大空間配置創新資源、提升創新能力提供了機遇。那么,開放經濟發展、創新能力提升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競爭力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持續的擴大開放能否促進集群創新能力的提升?本文將圍繞這些問題利用我國各省市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的數據展開實證研究,以期能夠為開放經濟條件下推進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發展提供可行思路。
二、文獻綜述
國外有關產業集群競爭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英國新古典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他認為外部經濟性促進了企業在特定區域的集聚,造成了技術的外溢和生產成本的降低,從而使產品在市場更具競爭力。Weber的工業區位理論從區位因素的角度指出產業集群的優勢來自于同產業的地方集聚效應。Krugman 的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指出規模報酬遞增基礎上的集聚規模擴大造成的成本降低促進了競爭力提升。Porter(1990)提出的“鉆石模型”與Padmore & Gibson(1998)提出的GEM 模型從多因素視角研究了產業集群競爭力的決定,此后許多研究都沿用了這種分析思路。J?rg Meyer-Stamer(2003)從微觀、中觀、宏觀和兆觀四個層面解釋了產業集群競爭力來源,O'Mahony(2009)、Capaldo(2014)分別實證檢驗了知識網絡與地理鄰近與集聚對集群競爭力的影響。
國內學者關于產業集群競爭力的研究始于20 世紀90 年代末,仇保興(1999)認為依賴于小企業集群內部信任和承諾協作提高了企業的效率和市場競爭力;王緝慈(2001)認為可以從外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信任為基礎的經濟網絡關系和知識與技術的擴散與創新三個方面來分析產業集群的空間集聚優勢;魏守華(2002)認為集群競爭優勢來自生產成本、產品差異化、區域營銷、市場競爭以及區域創新能力等經濟要素;吳松強(2018)研究發現知識搜索可以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對創新的影響作用,國內外研究的看法基本一致,即創新將會推進產業集群競爭力的提升(Fagerberg,1987;王述英,2006;張揚,2017)。開放經濟方面,有些學者研究了開放度的影響(徐康寧,2001;李亞雄,2006),有些學者研究了 FDI 的作用(沈坤榮,1999;夏京文,2009),基本觀點是經濟的開放會促進產業集群競爭力的提升。
國內外關于關于開放經濟、創新能力對產業集群競爭力影響的研究也很多,但對于對外開放影響集群競爭力過程中,創新所發揮的中介傳導作用的研究并不多。全球一體化使集群企業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創新資源,利用更廣闊的國際市場空間加快創新產品的效益實現。因此,深入研究對外開放對產業集群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兩方面的作用機制,在雙循環發展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際意義。
三、開放經濟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狀
(一)開放經濟發展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尤其是2001 年加入WTO 以后,進出口貿易增長更加迅速。2020 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額達到2.59 萬億美元,較入世前2000 年增加了10.4 倍,年均增長13.11%。同年貨物貿易進口額達到2.07萬億美元,較入世前2000 年增加了9.2 倍,年均增長12.38%,連續多年成為世界進口第二大國家。

圖1 中國進出口貿易發展(2000-2020)
利用外資方面,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始終保持較快增長,2000 年,FDI 總量為 407.2 億美元,2020 年達到 1443.7 億美元,增長了3.5 倍。

圖2 中國外商直接投資(2000-2020)
(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狀況
隨著科技研發力量的不斷提升,我國在技術領域取得了越來越多的突破,高新技術產業獲得快速發展。尤其是“十八大”以來,隨著“創新發展”理念的不斷深入,高新技術產業總體規模不斷壯大。2014 年,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營業收入為21.4萬億元,到2020 年,增加到52.08 萬億元,增加一倍多,年均增速達到15.7%。而同期產業凈利潤增速達到16.0%,規模與效益均保持較高速增長。

圖3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主營業務收入與凈利潤(2014-2020)
四、模型構建及變量說明
(一)模型構建
1.獨立效應模型。
為驗證開放經濟與創新能力對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競爭力的獨立影響,我們分別建立包含開放經濟變量和創新能力變量的面板數據模型進行檢驗,模型如下:

在式(1)、(2)中,i、t分別代表地區和年份,μit、εit表示模型的隨機擾動項。HICCit表示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競爭力,OPENit表示地區開放經濟發展程度,INNOit表示創新研發能力,β1、θ1分別表示開放經濟與創新能力對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的獨立影響力。
2.中介效應模型。
中介效應實際是考察原因變量是否通過中間變量影響了目標變量,我們所關注的是開放經濟是否以創新能力為中介影響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的競爭力。借鑒江艇(2022)的研究,建立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三)變量說明與指標選取
1.被解釋變量。
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競爭力(HICC)。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具有競爭優勢的體現是其產品具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企業有著較強的獲利能力、產業集群具有一定的規模水平以及較強的技術增值能力,因此,使用各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的營業收入占全國比重、凈利潤與年末資產總額比值、產業資產總額占全國比重、技術收入全國比重表示地區產業集群的市場占有率、獲利能力、產業規模水平、技術收入四個方面的競爭優勢,并使用熵值法得到集群競爭力綜合指數。
2.核心解釋變量。
開放經濟(OPEN)。集群開放度的本質是集群企業參與國際分工體系的深度與廣度,如果集群企業產品在市場具有競爭優勢,其產品出口就會更多,因此使用地區高新技術產業出口與其營業收入的比值代表開放經濟。
創新能力(INNO)。創新能力源于創新投入、技術轉化、創新績效與創新發展四個方面,分別使用R&D 投入與營收比值、單位孵化器畢業企業數、技術收入與R&D 人員全時當量比值、R&D 人員占從業人員比例代表這四方面要素,并使用熵值法得到創新能力綜合指數。
3.控制變量。
產業聚集度(區位熵LQ),計算方法為:

Hjt為j省t年高新技術企業營業收入,GDPjt為j省t年GDP。LQ≥1,高新技術產業在該地區相對集中,LQ<1,集中度較低,LQ值越高,集聚水平越高。
資本深度(LACA),即資本勞動比,以產業年末資產總額與職工總數之比表示;地區金融發展水平(FINA),以地區金融機構年末存貸款余額占GDP 比重表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RGDP)用人均GDP 表示;企業規模水平(SCAL),以產業工業總產值與企業總數之比表示。
(四)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選取全國30 個省市自治區2014-2020 年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和地區經濟指標(西藏有數據缺失,故剔除),數據來源于《中國火炬統計年鑒》和中國經濟網《產業數據庫》,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下表1 所示。

?
從表1 可以看出,各地區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其中金融發展水平差距最小,企業平均規模、地區開放程度等方面差距較大,說明各地區經濟、貿易、科技等方面發展不平衡。
進一步對自變量相關性進行檢驗,考慮量級的可比性,分別對資本深度、金融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企業規模水平四個實體指標取對數,檢驗結果如表2。

?
從結果來看,絕大多數系數絕對值小于0.5,可以忽略自變量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對實證產生d 影響。
五、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獨立效應檢驗
使用模型(1)和模型(2)分別檢驗開放經濟與創新能力對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競爭力的獨立效應,因為兩個模型都是單要素回歸,因此回歸分析時使用混合模型,結果見表3。

?
從實證結果可以看到,開放經濟對集群競爭力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融入全球分工體系,企業效益增加的同時,也面臨激烈的外部競爭,要求企業必須加強技術創新才能在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同時,外資的進入促進了本土企業技術水平與生產工藝的提升,推動了集群競爭力的提升。創新能力也對集群競爭力有著顯著促進作用。一方面技術創新提高了集群企業生產效率,另一方面新技術新產品能夠形成一定的市場壟斷優勢。
進一步驗證開放經濟影響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競爭力的創新能力中介效應。使用模型(3)、(4)、(5)分別進行回歸,結果見后表4。
模型(3)結果說明,開放經濟對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競爭力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也預示開放經濟對集群競爭力的影響可能存在中介效應。從模型(4)可以看出,開放經濟對集群創新能力產生了顯著的影響,但其結果卻是顯著抑制創新能力的提升。從模型(5)的結果看,開放經濟與創新能力對集群競爭力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綜合以上結果可知:開放經濟對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競爭力的影響存在中介效應,但開放經濟通過創新能力的傳導并不是強化了其對集群競爭力的促進作用,反而是使其直接正向影響的效果有所下降,原因就是開放經濟的發展抑制了集群創新能力的增強。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主要原因可能考察周期的長短不同所致。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在諸多產業領域的生產技術都與發達國家有著較大的差距,通過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與再創新,促進了企業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的提升。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在各方面的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都有了較大的提升,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也不斷縮小。這種情況下想引進更高端的技術已經十分困難,原因是這些技術正是發達國家公司保持市場競爭優勢獲取高額壟斷利益的根本。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會通過購買者約束(buyer resistance)和資源約束(resource requirements)等手段限制我國企業開展自我創新來提升技術水平,國外政府也通過各種非市場手段實施“產業阻擊”,限制我國企業獲得創新資源。因此,進一步的對外開放短時期內使得本土企業在開展自我創新活動受到打壓和限制,創新能力反而受到了抑制。但長期看,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企業面臨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創新資源更多機會,從而會推動創新能力的提升。

?
考察其他變量的影響,從模型(5)可以看到,產業集聚程度對集群競爭力有著較為顯著的影響,說明產業集聚度越高的地區其產業集群就越有可能獲得更高的競爭優勢。企業在空間的高度集中,能夠促進企業相互間生產與服務的暢通銜接,推動集群企業間技術貿易、技術合作、聯合開發的進程,從而帶來成本降低和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資本勞動比的提高對集群的競爭力起到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在技術不變條件下,人均資本增加帶來的產出往往呈遞減增加態勢,企業集聚催生的激烈市場競爭和產品價格下跌也限制了企業生產擴張,帶來集聚區域規模報酬遞減。金融業發展對集群競爭力沒有起到有效的促進作用,說明我國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體系對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的支持仍存在較為嚴重的缺位。經濟發展水平對地區高技術產業集群的綜合競爭能力有著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科技創新和技術研發投入水平越高,同時能夠吸引更多的投資和人才聚集,從而推動地區產業生產效益和競爭力的提升。企業規模對產業集群競爭力的影響并不顯著,說明企業競爭力并不以規模為決定因素,過于龐大的組織機構往往存在信息傳遞損失、投資決策拖延、市場應對滯后等問題,反而不利于其抓住市場機遇獲取競爭優勢的目標實現。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全國30 個省市自治區的數據驗證了開放經濟與創新能力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競爭力的影響,結果發現,對外開放和創新能力的提升能夠促進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競爭力的提高,同時以創新能力為中介的傳導作用反而使開放經濟對集群競爭力的促進作用有所下降。但這種下降是短期效應,長期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加快構建背景下,加大對外開放能帶來創新能力的提升。
研究結論的啟示是:第一,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已深度廣泛嵌入到全球生產體系中,加大開放力度短期看可能會對集群企業的技術創新造成一定的沖擊,但長期會推動創新能力的提升。第二,堅持國內大市場建設。擴大對外開放可以使本國企業充分利用好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也勢必帶來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在當前國際環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背景下,應當加強國內大市場建設,以國內需求滿足集群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資金回流的需要,形成技術創新的良性循環,不斷提升集群企業自我創新能力。第三,持續推進技術創新。未來市場競爭是技術的競爭,創新能力的競爭。加大科技研發力度,不斷推進技術水平的提升,是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增強產業集群競爭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要加強應用技術的研發,重視基礎技術和關鍵技術的攻關,構建多元化技術創新體系,增強綜合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