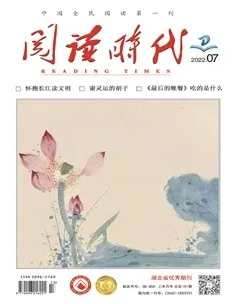她在詩的花園里侍弄一生
梁霄

《狄金森書信選》中收錄的第一封信,寫于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12歲時。那是1842年4月,艾米莉在信中告訴她離家的哥哥奧斯汀:“母雞相處和睦,小雞長得飛快。恐將矗成龐然大物,若你歸家,凡眼不識大雞。”
哥哥奧斯汀是艾默斯特學院的學生,若干年后,他將追隨父親和祖父的職業追求,成為一名備受小鎮市民尊敬的嚴肅律師。與哥哥相比,艾米莉在童年時期并未肩負許多家庭責任。
除了在信中向哥哥詳細記錄自己今天又收獲多少枚雞蛋之外,艾米莉最大的興趣在于閱讀、烘焙、練習鋼琴與園藝。事實上,這些愛好伴隨著她的一生。即使在1862年,艾米莉寫下“靈魂選擇她自己的社群——然后——關上大門……”我們依然無法武斷地揣測,艾米莉也將這些愛好關在了門外。
艾米莉·狄金森讀過最多遍的書應該是欽定本《圣經》,這不僅僅是因為艾默斯特鎮頻繁的宗教活動——像許多清教徒家庭一樣,艾米莉在13歲那年從父親那里得到了屬于自己的第一本《圣經》。
《圣經》是艾米莉最初的文學養料,她讀了又讀,經常從記憶中引用。《圣經》里的故事和人物不斷出現在她的信件和詩歌中。“圣經是一本古老的書——/被逝去的人寫成”,艾米莉甚至曾單為《圣經》作詩一首。
另一個艾米莉終生閱讀的主題是莎士比亞,她參加了一個由艾默斯特的年輕人組成的閱讀小組,他們在集會時大聲朗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不過艾米莉永遠也沒有想到后世會將她與莎士比亞相提并論,美國著名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認為:“除了莎士比亞,狄金森是但丁以來西方詩人中顯示了最多認知原創性的作家。”
1845年5月,艾米莉在致朋友亞比亞·魯特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的植物長勢良好。附上一小片天竺葵葉,請為我壓干。”這里無意間泄露了艾米莉的秘密。15歲時,她或許已經掌握小鎮自然中的一切植物。
艾米莉終生都在父親建于“家宅”后面的溫室里玩賞侍弄,“我的花草鮮茂”——她時常向朋友描述花園的近況,又在冬天來臨時擔憂地詢問別人,“你還有鮮花嗎?”
艾米莉在艾默斯特中學就讀期間,著名地質學家愛德華·希區柯克成為院長,許多學生注冊了他的課程。希區柯克在課堂上講授火山、化石和巖層,這構成了艾米莉對于自然物理本質的理解,而阿爾邁拉·哈特夫人在植物學上對艾米莉的指導,又促使她擁有了第一本植物標本集。
后來,艾米莉開始在文字中以前所未有的植物學精度描繪花草。1882年10月,艾米莉輕盈地在信中向朋友訴說:“蜀葵把衣物扔棄一地,我忙著撿拾莖和花蕊。”因為熱愛園藝,艾米莉熟悉氣候、季節的變化,敏感于晝夜交替,也善于辨認棲息在植物間的蜜蜂、蠅蟲與鳥類。這一切都反映在她的詩中。
14歲時,狄金森對亞比亞·魯特想要“完成”一項教育的想法一笑置之——“到時你可能是柏拉圖,而我將是蘇格拉底”——她這么嘲弄自己的好友。
艾米莉的父親重視子女的教育,她早期的學校教育課程包括文學經典、拉丁語、數學和植物學。從艾默斯特中學畢業后,成績優異的她離家前往十英里之外的南哈德利就讀曼荷蓮女子學院。又是在和魯特的通信中,艾米莉巨細靡遺地記錄下自己當時的生活:
我們早上六點起床。七點吃早餐。八點開始學習。九點,學院大廳集合祈禱。十點一刻,背誦一篇古代史評論,聯系閱讀的哥爾斯密與格里姆肖。十一點,記誦蒲柏《人論》選節。十二點,體操運動……
艾米莉為自己在信中“有那么多廢話要講”而歡欣鼓舞,然而在曼荷蓮女子學院就讀一年以后,出于某種學者至今仍在揣測的原因,她再也沒有返校。
十年后,魯特選擇了婚姻所期望的角色和責任,而艾米莉則剛剛開始寫她的詩。
無論如何,艾米莉覺得她一生的教育永遠“尚未完成”,而她也要繼續在詩中說她的“廢話”。我們無法追究詩在艾米莉的生活中真正發生的具體時間,學者認為很可能是在1855年(她在1850年收到一本愛默生的詩集作為禮物,似乎從那時開始寫詩),正是在這一年,艾米莉在“家宅”擁有了自己的臥室,二樓西南角的房間,而一張只帶著一個抽屜的木桌成為整個房間里被使用最多的家具。
哥哥奧斯汀于1856年結婚,和妻子蘇珊在“家宅”的毗鄰之地建起“長青居”,這為艾米莉帶來了更多的社交活動,人群讓艾米莉自由,也讓她感到焦灼。“很高興與姑娘們歡度一晚,但今天下午,我頗多拜訪,不留神,把心遺落沃納教授家。請為我的精神保留一角席位,就在溫妮(艾米莉的妹妹)后面。”這是艾米莉寫給蘇珊的信,她們二人隔著兩棟房子之間的草地互傳字條。在其中的一張上,艾米莉對蘇珊寫道:“我們之間的紐帶非常纖細,是一根永遠不會溶解的頭發。”
日常生活的迅疾改變讓艾米莉·狄金森對命運變得敏感,自然時間與社會時間相互交疊,命運的步履加快了節奏。她開始面對擴大的家庭關系和不再封閉的社會空間,一顆備受呵護的心靈初次展開對外部的體驗,破碎的思緒撿拾起語言的骨血,這激發了真正的寫作,并在隨后持續數年。
艾米莉35歲的時候,她已經創作了超過1100首簡潔有力的詩歌(目前留存于世的詩歌共有1789首)。在這些詩歌所能抵達的最小的讀者范圍內,艾米莉審視著自然和藝術,反復質詢道德和信仰:一道被生活割破的傷口在她的詩歌中更加真實,而倘若任何追問被施加了期限和條件,那么它將無法在艾米莉那里得到回答。
如果“詩藝”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是做到“一件不可能發生但卻可信的事比一件可能發生但卻不可信的事更為可取”,那么艾米莉在詩中談論的那無法握著的“心”,那個“我為美死去”的事實,是不可能發生但卻可信的嗎?是什么在艾米莉的詩中充當了“不可能發生”與“可信”的分界點?
文學的修辭首先作為外涌的力量召喚了動人心魄的想象——青苔掩蓋了那些為美和真理而死的人的名字,而從甘愿為美殉身的“我”到達一種心靈交匯的良善,則需仰賴存在于詩歌里的詩人自己,是作為“我”出現在詩歌里的艾米莉·狄金森使我們相信,這個在一張從律師辦公室里隨手拿來的商業便簽上寫字的詩人,所說的一切都是可信的。
詩人的主體性和她的經驗不僅決定了語言的排布、詩行的韻腳,更決定了詩的情感邏輯能否讓詩不再成為一種“鬼演”,從而落腳于真實。恰恰因此,在歷史資料里研究詩人將永遠走向殊途,如果想與艾米莉相逢,不要踏上“家宅”里那個窄小陡峭的通往二層的樓梯——事實上,前來拜訪詩人的友客后來只能站在樓梯下與她對話,艾米莉其實躺在那座為美而死的墓中。
接下來的艾米莉·狄金森已經成為那位后世熟知的“奇人”。1865年以后,艾米莉不再大量寫詩,她杜絕一切社交活動,穿上一身白袍。除了因為治療眼疾而外出的幾次短途旅行,艾米莉再沒有踏出“家宅”的大門。
她寫給別人的信越來越短,留在文字里的時間也越來越短,或許是因為身體上的病痛,或許是因為與她通信多年的朋友接連去世。艾米莉·狄金森的一生與死亡如影隨形,她的父親死于1874年,母親死于1882年,哥哥的孩子吉伯在8歲時死于傷寒,那是1883年,而某個她可能愛過的法官死于1884年。
“死亡的深淵對我來說太深了,我的心還來不及從一個深淵爬起來,另一個就已經來了。”這一年,艾米莉在寫給朋友的信里說。如果我們在死亡龐大的陰影中再次談起“詩藝”,它將再也無關于符號、隱喻和命題,“詩藝”化身為一個簡單有力的動作,在雙腳還沒有被泥土掩埋之前,作出博爾赫斯所言的“嘗試”:“我們嘗試了詩;我們也嘗試了人生。而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說,生命就是由詩篇所組成的。”
艾米莉·狄金森因“布萊特氏病”(某種腎臟疾病)死于1886年5月。就在這一年春天,她還寫信給自己的姑媽伊麗莎白·狄金森·柯里爾:“藏紅花斗志昂揚,水仙花舒展到第二個節,讓我們攜手康復。”
艾米莉可能還沒有見證這年春天最茂盛的景象,馬薩諸塞州的雨水太多,夏季短,冬季漫長,若干年前,當她在凋敝的園中行走,找不出一朵可以壓干送給朋友的黃花時,無聲和細小的時間已經向詩人宣告了勝利。
面對死亡,艾米莉說自己“駐足在一幢屋前”,那屋頂似乎僅能“微微入目”“檐口飛張于地”。走入這幢屋子對于一位勇敢的詩人來說,就好像只是搬了一次家。托馬斯·溫特沃斯·希金森,這位艾米莉欽仰的導師,在葬禮上朗誦了艾米莉所喜愛的另一位艾米莉·勃朗特寫的詩,詩里說,“我沒有怯懦的靈魂”。
1845年,那是艾米莉只有15歲的時候,“她學習蜜蜂的拼寫,學習玫瑰的數學,她記住花園里生長的每一種東西的歷史”(摘自《詩的一生》),但與此同時,一雙篤信萬物有靈的眼睛又在對那些注定只存在于思想中的事物展開抽象觀察。在一封信里,她鄭重其事地寫下:“我真的相信,時間的車輪一定抹過了油,我記不起他何時經過。”
時間造成了一種物理性的改變,它的理智和堅定能讓樹的年輪一圈又一圈增長,讓裂縫爬滿磚石,讓一件或許拒絕了愛情的白袍泛黃。此時此刻,我們可能僅僅剩下了那張只帶著一個抽屜的木桌。
想象艾米莉·狄金森吧,她伏在桌前樸素地勞作,握筆的手凝成一個時間無法毀滅的姿勢——只能同情那張書桌了,它舊得非常寂寥,等待它化為齏粉的世界里,詩人已經不在其中。“別淡忘你誠摯的朋友。”艾米莉說。
(源自“讀庫”)
責編:王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