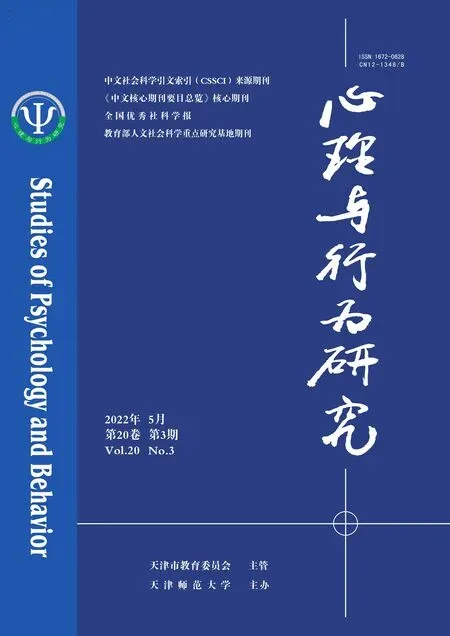歧視知覺對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的影響:多重中介效應分析 *
丁 倩 羅星雨
(信陽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信陽 464000)
1 引言
留守兒童指因父母雙方或其中一方在外地工作而被留在戶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雙方共同生活的18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趙景欣 等, 2013)。近十年,作為弱勢群體的留守兒童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留守兒童問題也引起了多個學科的廣泛關注。事實上,無論采取什么監護方式,留守兒童都面臨著一個共同問題,即父母一方或雙方長期不在身邊。在這種不利處境下,留守兒童經歷著內外化問題等諸多心理社會適應方面的挑戰(趙景欣, 劉霞, 2010)。作為一種典型的外化問題,攻擊行為既是留守兒童群體適應不良的突出表現(Hu et al., 2018),又嚴重影響青少年的身心健康(Wu et al., 2021)。因此,研究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與非留守兒童相同的是,留守兒童也面臨學業壓力、人際關系問題等負性生活事件,但不同的是,留守兒童由于社會經濟地位等原因往往體驗到更多的歧視(蘇志強 等, 2015)。歧視知覺(perceived discrimination)指個體由于自身所屬群體與主流群體不同而感受到區別對待的主觀體驗,這種區別對待可從他人的實際行為動作、惡劣的態度或相關不合理的制度中體現(劉霞 等,2011)。一般壓力理論認為,歧視是弱勢群體壓力的重要來源,而問題行為是應對壓力的一種策略,當他人沒有按照個體希望的方式來對待自己時,這種不良的關系可能導致攻擊等不良應對行為(Agnew, 1992)。也就是說,當留守青少年感受到來自他人的歧視時,隨之而來的壓力導致他們更容易采取攻擊的方式來應對。國內外研究證實,歧視知覺是產生攻擊行為的重要原因(傅王倩 等, 2016; Mulvey et al., 2021)。但以往研究在探討歧視知覺對攻擊行為的影響機制時,主要考慮的是單一情緒的作用(余青云, 張靜, 2018;Hartshorn et al., 2012; Xiong et al., 2021)。而歧視知覺引發的情緒往往是復雜的。因此,本研究基于一般攻擊模型,同時考察具有代表性的高喚起情緒和低喚起情緒—憤怒和抑郁,并將道德推脫作為影響決策的因素納入模型,以期為歧視知覺影響攻擊行為的作用機制提供情緒到認知決策的新視角。
1.1 抑郁和憤怒的中介作用
一般攻擊模型認為,情境因素輸入變量先通過個體的內部狀態,即情緒、認知、喚醒三個方面的作用,再經過個體的評估與決策,最終導致攻擊行為(Anderson & Bushman, 2002)。根據一般攻擊模型,歧視知覺作為情境輸入變量,可能經過情緒、決策等一系列心理過程,進而引發敵意性攻擊。
抑郁作為一種感到無力應對外界壓力而產生的消極情緒,可能在歧視知覺與攻擊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余青云, 張靜, 2018)。素質-壓力模型認為,個體易感性和外界壓力的共同作用導致了抑郁狀態(Zuroff et al., 2004)。歧視是留守兒童的壓力來源之一,高歧視知覺的個體對外界環境更加敏感,面臨著自身高易感和外界高壓力的雙重困難(劉霞 等, 2011; 余青云, 張靜, 2018)。因此,長期感知到歧視的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抑郁癥狀。研究也證實,歧視知覺正向影響青少年抑郁(李董平 等, 2015; Jiang & Dong, 2020)。而抑郁也會帶來攻擊行為等外化問題(陳益專 等, 2018;Beyers & Loeber, 2003)。抑郁造成的消極情緒調節困難可能會提高人際沖突(Wolff & Ollendick,2006);青少年抑郁甚至能預測未來故意傷人、殺人等犯罪行為(Kofler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抑郁在歧視知覺與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抑郁往往表現出情緒低沉、疲憊等癥狀,屬于低喚起情緒(Byrne, 1976),而憤怒屬于高喚起情緒(Russell & Mehrabian, 1974)。根據前人研究,相比于抑郁等低喚起類情緒,高喚起類情緒如憤怒對攻擊行為的作用可能更大(梁靜, 張耀華, 2020; 余青云, 張靜, 2018)。歧視知覺引發抑郁的同時,還可能引發憤怒。挫折-攻擊理論認為,挫折引起某種形式的攻擊行為(Dollard et al., 1939)。挫折是歧視知覺的產物,如果一個人得不到平等的對待,需求滿足受阻,憤怒的體驗可能導致攻擊行為。具體來說,歧視知覺致使尊重、歸屬、被愛等心理需求無法滿足,這種挫折會喚醒以憤怒為代表的眾多負性情緒,而憤怒是產生攻擊行為的重要原因(梁靜, 張耀華, 2020)。實證研究發現,情緒波動較大是青少年群體的主要特征之一(桑標, 鄧欣媚, 2015),歧視知覺使他們更易憤怒(Hansen & Sassenberg,2006)。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設2:憤怒在歧視知覺與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1.2 道德推脫的中介作用
根據一般攻擊模型,情緒會影響個體的評估與決策,進而導致攻擊行為(Anderson & Bushman,2002)。具體來說,抑郁和憤怒使個體在一定程度上產生認知扭曲(Johnson et al., 1992)。研究表明,憤怒使人們放松對自身的道德監控,造成認知扭曲,例如道德推脫機制(Caprara et al., 2013;Paciello et al., 2008)。道德推脫(moral disengagement)指個體在做出不道德行為時產生的認知傾向,包括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合理解釋以顯得傷害性小、減少自己的責任、降低對受害者痛苦的認同(Bandura, 1999)。通常,個體會使用自己的道德標準調節自身的行為,當個體行為與其道德標準相抵觸時,則產生內疚、自責來阻止其不良行為如攻擊,然而,道德推脫使這種道德的自我調節功能失效(Bandura, 2002),它使個體在違背自身道德標準時可以輕松推卸掉內疚感與自責感,從而表現出攻擊行為。大量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Kiriakidis, 2008; Pelton et al., 200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抑郁/憤怒和道德推脫在歧視知覺與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此外,歧視知覺也可能直接導致個體的道德認知扭曲,引發道德推脫。歧視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王芃 等, 2013)。感受到較高歧視的個體經歷著區別對待、體驗著惡劣態度(劉霞 等,2011),這是一種被不道德對待的經驗,而這種經驗可能會促使個體把不道德地對待他人看作是可接受的。類似地,研究發現,受虐個體更容易表現出道德認知扭曲(Koenig et al., 2004),把自己的不道德行為視為可接受的,產生更高的道德推脫(孫麗君 等, 2017)。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4:道德推脫在歧視知覺與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精神動力學認為抑郁是憤怒內化的結果(Bridewell & Chang, 1997),且抑郁青少年有時也會表現出易怒(Leadbeater & Homel,2015)。憤怒與抑郁在理論與實證上存在較高的相關性。而歧視知覺不僅使個體陷入抑郁(李董平等, 2015),還激發其憤怒(Hansen & Sassenberg,2006)。因此,本研究將二者共同納入模型,在二者之間建立相關,以考察高喚起情緒和低喚起情緒對攻擊行為的影響有何異同。綜上所述,基于一般攻擊模型和相關實證結果,本研究擬建構一個整合的多重中介模型,探討歧視知覺影響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的情緒和認知機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隨機抽樣,選擇安徽省某兩個鄉鎮的兩所普通初中和高中,從每個年級選取2~3個班級,篩選父母一方或雙方外出務工的18歲以下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回收有效問卷662份。其中,男生340人,女生322人;初中生219人,高中生443人;平均年齡15.96歲,標準差1.48歲。父母一方外出的196人,雙方外出的466人。就父親(母親)受教育程度而言,小學及以下占比31.6%(47.4%),初中占比55.9%(46.4%),高中或中專占比11.8%(5.7%),大學及以上僅占比0.7%(0.5%)。
2.2 研究工具
2.2.1 歧視知覺
采用謝其利等人(2016)修訂的個體歧視知覺問卷,單維度,共3個項目。采用從“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的5點評分,各項相加的總分越高表示個體體驗到的歧視知覺越多。本研究中,該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0。
2.2.2 抑郁
采用龔栩等人(2010)修訂的抑郁-焦慮-壓力量表的抑郁分量表,共7個項目。采用從“0=非常不符合”到“3=非常符合”的4點評分,各項相加的總分越高表示抑郁癥狀越嚴重。本研究中,該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8。
2.2.3 憤怒
采用李獻云等人(2011)修訂的Buss和Perry攻擊問卷的憤怒分量表,共6個項目。采用從“1=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的5點評分,各項相加的總分越高表示憤怒情緒越多。本研究中,該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4。
2.2.4 道德推脫
采用潘清泉和周宗奎(2010)修訂的兒童道德脫離量表,包含6個維度,共18個項目。采用從“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的5點評分,各項相加的總分越高表示道德推脫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8;道德合理化、責任擴散、有利比較、去人性化、歪曲結果和責任轉移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72、0.62、0.58、0.64、0.71和0.65。
2.2.5 攻擊行為
采用李獻云等人(2011)修訂的Buss和Perry攻擊問卷的身體攻擊和言語攻擊分量表,共12個項目。采用從“1=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的5點評分,各項相加的總分越高表示攻擊行為越嚴重。本研究中,兩個分量表總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8;身體攻擊、言語攻擊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3和0.79。
2.3 施測程序及數據處理
以整班抽取結合自愿參加的原則進行問卷調查,在施測前已取得學校領導、班主任及學生本人的知情同意。采用不記名方式,由經過培訓的心理學專業研究生詳細講解指導語后,被試在15分鐘內獨立作答全部問卷。采用SPSS25.0進行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采用Mplus8.3進行多重中介模型檢驗。此外,參考以往研究(傅王倩 等,2016; 李董平 等, 2015; 蘇志強 等, 2015),本研究將性別、年齡、留守類型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納入相關分析,并依據相關顯著性予以控制。
2.4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自我報告收集數據可能導致共同方法偏差問題。一方面,本研究在程序上通過匿名調查、適當變換反應語句等方式進行了一定控制。另一方面,本研究在統計上采取Harman單因素檢驗進行了共同方法偏差的檢驗。結果顯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8個,其中第一個因素解釋的累計變異量為27.87%,小于臨界值40%,說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3 結果
3.1 相關分析
以各變量的總分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表明,歧視知覺、抑郁、憤怒、道德推脫、攻擊行為兩兩顯著正相關(見表1)。

表1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矩陣
3.2 多重中介效應檢驗
在控制性別和留守類型的條件下,通過Mplus8.3建構結構方程模型,檢驗抑郁、憤怒和道德推脫在歧視知覺與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擬合結果顯示,模型的各項指標良好(χ2/df=3.57, TLI=0.93, CFI=0.94, RMSEA=0.06,SRMR=0.05)。歧視知覺顯著正向預測抑郁(β=0.51,SE=0.04,p<0.001)和憤怒(β=0.45,SE=0.04,p<0.001);歧視知覺(β=0.18,SE=0.05,p<0.001)、抑郁(β=0.32,SE=0.06,p<0.001)和憤怒(β=0.16,SE=0.05,p<0.01)顯著正向預測道德推脫;憤怒(β=0.87,SE=0.04,p<0.001)和道德推脫(β=0.24,SE=0.04,p<0.001)顯著正向預測攻擊行為,但歧視知覺(β=-0.01,SE=0.04,p>0.05)和抑郁(β=-0.07,SE=0.05,p>0.05)則不能預測攻擊行為(見圖1)。進一步采用偏差校正非參數百分位法在抽樣5000次的條件下對各條中介路徑進行檢驗,結果表明:抑郁、憤怒和道德推脫在歧視知覺與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起多重中介效應,其中四條路徑產生的間接效應顯著(見表2)。

圖1 抑郁、憤怒和道德推脫的多重中介作用

表2 中介效應分析
4 討論
本研究發現,歧視知覺對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的總效應顯著,這與以往研究的結果一致(傅王倩等, 2016; Mulvey et al., 2021)。留守兒童作為弱勢群體往往體驗著周圍人的歧視,導致其長期處于壓力之下,而攻擊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有效緩解壓力的途徑,這符合一般壓力理論的觀點(Agnew,1992)。以往研究也關注了歧視知覺對具有留守背景個體攻擊行為的影響,但更多關注的是大學生群體(劉鐵川 等, 2021; 余青云, 張靜, 2018)。本研究則顯示,這種不良效應同樣存在于青少年群體,該發現為歧視知覺影響留守兒童攻擊性提供了新的證據。
4.1 憤怒、道德推脫的簡單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憤怒、道德推脫分別在歧視知覺與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起簡單中介作用。首先,憤怒的中介作用符合挫折-攻擊理論,即挫折引起的憤怒和敵意會激起攻擊行為(Berkowitz,1989)。挫折是阻礙個人達到目的的外部情境或目的行為受阻而激發的心理緊張狀態(Dollard et al.,1939),歧視阻礙了歸屬、尊重等基本需求。因此,歧視知覺誘發憤怒,進而導致攻擊行為。其次,道德推脫的中介作用符合道德認知理論。留守青少年作為弱勢群體,在面對持續不公平對待,感知到歧視的時候,可能會放松對自身的道德監控(Koenig et al., 2004),產生道德推脫,將個體的不道德行為進行合理化(孫麗君 等, 2017),順理成章地做出包含攻擊在內的過激行為。此外,父母一方或雙方不在身邊可能造成家庭道德教育的缺失(王露璐, 李明建, 2014),留守兒童與其寄養監護者通常難以建立情感交流,使得憤怒缺乏有效的釋放途徑。因此,對留守兒童這一群體來說,憤怒和道德推脫是其攻擊行為的重要風險因素。
同時,本研究發現,歧視知覺不能通過抑郁的簡單中介作用影響留守青少年的攻擊行為,表現為抑郁對攻擊行為的影響通過道德推脫的完全中介作用來實現,這與陳益專等人(2018)的研究結果相似。以往有研究發現抑郁能直接影響攻擊行為(余青云, 張靜, 2018; Beyers & Loeber,2003),但本研究發現,這種關聯并不是直接的。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抑郁作為低喚起情緒,通常表現出情緒低沉、疲憊等癥狀(Byrne, 1976),使得個體沒有足夠的能量做出直接的、向外的攻擊行為,而是加劇了向內的攻擊,如自傷、自殺(余青云 等, 2021)。
4.2 憤怒/抑郁和道德推脫的鏈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憤怒/抑郁和道德推脫在歧視知覺與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支持了一般攻擊模型(Anderson & Bushman,2002)。憤怒和抑郁作為個體內部情緒因素,其帶來的認知扭曲可能會影響個體在做出攻擊行為前的評估與決策。具體來說,憤怒和抑郁造成個體在道德認知方面的失調,產生道德推脫,進一步加劇個體的攻擊行為。雖然,有研究者根據一般攻擊模型構建了“外部環境→道德推脫→攻擊行為”的作用鏈(孫麗君 等, 2017),但并未探討道德推脫的具體“角色”,而本研究則嘗試將道德推脫作為影響個體決策的認知因素引入模型。此外,本研究還從情緒因素的角度拓展了該作用鏈。從模型路徑系數來看,抑郁對道德推脫的影響要大于憤怒對道德推脫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憤怒作為一種高喚起情緒往往是爆發性的,而抑郁作為一種低喚起情緒具有彌漫性,也意味著更多的反芻思維(Nolen-Hoeksema et al., 2008),使個體有更多的時間為不道德行為找到合適的“借口”,這大大提升了道德推脫產生的概率。
總體來看,本研究結果支持高喚起情緒憤怒比低喚起情緒抑郁對向外的攻擊行為的作用更大的觀點。以往也有研究發現,低喚起情緒抑郁對向內攻擊比向外攻擊的作用更大(余青云 等,2021)。可見,同時考慮兩種情緒或兩種行為可以更好地比較情緒的作用特征。事實上,不僅抑郁會影響向內的攻擊,憤怒也會影響向內的攻擊如自傷(丁倩, 羅星雨, 2022)。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嘗試同時考察高喚起情緒憤怒、低喚起情緒抑郁對向內攻擊和向外攻擊的作用,進一步理清不同喚起情緒對不同指向的攻擊行為的作用。
4.3 研究不足與意義
本研究存在著一些局限性。其一,雖然本研究建構的中介模型基于一定的理論基礎,但橫斷研究不能完全推斷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未來研究可以采用實驗方法或縱向數據進一步檢驗本研究結論。其二,本研究中憤怒和攻擊行為的測量采用了同一工具的不同分量表,這也可能會影響憤怒對攻擊行為的高度預測,未來研究可以采用不同的測量工具繼續檢驗憤怒與攻擊行為的關系。
盡管存在局限性,本研究仍然對我國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的研究與干預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在理論意義方面,以往研究在探討歧視知覺對攻擊行為的影響機制時,主要考慮的是單一的情緒或個人特質的作用(劉鐵川 等, 2021; 余青云, 張靜, 2018; Hartshorn et al., 2012; Xiong et al.,2021)。本研究則同時考慮了高喚起情緒憤怒和低喚起情緒抑郁的作用,并將道德推脫作為影響決策的因素引入到一般攻擊模型,不僅支持了該模型的理論觀點,也為不同喚起程度的情緒影響攻擊行為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模式提供了實證證據。在現實意義方面,首先,留守青少年往往存在認知偏差(戴斌榮, 2012),可能高估了實際存在的歧視,本研究提示可以從主觀知覺的角度進行干預,減少留守青少年的不合理認知,以降低其歧視知覺。其次,本研究提示加強留守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合理疏導其負性情緒,減少抑郁、憤怒,尤其要重視憤怒這類高喚起情緒。最后,加強道德品質教育,彌補可能存在的家庭教育缺失的風險,幫助留守青少年降低道德推脫,減少攻擊行為。
5 結論
(1)憤怒在歧視知覺與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起簡單中介作用;(2)道德推脫在歧視知覺與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起簡單中介作用;(3)抑郁和道德推脫在歧視知覺與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4)憤怒和道德推脫在歧視知覺與留守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