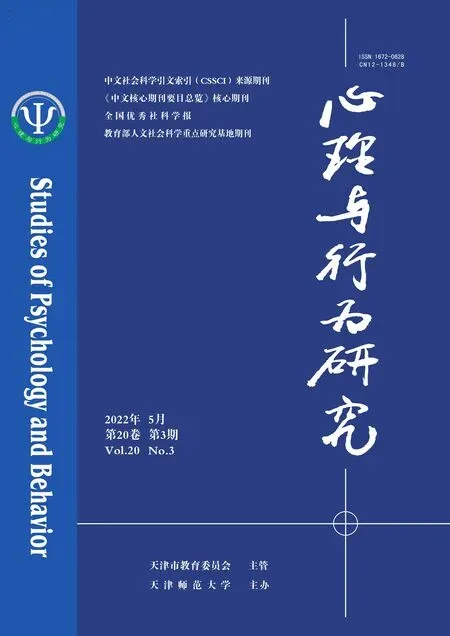父親和母親自主支持的特點及其與青少年社會適應的關系:自尊的中介作用
孫洪蕊 柳銘心 張興利,3 周晨浩,4 刁雅欣,3 包乃麗,3
(1 中國科學院行為科學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國兒童中心,北京 100035) (3 中國科學院大學心理學系,北京 100049) (4 首都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北京 100048)
1 引言
自主支持(autonomy support)是指父母鼓勵孩子做出自我認可的決定和選擇的一種教養方式(Deci & Ryan, 1987),具體表現為承認孩子的觀點和感受,提供做出選擇的機會,盡可能提供有意義的指導并在引入規則或選擇時做出有意義的解釋,減少控制性語言和行為,如負罪感、愛的撤回等(Fousiani et al., 2014; Joussemet et al., 2008;Vasquez et al., 2016)。自主支持是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框架中的重要概念。自我決定理論認為人具有積極地成長和自我調節的傾向,自主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Deci & Ryan,2000)。作為一種教養方式,自主支持更強調培養孩子的意志感和心理自由(即感覺自己有意志,是自己行為的來源),而不僅僅是培養孩子的獨立性(Fousiani et al., 2014; Soenens et al., 2007)。
國內外諸多研究表明,父母是青少年社會化的重要媒介(Pinquart, 2017),父母自主支持與青少年積極社會適應有正向關系(唐芹 等, 2013; 吳妮妮, 姚梅林, 2013; Bean & Northrup, 2009; Duineveld et al., 2017; Vasquez et al., 2016),與內外化問題行為有負向關系(陳云祥 等, 2018; 鄧林園 等, 2019;李若璇 等, 2019; van der Giessen et al., 2014)。青少年社會適應指個體在與社會環境的交互作用中,通過順應環境、調控自我或改變環境,最終達到與社會環境保持和諧、平衡的動態關系,是個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心理、社會協調狀態的綜合反映(鄒泓 等, 2015)。它是一個多維概念且涉及多個領域,比如自我適應、人際適應、行為適應、環境適應等,評估體系還需從積極和消極兩種狀態對社會適應狀況進行評價,因為積極適應和消極適應并非完全對立,良好的社會適應狀況是高水平的積極適應和低水平的消極適應的綜合反映(鄒泓 等, 2012)。
已有研究發現母親的自主支持可以顯著促進青少年社會適應能力的發展(Soenens &Vansteenkiste, 2005)。來自縱向追蹤研究的結果也發現母親早期自主支持教養行為可以間接影響子女青春期社會適應能力的發展(Matte-Gagné et al.,2015)。前人研究多以父母或母親自主支持為研究出發點,鮮少考察父親在其中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希望考察父親和母親的自主支持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的影響機制,并進一步探討父親母親自主支持的不同組合模式對青少年社會適應發展的影響。
自主支持教養條件下的青少年會擁有更多獨立解決問題的機會,得到更多的傾聽和尊重,因此會形成更積極的自我認知和評價(Bean &Northrup, 2009),從而具有更高的自尊(彭順 等,2021; 張景煥 等, 2013; Deci & Ryan, 1995)。自尊(self-esteem)是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對自我價值的情感體驗和評價(潘穎秋, 2015)。良好的自尊作為青少年重要的內部心理資源,不僅能促進其更好的社會適應(鐘瓊瑤 等, 2017),而且在應對威脅和壓力時起到保護和調節作用,同時也是接受和調動社會支持的前提(Ambriz et al.,2012)。已有研究發現,高自尊是成年人社會適應最強的預測因子(Neely-Prado et al., 2019)。而低自尊與青少年社交焦慮顯著相關(張亞利 等, 2019),而且是吸煙、酗酒,以及手機、網絡成癮等不良適應行為的重要預測因素(Hale et al., 2015; Sariyska et al., 2014)。由此,本研究將探查自尊在父母自主支持與青少年社會適應之間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探討了青少年父母自主支持的發展特點、父母雙親自主支持與青少年社會適應之間的關系模式及其可能的中介機制,為家庭如何促進青少年的社會適應提供實證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取方便取樣的方法,對山東省無棣縣6所中小學進行施測(1所高中、3所初中、2所小學)。共1981人完成問卷作答,其中93份問卷因答題時間少于150秒或明顯作答不認真而被剔除,最終有效被試1888名,有效率95.3%。其中男生882人(46.7%),女生1006人(53.3%)。農村學生1225人(64.9%),縣城學生663人(35.1%)。六年級259人(13.7%)、初一355人(18.8%)、初二370人(19.6%)、初三473人(25.1%)、高一243人(12.9%)、高二188人(10.0%),平均年齡為14.59±1.53歲。樣本中父親、母親受教育水平在大專及以上者分別占11.4%和8.2%,高中及高中未畢業者占20.8%和16.2%,初中及初中未畢業者占54.7%和45.5%,小學及小學未畢業者占13.1%和30.1%。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自主支持量表
采用Wang等(2007)修訂的父母自主支持量表,共12個項目。量表采用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的5點計分,量表得分為所有項目得分平均值,得分越高代表父母自主支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父親和母親自主支持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是0.93和0.91。
2.2.2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編制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中文版(汪向東 等, 1999),共10個項目。量表采用1(“完全不同意”)到4(“完全同意”)的4點計分,其中5個題目反向計分,即3、5、8、9、10題。量表得分為所有項目得分平均值,得分越高說明自尊水平越高。由于第8題在理解上存在文化差異,有研究者建議將其刪除(田錄梅, 2006),且在本研究中其修正后的項目與總計相關性為0.28(小于0.5),故刪除第8題。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8。
2.2.3 青少年社會適應狀況評估問卷
采用鄒泓等(2012)修訂的青少年社會適應狀況評估問卷,共50個項目,分為自我適應(自我肯定、自我煩擾)、人際適應(親社會傾向、社會疏離)、行為適應(行事效率、違規行為)、環境適應(積極應對、消極退縮)4個領域,共8個維度。每個領域中的兩個維度分別測量個體的積極適應和消極適應,可以提取出二階因子積極適應和消極適應。采用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的5點計分。消極適應維度全部采用反向計分,各維度得分為相應項目得分平均值。本研究中各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在0.80~0.94之間。
2.3 數據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采用問卷星施測。使用SPSS23.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利用其PROCESS v3.3組件的Model 4進行多元回歸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進行中介效應檢驗,重復抽樣5000次,計算95%的置信區間。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自我報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數據收集過程中,采用匿名方式進行作答,以及部分項目使用反向計分進行控制。數據收集完成后對變量進行Harman單因素檢驗。因素分析共提取出16個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個公因子的方差解釋率為29.16%,低于臨界值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青少年父母自主支持的特點
父親和母親自主支持在年級上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如表1所示。為了進一步考察父母自主支持的影響因素,將生源地(農村、縣城)、年級(六年級至高二)作為組間變量,父母作為組內變量,對自主支持得分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效應量采用η2p估計(鄭昊敏 等, 2011; Lakens, 2013)。

表1 青少年父母自主支持的描述性統計(M±SD)
結果顯示,生源地對自主支持的主效應不顯著,F(5, 1876)=1.39,p=0.238,η2p=0.001。年級對自主支持的主效應顯著,F(5, 1876)=5.70,p<0.001,η2p=0.015。父母對自主支持的主效應顯著,F(1, 1876)=28.26,p<0.001,η2p=0.015,父親自主支持顯著高于母親自主支持。生源地、年級與父母對自主支持的交互效應不顯著,F(5,1876)=0.87,p=0.501。生源地與父母對自主支持的交互效應不顯著,F(1, 1876)=0.42,p=0.515。年級與父母對自主支持的交互效應顯著,F(5,1876)=3.22,p<0.01,η2p=0.009。簡單效應分析發現,小學六年級(p<0.001)、初一(p<0.001)、初二(p<0.001)年級的青少年感受到的父親自主支持顯著高于母親自主支持,初三(p=0.148)、高一(p=0.529)、高二(p=0.999)年級的青少年感受到的父親和母親間自主支持無顯著差異。此外不同年級的青少年之間感受到的母親自主支持存在顯著差異(p<0.001),小學六年級的青少年感受到的母親自主支持顯著高于初一(p=0.003)、初二(p=0.001)和初三(p=0.030)的青少年,高二的青少年感受到的母親自主支持顯著高于初一(p<0.001)、初二(p<0.001)、初三(p<0.001)和高一(p=0.014)的青少年;不同年級的青少年之間感受到的父親自主支持存在顯著差異(p<0.001),小學六年級的青少年感受到的父親自主支持顯著高于初一(p=0.008)、初二(p<0.001)、初三(p<0.001)和高一(p=0.013)的青少年,高二的青少年感受到的父親自主支持顯著高于初一(p=0.030)、初二(p=0.004)、初三(p=0.002)和高一(p=0.037)的青少年。見圖1。

圖1 不同年級青少年感受到的父母自主支持
3.3 父母自主支持的不同組合模式下青少年社會適應發展結果
采用中位數分割法(Tan & Goldberg, 2009),把父親、母親自主支持分別劃分為高分組和低分組,并進行四種不同組合:第1組,雙低組;第2組,父高母低組;第3組,父低母高組;第4組,雙高組。方差分析結果發現,在自尊、社會適應的自我、人際、行為、環境四領域及積極適應、消極適應這些變量上,自主支持不同組合的主效應都顯著。事后檢驗結果表明第4組顯著大于1、2、3組,2、3組顯著大于第1組,2、3組間無顯著差異(見表2)。

表2 四種父母自主支持模式下的青少年社會適應發展(M±SD)
3.4 青少年社會適應、自尊與父母自主支持的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見表3):父親、母親自主支持與青少年社會適應總分,及自我適應、人際適應、行為適應、環境適應的四個領域發展均顯著正相關;與積極適應顯著正相關,與消極適應顯著負相關。自尊也與青少年社會適應總分,及自我適應、人際適應、行為適應、環境適應的四個領域發展均顯著正相關;與積極適應顯著正相關,與消極適應顯著負相關。

表3 青少年社會適應、自尊與父母自主支持的相關分析表
3.5 自尊的中介作用
在控制生源地、年級、性別、父親和母親受教育水平條件下,使用SPSS中PROCESS v3.3組件的Model 4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母親、父親自主支持對青少年社會適應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β母親=0.18,p<0.001; β父親=0.14,p<0.001),自尊對社會適應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β=0.63,p<0.001)(見表4)。

表4 中介模型的回歸分析(標準化)
對自尊在母親、父親自主支持與青少年社會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應進行分析表明,自尊在母親自主支持對社會適應影響中的間接效應為 0.16,且其Bootstrap 95%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明自尊在母親自主支持與社會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自尊在父親自主支持對社會適應影響中的間接效應為0.14,且其在父親自主支持與社會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應也顯著(見表5)。

表5 中介效應的Bootstrap檢驗結果
4 討論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感知到父親和母親自主支持發展趨勢一致,均表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初一初二時期,父母自主支持水平降低,可能由于在小學階段父母以控制行為為主,而孩子進入初中以后父母沒有及時調整自己的教養方式,給予青少年的自主支持不足;也有可能是因為青少年進入青春期,自我意識增強,親子矛盾增多(De Goede et al., 2009),青少年感知父母的自主支持能力減弱。這也提醒父母應特別重視此階段青少年的成長,一個人從童年期到青少年期會經歷很多生理和心理的變化,父母必須及時調整自己的教養方式(王麗, 傅金芝, 2005),給予青少年更多的自主支持,以促進其健康發展。進入高中后,父母自主支持水平呈現上升的趨勢,原因可能是本次調查的高中是寄宿學校,青少年離開家以后得到更多自主的機會,而且父母也逐漸認識到培養青少年自主性的重要性(Rogers et al.,2020),從而達到供需更加平衡的狀態。
本研究發現,小學六年級以及初一、初二年級的青少年感知到父親自主支持顯著高于母親的自主支持,這跟西方國家研究結果是不一致的(Duineveld et al., 2017)。可能由于文化差異,在中國還是以“男主外,女主內”傳統模式居多,母親關注和參與孩子的生活學習更多,對孩子的管教行為也更多,所以相對于父親,青少年與母親的沖突更多(方曉義, 董奇, 1998);而父親雖然可能與孩子的接觸時間少,但是由于現代父親育兒觀念及方式的轉變,孩子對父親的心理親近感很高(李曉珊, 2017)。本研究還發現在高中階段,父親和母親自主支持間沒有顯著差異,可能是此次調查的高中學生在學校居住,與父母接觸時間少,所以對父母之間的差異感受不敏感。
本研究結果表明,父親、母親自主支持水平越高,青少年自尊水平越高,總體社會適應能力,以及在自我適應、人際適應、行為適應、環境適應四個領域內都有更好的表現,而且青少年在積極適應方面發展越好,其消極適應方面的問題越少。這說明自主支持不論來自于父親還是母親,對青少年的成長都是有益的。本研究結果很好地支持了自我決定理論,父母的自主支持使青少年體驗到自己是行為的發起者,激發了他們的內在動機;面對父母的建議或指導時,他們也會有一個更開放的心態,更有可能去接受,并將父母的價值觀內化并融合到自己內心中,從而表現出更多的積極行為(Ryan & Deci, 2000)。而如果青少年感覺自己行為是被控制的,他們更有可能通過違抗和不服從父母來捍衛他們的自主性(van Petegem et al., 2015)。
本研究發現能得到父親和母親兩種高自主支持的青少年在社會適應各維度及自尊的發展上顯著好于其他3組,這說明高父親自主支持和高母親自主支持產生了積極的累加效應。此結果與以往研究一致(Vasquez et al., 2016)。一項對36篇有關父母自主支持研究文獻的元分析發現,能得到父親和母親雙重自主支持的青少年學業成就及心理健康發展更好(Vasquez et al., 2016)。此結果在其他領域得到一定的研究支持。一項考察育兒風格的研究也發現,父母雙方都采用權威型教養方式的青少年表現出較少的偏差行為(如逃學、攻擊行為、偷盜和物質使用)、較低的抑郁得分以及較高的學校投入(如學校興趣、師生關系、作業完成度等)(Simons & Conger, 2007),而且父母參與水平對兒童的學校適應的影響也有類似效應(Tan & Goldberg, 2009)。所以在青少年的成長之路上,父親和母親最好都能參與進來,并給予青少年自主支持。
本研究還發現父親和母親自主支持不僅可以直接促進青少年社會適應,還可以通過提高自尊間接促進其發展,與假設一致。這是由于青少年感知到的自主支持有助于構建一個連貫的自我意識,有較高的自我價值感,能夠對自己的態度、情感以及評價保持肯定,進而有助于形成高水平的自尊(彭順 等, 2021; Deci & Ryan, 1995)。而具有較高自尊水平的青少年在自我肯定、親社會傾向、行事效率、積極應對等方面發展得更好,個體能夠通過不斷地學習、與他人交往來提升自己的社會適應能力(鐘瓊瑤 等, 2017)。
本研究的理論和應用價值主要有以下幾點。自主支持這種教養方式可以提高青少年自尊及社會適應,有利于青少年的成長,值得推廣學習。根據自主支持的年級發展特點,家長要及時調整教養方式。本研究還綜合考慮父親和母親自主支持作用并發現,對青少年來說,父親和母親自主支持可以相互補償,所以一定要重視父親的作用,鼓勵父親更多地參與青少年的成長。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取樣上,樣本均來自縣城和農村,雖然樣本量較大,但相對同質,還需在其他樣本中進一步驗證。其次,本研究中父母自主支持均由青少年報告,但青少年感知到的自主支持與父母實際提供的自主支持間是否有差異,還需進一步探討。
5 結論
(1)青少年感知到父親和母親自主支持發展趨勢一致,均表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并在初二時期出現拐點。(2)父親和母親的自主支持與青少年自尊及社會適應各領域的發展均呈正相關,而且父親和母親自主支持的作用不僅具有累加效應,還可以相互補償。(3)自尊在父、母自主支持和社會適應之間均起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