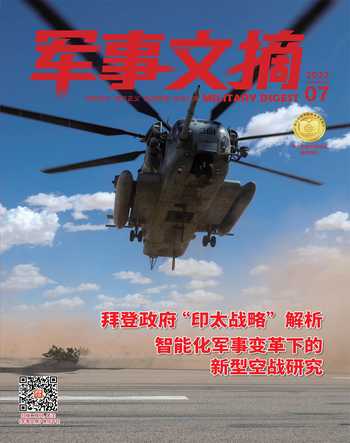淺析美軍“動態兵力運用”概念的內涵及影響
陳雨茗 安文 禤白澤

自《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提出“動態兵力運用”(Dynamic Force Employment,DFE)概念以來,美軍在全球各熱點區域持續、小幅地調整海軍航母打擊群、空軍戰略轟炸機等兵力,并通過不斷的作戰實驗和聯合演練持續調整和優化兵力部署。美軍的這些舉措旨在加強全球遠程兵力投送能力,同時提升與盟國和伙伴國家聯合運作的集體作戰能力,最終實現美軍力量從“連續駐扎”向“動態兵力運用”轉變的戰略目標。
2017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2018年的《核態勢評估》報告和2019年的《導彈防御評估》報告,都對對手日益擴大的遠程火力打擊威脅表示擔憂。同時,自《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把中俄列為“戰略對手”后,美國加速其全球戰略調整,圍繞“國家間的戰略競爭現在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問題,而非恐怖主義”基調實施戰略重點轉移,并把矛頭直接指向中俄。戰爭環境的改變要求美軍能夠在得到臨時通知并幾乎不讓敵人獲得提前預警的情況下,向世界各地投送軍事力量、進行重大軍事部署,從而威懾潛在對手。
冷戰結束后,兩極對抗與全球性大規模戰爭爆發的可能性降低,各國紛紛降低軍備投資,以將預算投入到民生建設與經濟發展中,加之部分國家民族意識、主權意識高漲,因此,排斥他國在國內的軍事存在與基地需求。此種情況使得美國維持海外基地的成本不斷提高。加上本身國防預算與兵力規模縮減,美國開始從追求增加海外駐軍與海外基地數量,轉為強調全球機動、快速反應與精準打擊的能力,以維持自身在各地區的軍事存在與國家利益。《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提出,為了提升兵力調動和態勢復原的能力,要將現行大型、集中、未被強化建設的軍事基地,轉型成小型、分散、具有復原力和適應力、且能進行積極和消極防御的基地。
兵力構成和作戰概念是贏得大國競爭勝利的關鍵。美軍作為一支走“技術流”的軍隊,歷來追求通過創新作戰概念謀求作戰優勢。面對新的對手和威脅環境,在無法快速研發大量新型高性能武器裝備的前提下,美軍追求盡快開發新型兵力設計概念,改變兵力運用方式,塑造一支彈性、靈活、適應性強的作戰力量,確保競爭優勢。《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提出,過去15年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延宕了美軍作戰準備、裝備采購和現代化更新的進程。為贏得未來的戰爭,必須盡速實現關鍵軍事能力的現代化,調整兵力的運用方式,發展創新的作戰概念,建構一支具有殺傷力的部隊。
《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對“動態兵力運用”概念的目的與功能進行了說明:“全球戰略環境需要越來越多的戰略彈性與行動自由。動態武力運用概念將改變聯參本部使用聯合部隊的方式,以提供主動先制的、且可伸縮的任務優先選項。動態兵力運用將更為彈性地使用戰備的兵力,先制、主動地塑造戰略環境,同時保持應對突發狀況和確保長期作戰所需的戰備能力狀態。”由此可見,“動態兵力運用”概念的目的是增加美軍作戰彈性,使潛在的對手難以預測美方的軍事部署行動,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同時在不被對手獲取情報的前提下向各地輸送軍事力量,為己方戰略決策者提供更好的軍事選項,迫使對手在不利條件下作戰,最終挫敗對方行動,實現己方意圖。

《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封面

美軍歷來追求通過創新作戰概念謀求作戰優勢
制定“動態兵力運用”概念的始作俑者是前美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他認為美軍的行動在戰略上應該是可以預測的,同時在戰役戰術層次上要更加靈活,讓對手難以預測。即美國的對手一方面應該清楚華盛頓會采取何種政策,畏懼“美國強大的戰斗鐵拳”;另一方面,卻對諸如“美軍在何地、用多少兵力在擔負何種作戰值班”的問題難以猜透,以此讓美國的潛在對手產生特有的“戰役戰術混亂”,剝奪其準備抗擊美軍作戰行動的能力。由此可見,“動態兵力運用”概念是一個專為應對大國競爭設計的兵力管理工具,同時也是一種力量部署模式,通過增強美軍兵力部署的突然性、模糊性和非線性,提升美軍生存力和威懾力,達到“戰略上可預測、行動上不可預測”的效果。
2018年4月,前美國參聯會主席約瑟夫·鄧福德在國會證詞中提到,美國將面臨中俄的長期戰略競爭威脅,“動態兵力運用”概念使美國能夠透過可伸縮的軍事存在來主動塑造環境,迅速部署兵力,以應對新興作戰需求,同時保持長期作戰準備。并表示“動態兵力運用”概念具有不可預測性、敏捷性和主動性等三大關鍵特征。其中,不可預測性是指通過靈活的兵力部署,讓競爭對手毫無準備,使其質疑部署的戰略意圖,最終放棄原來的戰略統籌或戰役計劃;敏捷性是指力量預置能夠做到快速靈活;主動性是指美軍的部署行動經過多次思考和論證,并非疲于招架的應急之策。前美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評價“動態兵力運用”概念為應對大國戰略競爭的“良方”,并表示該概念可以讓美國在應對全球挑戰時具有更大的戰略靈活性。
由于“動態兵力運用”概念主要定位于應對來自中俄的戰略威脅,因此該概念的驗證實踐主要體現在印太與歐洲地區。自概念公布后,美軍各軍兵種即不斷配合進行日常訓練。
2020年4月17日,美空軍全球打擊司令部將5架原駐扎于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的B-52轟炸機撤回美國,宣布結束進行16年的進駐關島之“持續轟炸機進駐”任務,過渡到“動態兵力運用”模式,隨后,美印太司令部及太平洋空軍陸續針對此概念展開部隊相關能力培訓,以展示“動態兵力運用”的投射效果;2021年3月12日,美空軍第19戰斗機中隊和夏威夷航空國民兵第199戰斗機中隊的F-22戰機飛赴巖國基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動態兵力運用”任務,并與美陸戰隊F-35B、日本航空自衛隊F-35A及其他戰機進行聯合演訓;2021年12月3日,來自美空軍阿拉斯加艾爾森空軍基地第354戰斗機聯隊的F-35A戰斗機抵達位于日本巖國的海軍陸戰隊航空站,執行“鋼鐵匕首行動”任務,在部署過程中,美空軍與海軍陸戰隊第三遠征軍的F-35B戰斗機進行了戰力整合,驗證了美印太戰區快速動員和部署第五代空中力量的能力。

“動態兵力運用”概念的提出者——前美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

美海軍杜魯門號航母
2018年4月至7月、8月至12月,美海軍杜魯門號航母打擊群連續兩次進行為期三個月的部署,此次任務是航母打擊群自1990年代初以來首次于北極圈活動,旨在打破以往部署方式,增加競爭對手預測、追蹤、應對的難度;2019年10月27日,由B-52和B-2所組成的轟炸機特遣隊由美本土飛赴歐洲,與常駐英國的B-52轟炸機會合參加全球閃電演習,并與北約盟國進行聯合演訓,以此向歐洲盟友傳遞美戰略轟炸機有能力隨時從美國本土馳援歐洲戰場的政治訊號;2021年6月,美陸軍第41野戰炮兵旅先后部署波羅的海、黑海、德國及北非等地,驗證其機動能力,最后更深入極圈,進行代號火力震撼的射擊演練,以展現美軍能在短時間內轉戰各地,快速部署、投射兵力的能量,并證明有能力在全球各地以自己選定的時間、地點執行各項任務。
從美軍持續進行的各種作戰試驗來看,“動態兵力運用”概念旨在打破既有框架,令對手難以預測其戰術戰法,以確保更大的戰略主動性、因應方案選擇性、戰術靈活性、作戰彈性、部隊韌性與安全性等。
在“動態兵力運用”概念下,美軍轟炸機不再常態駐防于關島,而是調回美國本土。這引起了二戰后有大量美軍駐防的日本之擔憂,擔心美國對協防日本的承諾是否降低,以及擔心該概念的部隊調動模式,將會使美國難以對地區沖突做出快速的反應,從而降低美國的威懾能力。歐洲盟國亦有相同的擔憂,擔心“動態兵力運用”的“不可預測”,容易導致決策的復雜化,提高誤判的風險。此外,“動態兵力運用”強調快速的兵力分合,平時分散部署有賴自身基地和盟國愿意提供足夠的前進基地,及其相關的設施建立與后勤支援、預算分攤。同盟國家擔心一旦美國與潛在對手發生沖突,自身的區域經濟發展會受到影響,甚至會受到報復與襲擊,從而降低與美國的合作意愿,不同意美軍進駐或使用其國內的設施。
美智庫專家認為,“動態兵力運用”概念下的長途、頻繁的部隊調動,雖然會增加對手預測、追蹤與制定因應計劃的困難,但也會使美軍承受更大不確定性的風險。第一,美軍艦隊和軍機需不時航行于各大洲、各大洋,需要大量中繼補給能力,而中繼補給與補給線容易成為潛在對手的首要攻擊目標;第二,一旦形勢遽然升高,美軍需要長途、遠距調動軍隊,無法迅速因應沖突而失去先機,潛在對手則以逸待勞、容易掌握主動權;第三,“動態兵力運用”為追求作戰不可測,往往會刻意標新立異,執行非常態任務、采用非固定航行路線等,這會造成作戰人員過度疲乏并承受更大的壓力,反而會增加戰場的不確定性。
“動態兵力運用”概念主要寄希望于平時透過動態威懾達到遏制擴張;若威懾失敗而發生戰爭沖突,則希望藉由分散的部署方式,減少遭受彈道導彈集中攻擊的損害程度,再以迅速兵力集中的方式予以攻擊。以“動態兵力運用”作為財政、兵力縮減下的過渡兵力運用模式,將難以因應遽然升級的大國沖突危機。前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在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表示,從美國馳援“第一島鏈”一般需要21天,最快也要17天,因此,需要大幅提高國防預算,以在高風險地區長期駐扎部隊,并建設更多能容納輪流駐防部隊的基地。
責任編輯:陳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