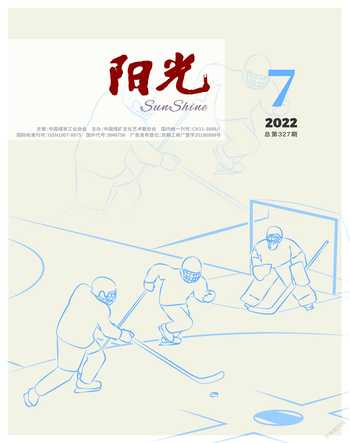風爐札記
喜歡風爐,由來已久,對風爐有著別樣的情愫。
風爐的歷史要追溯到中國的唐朝,陸羽《茶經》記載:“風爐,以銅鐵鑄之,或運泥為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緣闊九分,令六分虛中,致其圬墁,凡三足。古文書二十一字,一足云‘坎上巽下離于中’,一足云‘體均五行去百疾’,一足云‘圣唐滅胡明年鑄’。”這段古文的意思是:風爐用銅或鐵鑄成,也可揉泥制作。像古代鼎的形狀……一足寫:上水下風中間火,風能旺火,火能熟水;一足寫:祈愿身體五行平衡,百病消除;一足寫:唐朝剿滅安祿山叛亂之次年鑄造。
《茶經》是唐代陸羽經過多年撰寫的一部著作,是中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茶書,凡與茶有關的各種內容都有敘述。風爐,就是《茶經》里記載的二十四種飲茶器具之一,是陸羽設計制作并命名的一種煎茶爐具。
《茶經》風行后,風爐作為二十四器中的重器,不僅標志著茶道的精神,也成為行茶最重要的環節,亦即煎茶的器物展示。它在生活場景中有著山高水長的意象。晚唐散文家皮日休《茶中雜詠·茶鼎》的詩:
龍舒有良匠,鑄此佳樣成。
立作菌蠢勢,煎為潺湲聲。
草堂暮云陰,松窗殘雪明。
此時勺復茗,野語知逾清。
皮日休欣賞的茶鼎是以安徽舒城縣的匠人制作甚佳,樣式精致美觀。擺在屋子里像林間的靈芝般耀眼,潺潺煎茶聲似溪水緩緩流淌。暮色之下或雨雪天,人們圍爐而坐,飲茶聊談,那種閑適的心境,令人愜意。茶興于唐,而盛于宋。風爐也多見于宋人吟詠。陸游的“明窗睡起渾無事,篝火風爐自試茶”“茶爐煙起知高興,棋子聲疏識苦心”,又“公閑計有客,煎茶置風爐”。釋永頤《茶爐》詩:“煉泥合瓦本無功,火暖常留宿炭紅。有客適從云外至,小瓶添水作松風。”黃庭堅《奉同六舅尚書詠茶碾煎烹》:“風爐小鼎不須催,魚眼長隨蟹眼來。”所詠皆是風爐。
一日去上海博物館參觀,看到一款一九七八年出土的宋代鼎形風爐。盡管出土的鼎形風爐不像陸羽記載的那樣錦飾精美,但陸氏風爐在人們心目中似乎成了一個標準。后世風爐的制作在求雅的路數上多有拓新。宋代后期,煮茶的器具多用銅制作,還出現了竹火爐。到了元代,茶爐的制造工藝更加精美。中國農學家、茶葉專家吳覺農所著《茶經述評》里講到,元代杭州城里有一大戶人家,要求匠人用金鑄造,風爐上面雕有云錦似的花紋,表面光滑美觀,深受人們追捧。使得那些官吏商賈紛紛仿效。明代的風爐傳承了前朝的工藝傳統,材質上多用銅、陶土與瓷土制作,做工上講究雕刻技藝的運用。在清朝,皇室貴族的風爐更顯貴氣、華麗。《博物館觀看之道·中國篇》(明、清器物)課程講述,清朝皇宮用金和銀等制作的風爐,無論材質與制作,還是工藝與裝飾都非常講究。慈禧太后的御用風爐用黃釉制成,釉色嬌嫩,釉面肥潤,堪稱晚清時期的極品。
但是,到了民國時期,山河動蕩,民不聊生。有多少人還能有這種閑情逸致,圍爐煮茗。即使聊起茶道,也多以茶杯和茶本身的色香味形為中心,很少談到茶道用具風爐,風爐漸漸的不再是茶道用具的核心了。隨著時代的變遷,原先專指煎茶用具的風爐大部分用來其他燒煮:煎藥、煮水、溫酒、煲湯……燒煮食物,隨心而為,使得原本在人們心目中高雅的風爐,逐漸變為老百姓家里移動的土灶、應急用的燒飯炊具。根據普通百姓的需求,風爐的制作也由原來的精美器具變成粗制簡陋的一般爐子。后來,民間把風爐的制作演變成多種形式的炊具爐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煤球爐,其次是煤油爐(我們家鄉稱洋風爐)。這些爐子用鐵制成,有的用紅土泥燒制而成。一件器物是一個時代生活文化的縮影。風爐的演變越來越通俗、越來越多地走進大眾生活。雖然風爐變了,可我們的茶道精神依然存在。茶道中仍有一些風爐保持著中國古式風爐的樣子,作為承襲和裝飾之用。曾經,我和同事去喝茶,看到一只古色古香的琉球風爐,我幾乎是脫口而出:“真品還是贗品?”服務員禮貌性地說:“仿制品。”世事變遷,真正的風爐恐怕只有達官顯貴人家才能得見。而這種稀有的風爐算得上是藏品了。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百業蕭條,百姓生活貧困,我們蘇北農村大多用煤球爐燒水做飯。糧食是分配的,燒柴也稀缺,即使有糧,恐怕也沒柴燒。煤球爐做起飯來既臟又慢,那蜂窩煤碰到就是一片烏黑,而且很難引火。那時我還在上小學,放學回家,時常見到幾戶人家在弄堂口的煤爐冒著滾滾濃煙,主人既嗆又咳拿著芭蕉扇子對著爐口扇啊扇。好不容易引著了火,還得耐著性子等它慢慢燒。一鍋水,最快也要一小時左右才能燒開。所以,人們往往到鄰居家借火,用一個新的蜂窩煤換一個正燒紅的“二手煤”作引火,這樣省力又燒得快。我的父母有時在夜里三更便起床引火生爐,然后再睡個回籠覺,等一鍋水燒開,天也亮了。
后來,母親買了一只洋風爐。相比煤球爐,洋風爐小巧、干凈,便捷多了。洋風爐燒的是煤球,而是煤油,我們家鄉稱其為“洋油”。洋風爐是我家的高檔灶具,不常用,也舍不得用。因為風爐燃的洋油比較貴,又是憑票購買的緊缺貨。可母親為何要買洋風爐?那時大集體生產,母親天天在農田干活,收工回家后還要灶前灶后燒飯,房前屋后種菜,飼養雞鴨豬羊……一個磨蹭,開工遲到就會被扣工分。農忙時節,為了能準時吃上飯,為了準點上工,母親買來洋風爐,以解燃眉之急。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母親把洋風爐傳給了結婚生子后家務纏身的我。她說,燒菜用風爐,省工夫。
洋風爐幫我度過了忙亂的育兒時光。如今,兒子已長大,洋風爐也被先進的灶具替代,藏進了閣樓。一日打掃衛生,我把風爐取出來,擦拭干凈,準備把它點燃,重溫一下舊時光。忽又想到,爐里已沒“洋油”,也無處去買。我望望家里一應俱全的現代化灶具:煤氣灶、電磁爐、微波爐,又留戀地看看洋風爐,既欣喜又感慨……
沈漫漫:本名沈萍,江蘇啟東人。江蘇省南通市作家協會會員,曾獲上海市“傅雷杯”全國文藝評論獎等,有散文入選《中國當代散文精選(2021卷)》《江蘇散文選(2021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