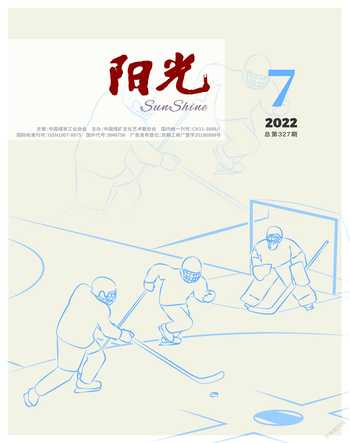萬物皆有生命:堅硬與柔軟存在的方式
左岸
生命,從狹義講是活著的一種生物,它包含死亡和化為烏有。但是從廣義上說,萬物皆有生命。科學家早就認定地球是另一種形式的生命體。僅從我們生活的世界來說,大到山川河流海洋,小到冰冷的石頭,一片云、一滴雨、一條魚、一朵花、一把椅子、一本書、一只螞蟻等,甚至我們肉眼看不見的細菌和微生物都有生命。只不過存在的方式不一樣。
讀著名詩人王愛民的詩,強烈地感受到他對生命的全方位認知。他以“向大地矮下半個身子,紙上輕落草色”(《心在左,靠右側通行》)為自己定位:大自然是賴以生存的母親,敬畏她,用自己的筆去描摹所有生命,畢其一生,殫精竭慮,在所不辭。
因為有了非同尋常的認知,在他的筆下什么都是有生命的:“一只鞋在腳,另一只苦苦尋找/像一條小路,拐彎地愛著。”我們說詩人賦予鞋或許低端感情,但是唯其才能打動人,擬人化的手法,使人感覺越小越細的事物越能打動人。如果說鞋延伸了一條小路,夠詩意了,但是詩人更進一步用“拐彎地愛著”,這里生出多少不盡之意。后現代詩的特征之一即是節外生枝,多義且產生延伸的美。“鞋”這個意象詩人反復詠唱,像“故鄉是一只回不去的鞋/不怨路不平”(《用方音把故鄉一天天喊大》),那是什么緣由呢?尤其“時光甩掉的鞋子,看閑云也有悲傷”(《我有草藥三千煮出人間清歡》),此時我們才明白詩人賦予“鞋”一種生命,“鞋”與主人息息相關,也可說它是詩人借此傾訴自己對人生甘苦的傾訴。
同時我們看到詩人對螞蟻也是傾注了特有的感情,以螞蟻為題材的詩古今中外數不勝數,關鍵詩人有自己的“面孔”,識別率非常高,像:“螞蟻扛起的暮色,比自己大”(《我有草藥三千煮出人間清歡》),簡直語出驚人,詩人在此向微小的生命躬身,恰恰證明自己有一顆慈悲的心。
再讀《時間踩過一只螞蟻》,整個色調頗顯蒼郁,詩人采用排比的句式,摘來令人眼花繚亂的物象將自己的苦澀展示無遺,人是渺小的,堪比螞蟻,死亡是必然的,但是苦難恰似一塊磨石,能砥礪那些敢吞不幸的人們,而磨難與不幸恰恰是詩人創作的原動力。詩評家范遷說過:“苦難是只永遠盛不滿的杯子,而所有偉大的詩人總是從杯中啜飲苦澀的養分。”詩人筆鋒一轉,帶來明亮的色調:“遺漏下來是幸運的/一條條細小的光線/爬上腳面。”一個微妙的白描,是此詩的謎底,使我們恍然大悟,從緊迫中脫離,來一次深呼吸。
我們說詩歌與詩是有根本區別的,雖然都是抒情為載體,但抒情的核心截然不同,詩歌是在大庭廣眾之下同一時間的接受與呼應,往往是群眾性的。而詩,是寫給一個人看的,之間只有靈魂的溝通與交流,歸根結底,受眾群體是不一樣的。
我認為王愛民的詩基本屬于后者。意象是詩歌的生命。沒有意象就沒有詩歌。“意象是通過借助被主觀情感投注了的客觀物象,并對其運用象征、比喻等手法而獲得的一種主觀情感的具體表現。”簡而言之,象即物象,意即想象。新鮮的神奇的意象是決定一首詩的成色。但對于王愛民的諸多詩歌來說,他確實已進入兩種意象的交叉融合。當我們讀到:
“不再害怕一塊石頭落下砸頭/把桃花看白/一雙眼睛里撈出水底天/把書讀出香味,黑筆寫出藍字/頭下墊一本詩集,當枕頭”(《心在左,靠右側通行》)。詩人用七個意象一氣呵成,組合成一種氣氛、一種意境。再如:“秋風把一棵樹一座塔吹斜/把一個人的影子扶正/把牛角羊角吹彎,然后鉆進去筑巢”(《骨頭里有一塊塊鐵鳴叫》),通過并排的意象,道出自己的冷幽默,在令人忍俊不禁的氣氛里領略到鐵漢柔情的形象。
其實詩人所寫的詩都是為自己塑像。也可以說既是大眾的又是個人的,個人色彩越強烈,識別度就會越高,優秀詩人都是不可復制的。
“炊煙逆勢上揚,要趁早洗白天空/早起下地的人,鐮刀崩出豁口/骨頭里有一塊塊鐵鳴叫/石頭含霜,趕遠路的人抱緊身子/一夜白頭”(同上)。一連串的動詞使用:洗、崩、叫、抱等,凡讀至此,無不瞠目結舌。這些叫人心跳的句子,有一種金屬的味道,這些硬核的意象,組成了遼河平原上獨有的風景,它的反光對故土對家鄉至死不渝的眷戀。
應該承認王愛民是一位非常男人的詩人。當讀到“從石頭里取鈣/讓黑夜吃掉烏鴉黑色的預言/天空吐出個銀牙,堵住漏洞的大風/時光甩掉的鞋子,看閑云也有悲傷”時,(《我有草藥三千煮出人間清歡》)我仿佛看到北方大漢持銅琵琶、鐵綽板吟唱東北風。
當我讀到:“大地輕輕翻身/天空是一只巨大的碗/倒扣紛紛淚水/把生死再清洗一遍”(《我們跪拜山是一座碑》)或“水喚醒水,水洗凈水/水回到水的骨頭,回到你的千古愁腸/只有水是你的懷抱/容納你,安撫你,托身于你/像一枚粽子的縱身一躍”(《在端午,一枚粽子縱身一躍》),這些驚艷的意象讓人自然想起龐德對意象的解釋:“意象是在一瞬間顯現理性和情感的復合體,是詩人最重要的顏料和詩歌的核心,是一種超乎系統化語言的語言,只有它才是詩人傳情達意的特殊工具。”
詩歌技巧是詩人的殺手锏,其核心是形象思維。艾青說過:“寫詩的人常常為表達一個觀念而尋找形象。”如何表達,這里有一個時代感問題,詩歌的發展也是與時俱進的,不會停止。復雜與簡潔互映。詩人馬永波提倡“難度寫作”這一詩歌文學創作主張,以此來強調文學對現實的批判力量以及詩歌作為人類精神明燈的指引和提升力量。他所針對的背景是當下“碎片化、庸俗化、欲望化的消費寫作”,目的是倡導健康向上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與經驗廣度的整體性寫作。
可以說詩人在這個領域作了身先士卒的表率。他的諸多詩作意象跳躍性很大,比如“太陽愛著大地,枝條撫摸頭頂/一朵花從墻根牽出一頭牛/藤蘿奔騰上架像更多低頭吃草的馬/再愛一會兒,雨才會喊出熱愛”(《喊出心底熱愛》)。意想不到的意象扭到一塊兒,使讀者視野開闊了許多,收到十倍的愉悅。再讀“大地輕輕翻身/天空是一只巨大的碗/倒扣紛紛淚水/把生死再清洗一遍”(《我們跪拜山是一座碑》)。讀到這里我想起詩人何宗文主編的《現代通用寫作》中說:“所謂意象跳躍,也叫省略法,就是指各組意象之間有意省略中介,一個意象向另一個意象過渡不作交代性敘述,表面上看來是脫節,難以理解,實際上存在一種內在聯系。”以期抵達“詩歌意象的跳躍美。不但使得詩歌意境開闊,更富有情韻,而且使詩句緊湊,更富刺激性,引導讀者發揮聯想,去體味比句法關系更緊密更深刻的意義”。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詩人的作品里經常出現意象的異質遠喻的表現手法。舉例:
“鐮刀崩出豁口/骨頭里有一塊塊鐵鳴叫/石頭含霜,趕遠路的人抱緊身子/一夜白頭”(《用方音把故鄉一天天喊大》)。
“馬眼睛里/降在一個個小時候的名字上/降在我的小小諸侯國,我的江山/村子離月亮不遠,比霜白”(《骨頭里有一塊塊鐵鳴叫》)。這里的“骨頭”與“鐵鳴”兩個不同物質扭到一塊兒,“馬眼”與“名字”根本不沾邊,卻被詩人合金到一起,起到意想不到的詩境。
回顧一下:“異質遠喻”原則是英美別樣新提出的一個重要的比喻原則,為了擴大比喻的容涵,使想象的空間更廣闊,常使喻體和喻旨分屬完全不同的經驗領域。從而豐富了詩的寫作領域。
我在解讀大量鋪墊詩人作品中“男人”形象的同時,還揣摩到詩人另一個跳動脈搏,那就是他通過對家鄉的傾注感情“柔情似水”,使其實際的風格有了立體的效果。
詩人在《方音把故鄉一天天喊大》一詩里就有淋漓盡致的傾訴,比如:
“彎彎的風/吹進母親的骨縫把母親吹彎/把母親的頭發吹白/白發不斷起落/像她一連聲的囑咐和叮嚀/她似乎要將手里的風洗白。”
“月亮有母親的體溫/我把它當成硬幣/天天揣在身上”(《把月亮天天揣在身上》)。
“天漸涼,河水消退/父親把風刮出的眼淚/收回眼眶/遠山在更遠處”(《立秋》)等。
詩人如數家珍,把童年對故鄉對父母的深情通過質樸的細節描畫出來,完成人類“普遍的經驗”這一效果。我們從這一部分詩作中窺出詩人性格的另一面,他不是把生活看得完美無缺,而是抑郁憤懣孤獨冷寂不時在字里行間出現。使讀者更加相信他的真實,即所謂“低視線寫作”。
詩歌也有血緣關系。詩人不斷把故鄉作為自己寫作的天堂抑或自己詩歌的根。“一張紙老了/回歸泥土/還保持泥土的顏色”(《一張紙》)。道出自己始終不渝的信念。
“故鄉的倭瓜爬過了墻頭/提水人桶里晃動個月亮/卷心菜收回層層包裹的小心臟/弦上晚來風緊/離家人比鄉間小調走得慢/我比風更涼走累了/靠上你的肩膀”。
詩人還喜歡用白描的手法對老家的山山水水細微雕刻,在他看來在這片土地上所有的東西都是他的親人,他是故鄉的孩子。讀來令人動情。詩人對故鄉的“月亮”這個意象,反復詠唱,愛不釋手:
“天上一輪月亮/照在城里/一池水蕩漾/照在故鄉/撒滿了一地鹽”(《把月亮天天揣在身上》)。
采用城市與鄉村的對比:一池水與一地鹽的形容,尤其后者這個“鹽”讓我讀到清冷空曠之畫面。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有句名言:“我的像郵票那樣大小的故鄉是值得好好描寫的。”我深信有出息的詩人都離不開這個軌跡,我欣喜詩人做到了。因為在他的筆下,萬物都是有生命且有靈性的。梭羅說過:“心靈與自然相結合才能產生智慧,才能產生想象力。”從另一個角度分析自然界所有物質都要具備明面與暗面,以此啟示我們的創作方向。
讀罷詩人王愛民這組詩,在我腦海中漸漸形成他詩的整體形象:堅硬如猛虎細嗅薔薇,柔軟似東風輕撫柳條。堅硬與柔軟是文學創作的左右心室。境界的高蹈和內心的痛疼是立詩之本。
我想用著名詩人、詩歌批評家譚延桐的一句話結束這篇小文:“只有獨立的思想才能延伸詩歌的無限性。”贈與王愛民共勉。
左 岸:本名楊庭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人民日報》《詩刊》《詩選刊》等。出版詩集《一只晴朗的蘋果》《靈魂21克》,小小說集《小鳥是冬天樹上的果實》《冰乳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