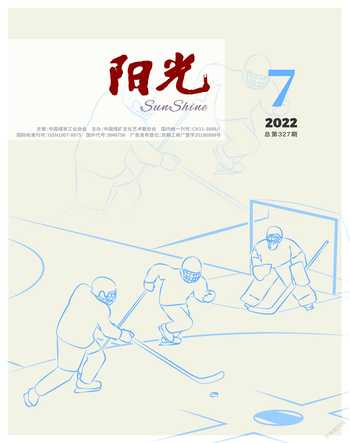大豆引
張艷
大豆古時稱作菽。我們村子里的大豆叫作黃豆,長在村南最好的土地上。菽與黃豆,一個雅號,一個俗稱,對少年時期的我來說都是溫暖的。
一
一場好雨打濕了村南的土地,一株株粗壯的豆棵,雨一下,風一吹,豆莢就可著勁兒地長。秋風起,豆莢漲得肚子大大的,泛起黃色的孕斑。等被砍下放在院里,兩個大太陽天就曬得焦黃了,拴著皮條的鞭子抽打幾番,豆粒們歡快地跳脫出來。鞭子抽打豆棵的聲音脆響,一下,一下,真是好聽。豆棵在被翻滾抽打后,陷入了沉醉。有如釋重負的坦然,也有完成使命的欣慰。黃豆粒圓滾滾地裝滿大缸,放在倉房,日子才過得踏實。
《春秋說題辭》有粟(即小米)之五變:“一變而陽生為苗;二變而秀為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黃豆其實與其相似。黃豆的變身大約有三步:豆棵生莢,莢熟豆落,豆做成食。
我所生活的華北大平原,雖說沒大規模地種植黃豆,但哪個農人家里一年四季能缺了黃豆?它與大米、芝麻等一樣金貴,被放在家中最保險的地方。
比如我家,黃豆是盛放在大肚子廣口的陶缸里的。每年特定的時間用它來做大醬。家里突然來了貴客,就舀上一碗黃豆去李老頭那兒換豆腐,或者炒一碗黃豆做成美味的鹽豆來招待客人。
二
在我們家的飯桌上,幾乎長年都有一碗黑亮的大醬。農忙時節,干了一天活兒,累得渾身酸疼,看見飯桌上油汪黑亮的黃豆醬,便來了精神,拈起大蔥一蘸放嘴里,鮮咸甜綿,就著窩頭,那叫一個香!古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一餐飯,一頓菜,無需昂貴的食材或繁復的烹飪,只需一勺樸實無華的醬,足以讓簡單的食材變得美味。這相當于百味里的統領,讓娘變成了烹飪的好手。
至今不知道大醬為什么能放上幾個凜冬也不壞,而且越放越濃香,越放顏色越黑亮。剛進臘月門,娘就開始準備了,黃豆先炒熟,炒黃豆的大鍋是平時用來蒸饅頭的。在沒有電器化廚具的時代,這大鍋就是家中的主心骨,一口油亮的大鍋代表家中人丁興旺。村人兩家之間結了怨,如果一家把另一家的鍋用磚頭砸了,這仇算是結深了。我坐在灶下燒火,娘站在一旁用小掃帚(鍋刷)唰唰地攪動黃豆。唰唰聲中,劈劈啪啪,黃豆在飛跳。一會兒香味飄出,豆子們相繼被炒熟。熟的豆子要磨成面,這個工作在家是做不來的,村東頭的磨坊,那幾天是最忙的。轟轟的磨面機一開,全村人都能聽到,就會端著炒香的黃豆來排隊。我常常是饞得緊,將磨好的豆面偷偷抓起一把塞在嘴里,噎得臉紅脖子粗直翻白眼。
娘做大醬,就跟變戲法似的:把豆面按照一定的比例加入白面粉,團成一個個手掌心大小的球形捂到一口醬缸里發酵,要等一百天。說起這口醬缸,應該有些年頭了,紫釉大肚,上面纏繞攀枝花紋,靜靜地蹲在南墻根兒下。醬缸要用青條石壓緊,不能進水,更不能進土。一百天后,啟封醬缸,加上足夠的鹽水在陽光下暴曬幾日后再密封,如此這般。十月懷胎,百日釀醬。娘有一套自己的做大醬的程序,且爛熟于心。
捂醬球的日子感覺很漫長,需要等,也值得等待。記得掀開大醬缸的那一刻,滿屋子里飄浮著醬香。娘做醬時有點兒神秘,身上的衣裳整整齊齊,比過年時在灶王爺前跪著磕頭都鄭重。娘說,做醬是個干凈活兒,不能沾了生水,不能手上有油,衣裳得素凈,心得虔誠。
我知道這是一門兒真正的手藝,同木匠、打鐵匠一樣,是口口相傳的老技藝,是一代又一代的傳承。
《齊民要術》里記載著每年的十二月與正月是做豆瓣醬的好時節。據說做醬有許多講究:孕婦不能做醬,醬會變苦;老太太不能做醬,醬會變銹;秀才不能做醬,會淡出只鳥來。這純屬瞎說,我娘這個小老太太做的醬從來都是一等一的好吃。而我大娘做的醬就有一股臭腳丫子味兒。那味道你聞了后,會在鼻腔內存儲很久,以至于一想起便想吐。看來,醬也是有脾氣的,如果跟人較起勁來,那還真是件麻煩事。
我娘變換新的做法,加入了一些辣椒碎和蠶豆瓣,風味立刻變得不同了,醇厚的鄉土味道更加濃烈。后來當我知道娘的作法跟有名的郫縣豆瓣醬相似時,我驚訝地望著我娘,問她,可曾有高廚指點?娘笑而不答。豆瓣醬是在清康熙年間由一位入蜀的移民發明的。傳說他在入蜀時途經郫縣,其賴以充饑的蠶豆遇連日陰雨而生霉卻又不舍得扔掉,便拌進辣椒為食,沒想到竟然鮮美無比。其后制作豆瓣醬便以此為主料,這就是郫縣豆瓣醬的起源。我娘真是不凡啊!娘的發明還多著呢。有一年家中得一大塊五花排骨,娘把它煮熟,放到醬缸中儲存,醬的醇厚慢慢煨到肉脂中,吃時,有一種從未有過的厚重味道,配上酸菜一燉,那真是大醬排骨滋味長啊!
做醬羹的歷史可謂久遠。醬的釀造最早是在西漢。西漢元帝時代的《急就篇》中有記載,“蕪荑鹽豉醯酢醬”。唐·顏氏注:醬,以豆合面而為之也。在沅陵出土的漢代《美食方》中有名為“菽醬汁”的調味品,即以豆為原料的醬汁。從古人的記載和注解中可以看出,豆醬是以大豆和面粉為原料釀造而成,為何漢代人只用大豆混配面粉做豆醬?或許是因為大豆含蛋白質豐富,面粉含淀粉較多。蛋白和淀粉同時存在,更適宜多種有益霉菌的繁殖,大量的菌體產生各種酶,使原料中的各種營養成分充分分解而生成了風味獨特的豆醬。
三
黃豆做成豆腐,據說是西漢淮南王劉安的發明,千年來文人們并未做真假的考證,但喜歡常以此為題,寫入詩詞歌賦。“一輪磨上流瓊液,白沸湯中滾雪花”“磨礱流玉乳,蒸煮結清泉”,便是做豆腐的生動畫面。蘇東坡曾寫過“煮豆作乳脂為酥,高燒油燭斟蜜酒”的詩句,他是有多愛吃這乳脂般的豆腐啊!元末明初大學者謝應芳,晚年食豆腐出名,“淡而不厭知者誰,中庸君子古來稀”“不是醍醐,卻又勝似醍醐”,堪稱對豆腐夸到極致。當代文人汪曾祺老先生亦視豆腐為上上品。
如今吃水嫩嫩的豆腐,尤其是吃出小時候那種味道可不是容易的事。制作時間當然不可壓縮,從浸泡黃豆到磨豆漿、過濾、熬豆漿、點制、出成品,非得多半天工夫不可。村里李老頭兒專做豆腐。李老頭兒做的豆腐真香,還出數,禁吃。只要一聽到“”的聲音,那就是李老頭和豆腐出場了。急急端上一碗黃豆跑出門:大伯——來兩塊大豆腐,切成格子塊!用一碗黃豆可以換兩大塊豆腐,能吃好幾頓。那時很少見到錢,黃豆換豆腐,雞蛋換油,玉米換蔬菜,交換的方式簡單而頗有古風。
這么白嫩潤滑的豆腐立刻吃掉往往會產生食在天堂的富足感,但還是耐著性子把切成四四方方的小格子塊放蓋簾上碼整齊,凍在嚴冬的房檐下,幾個冷天,就可凍成豆腐坨。燴菜的時候放幾塊進去,綠的白菜,紅的臘肉,白的豆腐,再抓上一把紅薯粉條,這樣一大鍋燴菜,“咕嘟咕嘟”一燉,大年就合著溫暖的菜香味到來了。
李老頭的磨坊是用他家最好的一間屋子改造出來的,門楣上用石灰寫出“磨坊”兩個字,“坊”字最后一撇包裹在“磨”字上,神秘感撲面而來。磨坊一般不讓小孩子進,這就更加重了我對磨豆腐的好奇,好吃的豆腐究竟是如何做出來的?有時大人進去,我便偷偷跟著溜進去。那時豆腐是純手工做出來的。屋子正中間那盤石磨真大,足有我兩個身高寬,濕淋淋的胖黃豆,金黃中透著芳香,一勺勺放入磨盤中間的洞里,有幾顆落在石磨上跳著芭蕾,能聽見足尖轉動的聲音。兩個人推動上層的磨盤,“轟隆隆”轉起來,白色的漿水順著石磨邊緣溢出,再順著石槽流進地上放的大桶里。泛著白色泡沫的大桶似乎蒸騰著熱氣。再看鍋臺上方,李老頭天天敲的梆子潤亮亮地似個小枕頭掛著。大鍋里,沸騰的漿水似乎馬上要漾出來,其實不用擔心,主人早已了然于心。煮開的漿水倒進系在從房梁伸下來的搖架的包袱里過濾。再轉眼,稀稀的一大鍋漿水就凝結成香得無法言表的豆腐塊兒了。一大家人齊上陣,有加豆子的,有推磨的,有看鍋的,好不熱鬧,他們臉上專注的神情讓人看了著迷。
是不是很麻煩?當然麻煩。有時候,麻煩做出來的東西才夠滋味。精工出細活兒,還出味道呢。
四
豆棵上長著嫩青的豆莢時,揪一把回家,放在鍋里加水加鹽煮了吃,是另一種風味。但這種時候是很少的,母親覺得這樣吃就是敗家。清水煮豆拿在手中的那一刻,眼前飄著一種來自土地的腥香,腥香中有清甜。我對這種味道尤其迷戀。寒冬臘月的天,如果家里實在一點兒菜都沒有了,娘會做鹽豆。干黃豆放炒鍋里慢慢煸熟,起鍋后趁黃豆熱著拌進蔥花醬油,再加上小半匙葷油,用蓋碗蓋好,片刻,則成一道上好的菜。吃起來有黃豆的香,有微微的韌,有作料的復合味道。
我時常想起那個場景:娘正費勁地把缸底的一把黃豆出來,放炒鍋里煸香,門“吱呀”一聲打開,二姨招呼都沒打就進來了。貧寒與窘迫的光景娘是不愿讓外人看到的,盡管二姨不是外人。二姨從挎著的包里神秘地捧出一塊兒老臘肉。我記得,吃飯時,娘的眼睛紅紅的,二姨卻有說有笑,一個勁兒的逗著我們開心。
五
黃豆可入藥。有一個治療頸椎病的方子,黃豆納入囊中,做成黃豆枕頭,每晚枕睡,治療頸椎。孫思邈《千金要方》中就提到過,用“大豆一斗”,納入囊中,做成枕頭,可“治頭項”。這是借用了黃豆的滾動,來按摩頸部,緩解肌肉和韌帶的酸痛。
多少年了,這些帶有清香味的大豆,仍然是我的心頭之愛。那濃濃的味道,令我從未忘記過鄉村。
有人說,美食和風景可以抵抗所有的悲傷和迷惘。來自故土的每一份食物也曾撫慰過我思鄉的情懷。鄉間的日子雖然瑣碎平凡,親人們卻不忘一次次在不同的季節里賦予它們新的儀式感。比如現在,一到春天,我就想念馬齒莧餡兒的大包子;一到仲夏,我就想念蔥白蘸油汪黑亮的黃豆大醬;一到金秋,我就想念帶著腥香味的煮鮮大豆;一到凜冬,我就想念大塊兒的豆腐燉酸菜。每吃完一道菜就會實現一個我回家后的愿望,安撫我散布在回家途中的醒目路標——鄉愁。
張 艷: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會員,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駐校作家,作品發表于《中國自然資源報》《中國礦業報》《散文百家》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