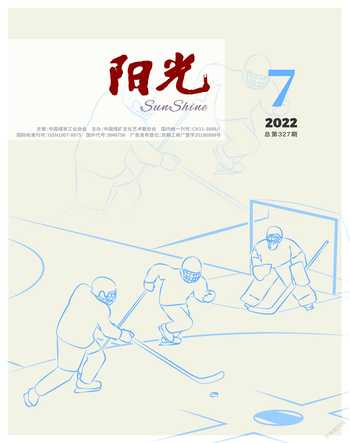岷水流過(guò)都江堰
宋揚(yáng)
“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千水自西來(lái),萬(wàn)源終歸東。每一滴水都逃不出造化的安排,每一條江河都沿著自西(北)向東(南)的路徑日夜不息,或萬(wàn)馬奔騰,或溫婉無(wú)聲。
有一條江,也沿著這個(gè)軌跡晝夜不舍。它從川西高原阿壩藏族自治州弓杠嶺和郎架嶺的雪山之巔出發(fā),穿成都平原,經(jīng)青神、樂(lè)山、犍為,于宜賓注入長(zhǎng)江。它就是天府之國(guó)的母親河——岷江。
岷江于幽微處發(fā)端,誰(shuí)能想象水的原初只是雪山頂?shù)囊黄┗蚴堑氐紫碌囊谎廴K牧鲃?dòng)與歸宿是征服,是裹挾,是沖撞,是凝聚,是操著不同鄉(xiāng)音、攜帶不同土質(zhì)的水民族的融合、分離、再融合,最后百川歸海,到達(dá)宿命的終點(diǎn)。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wàn)里船”。沒有千秋西山雪,成都市區(qū)可行萬(wàn)里船的錦江(岷江支流之一)就是一溝死水。成都平原整個(gè)地勢(shì)從都江堰市玉壘山向成都市中心城區(qū)東南方向傾斜,都江堰距成都不出五十公里,落差竟達(dá)二百七十三米,坡度不小。岷江是成都平原頭頂?shù)氐赖膽医∪绻篷R由韁,任沖出川西山谷的岷江水恣意奔突,成都注定會(huì)被洪水淹沒成魚國(guó)鱉府。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岷江水患,長(zhǎng)期禍及西川,鯨吞良田,侵?jǐn)_民生。而這種情景,恰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前的真實(shí)景況。
半是魔鬼半是仙,水的潤(rùn)澤與殺伐從來(lái)相生相伴,一如人的敬畏帶給水尊嚴(yán),也如人的無(wú)知和生存的無(wú)奈帶給水羞辱與傷害。每年清明節(jié),都江堰放水大典隆重舉行,人們祭拜岷江,感恩岷江,又源源不斷地將生產(chǎn)、生活廢水傾瀉入岷江。一條渾身碧綠的翠龍?jiān)趰{谷深溝中奔跑,它流過(guò)高樓摩天、機(jī)車轟鳴的城市,它的碧綠慢慢衰減,直至它獻(xiàn)祭出澄澈,以污濁自己的方式清洗、包藏、容納工業(yè)文明的一切衍生物。
不到都江堰,你對(duì)蜀水的理解一定是偏頗的。你會(huì)錯(cuò)覺于蜀水只是“黃四娘家花滿溪”的雅致,只是“影入平羌江水流”的寧?kù)o,只是“門泊東吳萬(wàn)里船”的喧騰。只有登上玉壘山,你才能讀懂錦江秋色自天地洶涌而來(lái)的磅礴氣魄,讀懂造就這蜀山秀色的正是眼前波瀾壯闊的滔滔岷江。無(wú)數(shù)次見過(guò)水,見過(guò)無(wú)數(shù)地方的水,都遠(yuǎn)不及站立在魚嘴(分流堤)前,眺望蜀水滾滾西來(lái):仰天嘯,壯懷烈,我不由萌生出按劍俠客蕭蕭寒風(fēng)中與天地對(duì)峙的豪邁。恍惚間,我化為了一柄劈波斬浪的利劍。劍鋒所指,魚嘴所向,岷江水霍然二分。冬夏枯榮,水退水升,或四六,或二八,這劍、這魚嘴調(diào)節(jié)內(nèi)外二江流量竟如此靈活!“深淘灘,低作堰”,堰不必太高,灘必須深淘。李冰父子深諳治水先驅(qū)大禹思想之精髓。“治水之道,宜疏不宜堵”是大禹留給治水蜀人的警世恒言。
人與水的初戰(zhàn),與自然斗其樂(lè)無(wú)窮的豪邁和對(duì)水性的尊重雙管齊下,力量、馴服、誆哄、疏導(dǎo),各顯神通。被分水堤切割到內(nèi)江的水,并未就此舉起雙手投降。離堆前,洄水窩,潛龍至此,誤入淺灘不戰(zhàn)而屈人膝下的屈辱感,終于有了發(fā)泄之所。如飛龍?jiān)谔欤匦⒗④f射、沉入、翻涌,驚濤拍岸,濺玉飛雪,拋撒龍鱗萬(wàn)萬(wàn)千。
幾番苦痛,糾纏,掙扎,消磨盡最后一絲憤怒,水龍?jiān)趯毱靠谡业匠隹凇kS后,龍?bào)w幻變?yōu)榻埠印⒆唏R河、柏條河和蒲陽(yáng)河流向廣沃的成都平原,它們是都江堰這顆永不停止跳動(dòng)的心臟搏射出的四股生命之血,每一股又延伸到更貼近城市、鄉(xiāng)鎮(zhèn)、村莊的毛細(xì)血管,水網(wǎng)縱橫,維系起天府之國(guó)的滋潤(rùn)與豐收。沒有這四條河的疏浚,洶涌至寶瓶口的水,將以野蠻的姿勢(shì)泛濫摧毀整個(gè)成都平原。沒有都江堰水利工程對(duì)水的調(diào)節(jié)輸出,成都平原在枯水季又成一片焦土。
岷江從山谷沖出來(lái)時(shí),是一首九曲回腸的川江號(hào)子。奔涌到伏龍觀下,是一曲與命運(yùn)抗?fàn)幍慕豁憳?lè)。流過(guò)寶瓶口,流過(guò)都江堰城區(qū)的南橋,流進(jìn)漠漠大荒,岷江的沉悶嗚咽才漸消漸止。平原如砥,如剛猛的拳頭砸在棉花堆上,岷江不可一世的奔涌之力悄悄被闊野化解。至此,我寧愿稱它們?yōu)槭袼瑴赝瘛⑵届o、潺緩的蜀水。都江堰水利工程終以佛一樣的胸懷令洶涌的岷江接受了蜀人對(duì)舊山河的重新安排,完成了岷江與“天府之國(guó)”的相互成全。
先民開掘道路,多沿江而建,江有多長(zhǎng),路就有多長(zhǎng)。“西關(guān)”“玉壘關(guān)”高聳于江邊玉壘山的虎頭崖上,扼古道之咽喉。雄關(guān)外,古道邊,秋草碧云天。岷江東畔,“松茂古道”是連接成都平原和川西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的一條重要走廊,其寬不過(guò)兩米,最窄處兩個(gè)人不可并行,全長(zhǎng)三百多公里,可抵達(dá)更遠(yuǎn)的新疆、西藏。正所謂“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坐地日行八萬(wàn)里,巡天遙看一千河”。時(shí)代發(fā)展高歌猛進(jìn)。岷江之濱,從“松茂古道”到成(都)阿(壩)公路,到都(江堰)汶(川)高速,到正在建設(shè)的西(寧)成(都)高鐵。未來(lái),人們可以各種方式進(jìn)入莽莽蜀山,追溯蜀水之源。老子云:“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于江海。”都江堰水利工程是蜀地天水、靈山、智人協(xié)和統(tǒng)一之結(jié)晶。人與山與水和諧共生,這是水之道,是山之道,也是人之道。
都江堰水利工程百代長(zhǎng)春,以不變的流淌,向下、向外,再向下、再向外,恒定為成都平原輸送生命之源。這當(dāng)然也要?dú)w功于世世代代為都江堰的歲修獻(xiàn)出金銀物資、血肉之軀、甚至生命的人。
野渡無(wú)蹤賢哲慈懷憐萬(wàn)物,索橋重建夫妻大德濟(jì)群生。安瀾索橋,老百姓又叫它“夫妻橋”。這座橫跨都江堰水利工程內(nèi)外二江的交通樞紐明末毀于張獻(xiàn)忠入川。清嘉慶八年(1803),當(dāng)?shù)厝撕蜗鹊路驄D倡議集資重建時(shí),何君竟慘遭欲長(zhǎng)期收取兩岸百姓高額渡船費(fèi)的“水霸”之毒手。玉壘山下,矗立著一座高高的“德政坊”。清光緒年間,水利同知(知府副職)敬修之察民無(wú)力負(fù)擔(dān)歲修之竹料,遂改民間攤派為官方采購(gòu),此制沿用至今。
水運(yùn)系乎國(guó)運(yùn),治水方能治蜀。從來(lái)富民先治水,休言吃飯必由天。李冰治水時(shí)代之后的今天,“人民渠”“東風(fēng)渠”兩大高速水道相繼建成。都江堰灌區(qū)從成都平原擴(kuò)灌到川中、川北丘陵區(qū)。二○二一年,都江堰灌溉面積發(fā)展到一千一百三十萬(wàn)畝,涉及成都、綿陽(yáng)、德陽(yáng)、遂寧、資陽(yáng)、樂(lè)山、眉山七市四十縣。灌區(qū)以占全省約百分之五的土地貢獻(xiàn)出全省近百分之二十五的糧食產(chǎn)能。岷江讓遠(yuǎn)古蜀民留下的洪澇交織的記憶從此一去不復(fù)返,天府四川“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時(shí)代已經(jīng)到來(lái)。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岷江自西,濤濤流過(guò)都江堰。這一流,就是千年萬(wàn)年……
宋 揚(yáng):中國(guó)散文學(xué)會(huì)會(huì)員,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作品發(fā)表于《人民日?qǐng)?bào)》《散文》《延河》《野草》《青海湖》等報(bào)刊,出版散文集《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