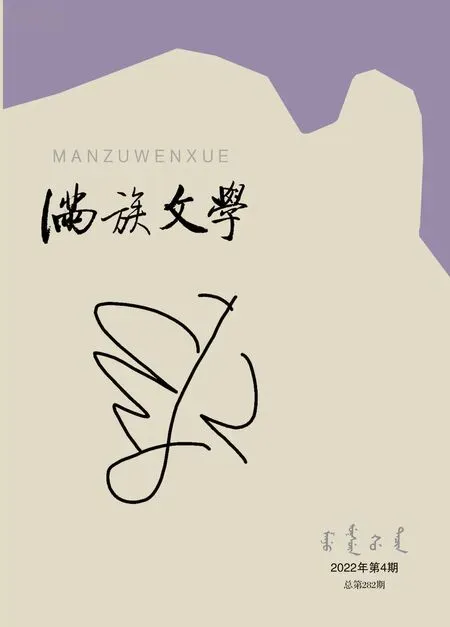來(lái) 途
夏 商
紐約時(shí)間5 月23 日下午,朋友圈流傳評(píng)論家林建法在沈陽(yáng)去世,噩耗證實(shí)后,我委托小說(shuō)家于曉威代買(mǎi)一只花圈,以送林老師一程。我們聊到了死亡,我印象中的林老師還是二十一年前那個(gè)玉樹(shù)臨風(fēng)的中年人,他來(lái)浦東找我談點(diǎn)事,在塘橋的一家海鮮小館,我們小酌,餐后送他去輪渡站回浦西旅館,他在擺渡船上,我在岸上,彼此揮手,未曾想這就是我們?nèi)馍淼挠绖e——他常來(lái)上海,來(lái)去匆匆,我懶散不愛(ài)出門(mén),后來(lái)就再?zèng)]遇上,直到傳來(lái)他的死訊——近幾年聽(tīng)說(shuō)林老師罹患重疾,對(duì)他的離去有心理準(zhǔn)備,可七十三歲畢竟不算高壽,不免唏噓和哀傷。
等落實(shí)了林老師的花圈,曉威給我布置一個(gè)任務(wù),給他業(yè)余幫忙的《滿(mǎn)族文學(xué)》“名家回顧處女作”欄目寫(xiě)一篇文章,第一反應(yīng)我想婉拒,一來(lái)這些年手里在寫(xiě)新長(zhǎng)篇,為不分心謝絕了所有約稿。二來(lái)自覺(jué)尚年輕,怎已倏忽到了回憶處女作的年齡。轉(zhuǎn)念一想,眼下我的年齡,跟二十一年前的林老師接近,已是如假包換的中年人了,再想到自己的父親,也不過(guò)活了七十五,如果壽命可作遺傳參數(shù),生命的倒計(jì)時(shí)也就二十多年了,之所以自覺(jué)尚年輕,不過(guò)是一廂情愿的自我欺騙,不甘老去罷了。
回憶是老去的必修課,恍惚間,從事寫(xiě)作已逾三十年,半截黃土回望,那就寫(xiě)一篇吧。
處女作當(dāng)然沒(méi)齒難忘,一篇二千字左右的散文,題為《雨夜陷阱》,發(fā)表于《劍南文學(xué)》。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有幾本公開(kāi)發(fā)行的地級(jí)刊物,譬如南京的《青春》、常州的《翠苑》、個(gè)舊的《個(gè)舊文藝》、杭州的《西湖》、成都的《青年作家》,頗有些特色和聲譽(yù),也包括這本綿陽(yáng)的《劍南文學(xué)》。
雖記得篇名,可因年代久遠(yuǎn),具體發(fā)表在哪年哪期,卻記不清了。昨天花了一個(gè)多小時(shí),在書(shū)架上尋這本樣刊,惜未找到,搜索引擎輸入“劍南文學(xué)雨夜陷阱”,亦未查到匹配條目,想破頭,大致是發(fā)表于1988 年或1989 年,而收到用稿函,應(yīng)是春天或秋天。
那時(shí)我在一家化工廠當(dāng)操作工,因離家騎車(chē)才十分鐘,所以中班都回家吃晚飯,然后再騎回廠,待晚上十點(diǎn)下班。途經(jīng)港機(jī)新村公交站,一個(gè)我喜歡的姑娘正在黃昏中候車(chē),她很像演黃蓉的翁美玲,大眼睛,小個(gè)子。她在針織五廠當(dāng)擋車(chē)工,我們是在一次團(tuán)委組織的聯(lián)誼會(huì)上認(rèn)識(shí)的。我剎住車(chē)把,單腳踩地跟她打招呼,她笑起來(lái)牙齒很齊,說(shuō)你衣服上哪能都是白斑?我低頭一看,那些白斑像鳥(niǎo)屎,牢固地黏在滌卡工裝上,是每個(gè)化工操作工都有的勛章——原料反應(yīng)后的糊狀物——我為邋遢而羞愧,后來(lái)都不好意思約她看電影了。
每個(gè)在女孩面前丟的臉,都會(huì)記憶深刻,之所以能確定那天穿滌卡工裝,是因?yàn)橄奶炫聼嵛掖┒绦洌炫吕湮掖┟抟\,穿滌卡只能是春秋兩季,雖模糊了雜志的發(fā)表期數(shù),那個(gè)姑娘略帶嫌棄的笑意卻至今清晰,說(shuō)明記憶本身的篩選功能大于我的遺忘。
公交車(chē)來(lái)了,她上了車(chē),我也離開(kāi)車(chē)站。前面不遠(yuǎn)就是我家所在的臨沂三村,上樓時(shí),照例看了下門(mén)洞旁的綠皮信箱,此乃兵營(yíng)式住宅樓的標(biāo)準(zhǔn)信箱,一幅大鐵皮折疊在墻上,劃分成二十四個(gè)小格。代表這個(gè)門(mén)洞有二十四戶(hù)人家(一層四戶(hù)共六層)。信箱口是條細(xì)縫,只能塞進(jìn)薄信,彼時(shí)上海家家戶(hù)戶(hù)都訂《新民晚報(bào)》——尚未像千禧年后增頁(yè)擴(kuò)版,還是兩張八開(kāi)小報(bào)——折后塞不進(jìn)信箱口,露一部分在外。
對(duì)我這種時(shí)時(shí)收到退稿的文學(xué)青年來(lái)說(shuō),每份謄在文稿紙上的稿件都比《新民晚報(bào)》還厚,所以干脆不像鄰居那樣把信箱鎖住,虛掩著,讓郵遞員打開(kāi)塞入,郵件反而不會(huì)掉地上。
我是從征地進(jìn)工廠后開(kāi)始寫(xiě)作的,我家在浦東一個(gè)叫周家弄的自然村,隸屬于川沙縣,離當(dāng)時(shí)還未撤銷(xiāo)的南市區(qū)所轄浦東飛地較近,騎車(chē)七八分鐘就是著名的南碼頭輪渡站。80 年代初葉,總有動(dòng)遷的消息在傳。像暗火,風(fēng)一吹就燃,很快又熄了,過(guò)一陣又燃。如此數(shù)年,最后周家弄連同更大范圍的拆遷,落實(shí)在南浦大橋這個(gè)項(xiàng)目上。
我家所在的位置,并不在橋堍范圍,而是用于安置動(dòng)遷戶(hù)的臨沂新村建設(shè),直到今日,我還能辨識(shí)出我家大體的位置,從浦東南路拐進(jìn)浦三路,步行六七分鐘,路邊有個(gè)變壓器,對(duì)面即是已無(wú)痕跡的我家舊址:一座社區(qū)商業(yè)建筑的一隅。
我兒時(shí)住在滬西祖母家,九歲才回浦東讀一年級(jí),初二輟學(xué)。至于輟學(xué)的原委,曾在微信朋友圈有過(guò)交代,為填充本文的完整性,摘抄如下:
打的遇到一初中同學(xué),竟還認(rèn)得我,送我到目的地后執(zhí)意不收車(chē)費(fèi),推了幾下我嫌難看,就隨他去了。他想留微信,我借口不用,就沒(méi)留,不是不念舊,實(shí)在是沒(méi)什么話(huà)題了。短暫的車(chē)程中他說(shuō)同學(xué)知道我成了作家都以我為榮,我說(shuō)我輟學(xué)時(shí)還不叫夏商你們?cè)趺粗赖模克f(shuō)學(xué)校搞過(guò)兩次大的校慶,有些同學(xué)去了,在杰出校友名錄里有你。問(wèn)我當(dāng)時(shí)為什么突然轉(zhuǎn)學(xué)了,校慶也沒(méi)見(jiàn)我在場(chǎng)。我笑笑沒(méi)說(shuō),告別后不禁勾連起不愉快的回憶。我就讀的浦東中學(xué),是一所沒(méi)落的老民國(guó)名校,我不算優(yōu)等生但也不算差生,語(yǔ)文老師和書(shū)法老師都很喜歡我,還代表學(xué)校參加過(guò)川沙縣的作文比賽。初二上半學(xué)期的一個(gè)下午,地理課,我做小動(dòng)作(當(dāng)然這不對(duì)),教地理的是個(gè)五十多歲的老寧波,一句話(huà)不說(shuō),沖下來(lái)就是一個(gè)耳光,我那時(shí)跟鎮(zhèn)上一個(gè)南拳武師學(xué)散打,又正是看七俠五義的年齡,男兒怎可以被抽耳光,立刻和他對(duì)打,無(wú)奈力氣小被打得鼻血直流,當(dāng)然他也中了我?guī)兹痪梦揖碗x開(kāi)了學(xué)校,同學(xué)們不知道以為我轉(zhuǎn)學(xué)了,其實(shí)是被勒令退學(xué)了。所以我永遠(yuǎn)記得那個(gè)寧波人,所有喜歡體罰的老師都不是好老師。過(guò)了若干年,當(dāng)初喜歡我的那個(gè)語(yǔ)文老師告訴學(xué)校我成了青年作家,校慶辦就有人電話(huà)邀請(qǐng)我,我謝絕了,又過(guò)十年,好像是百年校慶,又轉(zhuǎn)彎找到我,我還是謝絕了,并且希望不要再把我印在杰出校友錄里。我真的不是杰出校友,而是一個(gè)被斥退的學(xué)生,如果真的坐在主席臺(tái)上,和學(xué)弟學(xué)妹們說(shuō)些什么呢,內(nèi)心來(lái)說(shuō),我不認(rèn)為這是一所對(duì)學(xué)生負(fù)責(zé)的學(xué)校,而且把當(dāng)年的棄生放進(jìn)杰出校友錄這個(gè)舉動(dòng),顯得那么猥瑣,那么市儈。既然當(dāng)初一別兩寬,那就往后各生歡喜。
輟學(xué)那年我十五歲,力比多旺盛的少年,除了跟社會(huì)上的小混混打打群架,就是到文化宮或電影院門(mén)口搓妹妹,搓妹妹有時(shí)也叫搓垃山,是上海話(huà)切口,撩妹的意思。有一次,為了一個(gè)姑娘,一個(gè)矮壯的黑漢找到我家,可把我父母嚇壞了,剛巧奶奶要去建湖老家,就讓我跟著去住一陣。
建湖老家的那個(gè)村子叫東夏村,旁邊還有一個(gè)樓夏村,據(jù)夏氏家譜記載,最早的老祖宗是長(zhǎng)沙刺史,后來(lái)到了蘇州,朱元璋紅軍趕散,家族被驅(qū)趕到蘇北,據(jù)說(shuō)東夏村這一支是大老婆生的,樓夏村這一支是小老婆生的,反正“夏”在這兩個(gè)村是絕對(duì)大姓。
一住就半年多,跟一個(gè)只比我大一歲的本家叔叔——更夸張的是,村里還有六七十歲的本家哥哥——學(xué)會(huì)了摸泥鰍,有一次摸到了一條大蛇,嚇得趕緊扔了。
我好像喜歡上了鄰居家那個(gè)在縣城讀書(shū)的女孩,她每星期回來(lái)一次,不常能見(jiàn)到,我很希望能邂逅她,可直到回上海,我們加起來(lái)的對(duì)話(huà)也沒(méi)超過(guò)十句。
這期間,上海家里的動(dòng)遷正式開(kāi)始了,作為土地被征用的補(bǔ)償,我作為農(nóng)民工被分配進(jìn)上海助劑廠,在我們那片,有化工廠三只雞之說(shuō),一只“雞”指位于南碼頭的溶劑廠,一只“雞”指位于六里橋的制冷劑廠,還有一只“雞”就是位于白蓮涇的助劑廠,雞是劑的諧音,三家效益都不錯(cuò),能“吃到”其中一只“雞”就算分配得不錯(cuò)。
但還不能立刻上班,要滿(mǎn)十六足歲方可報(bào)到,若不然有童工之嫌。所以我清楚記得,去工廠報(bào)到是1985年12月15日,我十六歲生日那天。
助劑廠是上海化工局下屬的全民企業(yè),征地工屬于大集體,是廠內(nèi)備受歧視的“二等公民”,干的也是最累最臟的活,我在一車(chē)間固色劑工段翻三班,跟刺激性很強(qiáng)的甲醛和冰醋酸打交道,干活時(shí)戴兩只口罩,鼻腔內(nèi)仍是怪異的氣味。
工廠里有形形色色的人,食堂里常見(jiàn)一個(gè)漂亮的女廠醫(yī),長(zhǎng)得像電影明星李秀明,都在傳她跟銷(xiāo)售科的一個(gè)男人“軋姘頭”,她腰桿挺直,白大褂遮不住很高的胸脯,好像對(duì)那些閑言碎語(yǔ)無(wú)動(dòng)于衷,她是我當(dāng)年的夢(mèng)中情人。隔壁工段有個(gè)龍哥,跟他弟弟合伙在老西門(mén)開(kāi)水果店,他有很多葷段子,總是把男女之事描述得繪聲繪色,后來(lái)才知道,他竟然是個(gè)“同志”。還有那個(gè)反應(yīng)遲鈍的老司爐工,據(jù)說(shuō)年輕時(shí)是個(gè)花癡,吃藥把腦子吃壞了。他那兒的暖氣片比別處暖和,夜班時(shí)我常去“蹭熱度”,每次拿一本小說(shuō),趴在暖氣片旁讀。一暖和人就容易犯困,有一次,腦袋磕在暖氣片上,烙了道紅印,很久才蛻出皮膚原來(lái)的顏色。
我一直想逃離工廠,倒不是吃不起苦,主要是沒(méi)什么前途。班里有個(gè)胖子,私下說(shuō)想去日本打工,我問(wèn)他去日本怎樣賺錢(qián),他說(shuō)背死人很賺錢(qián)。見(jiàn)我面露驚色,他笑了,你也想去日本啊,去考個(gè)廚師證吧。我真就去學(xué)了烹飪,至今還能做一兩百種不重樣的菜。
去日本哪那么容易,當(dāng)然就沒(méi)去成。我準(zhǔn)備辭職開(kāi)個(gè)熟食店,從六里橋到南碼頭,騎車(chē)到處轉(zhuǎn),考察的結(jié)果是,郵票大的地方已有十幾爿熟食店,只好打消了念頭。
無(wú)論是日本打工還是開(kāi)熟食店,都是為稻粱謀,身體內(nèi)有一個(gè)更強(qiáng)烈的聲音,你該把那些奇怪的想法寫(xiě)出來(lái),萬(wàn)一發(fā)表了呢。身體內(nèi)還有另一個(gè)聲音,你一個(gè)初二沒(méi)畢業(yè)的農(nóng)轉(zhuǎn)非小青工奢望當(dāng)作家,簡(jiǎn)直是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這個(gè)詞,我是從《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前言里看到的,這本約瑟夫·海勒的名著是小閔推薦給我的,他是南碼頭新華書(shū)店的營(yíng)業(yè)員,一個(gè)國(guó)字臉的文學(xué)青年,他不寫(xiě)作,卻似乎很了解文學(xué)行情。有一次他神秘地從書(shū)架背后取出兩本書(shū),一本是讓-保羅·薩特的《厭惡及其他》,一本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說(shuō)是緊俏貨,特地給我留著,跟往常一樣,但凡他推薦的書(shū),我立刻就買(mǎi)下了。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書(shū)店?duì)I業(yè)員小閔啟蒙了我的文學(xué),為我打開(kāi)了窗戶(hù),讓我知道小說(shuō)還有那么多寫(xiě)法,他是為我提供第一份文學(xué)書(shū)單的人,有些書(shū)目直到今天仍不過(guò)時(shí)。
書(shū)店去多了,有幾張老面孔,看到彼此買(mǎi)的書(shū),會(huì)聊幾句,慢慢就有點(diǎn)熟絡(luò)。其中一個(gè)姓奚的青年,比我大幾歲,也喜歡買(mǎi)文學(xué)書(shū)。這天下午又在書(shū)店遇到,他告訴我一個(gè)信息,上海牙膏廠周末要辦一場(chǎng)文學(xué)沙龍,如果不嫌遠(yuǎn)可以去參加。我說(shuō)大自鳴鐘的那家牙膏廠?小奚說(shuō)沒(méi)錯(cuò)就在大自鳴鐘。我說(shuō)那我認(rèn)識(shí),安遠(yuǎn)路膠州路那兒,離我奶奶家不遠(yuǎn)。
到了周末,晚飯沒(méi)吃就出了門(mén),南碼頭輪渡口旁有爿點(diǎn)心店,買(mǎi)了兩只香菇菜包,擺渡船上吃完,一靠岸,就往滬西方向騎去。牙膏廠我常經(jīng)過(guò),跟去奶奶家的路基本重合——自小往返于滬西浦東,沿途的每個(gè)拐角都熟稔于心——可那天愣是繞了好幾圈才找到門(mén)牌,此刻回想,只能是一個(gè)原因,因激動(dòng)而“慌不擇路”。
那真是一個(gè)文學(xué)的時(shí)代,不,應(yīng)該說(shuō)是文學(xué)青年的時(shí)代。進(jìn)了廠門(mén),找到那個(gè)房間,已坐了不少人,還有人陸續(xù)而來(lái),沒(méi)有糕點(diǎn),沒(méi)有水果,連瓶裝水都沒(méi)有(好像那時(shí)市場(chǎng)上還沒(méi)有瓶裝水)。我看到了小奚,他忙前忙后,對(duì)環(huán)境很熟悉的樣子,才意識(shí)到他應(yīng)該就在牙膏廠工作,輕聲去問(wèn)他,他點(diǎn)點(diǎn)頭,說(shuō)自己是團(tuán)干部,是這場(chǎng)文學(xué)沙龍的組織者。
小奚在開(kāi)場(chǎng)白里說(shuō),今晚來(lái)了一百多位文學(xué)愛(ài)好者,有的從遠(yuǎn)郊趕來(lái),最遠(yuǎn)的來(lái)自昆山和蘇州。我左右看看,男性居多,女性大約兩成,年齡大致在二三十歲,也有少量中年人。大家都很局促,用今天的話(huà)說(shuō),都有點(diǎn)社交恐懼癥。舉辦沙龍的目的當(dāng)然是交流文學(xué),可大家都不知從何說(shuō)起。
不過(guò)活動(dòng)還是有兩次高潮,一次是小奚介紹邀請(qǐng)來(lái)的兩位文學(xué)編輯,一位來(lái)自《上海文學(xué)》(也可能是《萌芽》),另一位來(lái)自《勞動(dòng)報(bào)》“文華”副刊。文學(xué)愛(ài)好者見(jiàn)到文學(xué)編輯,相當(dāng)于觀眾見(jiàn)到大明星,很多人都去索要名片,我心里也想,屁股卻黏在椅上。這是我第一次見(jiàn)到活的文學(xué)編輯,膽怯得呼吸都短,根本沒(méi)勇氣去套近乎。
再一次是活動(dòng)快結(jié)束時(shí),主辦方給每位文友發(fā)了一本油印小本子,里面是文學(xué)刊物的主編名字、電話(huà)(當(dāng)時(shí)很多城市的號(hào)碼還是四位數(shù)或五位數(shù))和地址(郵編還沒(méi)有出現(xiàn))。這個(gè)小本子對(duì)文學(xué)愛(ài)好者來(lái)說(shuō),簡(jiǎn)直是久旱甘霖。因?yàn)楹芏嗳烁静恢老蚰睦锿陡澹源蠹叶己苷駣^,有人還歡呼起來(lái),感覺(jué)距離成為作家又近了五厘米。
有了這個(gè)小本子,意味著稿件有了去處,我的寫(xiě)作熱情被激發(fā)了,買(mǎi)了很多五百格文稿紙,層出不窮的故事向我涌來(lái),好像總也寫(xiě)不完。這個(gè)小本子收集的文學(xué)雜志很全,我也搞不清名刊和小刊的區(qū)別,幾乎給里面所有的刊物都投過(guò)稿。
因?yàn)槌醵掳雽W(xué)期都沒(méi)念完,文字基礎(chǔ)太差,稿件無(wú)一例外被退回了。退稿上常有紅筆涂改,那時(shí)的編輯認(rèn)真,即便不留用,有時(shí)也會(huì)幫作者改錯(cuò)別字和病句,一次次退稿,當(dāng)然是一次次打擊,讓我知道搞文學(xué)不比在車(chē)間干體力活,光有一股蠻力就可以。
為增加詞匯量,我把1979 年版《辭海》啃了一遍,灰色封皮的《同義詞詞林》也被翻爛了。可寫(xiě)作光有詞匯是不夠的,得借助大量的閱讀來(lái)提高語(yǔ)感和敘事能力。退回的稿件我會(huì)修改一遍,換一家刊物再次寄出,買(mǎi)郵票花了我不少零花錢(qián),明知發(fā)表渺茫,依然樂(lè)此不疲。這種盲目的、大海撈針式的投稿,或許是出于試圖改變命運(yùn)的執(zhí)拗,也是對(duì)迷茫人生賦予意義的一種無(wú)意識(shí)。不夸張地說(shuō),退稿肯定不止兩百次,甚至超過(guò)三百次。那個(gè)幾乎每天都會(huì)撞見(jiàn)的郵遞員估計(jì)把我當(dāng)作了偏執(zhí)癥患者,他是個(gè)瘦猴,左腮有顆痣,痣上有根毛,我把他的形象寫(xiě)進(jìn)了一個(gè)短篇小說(shuō),寄給《四川文學(xué)》,卻再無(wú)回音。因?yàn)闆](méi)留底稿,成為唯一佚失的一篇小說(shuō)。后來(lái),我就用復(fù)印紙謄寫(xiě)稿子了。
讓我們回到那個(gè)黃昏,穿著滌卡工裝回家吃晚飯的我,上樓時(shí),照例看了下門(mén)洞旁的綠皮信箱。里面有封信,與之前原去原回的厚信封不同,薄薄一箋,顯得非同尋常。我的心跳猛然加快,雞皮疙瘩都站起來(lái)了。
沒(méi)勇氣立刻拆開(kāi),把它折進(jìn)口袋,吃過(guò)晚飯,噔噔噔下樓回廠。
此刻,天還沒(méi)有完全黑,路燈已亮,騎在浦東南路上,樹(shù)梢上的月亮從來(lái)沒(méi)那么近。我剎住車(chē)把,單腳踩地,把信封撕開(kāi),一個(gè)叫張曉林的編輯的親筆信,字跡規(guī)整流暢,對(duì)作品表示了欣賞,告知將擇期刊出。從拿到信到撕開(kāi),已遲疑了近一小時(shí),雖猜到內(nèi)容,看到白紙黑字的確認(rèn),仍抑制不住戰(zhàn)栗。尚未讀完,潸然淚下。
幾個(gè)月后,收到了《劍南文學(xué)》樣刊,散文欄目中赫然印著:《雨夜陷阱》,署名:夏文煜。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原名發(fā)表文學(xué)作品。
說(shuō)也奇怪,此作發(fā)表不久,陸續(xù)又收到幾家報(bào)刊的用稿函,我厚顏無(wú)恥地認(rèn)為,哪有天上掉餡餅式的時(shí)來(lái)運(yùn)轉(zhuǎn),這一定是我寫(xiě)作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的結(jié)果。又過(guò)了兩年,我的自由投稿獲得了突破,小說(shuō)漸次被《花城》《鐘山》《上海文學(xué)》《作家》等刊物留用,從發(fā)表第二篇文字開(kāi)始,我取了一個(gè)叫夏商的筆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待了七年后,我終于逃離了工廠。事實(shí)上,文學(xué)并沒(méi)有成為我謀生的手段,但我知道,正是因?yàn)橛辛宋膶W(xué)的滋養(yǎng),重塑了我的格局,令我敢于面對(duì)龐雜的世事,敢于面對(duì)更紛亂的生活。
我想,處女作的發(fā)表,對(duì)每位作家來(lái)說(shuō),都是創(chuàng)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它就像1,雖是最小的數(shù)字,可沒(méi)有這個(gè)1,就不會(huì)派生出2,派生出3,派生出4……,后來(lái)我出版了小說(shuō)集,出版了長(zhǎng)篇小說(shuō),出版了自選集,出版了文集,這些成果當(dāng)然也會(huì)產(chǎn)生喜悅,可都沒(méi)有處女作發(fā)表時(shí)的那種戰(zhàn)栗感,在我此后的寫(xiě)作生涯中,也沒(méi)有因發(fā)表或出版而再次流下淚水。
2022年6月8日凌晨于紐約長(zhǎng)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