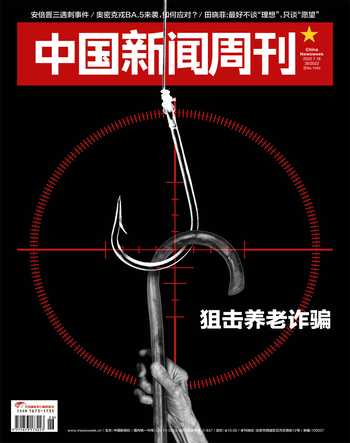田曉菲:最好不談“理想”,只談“愿望”
李靜
誰能想到陶淵明詩歌的境遇會與我們當下的生活有什么聯系呢?有的。并不因為他所述的“桃花源”,而是我們今天讀到的陶淵明,真的是一千六百年前那個超脫淡泊的隱逸詩人嗎?在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文學教授田曉菲的《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她尋找那些湮滅的證據,像一個偵探般,在歷史和文字造成的迷宮里不斷尋找、甄別、調查,她發(fā)現了差異甚多不同時代的傳世手抄本,在流傳過程中,它們不斷被改寫,被演繹,甚至變得面目全非,每個手抄本背后似乎都站著不同的陶淵明。在她看來,雖然今天的互聯網文化缺乏物質實體,“它卻和手抄本文化具有根本的相同之處。”
不久前,“田曉菲作品系列”在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收入田曉菲2000~2016年寫作的四部中古文學研究專著:《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文化》《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
在學術著作之外,她自己又何嘗不是另一個被想象、被演繹的“陶淵明”。相比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哈佛學者,在互聯網世界里,田曉菲被人們廣為傳播的故事,卻是13歲作為“天才少女”被北大破格錄取,以及她與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的婚姻。即使她不滿35歲成為哈佛大學東亞系最年輕的正教授,兩度出任哈佛東亞地域研究院主任,并獲哈佛大學卡波特獎等學術和教學獎。但是,眾多與性別、年齡有關的傲慢與偏見,并不因為她是學者就放過她,且大約因為她的經歷有傳奇色彩,標簽化、庸俗化的編造和猜想還更要加在她的身上。
1971年出生于哈爾濱的田曉菲,受父母和家庭影響,從小喜愛讀書,家中藏書是她的閱讀寶庫。據她自己說,八九歲時讀希臘神話,留下深刻印象,因為看到神的局限,英雄的悲劇,又正是在這局限與悲劇里,展現了他們的力。王力的《古代漢語》和吳楚材、吳調侯的《古文觀止》,是她的古漢語入門教材,其中最喜歡《左傳》和《國語》選段,不為別的,單只是欣賞里面的辭令:那么悠揚委婉,卻又絕不肯委屈。蔡東藩從兩漢到民國的歷史演義,也是童年時代的她很愛讀的書,雖然直到多年后,她才意識到所有的歷史都不過是演義,敘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敘述的內容更重要。
從兒童時代開始在報刊發(fā)表詩文,到17歲那年,田曉菲已出版3本詩集。有一段關于她少女時代最出名的傳說,是關于她和詩人海子的友誼,據說海子曾告訴她,如果能堅持,她將成為一位偉大的詩人。田曉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其實并不認識也從未見過海子,但她覺得這個故事反映出來的編故事人心態(tài)很有趣,“因為完全不懂寫詩是怎么回事。寫詩不是減肥,難道是某種需要‘堅持’的活動嗎?‘堅持’聽起來真是辛苦,從‘堅持’而能成為偉大的詩人,必無此理。”
坊間傳說從不講究道理,甚至沒有新意,另一些傳說有關田曉菲的婚姻與愛情。約二十年前有篇發(fā)表于某通俗雜志的文章編造出她和她先生戀愛、求婚的細節(jié),甚至編造了他們的結婚日期,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而事實上,田曉菲很在意個人隱私,“如果你看到關于我們的故事里有很多個人生活細節(jié)和對話,那一定是捏造的。”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些關于他們婚戀的編造好象是從最蹩腳的三流小說里抄來的情節(jié),“簡直太沒有想象力”。
了解一個人最好的方式,明明應該是她的書籍。這些年,田曉菲從事最多的是學術寫作,她一直對魏晉南北朝的文學與社會有強烈的興趣,近期又開始研究唐代,此外對明清文學甚至現當代文學都有論述。她的專著并不因專業(yè)而枯燥,在考據引用、嚴謹學術的闡釋范式中,她仍然保留詩人的文學化表達,對于一些文學史上的現象不乏新鮮見解,論證時的對比跨越雅俗古今。她從不是一個獨守書齋埋于故紙堆中的學者,她看金庸小說,也看周星馳的《大話西游》和《少林足球》,在研究“三國想象”的變遷史時,還專門去看三國粉絲的網絡文學作品。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中,與她的文章、著作一樣,她對當下活生生的社會文化和現實,都有自己的關懷與思考。

我沒計算過時間分配比例,也無法計算。我為研究生討論班備課,和自己的學術研究往往不可分開;為本科生備課則和自己的學術研究沒有直接的關系,是很不一樣的體驗。但無論哪種課程,我投入的時間和精力確實都非常多。這有好幾個原因:一,我喜歡教書,喜歡我的學生;越是“難教”的學生,就越是在幫助我成為一個更好的老師。二,我總是從教學過程中學習到、領悟到很多東西,“教學相長”不是虛言。三,教書是我的工作,我有一個信念,就是一個人無論是做什么職業(yè),都應該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對自己做的工作有一種驕傲感,對得起自己的薪水;所以,如果我是個鞋匠,我也一定是個兢兢業(yè)業(yè)的有很多回頭客的鞋匠,這是我的本性。四,作為中國人,我對自己的工作還有一種更大的責任感:在美國大學教中國古典文學,就好比是為中國古典文化做代言人,我們所面臨的現實,是和我們國內大學中文系的同行非常不同的;中國古典文學本身就已經屬于冷門,這意味著我們就更是必須能夠在多種意義上承擔好“翻譯”的工作。近幾年,從研究生到本科生,越來越多的學生是華人,族裔比例失調,而我最大的希望,是學生種族、語言、文化背景的多樣化,因為,請你想象一下:如果在未來的世界,只有中國人才對中國文學感興趣,那豈不是中國文化最大的悲哀嗎!這里當然有一些因素是超出我們控制的,但是作為一個中國古典文學教授,我有一種責任感。
你想中國的大學生會覺得他們看不明白荷馬史詩或者莎士比亞戲劇嗎?他們在看《堂吉訶德》時會覺得有雙重隔閡嗎?中國古典文學和所有其他語言文化的文學一樣,既有歷史文化的特殊性,也有人性的普遍性。它不是人類世界文學中不可理解不可接近的怪物,也千萬不要自己把自己定位成不可理解不可接近的怪物。
最好不談“理想”,只談“愿望”。理想是個“大詞”,愿望是個“小詞”。“理想”是固定的,僵硬的,帶有束縛性和壓迫性的,它或者還沒實現,或者已經實現,已經實現的就不再是理想,還沒實現的時候,總是迫使一個人把注意力放在“還沒有”上;但是“愿望”卻是可以不斷變化、不斷發(fā)展、不斷擴大的。不同的年齡當然有不同的愿望,而且同樣的愿望也可以不斷地修正和調整。向自己的愿望所在的那個方向永遠不斷地接近,是人生最大的樂趣所在。在寫作方面,無論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學術寫作,我目前的愿望是能夠精確地、清晰地、有力地表達自己想說的東西,因為隨著人生經驗的積累和知性的成長,隨著想法日益復雜、豐富、清晰,會強烈感到對思想的表達也需要同步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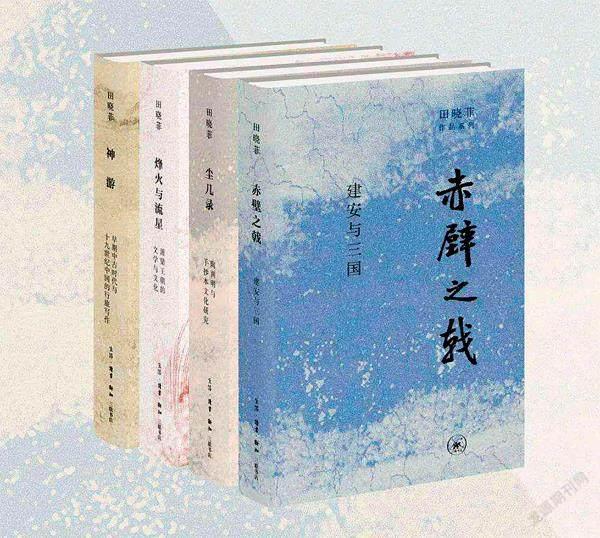
“田曉菲作品系列”。
在有詩才的人的手里,什么都是可能的,只是有詩才的人“多乎哉、不多也”而已。沒有詩才的話,用新詩的形式也照樣表達不好當代生活。不過,寫詩歸根結底是個人的事情,只要自己高興和寫起來順手,盡可以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喜歡用什么語言和形式就用什么語言和形式,沒有必要去管別人尤其是學者說什么。
我們可以看看這樣的詩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或者,“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這是詩人的詩呢,還是每個人的詩?再看看這首題為《挽歌》的詩: “月亮下的小土豆/月亮下的小土豆/走來一只狗/嗅/月亮下的小土豆。” 這是每個人的詩呢,還是詩人的詩? 前些年我在做網絡詩歌研究時,對新體詩和舊體詩的題目很感興趣,比如當時曾看到舊體詩題為《二十五省份遭遇霧霾天氣、南京中小學緊急停課》,還有關于岳母手術住院、出院回家后以詩記之的題目。這些詩,從它們的相當典型的舊體詩題目,到它們的內容,都是“每個人”的詩。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來,后一種觀點也有其道理。為什么?因為文學和文化現象就和我們的世界一樣是在不斷變動中的。對于研究當代文學與文化現象的學者來說,必須保持思想的敏銳度和觀察的即時性,看到這些不斷發(fā)生的變化。我近年有一篇專寫聶紺弩的文章(以英文發(fā)表),最后就正是談到,近年來舊體詩和新體詩似乎顛倒了位置:新體詩越寫越放開了,越寫越平常心了、家常化了,在某些人看來就是“俗”了,這都是好事;相比之下,舊體詩反而越來越作姿態(tài)了,越來越被賦予宏大意義了,也越來越因為學院人士的介入而束手束腳、端起架子和僵硬了。
沒有出版詩集,并不意味沒有寫詩啊!我還在寫詩,而且自覺比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都要寫得稍微好一點(笑)。也許哪一天有興致、有時間,會把它們結集出版,也許決定等到死后再出——這主要得看老了準備離世的時候是不是決計給兒子或者哪個從前的學生添一些頭痛麻煩。誰知道呢?人生應得有點“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的態(tài)度。
我有很多標簽,很多身份,沒有一個單一的標簽和身份能夠代表我。別人給我標簽,是別人的事,和我沒有關系,因為別人怎么看你,從來都不反映你在哪里,只反映他們自己在哪里或者“還在”哪里。
個人可以迷茫,但并不渺小和無力。對于你的愛人、孩子、父母、親人、朋友、同事甚至鄰居來說,你的存在非常重要,非常真實,怎么能說你是無力和渺小的昵?
我這里的回答只代表我自己:我認可這句話,但是我不認為聰明的反面是勤奮。事實上我并不喜歡“勤奮”這個詞,因為聽上去充滿了“吃苦”的回聲。古今中外不乏“沒有痛苦、就沒有收獲”(No pain, no gain)這樣的陳詞濫調,都很誤導人,因為咬牙吃苦才得來的“收獲”總是相當平庸、微小、可憐的。在我看來,真正的關鍵詞是“熱情”:如果對自己做的事情滿懷熱情,那么做起來就充滿樂趣,那么做這個事情的本身就已經是極大的收獲,就更不用說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收獲了。
歷史中沒有對具體問題的具體答案,因為每個具體問題都是具有現時性的,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是,有一些古老的智慧,可以為我們在當代世界遇到的具體問題提供一些抽象的參考。比如說,“變通”這個概念。宇宙萬物都在永遠不停地運動和變易,不變則不通,不通則不久。內與外的界線是人為的建構,而且也是在不斷變動的。從歷史上看,混雜與流動才是人類的常態(tài),也是進化的基礎。
謝謝你的問題。世界,國家,都是由個人構成的。個人可以迷茫,但并不渺小和無力。對于你的愛人、孩子、父母、親人、朋友、同事甚至鄰居來說,你的存在非常重要,非常真實,你的言行可以傷害或者安慰,可以使人憤怒或者感動,可以讓一顆心破碎或者狂喜,怎么能說你是無力和渺小的呢?或者,從反面來說,這世界上又有幾個人,作為“個人”,相對于“時代”,或者就相對于這個“疫情”來說吧,是巨大的、始終清晰無疑的和獨自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呢?沒有一個人。我們每個人第一最重要的工作是面對和處理好我們自己,在面對和處理自己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是最強大的,因為我們對自己的心態(tài)、情感、言語、行為,有著百分之百的決定權,而我們的心態(tài)、情感、言語和行為又可以影響我們周圍的人和環(huán)境。歸根結底,我們每一個人,都只能,也完全有能力,從我們每個人所處的位置,在我們個人的能力范圍所及之內,為世界打開一盞照明的燈。
我年輕的時候,從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經歷過巨大的痛苦、挫折、失敗,迷茫和煩惱也非常多。但這些都是好事:沒有煩惱和迷茫,就不會去主動地、自覺地、強烈地追求歡樂和清晰。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充滿反差的時代,但有了反差,才會促使我們作出比較和判斷,我們才會異常清楚和強烈地知道我們自己到底要什么、什么東西對我們來說最寶貴。否則,我們的日子會變得太舒服、太自滿、太麻木和混沌,好象喂飽的家禽一樣。所以,迷茫不是壞事,只要別讓自己沉溺下去,就會反過來變成一種力量,帶來積極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