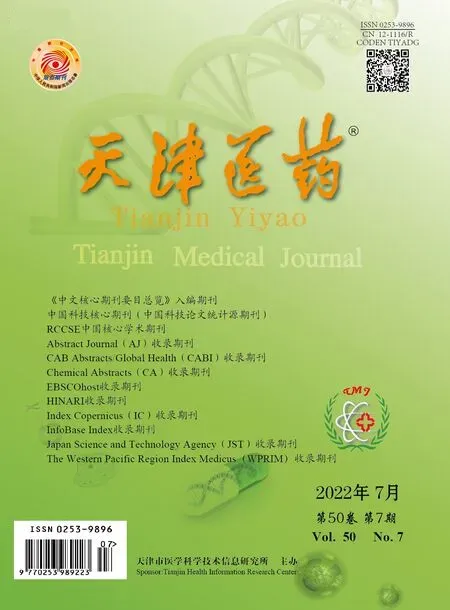乳腺癌髓系來源抑制細胞與外周血單核細胞的相關性及對預后的影響
杜偉嬌,張家麗,于文文,沈夢,曹水
大量研究已經證實,乳腺癌、肺癌等多種實體腫瘤免疫微環境存在高度異質性[1-3]。隨著抗腫瘤免疫治療的日益發展,通過腫瘤免疫評分來判斷預后及療效是研究的熱點。研究發現髓系來源抑制細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可能有一定的預后預測作用[4-5],乳腺癌腫瘤浸潤MDSCs的預后意義尚不明確。有研究報道,即使早期乳腺癌也可以通過激活γ干擾素(interferon γ,IFNγ)信號通路的方式誘導系統性免疫改變,繼而影響外周血髓系及淋巴系細胞,提示這些免疫細胞可能反映了乳腺癌患者的總體免疫狀態[6]。乳腺癌腫瘤浸潤MDSCs與外周血白細胞、中性粒細胞、單核細胞、淋巴細胞計數及單核細胞/淋巴細胞比值(monocyte-tolymphocyte ratio,MLR)、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相關性的研究尚鮮見報道。本課題組前期研究觀察到乳腺癌患者腫 瘤 組 織 中 浸 潤 的 MDSCs 表 型 為Lin-CD33+CD13+CD14-CD15-[7]。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Ⅰ~Ⅲ期乳腺癌術后患者的腫瘤浸潤MDSCs比例、血常規指標及臨床病理特征,初步探索MDSCs與患者預后的關系。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天津市腫瘤醫院2009年2月—12月接受根治性乳腺癌手術及腫瘤組織MDSCs檢測的32例乳腺癌患者的血常規指標、臨床病理資料,MDSCs 表型為Lin-CD33+CD13+CD14-CD15-,MDSCs比例指其在腫瘤單細胞懸液CD45+細胞中所占比例。具體檢測方法參照本課題組已發表的文獻[8]。納入標準:(1)組織病理學確定為原發性乳腺癌。(2)接受根治性手術治療的患者。(3)按照同期治療原則接受術后放化療及內分泌治療。排除標準:(1)近1個月內有感染癥狀。(2)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史。(3)應用激素治療。(4)失訪。本研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批件號:
Ek2019143)。
32例患者均為女性,年齡30~65歲,中位年齡52歲。未絕經17例,絕經15例。病理類型(參照世界衛生組織2003年分類標準):浸潤性導管癌非特殊型26 例,浸潤性小葉癌3例,浸潤性乳頭狀癌1例,浸潤性微小乳頭狀癌1例,小管癌1例。組織學分級:Ⅰ級1 例,Ⅱ級21 例,Ⅲ級4 例,未分級6例。根據美國腫瘤聯合會制定的第七版分期標準:ⅠA 期8例,ⅡA 期8 例,ⅡB 期4 例,ⅢA 期6 例,ⅢB 期1 例,ⅢC 期5期。T 分期:T1期9 例,T2期21 例,T3期1 例,T4期1 例。N 分期:N0期17例,N1期4例,N2期6例,N3期5例。脈管瘤栓陽性1 例、陰性31 例。雌激素受體(ER)≥1%24 例、<1%8 例;孕激素受體(PR)≥1% 27 例、<1%5 例,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HER)-2(-/+/++)28 例、HER-2(+++)4 例。Luminal A 型10例,Luminal B型15例,HER-2過表達型4例,三陰性3例。30例行乳腺癌根治術,2例行保乳手術。新輔助化療2例,術后輔助化療31 例。術后輔助放療11 例,術后輔助內分泌治療20例。主要復發轉移部位:胸壁、肝、肺、骨。
1.2 隨訪 所有患者均通過電話或門診隨訪,隨訪截止時間2019年12月31日,隨訪5.9~125.7個月,中位隨訪時間122.2個月。無復發生存期(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time,RFS)定義為從手術切除到首次復發時間。5 年或10 年無復發生存率定義:從手術時間開始5 年或10 年無復發患者例數/總患者例數×100%。
1.3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26.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服從正態分布用±s描述,不符合正態分布用中位數及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計數資料用例(%)表示。不同臨床病理特征患者MDSCs 比較應用非參數檢驗Mann-WhitneyU檢驗。通過Spearman法分析MDSCs與外周血白細胞的相關性。應用Kaplan-Meier法繪制生存曲線,采用Logrank 檢驗比較不同分組患者RFS 差異,雙側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乳腺癌腫瘤浸潤MDSCs 比例與臨床病理特點的關系 32 例乳腺癌患者腫瘤浸潤MDSCs 比例為0.4%~24.9%,中位數4.4%。不同臨床病理特征患者中,臨床分期Ⅲ期MDSCs 比例高于Ⅰ~Ⅱ期(P<0.05),而不同N 分期、絕經狀態、T 分期、病理類型、分子分型、Ki-67 狀態、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狀態患者MDSCs 比例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乳腺腫瘤浸潤MDSCs 與外周血白細胞計數等相關性分析 32 例乳腺癌患者外周血白細胞計數(5.9±1.4)×109/L,單核細胞計數(0.4±0.1)×109/L,中性粒細胞計數3.2(2.8,3.9)×109/L,淋巴細胞計數1.8(1.5,2.2)×109/L、MLR(0.2±0.1)、NLR1.6(1.4,2.0)。腫瘤浸潤MDSCs 與外周血單核細胞計數(rs=0.405)及MLR(rs=0.408)呈正相關(均P<0.05),見圖1;與白細胞計數(rs=0.233)、中性粒細胞計數(rs=0.224)、淋巴細胞計數(rs=-0.051)、單核細胞百分比(rs=0.162)、中性粒細胞百分比(rs=0.073)、淋巴細胞百分比(rs=-0.212)、NLR(rs=0.136)無相關性(均P>0.05)。根據Luminal 分型結果進行分層分析,25 例Luminal A/B型Ⅰ~Ⅲ期乳腺癌患者腫瘤浸潤MDSCs與外周血單核細胞計數(rs=0.486)、MLR(rs=0.530)呈正相關(均P<0.05),7 例HER-2 過表達型/三陰性乳腺癌中腫瘤浸潤MDSCs 與外周血單核細胞計數(rs=0.429)、MLR(rs=0.036)無相關性(均P>0.05)。根據有無淋巴結轉移進一步分層分析,17例無淋巴結轉移患者腫瘤浸潤MDSCs 與外周血單核細胞計數(rs=0.651)呈正相關(P<0.01),與MLR(rs=0.390)無相關性(P>0.05);15例有淋巴結轉移患者腫瘤浸潤MDSCs與外周血單核細胞計數(rs=0.147)、MLR(rs=0.361)均無相關性(均P>0.05)。

Tab.1 Comparison of MDSCs%in breast cancer tissues betwee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表1 不同臨床病理特征患者的乳腺癌組織浸潤MDSCs比例比較 [%,M(P25,P75)]
2.3 Ⅰ~Ⅲ期乳腺癌術后患者RFS的影響因素 截至隨訪結束,32 例患者中共11 例(34.4%)出現術后復發進展,其中Ⅰ、Ⅱ、Ⅲ期分別為0、7、4 例。32 例患者總體5 年、10 年無復發生存率分別為84%、62%。按照Ⅰ~Ⅲ期MDSCs中位數4.4%將患者分為高MDSCs 組(≥4.4%,16 例)和低MDSCs 組(<4.4%,16 例),2 組5 年無復發生存率分別為80%、88%,10年無復發生存率分別為58%、66%。生存分析結果顯示有淋巴結轉移患者RFS較無淋巴結轉移者更短(P<0.05),其余分組患者RFS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對32例患者分析發現,高、低MDSCs 平均RFS 分別為(102.7±9.1)個月、(107.9±8.3)個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2A。分層分析發現,25 例Luminal A/B 型患者中,高MDSCs 和低MDSCs 平均RFS 分別為(100.6±10.8)個月、(113.7±6.3)個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2B;17 例無淋巴結轉移患者高、低MDSCs 平均RFS 分別為(97.4±31.9)個月、(117.8±15.9)個月,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圖2C。

Tab.2 Univariate analyses on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FS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表2 不同臨床病理特征患者RFS比較
3 討論
腫瘤微環境中免疫細胞的數量及時間、空間分布均存在高度異質性[1],是探索新型免疫治療靶點及生物標志物的理論基礎。探索新型免疫評分體系是腫瘤研究的熱點及難點。肺癌、乳腺癌、尿路上皮癌等實體腫瘤中的MDSCs 顯示了一定的潛在預后預測價值[9-12],由于標本難以獲取,目前大部分相關研究針對的是外周血中的MDSCs。Yamauchi 等[13]報道外周血MDSCs 是非小細胞肺癌術后復發的預測因素。目前乳腺癌術后患者腫瘤浸潤MDSCs 對于RFS的預后意義尚少見文獻報道。

Fig.1 Correlation of MDSCs with monocyte count(A)and MLR(B)in 32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圖1 32例乳腺腫瘤浸潤MDSCs與單核細胞計數(A)、MLR(B)的相關性分析

Fig.2 RFS curves of high and low MDSCs in the whole group of patients,Luminal A/B type patients and patients without lymph node metastasis圖2 全組患者、Luminal A/B型患者和無淋巴結轉移患者高MDSCs和低MDSCs組RFS曲線
根據表型不同可將MDSCs 分為3 種亞型:單核細 胞 樣MDSCs(CD15-CD14+)、多 形 核MDSCs(CD15+CD14-)以及早期MDSCs(CD15-CD14-)[14-17]。Safarzadeh 等[4]入組20 例Ⅰ~Ⅳ期乳腺癌患者,發現外周血HLA-DR-CD33+MDSCs 及單核細胞樣MDSCs、多形 核MDSCs、早 期MDSCs 3 種 亞 型 的MDSCs 均與臨床分期及淋巴結轉移有關,提示乳腺癌外周血MDSCs 是預后的影響因素。Barrera 等[11]發現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特定細胞因子聯合外周血多形核樣MDSCs 是一項有潛力的疾病進展預測指標。本課題組前期在乳腺癌患者腫瘤組織中觀察到一群表型為Lin-CD33+CD13+CD14-CD15-的早期MDSCs[7-8],本研究發現Ⅲ期患者腫瘤浸潤MDSCs比例高于Ⅰ~Ⅱ期患者,與De Giorgi 等[6]研究結果一致,且MDSCs 與腫瘤的轉移進展相關,但并未觀察到腫瘤浸潤MDSCs 比例與病理類型、分子分型有關。
腫瘤浸潤MDSCs 的募集及誘導分化與白細胞介素(IL)-6、IL-10等多種細胞因子及細胞趨化因子受體5(cell chemokine receptor type 5,CCR5)等趨化因子在內的全身性炎癥狀態密切相關[15]。外周血單核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MLR 也是反映乳腺癌等實體腫瘤患者總體免疫狀態的重要生物標志物[18-20]。一項入組516 例轉移性乳腺癌患者的臨床研究發現外周血單核細胞計數、MLR 及循環腫瘤細胞數目均為總生存時間的獨立影響因素[6]。Sheng等[10]發現轉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的循環MDSCs 與外周血炎性指標NLR 呈負相關。本研究發現,Ⅰ~Ⅲ期患者腫瘤浸潤早期MDSCs 與外周血單核細胞及MLR呈正相關,而未觀察到與中性粒細胞等的相關性。亞型分析發現25 例Luminal A/B 型患者早期MDSCs與外周血單核細胞及MLR呈正相關,而其余7 例HER-2 過表達型或三陰性乳腺癌患者無此現象,有待增加例數進一步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淋巴結轉移的患者RFS 更短,Ⅰ~Ⅱ期與Ⅲ期患者、T1與T2~4期患者RFS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目前腫瘤浸潤MDSCs 評估預后的cut-off 值選取尚無統一標準,筆者通過中位數4.4%進行分組,生存分析結果顯示高、低MDSCs 組患者RFS 無明顯差異。根據分子分型分層后發現,在25例Luminal A/B 型患者中,高、低MDSCs 患者RFS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7 例無淋巴結轉移患者中,低MDSCs組無進展病例,而高MDSCs組3例復發進展,高MDSCs 組患者RFS 更差(P<0.05)。15 例有淋巴結轉移(N1~3)患者組,N1為4例,N2為6例,N3為5例,N 分期是乳腺癌患者預后影響因素,各個N 分期的樣本量較小,未能進一步分析淋巴結轉移患者MDSCs對RFS的預測作用。
綜上,本研究觀察到乳腺癌腫瘤浸潤MDSCs 比例與外周血單核細胞計數、MLR 呈正相關,在無淋巴結轉移乳腺癌患者中觀察到高MDSCs 患者RFS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