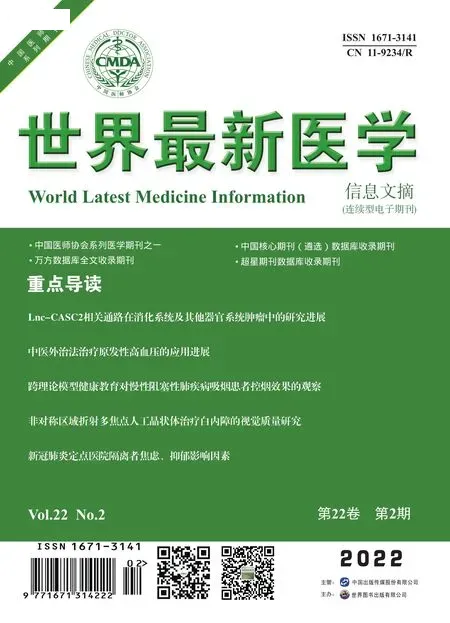新冠肺炎定點醫院隔離者焦慮、抑郁影響因素
羅燕蘭,寧俐文,曾憲鋒,張林潮*,韋金蓮,韋紅恩,段政萍,蔣維維,林彩虹
(1.廣西醫科大學附屬柳鐵中心醫院,廣西 柳州 545007;2.融水苗族自治縣人民醫院,廣西 柳州 545300)
0 引言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為“2019 冠狀病毒病”,簡稱“新冠肺炎”,是指2019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導致的肺炎。新冠肺炎在全球爆發,自2020 年1 月23 日至25 日,我國30 個省市區先后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I 級響應,我市于2020 年1月24 日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I 級響應,柳州市某院作為新冠肺炎三甲定點收治醫院,市內疑似、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均在隔離病房中進行治療。有研究發現,大多數甲型H1N1 流感患者在SCL-90 總分、總均分、強迫、抑郁、敵對、偏執和其他項目因子分與常模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1],甚至是康復出院后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礙[2]。對于其他隔離治療患者進行心理護理也有助于降低其焦慮、抑郁狀態[3]。因此,在院隔離治療的患者存在相當程度的精神、心理障礙風險,為優化突發衛生事件集中隔離點的心理干預工作,本課題組對柳州市某新冠肺炎三甲定點收治醫院的28 名進行心理狀況的評估、探索相關影響因素,并期望了解隔離這對于心理干預的傾向,為患者提供適宜的心理服務。

表1 28 名隔離者人口學變量統計(n,%)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調查時期于2020 年2 月20 日至2020 年2 月21 日,對我院隔離點28 名隔離者進行問卷調查,最終回收有效問卷28 份。被試的人口學資料情況,見表1。
1.2 方法
一般資料問卷包含一般人口學變量(年齡、性別、學歷、婚姻狀況、是佛有慢性病史、是否有精神科或心理科就診史)及被試心理干預的意愿與傾向的形式。
廣泛性焦慮量表(GAD-7)GAD-7 用于評估被試過去2 周內的焦慮情況,共7 個條目,采用4 級評分,從“完全不會”到“幾乎每天”分別計分為0~3 分,總分0~21 分,總分為0~4 為“無癥狀”;5~9 為“輕 度”;10~14 為“中 度”;15~21 為“重度”。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信度系數為0.913。
患者健康問卷自評量表(PHQ-9)PHQ-9 用于評估被試過去2 周內的抑郁情況,共有9 個條目,采用4 級評分,從“完全不會”到“幾乎每天”分別計分為0~3 分,總分0~27 分,總分為0~4 為“無癥狀”;5~9 為“輕 度”;10~14 為“中 度”;15~19 為“中重度”;20~36 為“重度”[4]。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信度系數為0.866。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5]本文采用該量表中文版本(姜乾金編制)的修訂版,量表共12 個題項,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個分量表組成,采用7 級計分,1= 極不同意,7= 極同意,以此類推。總分由各條目分累加,得分越高表示領悟社會支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總表的Cronbach’s α 信度系數為0.914,家庭支持α=0.821,朋友支持α=0.936,其他支持α=0.865。
1.3 統計學方法
運用SPSS 23.0 軟件,由于數據樣本量有限,因此本研究對數據進行描述統計、非參數檢驗、Spearman 相關分析、多元逐步回歸、多樣本Friedeman 檢驗等分析方式,進行因子之間關系的探索與預測,及隔離者對各種心理干預方式的偏好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醫務人員焦慮、抑郁檢出率
28 名隔離者,共有9 人檢出焦慮(32.14%),12人檢出抑郁(42.86%),同時存在焦慮和抑郁癥狀的有6 人(21.43%),見表2。

表2 28 名隔離者焦慮抑郁檢出率
根據癥狀嚴重程度來判斷是否接受心理咨詢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直接接受心理咨詢,較少隔離者直接拒絕心理咨詢,見表3。

表3 存在焦慮或抑郁的隔離者對心理干預的意愿調查
2.2 醫務人員焦慮、抑郁相關因素分析
2.2.1 一般人口學變量
對一般人口學變量運用非參數檢驗,了解隔離者焦慮、抑郁在不同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是否有慢性病史、是否有精神科、心理科就診史情況上的差異。表明隔離者的焦慮、抑郁水平在不同年齡、性別、婚姻狀況以及是否有精神科或心理科就診史無差異,但有無慢性病史(χ2=28.000,P=0.006<0.01)者的抑郁水平高于無慢性病史的隔離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4。
表4 焦慮、抑郁在一般人口學變量差異比較(±s,分)

表4 焦慮、抑郁在一般人口學變量差異比較(±s,分)
?
2.2.2 領悟社會支持水平與焦慮、抑郁的關系
將感悟社會支持各維度與隔離者焦慮、抑郁水平進行相關分析,見表5。
結合上述相關分析,運用隔離者的焦慮、抑郁水平作為因變量,將表5 所示存在相關關系的領悟社會支持、家庭支持、其他支持作為預測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變量納入方法為“步進”,探索上述各相關因子間的影響方向,最終余下的變量見表6。
“家庭支持”是焦慮水平的預測變量,“領悟社會支持”是抑郁水平的預測變量,回歸系數分別為-0.1498(t=-4.308,P=0.000<0.001)和-0.210(t=-4695,P=0.000<0.001),意味著高家庭支持、領悟社會支持感可預測較低水平的焦慮、抑郁水平。

表5 焦慮、抑郁、領悟社會支持與多維健康心理源Spearman 相關系數

表6 各變量與焦慮、抑郁水平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

表7 心理干預方式均分差異比較
2.3 醫務人員心理干預方式偏好分析
讓28 名隔離者,對六種心理干預形式打分,最喜歡打5 分,最不喜歡打1 分。運用多樣本Friedeman 檢驗及多重比較對各方式均分差異比較,見表7。
3 討論
有研究結果顯示,在廣州某醫院集中隔離這焦慮/ 抑郁發生率分別為11.87%、10.93%[6],張柳[7]等研究發現,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中,10 例(25.00%)患者出現焦慮,14 例(35.00%)患者出現抑郁。在本隔離點調查的28 名隔離者中,焦慮、抑郁的檢出率高達32.14%、42.86%,同時存在焦慮和抑郁癥狀的比例達到21.43%,均高于同類研究結果。
以往有研究發現心血管疾病患者焦慮、抑郁癥狀多發。許多研究發現,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中合并焦慮、抑郁、焦慮抑郁構成比例極高[8-9];另外,社會支持狀況越差、冠心病合并高血壓病、病程越長則抑郁癥狀越重[10]。結合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一致發現,有慢性病史(如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肝炎等)者的抑郁水平高于無慢性病史的隔離者,在其他人口學變量上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因此,對于存在慢性病史、心身疾病的集中隔離者,應更為注重其心理方面的評估與干預。
多項研究表面高領悟社會支持與較低的焦慮、抑郁水平有關。有研究發現,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是社區門診老年患者抑郁情緒的保護因素[11],韓桐師等[12]在對內科門診慢性病患者的研究中也發現,焦慮和抑郁與個體領悟社會支持水平顯著負相關。類似的,本研究結果也發現,集中隔離者的焦慮、抑郁水平與個體體驗到的社會支持感有關,且高家庭支持、社會支持感焦慮、抑郁的保護因素,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提高患者的領悟社會支持感、家庭支持感,有助于減少患者焦慮抑郁的情緒,對于隔離患者的心理干預,提高個體的社會支持感入手,具體可以以遠程的、宣傳冊等少接觸或零接觸的方式開展。
對于處于隔離病房中的患者而言,傳統的面對面心理服務方式不便開展,除此之外,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呈現多種心理干預方式或評估某種心理服務的效果,但對于心理干預方式喜好程度的調查比較少。筆者認為,了解服務對象的心理干預方式偏好有助于提高患者心理干預和治療的依從性、有效性。本研究根據對存在焦慮、抑郁的隔離者心理干預意愿的調查發現,絕大部分隔離者會根據癥狀嚴重程度來判斷是否接受心理干預。進一步的,筆者發現,在幾種心理干預方式中,隔離者整體對“文字對話咨詢”的接受程度最高,對“電話咨詢”“心理自助手冊”“視頻咨詢”的接受程度也比較高,對“藥物治療”接受度最低。
綜上所述,疫情期間集中隔離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容樂觀,而對于這個群體的心理健康服務應更為關注到患者本人的是否存在既往慢性病史,也應充分利用其社會資源、家庭支持,提高其社會、家庭支持水平,對于該群體的心理干預工作,應更為注重使用遠程形式,且應以能夠提供即時的溝通、反饋的形式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