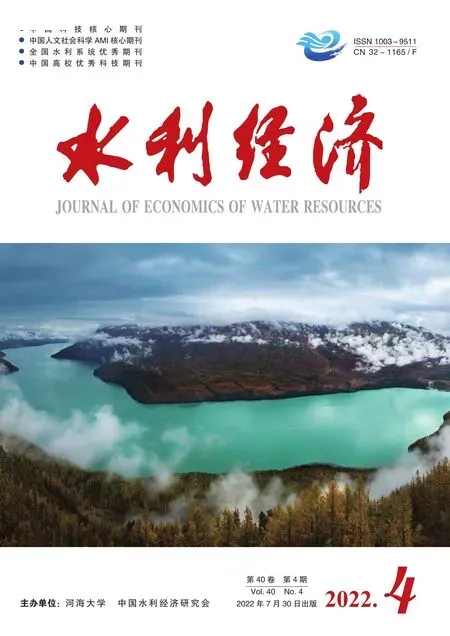江蘇省城市洪澇韌性評價及影響因素研究
嵇 娟,陳軍飛,2,3,周子月
(1.河海大學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2.長江保護與綠色發展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0098;3.江蘇長江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研究基地,江蘇 南京 210098)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歷史上最大規模、最快速度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20%增長到2021年的64.72%,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人增加到9.1億人[1]。在城鎮化進程中,城市作為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發揮著關鍵作用。與此同時,城市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經受諸多因素的沖擊和威脅,特別是極端天氣帶來的暴雨、洪澇等自然災害。我國許多城市都依河流、湖泊而建,更容易受到雨洪災害的影響。根據水利部《中國水旱災害防御公報》,2020年全國百座城市進水受淹或者發生內澇,受災人口高達7 861.5萬人,直接經濟損失2 669.8億元,占當年GDP的0.26%[2]。2021年,河南鄭州發生特大暴雨,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面對如此嚴峻的自然災害考驗,如何提高城市應對洪水災害的能力和城市自身韌性,最大程度消除雨洪災害帶來的消極影響,是城市發展需要關注和妥善應對的問題之一。因此,深入研究城市洪澇韌性評價問題,有助于提高城市洪澇韌性,促進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
1 文獻綜述
“韌性”一詞最初用來描述金屬在受到外力沖擊時保持穩定或恢復到原始狀態的能力[3]。生物家霍林[4]將韌性引入生態學領域,認為韌性是系統在危機發生時預測和解決外部沖擊的能力,同時保持其主要功能。隨著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亦有學者指出,韌性不僅可以長時間抵抗干擾,還可為城市提供機會和手段,以系統更新和新軌跡的形式應對干擾[5]。隨后,工程韌性[6]、經濟韌性[7]、生態韌性[8]的提出進一步豐富了韌性理論的內涵。韌性的概念更經常被用作指導有關城市的科學和政治討論的首要原則,并且提高韌性已成為近幾十年來有關城市的災害風險發展計劃的核心組成部分。城市洪澇韌性是指城市抵御洪澇、重建物理損壞和減少社會經濟損失、保障城市系統正常運行以及適應未來洪澇災害的能力[9]。
城市韌性的量化有助于有效引導城市建設和發展,因此,其測度和影響因素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點研究問題。國內外學者主要運用系統論和生態學相關研究方法和工具進行城市韌性評估,關注城市韌性評價、時空演化、城市規劃等,其中熵值法在城市韌性測度方面應用最廣泛。例如:孫亞南等[10]結合熵值法和泰爾指數來衡量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韌性差異,通過障礙度模型診斷其主要障礙因子并分析城市韌性的空間關聯網絡;彭翀等[11]構架了成本-能力-能效的城市韌性評估模型,測度長江經濟帶126個城市的韌性成本、韌性能力和韌性能效,然后通過GWR模型識別其主要影響因素和驅動機制;石濤[12]利用熵值法,從生態、經濟、社會、基礎設施4個層面計算黃河流域51個城市的韌性水平,并借助空間計量模型探尋其驅動要素;李雪銘等[13]基于DPSIR框架,運用熵值法和地理探測器技術綜合測度長三角地區26個城市的人居環境韌性,認為教育水平、經濟動力和能源壓力是主要影響因子。一些學者應用全生命周期法、TOPSIS法、系統動力學等來衡量城市韌性。例如:Li等[14]構建了災害全周期的洪澇韌性綜合評價體系,涵蓋洪澇前的抗災能力、洪澇后的應對和恢復能力,并提出專家權重的最大共識模型克服評價指標中的不確定信息;繆惠全等[15]基于城市災后恢復的4個階段(救援、避難、重建、復興),從政府與管理、經濟與發展、社區與人口、住房與設施和環境與文化共5個維度建立城市韌性評價體系;Moghadas等[16]應用AHP和TOPSIS的混合多標準決策方法,比較評估伊朗首都德黑蘭的雨洪韌性能力;Lu等[17]提出了一種基于粒子群優化算法-神經網絡-熵權法的混合算法用于評估城市群的災害韌性;Datola等[18-19]建立了多維的系統動力學模型來評估城市韌性,分析和模擬了與城市系統經濟、社會、環境和基礎設施方面相關的城市彈性問題。
從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成果可知,大部分學者都是從省域、區域、國家的層面評估城市韌性水平及其影響因素,并表現出有宏觀層面向微觀層面延伸的趨勢,但是仍然存在一定局限:一是未考慮不同災害對城市韌性指標體系構建的影響;二是當前的評價方法大多通過較為主觀的方式,缺乏客觀性。本文基于壓力-狀態-響應(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框架構建城市洪澇韌性評價指標體系,基于實數編碼加速遺傳算法的投影尋蹤模型(projection pursuit based on real-coded accelerated genetic algorithm, RAGA-PP)測度江蘇省13個地級市洪澇韌性水平,并應用灰色關聯度法分析其主要影響因素,以期為增強江蘇省應對洪澇災害能力、提高城市洪澇韌性提供參考。
2 模型構建與指標選取
2.1 研究方法
2.1.1基于實數編碼加速遺傳算法的投影尋蹤模型
投影尋蹤(projection pursuit, PP)是在應用數學、統計學、計算機科學和技術相結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統計模型,通過一定的組合投影方式將多維數據投影到低維子空間上,以分析高維數據的結構特點。PP模型有效避免了評價指標權重因人而異的隨機性,為高維復雜問題的綜合評價提供了明顯的優勢。
假設城市樣本集為{xij|i=1,2,…,n;j=1,2,…,m},其中xij是第i個城市第j個指標值,n和m分別為城市個數和評價指標總數。PP模型的主要建模過程如下[20]:
步驟1樣本評價指標值的標準化。為了消除城市洪澇韌性評價指標量綱不統一的影響,采用極值法對指標數據進行規范化處理。正向和反向指標歸一化公式分別為:
(1)
(2)
式中xjmax、xjmin分別為第j個樣本指標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步驟2構建城市洪澇韌性投影指標函數。PP模型核心就是找出最能體現城市洪澇韌性評價指標數據特征的最佳投影方向向量。將m維指標數據{xij|j=1,2,…,m}轉化為用向量a=(a1,a2,…,am)表示的各指標在各自投影方向上的最佳方向向量,則第i個樣本在的最佳一維線性空間的投影特征值zi可以表示為
(3)
式中:aj是單位向量a的分量。投影值zi的局部投影點之間應該盡可能保持密集狀態,可以更好地分為幾組,但是在整體上投影點應可能分散。基于此,投影指標函數可以表示為
Q(a)=SzDz
(4)
其中
rij=|zi-zj|

步驟3優化城市洪澇韌性投影指標函數。對于確定的城市洪澇韌性評價指標集,指標函數Q(a)的變化受到投影方向a的變化影響,不同的投影方向代表不同的數據結構特征,最優投影方向能夠最大限度地反映高維數據的特征。因此,求解最佳投影方向能夠解決投影函數最大化問題。指標函數最大化問題可以表示為
maxQ(a)=SzDz
(5)
(6)
步驟4確定城市洪澇韌性最優投影值。根據式(5),可得到最優投影方向向量a,代入式(3)可得各城市的投影指標值,即代表各城市的洪澇韌性水平。
在PP模型中,最優投影方向的識別即投影對象函數的最優解,是PP模型有效性和問題解決的關鍵步驟。基于實數編碼的加速遺傳算法(real-goded accelerated genetic algorithm, RAGA),模擬了適者生存和群體內染色體信息的交換機制,其能夠像加速遺傳算法一樣從局部優化中脫穎而出,以更高的概率實現全局優化,同時也克服了二進制編碼計算負載大、全局優化速度慢等缺點,增強了算法的優化能力。因此,本文構建基于RAGA-PP模型[21]的城市洪澇韌性評價模型,模型評價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RAGA-PP模型評價流程
2.1.2灰色關聯度分析
灰色關聯度分析是對一個系統發展變化態勢的定量描述和比較,用來測算因素序列與特定序列之間緊密程度的計算方法。只有厘清系統或者因素間的關聯關系,才能對系統有更為透徹的認識,分清主次因素。因此,本文運用灰色關聯度分析診斷雨洪視角下城市韌性影響因素的重要程度。若測算的韌性值與各指標的關聯度均大于0.5,表明指標對城市洪澇韌性有影響,關聯度數值越大,則指標對城市洪澇韌性的影響程度越大[22]。
2.2 基于PSR框架的城市洪澇韌性評價指標體系
2.2.1城市洪澇韌性的PSR理論框架
PSR是由經合組織(OECO)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共同推出用于研究環境問題的框架體系,從壓力、狀態和響應3個維度動態地、系統地反映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參考相關文獻[23-24],本文構建基于PSR理論的城市洪澇韌性框架如圖2所示。

圖2 城市洪澇韌性的PSR理論框架
城市洪澇韌性是壓力層的刺激性、狀態層的敏感性和響應層的適應性的綜合結果。城市雨洪系統在壓力的刺激下會發生變化,容易發生洪水災害,而城市的自然環境以及關鍵基礎設施可以緩解一些壓力。如果洪水壓力過高,根據雨洪災害傳遞的信號,城市將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進行洪水風險管理,然后對壓力子系統和狀態子系統做出反應。
2.2.2城市洪澇韌性的評價指標體系
本文以PSR理論框架為基礎,借鑒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25-27],構建城市洪澇韌性的評價指體系(表1),共包括18個具體指標。
其中,壓力層子系統是給城市雨洪系統帶來刺激的因素,壓力越大,城市韌性越弱。年降水量和高程都會影響城市雨洪系統壓力,降雨過多、地勢低洼都容易引起雨洪災害;此外,城市人口增多會使更多的人受到城市雨洪的威脅,從而加大系統壓力,因此選取年降水量、高程、人口密度3個指標作為壓力層因素。狀態層子系統反映城市雨洪系統狀態的敏感性,主要考慮自然和社會系統對雨洪的承受能力,選取了人均公園綠地面積、排水管網長度等7個指標。響應層的適應性則注重于城市系統對于雨洪來臨后能夠影響其做出反應的因素,這些因素能夠停止、恢復和預防生態系統對于人類的威脅程度。例如,每萬人醫療機構床位數越多代表人類遭受嚴重雨洪災害后得到醫療保障程度越高,城市系統對于雨洪適應性越強;居民的災害應急意識越強,面對風險時的抵御能力就越強,受到的傷害就越小。因此,選取可支配收入、防汛物資儲備調撥能力、公眾災害應急意識、第三產業占比等8個因素。指標體系中共有14個正向指標,4個負向指標。對于正向指標來說,數值越大,城市洪澇韌性越強;反之,數值越小,城市洪澇韌性越弱。

表1 城市洪澇韌性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
2.3 數據來源
江蘇省位于中國大陸東部沿海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下轄13個地級市(南京、無錫、徐州、常州、蘇州、南通、連云港、淮安、鹽城、揚州、鎮江、泰州、宿遷),是中國人口密度和綜合發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江蘇省河湖眾多,夏季雨量充沛,常年受雨洪災害影響。因此,以江蘇省為例評價城市洪澇韌性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數據來源于《2020年江蘇省統計年鑒》《2019年中國水旱災害防御公報》、氣象局網站、地理空間數據云、各地級市統計年鑒等。
3 結果與分析
3.1 城市洪澇韌性評價
3.1.1指標權重與分析
基于RAGA-PP的算法步驟,在MATLAB2018中編程建模,設定種群規模N=400,交叉概率為0.8,變異概率0.2,優化變量數目n=13,變異方向所需隨機數M=10,加速次數=7,可得到各指標的最佳投影方向向量,數值越大,表明該指標對評價體系貢獻度越高。根據投影方向向量的平方和恒為1,則可得到各指標權重及壓力、狀態和響應子系統的權重(表1)。
最佳投影方向單位向量數值越大,則對應指標在評價體系中所占權重越高,對城市洪澇韌性評價影響越大。在所選取的18個評價指標中,人口密度權重最大,表明該指標對城市洪澇韌性評價影響最為明顯。公眾災害應急意識、排水管道長度、固定資產投資、第三產業占比、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防汛物資儲備調撥能力對城市洪澇韌性影響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每萬人醫療床位、建成區綠化率、人均住房面積、高等院校畢業生數、人均公共綠地面積、高程、年降雨量、社會保障及就業占財政支出比重對城市洪澇韌性評價貢獻度相對較小。
通過匯總各項權重,得到壓力、狀態、響應3個子系統對城市洪澇韌性的影響程度,其權重分別為0.159、0.377和0.464。總體來看,狀態子系統的敏感性和響應子系統的適應性對城市洪澇韌性的影響較大,這也體現了城市系統的特點,在面對外來災害時,城市通過降低敏感性和提高適應性來抵御風險,很難減緩外界壓力的刺激。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基礎設施、生態狀態、經濟發展水平是提高城市洪澇韌性的關鍵。
3.1.2江蘇省城市洪澇韌性總體評價
式(3)計算得到江蘇省13個地級市的城市洪澇韌性的綜合投影值如表2所示。綜合投影值的大小反映了城市洪澇韌性的強弱,即綜合投影值越大,城市洪澇韌性越強,受到城市雨洪損害的程度越低。城市洪澇韌性值具體見表2。

表2 綜合投影值和Z-scores值
根據表2對綜合投影值大小進行排序,得到13個城市的洪澇韌性由大到小依次是南京、蘇州、無錫、常州、南通、鎮江、徐州、泰州、揚州、連云港、淮安、鹽城、宿遷。其中,南京市洪澇韌性最高,其值為3.252 3,主要原因是南京作為江蘇省省會,基礎設施較好,教育公平水平最高,防汛物資儲備調撥能力較強,公眾災害應急意識較強,醫療和通信服務最發達;宿遷市洪澇韌性最低,其值僅為0.668 4,主要原因在于宿遷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教育、醫療服務都相對較弱。此外,各城市的洪澇韌性值差距明顯,最高數值是最低數值的4.87倍。
為進一步分析城市空間分布特征,使用Z-scores方法[16]將江蘇省城市洪澇韌性水平分為5個等級,Z-scores值如表3所示。通過對江蘇省13個地級市進行分級統計,利用ArcGIS對城市洪澇韌性等級進行可視化處理,結果見圖3。

圖3 江蘇省城市洪澇韌性等級區劃
從城市洪澇韌性級別來看,江蘇省沒有處于低韌性等級的城市。其中,南京的城市洪澇韌性等級最高;較高韌性級別的城市有3個,分別為蘇州、無錫、常州;中等韌性等級的城市有4個,分別為南通、鎮江、徐州、泰州;較低韌性等級的城市有5個,分別為揚州、連云港、淮安、鹽城和宿遷。從地理區位上來看,江蘇省城市洪澇韌性水平具有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基本呈南高北低狀態,即蘇南地區明顯優于蘇北地區。蘇南是江蘇省較為發達的地區,配套設施相對充足,宜居環境較好,這間接說明江蘇省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等資源分布不均;蘇北地區需要獲得公平的發展和社會福祉,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提高江蘇省的整體洪澇韌性水平。
3.2 城市洪澇韌性影響因素分析
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法,可計算得指標因素與城市洪澇韌性灰色關聯度值如表3所示。

表3 指標與城市洪澇韌性的灰色關聯度
灰色關聯度數值越大,表明指標因素與城市洪澇韌性的關系越緊密,即指標對城市韌性的影響越大,反之亦然。根據表3可知,模型所選18個指標與城市洪澇韌性的關聯度均在0.6以上,由此可知所選指標對城市洪澇韌性均有較大影響,指標選擇較為合理。

圖4 指標排序
通過對灰色關聯度大小進行排序,可得影響城市洪澇韌性指標因素重要程度排序的雷達圖(圖4)。在城市洪澇韌性的評價指標中,防汛物資儲備調撥能力關聯度最高,高達0.953 8,由此說明在雨洪災害來臨時,快速的響應是城市對待洪澇風險最為重要的一步,政府以最快的速度做好應急響應,城市因洪澇造成的損失越小。公眾災害應急意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占比、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排水管網長度、高等院校畢業生數這6個指標關聯度均達到0.8以上,由此可知公眾災害意識、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與城市洪澇韌性息息相關。公眾擁有較強的災害意識,可以更好地預防和應對災害,保護自身生命財產安全甚至輔助相關部門開展工作。通過城市運行實踐可以發現,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在面對災害時能夠及時有效地啟動減災應急預案,且完善的基礎設施系統以及充分的資金、人才能夠保障城市功能的正常運行、恢復以及重建。每萬人醫療床位數、人均住房面積、人均擁有道路面積、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建成區綠化率這5個指標的值在0.7以上,剩余指標均在0.7以下。此外,從子系統角度分析,響應子系統中指標的關聯度明顯大于狀態子系統和壓力子系統,說明響應子系統對城市洪澇韌性的影響最大,政府不僅要提高應對災害的應急響應能力,提高公眾災害意識,也要不斷發展經濟,以便更好地投入城市洪澇韌性建設。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a. 南京市洪澇韌性最高,蘇州、無錫、常州處于較高韌性狀態,南通、鎮江、徐州、泰州處于中等韌性狀態,揚州、連云港、淮安、鹽城和宿遷處于較低韌性狀態;從地理區位上來看,該省城市洪澇韌性水平具有明顯的空間分異特征,基本呈南高北低狀態分布,蘇南地區明顯優于蘇北地區。
b. 韌性指標與城市洪澇韌性的灰色關聯度均達到0.6以上,指標選擇合理。其中,防汛物資儲備調撥能力、公眾災害應急意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占比、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排水管網長度、高等院校畢業生數等指標對城市洪澇韌性影響較大,且響應子系統的影響程度高于狀態子系統和壓力子系統。
4.2 建議
江蘇省作為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城市群建設的重點。面對嚴重的洪澇災害,江蘇省政府應采取必要措施平衡城市洪澇韌性的發展:
a. 重視居民災害意識的培養,使其具備必要的技能與知識,同時把重點放在社會資源的分配和提供上,權衡醫療、道路網絡等資源的分散化和市場化,使其在空間上能與城市洪澇韌性保持平衡。
b. 經濟發展是城市發展的基礎,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還是意識形態培養都離不開經濟基礎。江蘇省應致力構建具有韌性的城市經濟結構體系,不斷增強經濟建設的創新活力,建立有利于韌性城市經濟發展的有效機制,全方位多層次地提升城市的經濟韌性。
c. 加強城市基礎設施的洪澇韌性。城市基礎設施相當于人體骨骼,是城市韌性中最穩固的組成部分。將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納入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與韌性城市的發展規劃,貫徹落實“海綿城市”理念,提升基礎設施對于雨洪災害的抵御能力。
d. 重點加強蘇北城市建設,通過加大資金投入和人才引進,從而彌補蘇南地區和蘇北地區的發展差距。蘇北地區應重視改善醫療和教育,以確保資源和人口之間的適當平衡。蘇南地區則需要更多地關注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的平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