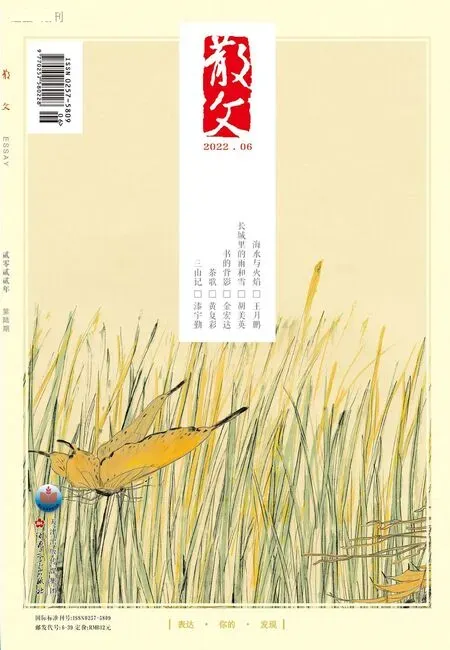大海的光芒
向以鮮
海洋進入詩歌,與大地進入詩歌一樣久遠,甚至可能更為久遠——如果我們相信所有生命的原始家園都在海洋之中——沒有大海,沒有大海的潮汐、浩瀚和無常,人類的詩歌將失去應有的深度、廣度,無與倫比的節奏,以及驚心動魄的美感。
在中國,雖然早在《詩經》和《楚辭》中就已出現了大海的意象,雖然孔子也曾有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烏托邦理想,但我認為,只有哲學家莊子才稱得上第一個歌唱海洋的詩人,他所描述的大海以及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鯤鵬形象,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先秦時代最壯麗的海洋之歌: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
這片神秘的海域,莊子有時也叫北溟,那兒潛居著長達幾千里的巨魚。和儒家相比,道家更向往大海,這不僅僅是因為大海之上有仙山瓊閣,亦因為大海的氣息更接近道家渾涵汪茫的理想。
莊子之后,寫大海的中國詩人漸漸多起來。建安十二年(207),魏武帝曹操北征烏桓回軍途中,登臨碣石寫下《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這是莊子之后寫海洋最有名的一首詩作。曹操之后,更多的詩人和作家注目海洋,西晉河北人木華還專門寫過一篇《海賦》:

完全是一派波譎云詭的世界。
差不多在曹操觀滄海的九百年之后,也就是宋哲宗紹圣四年(1097)夏秋之際,四川眉州人蘇東坡以衰病之軀被貶謫至海南儋州,在那個什么也沒有的(六無)荒島上生活了將近三年的時間。這時,蘇東坡想起了莊子《秋水篇》中的話: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
到了唐代,書寫海洋或涉及海洋的詩篇已然波瀾壯闊,并且別開生面。幾乎可以這樣說,盛唐詩歌的光芒,就是從大海之上綻放出來的。最初是大海上的月光,透明而皎潔的月光,不論是引領風氣之先的張若虛的“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還是開元名相張九齡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還有李白的“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都展現了明月與大海共生共息的奇觀。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張九齡《望月懷遠》首聯,甚至有以之為科考試題的。比如李華就寫過一首《海上生明月》的應試詩作:
皎皎秋中月,團團海上生。
影開金鏡滿,輪抱玉壺清。
漸出三山岊,將凌一漢橫。
素娥嘗藥去,烏鵲繞枝驚。
照水光偏白,浮云色最明。
此時堯砌下,蓂莢自將榮。
妙手天成的詩句是無法再演繹的,再大的才華也饒舌。晚唐人徐晦還寫過一篇《海上生明月賦》:
巨浸不極,太陰無私。褰積水之游氣,睹圓魄之殊姿。皓皓天步,蒼茫地維。泱漾崩騰,助金波玉浪之勢;晶熒激射,當三五二八之期。
時移世易,已經完全沒有海上明月的煙波浩渺之象了。
還是把目光收回到盛唐吧,那個時代才是漢語詩歌的奇跡時代。斗轉星移,月沉日升,接著,便是于沉寂之中等待光輝時刻的一躍而起,那是王灣的時刻,噴薄欲出的時刻:“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然后是杜甫的“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王之渙的落日也歸到了大海:“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再后來,隨著人們的足跡越來越寬廣越來越遙遠,大海的景象也越來越真實。晚唐詩人方干在《送僧歸日本》詩中寫道:“西方尚在星辰下,東域已過寅卯時。大海浪中分國界,扶桑樹底是天涯。”
在唐詩的大海,或大海的唐詩中,洛陽詩人王灣,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王灣為什么重要,當然是因為他的詩,準確地說,來自于他寫大海的兩句詩——是的,僅僅兩句,十個字,就夠了,十只大海舉起的手指,十束大海的光芒。
我常在想,要是王灣寫到的不是大海而是別的,他的名字就可能沒有那么明亮了。我們得感謝王灣的詩句,王灣也得感謝大海的饋贈。
唐代那樣多的明星詩人,人們能記住王灣,真的好難。康熙年間欽定的《全唐詩》規模宏大,計有九百卷,光是目錄就十二卷,共得詩四萬八千九百余首,凡兩千兩百余人,基本上囊括了有唐一代的詩歌成就。其中有幾個詩人,流傳下來的作品并不多,少的只有一兩首,便可“孤篇橫絕”,百代競傳,令無數動輒數百篇的大詩人也不得不為之側身讓路。就其傳唱之廣泛流播之敏捷,即使和唐代最卓越的詩人相比,亦不遑多讓。這樣的情形,彗星般的到來和離去,只在唐詩中可見。在后來中國一千多年的漫長詩史中,再也沒有出現過。細想起來,這實在是一件堪稱奇跡的事件,是其作品沒有能足夠多地流傳下來?還是本來就寫得不多,只是偶一為之,便云霞漫天觸手成綺?這也再一次證明了一個鐵的事實:只有時間才是世上最公正的裁判。詩歌,只與詩歌本身相關,與詩作的多少、長短、詩人的身份或權力無關。
王灣就是這樣一位幸運的詩人,我們今天只能讀到王灣的十首詩作和兩句殘詩。十首之中的八首(包括兩句殘詩),是靠其同時代的江南詩歌選家殷璠的《河岳英靈集》而保存下來的——如果沒有殷璠,我們很可能就不會知道燦爛的盛唐詩歌中,還有王灣這樣神一般的存在:
(王)灣,詞翰早著,為天下所稱最者,不過一二。游吳中作《江南意》詩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已來,少有此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為楷式。又《搗衣篇》云:“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所有眾制,咸類若斯,非張、蔡之未曾見也,覺顏、謝之彌遠乎!
由此可知,王灣未入仕(考取進士)之前,已寫下大量著名“詞翰”,世人稱道的是其中十之一二。王灣深通金句對于詩歌傳播的重要性,沒有金句的詩人不是一個好詩人。有的詩人寫了一輩子的詩,卻沒有寫出一句甚至半句口耳相傳的詩句,實在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王灣因為寫出了那十個字,別的真的可以不用再寫。
殷璠太欣賞王灣,以至于說他的詩作超過了張衡、蔡邕、顏延之和謝靈運。平心而論,那兩句“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現在看來并不算是太好的詩,也遠遠沒有張若虛“此時相望不相聞,愿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一樣的風流蘊藉。
能入殷璠之眼的,在當時一定是具有影響力的詩人,《河岳英靈集》可以視為盛唐詩歌的一個點將臺。他在詩選自敘中說,這個選本“起甲寅(開元二年),終癸巳(天寶十二載)”,共選錄當代詩人二十四家、詩二百三十四首(今存二百二十八首)。如雷貫耳的李白有十三首,王維十五首,高適十三首,岑參七首,孟浩然九首。僅僅留下十首詩作的王灣,卻在里面占了八首,分量不可謂不重。要知道,大詩人杜甫,連一首也沒有入選其中!殷璠選詩的時候,杜甫已經過了不惑之年,早已經寫出上千首作品。殷璠為什么一首杜詩也沒有選,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并不能完全用杜甫生前詩名不顯來解釋了事。事實上,杜甫其時已是長安詩壇的老面孔,早就是李白、高適和岑參的好友,喜歡和知道杜甫的人并不在少數。我覺得還是他們之間的詩歌美學訴求不同所致,杜甫詩歌所呈現出來的批判鋒芒和殷璠想要的“興象”迥然不同。
殷璠對王灣的超級熱愛之中,會不會有一絲絲家鄉情懷呢?我們知道,殷璠是丹陽(江蘇鎮江)人,王灣那首詩也正好寫于鎮江的風景名勝北固山下。
王灣是北方人,漫游到了江南,在現在鎮江的北固山下寫下聞名于世的《江南意》,殷璠的版本是這樣的:
南國多新意,東行何早天。
潮平兩岸失,風正一帆懸。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
從來觀氣象,唯向此中偏。
到了宋代計有功的《唐詩紀事》中,這首詩出現了較大的異文。首先是詩題之下有條注釋:“一作《次北固山下》”;然后是正文中出現了二十一個字的差異: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
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按照版本校勘的原則,通常應以最早的版本為準,加之殷璠又是王灣同時代的人,可信度應該更高。傅璇琮先生則從詩風上推測:《河岳英靈集》所載較為古樸,《唐詩紀事》所載則風華秀麗,是否經過后人修飾,不得而知。我個人還是更喜歡后者,明白曉暢而又氣象壯麗,富于殷璠所標榜的“興象”。其實,在北固山下是看不見大海的,王灣一生可能根本就沒有見過大海。古往今來的中國,雖然擁有幾萬里的海岸線,但是對于中國古典詩人來說,由于交通工具的限制以及崇山峻嶺的阻隔,絕大部分人沒有機會見到大海。但這并不妨礙詩人們對于大海的想象,想象,有時比親歷的真實來得更富于詩意和創造力,甚至更為真實。
王灣詩作的“興象”,與殷璠的詩歌理想和時代的召喚不謀而合。王灣中進士的時間在先天元年(712)或開元元年(713),寫作《江南意》的時間大約就在此后不久。王灣所處的時代,恰恰是盛唐詩歌一個比較特殊的時代。其時,王楊盧駱及陳子昂相繼謝世,李杜高岑才剛剛出生或還未長大成人。王灣中進士的時候,杜甫才剛剛出生,算是兩代詩人。兩人可能并沒有見過面。
王灣生得是時候,大海也來得是時候。盛唐時代真是一個詩歌的好時代,堂堂大宰相張說在他的政事堂上,在莊嚴肅穆的廳壁之上,親自手書并張掛的不是什么枯燥的官箴或人生座右銘,而是并沒有什么顯赫地位的詩人王灣的兩句詩:“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這個行為太富有幻想空間了,其間蘊蓄著一種神秘的誘惑,讓人禁不住想張開雙臂,去迎接一個光輝的時代:一輪火紅的太陽,就要從黑沉沉的大海波濤之間跳出來,那是太陽與大海交相輝映的光芒——從遼闊的海平面升起,也從大唐宰相的皇宮辦公室升起。
張說書王灣詩句于政事堂,可能不僅是出于個人的喜好,更有深沉的時代背景。明人胡應麟在《詩藪》中指出:
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中唐句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晚唐句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皆形容景物,妙絕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斬然。故知文章關氣運,非人力。
這話說得絕對了些,卻并非沒有道理。一個詩人是很難超越時代限制的。到了晚唐,詩人鄭谷在《卷末偶題三首》之一中只剩下羨慕的份兒:
一卷疏蕪一百篇,名成未敢暫忘筌。
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
至于清人王應奎《柳南隨筆》載:
顧復字復生,邑人也。習岐黃業,兼能詩。嘗有句云:“初暑余春氣,殘雷變晚晴。”余極愛之,謂可與唐人“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并傳。
實際上,兩者相去甚遠,尤其是“初暑余春氣”一句,雕琢而衰弱,完全不能與“海日生殘夜”之勃勃生機相提并論。
為什么那么多詩人要縱聲歌唱大海?只有大海這樣本質性的宏偉意象,才能喚起詩人心中沉睡的洪荒之美。大海潛存著一種古老的人民性,正如海子在詩中所詰問的那樣:
劇烈痛楚的大海會復歸平靜/當水重歸平靜而理智的大海/我的人民/你該藏身何處?(《太陽·七部書》)
看啊,唐詩的大海,正放射出無與倫比的光芒,比永恒的日輪更加奪目。
我再一次想到了莊子,化作一只大鳥的莊子俯視大地時,曾發出由衷的贊嘆: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詩人李賀從碧空向下觀察時,又看到了什么?
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
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
當詩人的意志上升到高不可即之時,如同一個身處太空的宇航員,他所看見的那顆精美的星球與其上發光的大海,正宛如一杯蔚藍瓊漿,在諸神的手中輕輕蕩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