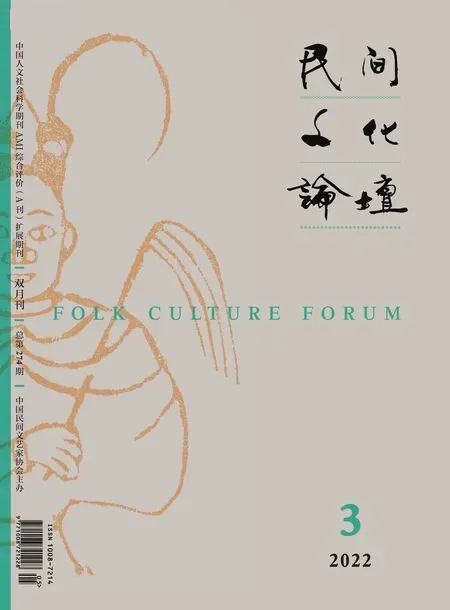張力下的繁榮:1980年代《故事會》轉變分析
—— 以1985年《故事會》為例
楊 早 王樸微
作為198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期刊之一,《故事會》長期以來在文學研究界一直沒能得到足夠的重視,文學接受層面的繁榮與文學研究領域的失語構成了極為明顯的對比。就目前學界研究狀況而言,首先在相關論文數量上差強人意,相關研究專著也僅有作家沈國凡所著《解讀〈故事會〉》①沈國凡:《解讀〈故事會〉》,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雖然提供了極為詳實、生動的史料,但仍屬報告文學作品,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其次,研究重點也多局限于兩大方向:一為對《故事會》不同歷史時期特點的概括研究,如李云所著《〈故事會〉前史(1963—1966)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②李云:《〈故事會〉前史(1963—1966)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海文化》,2009年第2期。,賈婭莉碩士論文《〈故事會〉雜志(1963—2005)研究》等③賈婭莉:《〈故事會〉雜志(1963—2005)研究》,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二為從出版編輯角度出發對《故事會》的編輯理念進行分析,如張黎敏、夏一鳴合著的《“兩創”視域下的主題出版——以〈故事會〉出版物為例》④張黎敏、夏一鳴:《“兩創”視域下的主題出版——以故事會出版物為例》,《科技與出版》,2018年第4期。,丁永勛所著《〈故事會〉品牌的成功經驗、存在問題及品牌升級之路》⑤丁永勛:《〈故事會〉品牌的成功經驗、存在問題及品牌升級之路》,《編輯之友》,2003年第1期。等。縱觀目前學界對于《故事會》的研究,盡管整體有向好態勢,但仍存在幾個顯著的問題: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對《故事會》缺乏整體性的細讀研究,多泛泛而論,少有深入的文本分析以及與雜志裝幀設計相結合的整體分析;其二,對《故事會》的歷史研究停留在對表層特點的探索,并未深掘其與時代變化的互動關系;其三,將《故事會》發展史分割為幾大階段獨立研究,缺乏將《故事會》各時期作為一個貫通整體的分析。
基于此,筆者嘗試以整體細讀為突破口,以1985年《故事會》為樣本進行對《故事會》的“再認識”。通觀《故事會》在1980年代的發展,1985年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年。這一年的《故事會》上承之前確立的基本編輯理念,下啟應對新時期新環境的變革,最能反映1980年代《故事會》的典型樣貌。本文試在整體細讀1985年《故事會》的基礎上,從其相對于《故事會》前期的“繼承深化”與“變革發展”著眼,分析其在1980年代所呈現出的復雜樣態,探究《故事會》能在這一時期各因素綜合造成的張力下取得平衡發展的原因。
一、前史:政治話語與民間話語的對話中介
創刊于1963年的《故事會》,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下“新故事運動”的直接產物。“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由毛澤東發起,這一運動的內部動因是對從中央到地方出現的較大規模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現象及呼聲的警惕,外部動因則是對部分國家興起反華浪潮的應對。在毛澤東看來,黨內外此時產生了嚴重的“右傾”,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顯得重要且必要,需要教育人民認識到階級斗爭的長期性、嚴峻性,以達到統一全社會認識的效果。
為了配合這一政治任務,1964年7月《故事會》在上海正式創刊,對外宣示的創刊宗旨正是:“叢刊《故事會》的目的是幫助故事員解決故事腳本的困難,向廣大工農群眾推廣優秀作品、擴大社會主義宣傳陣地、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①《故事會》編輯部:《稿約》,《故事會》,1963年第1輯。“配合運動進行教育宣傳”這一出發點決定了《故事會》這一刊物的基本性質與樣貌:進行教育,則需要所刊內容應緊密配合國家政治任務,針對民眾所出現的問題進行相應教化;進行宣傳,需要采用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形式,適合于廣大人民群眾的欣賞水平與欣賞習慣。要完成這一雙重要求,需要《故事會》實現政治話語與民間話語在某種程度上的“對話”。
如故事的生產方式,1960年代《故事會》的新故事多半來自于故事員“把富有思想性和戰斗性的小說、報道、戲劇、電影改編成故事,或者把當地先進人物的事跡改編成故事,用自己的口頭語言講給群眾聽”②《故事會》編輯部:《編者的話》,《故事會》,1963年第1輯。。“改編”本身可以保證故事在政治上的正確性,而改編這些素材的故事員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講演能力,但多為不脫離生產的工農兵群眾,且思想端正、政治覺悟較高,是群眾中的直接代表③參見侯姝慧:《1960年代新故事創作機制與文體的民間性研究》,《文藝爭鳴》,2013年第3期。,因此他們既對民眾擁有較高程度的了解,又能積極配合相關政策進行有效宣傳。在這一基礎上,“改編”成為了故事創作的主要方式,無論是電影小說還是現實事跡,都通過故事員這一角色加以收束并改造,這一生產模式成為兼顧政治話語與民間話語的“理想范式”。
在形式方面,《故事會》十分強調所刊故事的“口頭性”:“文字一定要口語化,必要的時候,可以用方言;難懂的方言,請加注解。”④《 故事會》編輯部:《稿約》,《故事會》,1963年第1期。在結構方面“新故事需要首尾完整,脈絡分明,層次清晰,一浪未平一浪又起的故事,以造成波瀾起伏,跌宕多姿的局勢”,“停滯靜止的細致心理描繪,大段的人物獨白,與故事無緊密關系的環境介紹,都同訴諸人們聽覺的故事藝術不協調”,⑤魏同賢:《新故事的政治意義和藝術特色》,《文史哲》,1965年第5期。換言之“易聽”“易講”成為故事創作的一個重要標準,從結構技巧到用詞用語都需要符合這一標準,以適應口頭宣講的需要與民眾的接受水平;對故事趣味性的要求也被納入故事創作要求之中,傳統評彈、評書等口傳藝術形式自然也得到頻繁的應用,以提高新故事對群眾的吸引力。
這一政治話語與民間話語之間的“對話”,在故事的題材內容方面反映也相當明顯。《故事會》基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農村問題與國際局勢的針對性,所刊故事內容多半集中于農村農民與軍隊戰爭兩個層面。農村故事多反映解放前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與壓迫,以及生產隊、人民公社成立后社員與殘留的階級敵人進行的斗爭,如《血淚斑斑的罪證》《窮棒子辦社》等;軍隊故事則多反映自中國共產黨成立革命武裝后與白匪、侵華日軍交戰的故事,如《故事會》第12輯“解放軍和民兵故事專輯”,集中講述解放軍與民兵部隊英勇戰斗,多次粉碎美帝國主義與蔣介石陰謀的故事。換言之,為“工農兵”服務的新故事運動,這一階段著重突出的是“農”“兵”兩大部分, “工人故事”則相對稀少。1965年《文學評論》曾發表一位工人所寫的文章《我們喜歡這樣的新故事》,指出“在業余的活動中,感到反映工人生活和斗爭的故事比較少”,“希望專業作者和報刊雜志多費點兒心,多寫點兒反映工人的作品,多發表點兒反映工人的作品”。①程滿麟:《我們喜歡這樣的新故事》,《文學評論》,1965年第2期。“工業”是新中國建立后以生產建設為目標的年輕元素,相比于農村與戰場,缺乏足夠的階級斗爭個案,也沒有現成的民間藝術形式可供套用,工業生產環境對于《故事會》的受眾而言也比較陌生,因此雖然“工”列名“工農兵”首位,工人故事卻相當稀缺,雖經呼吁仍然見效不大。《故事會》刊發故事題材的偏重,其實是政治話語與民間話語之間“對話”的結果。
《故事會》雖然對于政策始終保持積極配合的態度,但刊物本身內在的民間元素仍然讓它隨著“階級斗爭話語”的不斷強化,顯得跟不上形勢。1966年后,《故事會》被迫停刊。然而,1973年左右,響應黨的十大要“繼續搞好文藝革命”的號召,作為新故事組成部分的“革命故事”重新繁榮起來。為了適應這一需要,1974年3月,《故事會》在改名為《革命故事會》后正式復刊。
如果說1960年代《故事會》在新故事創作上還在尋求國家意識形態話語與民間話語某種程度上的對話,那么在1970年代的《革命故事會》中,意識形態話語則幾乎全面占據故事創作主導地位。在故事創作形式層面,對階級斗爭嚴肅性的強調使得故事的趣味性被沖淡,傳統的民間文藝形式也作為“封建毒草”被清除,②此時期新故事理論者開始將革命故事與“趣味技巧”“傳統民間故事”相割裂,將革命故事與后兩者劃分為敵對陣營:“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對此認識不足,認為講故事要‘吸引人’,就得靠所謂有‘技巧’的人來講。那么,究竟是什么樣的‘技巧’,‘吸引’什么樣的人呢?對不起,一概都不問了。這樣做,就會導致在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面前解除武裝。我們縣里有些地方,也曾經請過一些思想很不好的舊藝人來講革命故事,他們一登臺,就學什么馬叫、狗叫、賣關子、耍噱頭、亂拍驚堂木,搞低級趣味,故弄玄虛,嘩眾取寵,還往往塞進封、資、修的黑貨……事實證明,不問政治傾向,讓那些沒有經過改造、剝削階級思想根子很深的人去擔任故事員,不但不能用社會主義思想占領農村的文化陣地,而且還會有喪失這個陣地的危險。”參見上海市金山縣文化館:《開展群眾性的革命故事活動》,《革命故事會》,1974年第1期。故事講述呈現出口號化、宣講化的面目。這一時期新故事強調與彰顯的,是配合政治任務上的“靈活性”“即時性”特點,內容主要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故事”“學大寨故事”等等。與此相關,新故事的創作模式也發生了改變:以往“改編整理”的創作模式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個人、集體“直接創作”登上舞臺,配合任務的緊急性、即時性使得故事創作不再依賴于“分工式”的口述搜集或細致整理,快捷迅速的“直接創作”成為這一時期故事創作的普遍方式。
盡管《革命故事會》在理論層面仍然強調“密切聯系群眾”,但編輯現實是與民間話語隔膜與斷裂的。這種局面即使在1976年后也仍存在于新故事創作中,造成了《革命故事會》逐步走向沒落。據當時的故事員吳永昶回憶,在一次為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講故事的活動中,當他登臺剛報上故事題目后,“臺下的聽眾頓時都稀里嘩啦地站了起來,拍拍屁股跑了,將他孤零零地扔在那里”。③沈國凡:《解讀〈故事會〉》,第13頁。政策環境的改變、經濟格局與社會思潮的變化,讓《革命故事會》的“轉型”成為大勢所趨的現實要求。
二、繼承與深化:回歸民間與堅持教化
隨著改革開放,中國思想界與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轉變,階級斗爭思維被發展生產的要求替代,對極“左”思想的警惕與抵制一時成為時代主潮;知識分子也重新確立了自我身份認同,“純文學”“精英文學”開始蓬勃發展。大環境的變化,讓《革命故事會》的存在合理性受到了質疑。
在焦慮和壓力的催逼之下,1979年1月,《革命故事會》刊名更改還原為《故事會》,“革命”二字悄然隱去;同年9月,《故事會》的主辦單位上海文藝出版社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故事工作者座談會,這是一次關乎《故事會》乃至整個故事創作與研究界的關鍵會議,經過幾天緊張的討論,與會人員一致得出以下結論:
①“ 左”的思想的干擾和破壞,是新故事發展興旺的主要危險,因此,清除“左”的影響是當務之急。
② 新故事創作必須反映人民的要求,表達人民的心聲,只有這樣,才能為群眾所喜愛,所接受。
③ 新故事必須在傳統民間故事的基礎上加以發展,新故事必須保持故事應有的口頭文學的特色。
④ 要重視搜集整理現代流傳在人民群眾中的故事和傳說。①何承偉主編:《故事基本理論及其寫作技巧》,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29頁。
可以看到,在這些結論里除第一條是對“左”傾錯誤的反思之外,其余三條都是對1960年代新故事創作理念不同程度的繼承與深化。面對新時代的變化,《故事會》首先所做的是對以往辦刊經驗的總結以及對曾經所承載理念的反思與揚棄,在這一過程中,民間性、口頭性、人民性最終成為《故事會》所提煉出的三條經驗法則。
“民間”是《故事會》編輯為故事創作所尋找到的原點與生長點。1985年,《故事會》開辦了第一屆故事創作函授班并發放了相關教材,在教材中編者對“新故事”這一概念做出了以下定義:“新故事是在傳統民間故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時期的民間口頭文學。這就是說,新故事不是一種新產生的文學樣式,是傳統民間故事的繼續和發展。”②同上,第22頁。將新故事溯本歸源至傳統民間文學,重新明確了新故事的身份:新故事并非是單一地服務于政治的工具與傳聲筒,也并非如1970年代所認為的與傳統民間故事處于敵對關系,而是傳統民間故事在新時代的發展;新故事來源于民間,其目標注定追求適合最廣大群眾的口味,“精英文學”道路很難通過新故事這一載體實現。
基于這一前提,傳統民間文藝因素開始源源不斷地進入到新故事創作中,如果說1960年代《故事會》新故事對于傳統民間文藝的學習仍是有限度的,那么1980年代《故事會》新故事則體現出從形式技巧到情節內容,全面借鑒傳統民間文藝。如1985年第4期《故事會》刊登的《三請皮老虎》,故事講述了某年輕廠長再三請求一位當年被劃為右派的老工人擔任工廠顧問,卻遭遇老工人再三出難題刁難,最終年輕廠長依靠自己的才智逐一加以破解,成功請老工人出山的故事。盡管故事中的人物、背景等因素都是時代的寫照,我們卻可以從其中看出十分明顯的“三迭式”“考驗解題”等傳統民間故事內核,頗有“舊瓶裝新酒”之意。對民間的關照,不僅體現在新故事創作中,更體現在對傳統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之上。統計1985年《故事會》中的故事類別我們會發現,在這一年的278個故事(除笑話之外)中,由專人通過搜集整理所挖掘的傳統民間故事達到91個,占到全年《故事會》故事總量的近30%,這是專門刊發新故事的1960年代《故事會》與《革命故事會》所沒有的。同樣,口頭性也被《故事會》編者重新強調,并將其作為故事得以成為一個獨立性體裁的關鍵特征:
現在的新故事與傳統故事相比,在內容上和藝術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和變化。但由于新故事仍要具有易講、易記、易傳的口頭文學特點,所以,它也不應該因為在內容上和藝術形式上發生了一定變化,而成為一種新的藝術品種。①何承偉主編:《故事基本理論及其寫作技巧》,第24頁。
口頭性特征不僅體現在語言的口語化,也體現在敘述模式上的口頭性。試看以下兩例:
賴鳳仙這時捶胸頓足哭喊道:“虧得有您們幾位老哥在啊!要不,俺家好好一個黃花閨女,今晚不叫那大腳漢給禍害了?!哎嗨呀呀!俺母女倆這可怎么辦吶!還叫俺閨女見人不?!哎嗨嗨呀!娘呃!您們三位老哥可得給俺娘倆做主啊!”②聶建長:《黑店》,《故事會》,1985年第6期。
張家莊有個財主,姓張名修,苛刻起窮苦人來湯水不漏。百姓們都叫他“皮笊籬”。這年,秋雨多,莊稼一時上不了場,為了不誤農時,“皮笊籬”決定雇些短工收割莊稼。③邵世龍搜集整理:《謝謝東家》,《故事會》,1985年第6期。
交代人物簡單形象,人物語言生動鮮活,敘述情節簡潔生動,這些新故事呈現出了比以往新故事更純粹的民間文藝特征。如施愛東所言,“指向現代廣義故事概念的途徑主要有兩條:傳承主體為‘民間’;傳承本體為‘口頭散文作品’”④施愛東:《故事概念的轉變與中國故事學的建立》,《民族藝術》,2020年第1期。。對民間性與口頭性的承接與深化,是《故事會》對“故事”本質特征與獨立性的重新確定,背后蘊含的是《故事會》編者及故事理論者對新時代下“故事”之存在意義的探求。
此外,盡管對“左”傾道路進行了反思與批判,但《故事會》編者并未放棄故事的宣傳教育功能,而只是調整了其方向與性質:“由于我國的社會矛盾發生了很大變化,激烈的階級斗爭已告一段落,這樣,就使人民內部的矛盾突出了,這也促使人民群眾運用故事這種形式進行自我教育。”⑤何承偉主編:《故事基本理論及其寫作技巧》,第51頁。換言之,階級斗爭話語退位后,“自我教育”又被作為人民的一大需要,整合入故事的“人民性”特征中。在這一教育之中,有許多故事延續了之前對國家相關政策的宣傳,如1985年第2期中的故事《說不清與查得明》,故事講述了一位因“經過是非混淆年代,得出了一個結論:現在的事情說不清”而得名綽號“說不清”的老頭,與一位綽號“查得明”的年輕人之間發生的鬧劇故事,在故事結尾處,處理鬧劇的民警語重心長地教育“說不清”老頭說:“你的情況我全知道了,你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三中全會以后,恢復了我黨實事求是的光榮傳統,一切都注重調查研究,今天,‘說不清’遇到了‘查得明’,什么事都會搞清楚的”①好璧搜集整理:《說不清與查得明》,《故事會》,1985年第2期。。通過這一結尾的設計,使得整場鬧劇升華到了國家政策宣講層面,只是這其中不再有階級斗爭思維下對壞人的嚴厲打壓,而只是“人民內部”的溫和式批評教育,政治話語便在其中得到傳達。除對國家政策的宣傳外,《故事會》還一直堅持用故事向人們傳達一些基本的科學知識與道德倫理,發揮故事的認識功能與教育功能,如1985年第5期《吃石子》一則故事通過童話故事傳授了公雞吃石子的科學現象,1985年第8期《自作聰明的理發師》一則故事則諷刺了一位學藝不精而夸大宣傳的理發師,傳達“買賣應誠信”這一道德主題。可見《故事會》編者始終對于故事的“功用”與“意義”有著鮮明的追求。
為了確保故事創作實現上述效果,《故事會》編輯在這一時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與一般刊物編輯的職責不同,《故事會》編輯對于故事創作的介入程度極大,上至故事的情節、結構,下至故事的語言、長度,都經過編輯的介入創作,“編輯對來稿經常是改了又改,一篇稿子要翻轉許多遍,從而使每篇上版的故事都能讓讀者讀著好讀,讀后記住,還能講出來,并且能流傳”②秦文苑:《情趣向上 眼光向下——淺析〈故事會〉的編輯思想》,《出版科學》,2007年第2期。。這種創作模式,實際上與1960年代的集體合作、分工寫作模式極為相似,編輯以“第二創作者”的身份參與到故事的建構中來,這種模式保證了《故事會》較為統一的風格,也使得故事始終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口頭性”“民間性”“教化功能”。
三、變革與發展:追求快感與紙媒“再發現”
在1979年座談會所總結出的數條結論中,似乎看不到《故事會》編輯理念做出了多少較大程度的“變革”,一個重要原因是此時仍處于1970年代末,時代與社會的變化趨勢并沒有十分鮮明,市場因素尚未對辦刊環境造成壓迫性的影響。進入1980年代后,社會變化日益呈現出日新月異的特點,國家發展的方向也越來越明確。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突破了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對立模式,開始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③《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經濟體制改革》,1984年第5期。。種種跡象表明,“市場”這一因素開始以越來越重要的身份介入到經濟建設中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發展成為大勢所趨。
具體到期刊出版行業,市場因素的介入同樣日益明顯。1984年12月29日,國務院最終發布《關于對期刊出版實行自負盈虧的通知》,通知規定對除中央一級外其他的下級文藝刊物,一律不再提供經費補貼。④參見《國務院關于對期刊出版實行自負盈虧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5第1期。這一規定承接同年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相關政策,對地方小型刊物帶來極大沖擊,“市場銷量”立刻成為關乎這些刊物生死存亡的關鍵因素,迫使它們進行改革與調整。因此,《故事會》所面臨的一大變局,便是從昔日主要依靠政治體制進行出版、傳播,變為現在需要順應市場經濟體制進行出版、傳播,交換—消費模式的介入,使得讀者(消費者)這一角色的重要性凸顯出來,讀者的需要開始成為形塑《故事會》雜志的至關重要的因素。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開始高速增長,生產生活節奏逐步加快,彼時讀者的閱讀場景、閱讀目的等都發生了較大變化,《故事會》編輯們無疑對此有深切的體察:“這些年來,人民群眾忙于四化建設,在他們空閑下來的時候,常常通過說說笑笑,講述各類故事,以便在緊張的勞動后的休息中,得到精神上的一種享受,從而調劑一下自己的生活。”①何承偉主編:《故事基本理論及其寫作技巧》,第49頁。通觀1980年代《故事會》雜志,我們都會發現其編輯理念在順應著這一巨大變化,呈現出與前兩個時期截然不同的面貌。
首先,閱讀快感開始成為故事創作的首要元素,在函授學員教材中,《故事會》編者對于故事的娛樂功用賦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為什么要把快感作為新故事技巧系統的第一個要素?……從講演的實際情況來看,人們去聽故事,幾乎人人抱著娛樂的態度……現今聽眾對于新故事的趣味性和娛樂性的要求,可以說有增無減;不能使人們獲得快感的新故事,是進不了故事之林的,更無法流傳開來,只能是曇花一現。②同上,第136頁。
在這一宗旨下,對故事“趣味”與“快感”的要求便成為故事創作的重中之重。為了更好地達成接受快感,新故事創作開始著重強調故事書寫的傳奇性與曲折性。實際上,對傳奇性的要求原本便是傳統民間故事的重要特征之一,施愛東在考察明清以來民間故事時便指出:“故事并不指稱口頭講說的全部敘事文學,而是特指講述‘希奇事’的文學作品,所謂‘世上希奇事不奇,流傳故事果然奇,今朝說出希奇事,西方活佛笑嘻嘻’,指的就是故事的傳奇性特征。”③施愛東:《故事概念的轉變與中國故事學的建立》,《民族藝術》,2020年第1期。但相比較傳統民間故事,新故事通過對各種故事技巧的探索與運用,實現了比前者更具傳奇性、曲折性,更易吸引讀者注意的特點。
1985年《故事會》第一屆故事創作函授班教材的主要內容便是教授故事創作的實際技巧,包括如何描寫故事場面、如何加快情節節奏感、如何設置懸念、如何把握線索等等,這些復雜技巧在故事中的運用,使得新故事的傳奇程度、閱讀快感達到了超越傳統民間故事的高度。如1985年第8期《小巷怪案》一則,便是《故事會》中極具傳奇性故事的代表。故事講述了一件牽扯到三條人命的案件:有一家姓萬的四口人家,家中有大學副教授萬寶,為人脾氣倔犟,還有他的妻子玉蘭、夫妻四歲的兒子“猴猴”(因其調皮得名)以及萬寶的母親萬老太太。兒媳玉蘭對婆婆萬老太太態度十分惡劣,甚至發展到了不給婆婆吃飽飯的地步。某天玉蘭吃完早餐突然頭暈惡心,栽倒在家,民警趕來后發現已然七竅流血身亡,經鑒定是中毒而死。因為萬家婆媳不合眾人皆知,民警把懷疑對象放在了萬老太太身上,同時也根據相關線索懷疑是丈夫萬寶升為副教授后移情別愛,設計毒殺妻子。但老太太卻因為過于緊張,始終無法回答民警的詢問,直到一天,人們發現老太太在家中上吊自殺,只留下一封遺書堅稱自己不是兇手;隨著民警對萬寶調查的進行,“移情別愛”也被證實是子虛烏有。案件此時陷入僵局,民警嘗試從萬寶的兒子猴猴身上加以突破,不料想竟調查出正是猴猴殺死了自己的母親——因玉蘭常恐嚇兒子如果他長大后不孝順自己,就給他吃耗子藥,讓“上帝爺爺”教訓他,不懂生死概念的猴猴因為看見媽媽不孝敬奶奶,便直接將耗子藥摻入媽媽的牛奶中,想讓“上帝爺爺”也教訓一下媽媽,于是釀成慘禍。案件告破,得知真相的萬寶喪失理智,將猴猴扔下樓外,自己跳樓自殺,猴猴因摔在花壇僥幸得命,被民警收養,一個四口之家就這樣分崩離析。
不合的婆媳關系是貫穿這則故事的一大線索,在這一線索推動下整個情節發展呈現出一波三折的跌宕感:玉蘭之死給讀者帶來疑問,萬老太太之死又讓案件陷入僵局,民警與猴猴的對話又讓案件出現轉機;此外萬寶的“婚外情”事件也作為輔助線索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大大提升了案件的復雜性;人物的性格同樣為情節合理發展埋下伏筆,猴猴的調皮使其成為毒殺母親的兇手,萬寶的倔犟偏執也讓其最終無法接受現實跳樓身亡。整則故事情節離奇而驚悚,無論是對比傳統民間故事還是前兩個時期的《故事會》新故事,1980年代《故事會》中故事創作的傳奇性與技巧性都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帶給讀者更具刺激性的閱讀快感。
由于追求“接受快感”為旨歸,一直被《故事會》編輯所強調的“口頭性”也發生了變化,一些故事的敘事結構、情節發展的復雜性遠遠超過了以往口頭故事所能容納的范圍,因此也出現了口頭故事所沒有的描寫技巧,甚至不得不使用與“口頭性”相抵觸的書面化語言。這一點在中篇故事中體現得更為充分。以1985年第7期開始連載的中篇故事《綠茵女士》為例,故事講述的是一位名叫夏省吾的醫生在新中國成立前被國民黨官員迫害致瘋,后在新中國沉冤昭雪的故事。這則故事首先在敘述順序上打破了口頭文學慣用的順敘方式,在故事總體敘述上采用了倒敘、插敘方式,先描寫精神病院中夏省吾的瘋態,調查人員從其瘋語中得到“綠茵女士”這一線索,后加入大段插敘,通過夏省吾車夫之視角講述夏省吾新中國成立前被迫害的經過,閃回到調查人員順藤摸瓜,找到兩位“綠茵女士”,再次分別插敘對“迫害事件”不同角度的回憶,最后真相大白。相比較常見的民間故事,《綠茵女士》的故事結構呈現出少見的復雜性,無疑違反了民間故事一直強調的“易傳易記”特點。在具體敘述技巧層面,民間故事所不常見的場景描寫、氛圍渲染、心理描寫與書面化語言等因素也出現在這則故事之中:
那晚,夏省吾跟著黑漢子進了大門,沿著花圃旁邊滑溜溜的小道進了樓。這幢樓的底層高大空曠,象座陰森森的教堂;屋內陳設考究,但都蒙上了一層灰塵,霉氣撲鼻,卻不見一個人影,只聽到屋角里老鼠追逐嬉鬧發出的“吱吱吱”叫聲,和蝙蝠飛舞發出的“呼呼”聲。①孫慶章搜集整理:《綠茵女士》,《故事會》,1985年第7期。
除文本內容的變化之外,更能直觀反映出《故事會》追求快感宗旨的是雜志裝幀圖畫的變化。首先,從封面圖畫來看,1960年代《故事會》雜志封面樣式為兩套相似的“圖式”設計,兩套設計繪畫題材不脫工農兵生產生活,與每期所選故事并無具體聯系。而1970年代《故事會》雖然不同年份差別較大,但無外乎兩類設計方案:一為工農兵題材插畫的羅列,一為抽象的裝飾圖樣排列。但1980年代后,《故事會》封面卻發生了顯著變化,封面插畫開始由本期故事內容決定,并在題材上突破了“工農兵”這一固定范圍,轉而涉及古今中外各種背景。此外,在故事插畫方面,1980年代《故事會》首先在插畫數量上相比前兩時期顯著增多,以1965年、1975年、1985年三年首月雜志為例(見表一):

表 一
可以明顯看到,1985年《故事會》在總頁數少于前兩時期十余頁的情況下,插畫數量卻是1965年《故事會》的近兩倍、1975年《故事會》的近六倍,插畫密度大大提高,這無疑增加了雜志本身的觀賞性與可讀性。除數量改變外,插畫內容與傾向的改變也是這一時期的突出現象,前兩個時期《故事會》插畫創作多有兩種類型:一種為與文本內容無關的裝飾性插畫,以版畫為主;一種為與文本內容相關的插畫,但圖文關系卻是不緊密的,這些插畫多為對一般性風景的描繪以及對人物、場景的靜態表達,如1965年1月《故事會》中《兄弟民兵》一則,因故事發生在浙江沿海“鯊魚灣”,插畫師便創作了一幅海灣畫,但這幅海灣畫卻沒有任何與故事相關的成分,可謂“放之四海而皆準”,并沒有與文本內容產生強關聯性。而在1980年代《故事會》中,所有故事插畫首先與故事文本緊密結合在了一起,且尤其善于抓住故事中的沖突場景、緊張時刻,如1985 年第2期《山姑》一則故事,插畫師便抓住山姑與8位強盜纏斗的緊張場景加以描繪;再如1985年第10期《舌頭疑案》故事插畫,插畫師便著重描繪女尸橫陳在床的驚險場面,突出案件的離奇與驚險。這些無疑能夠幫助讀者在閱讀中建構對故事的想象,達到引人入勝的效果,增強雜志內容整體對于讀者的刺激性與感染力。
此外,相比前兩個時期題材單一(反映工農兵生產生活),風格單一(以白描、寫實為主)的插畫,1980年代《故事會》的插畫同樣呈現出明顯差異,在題材上隨故事一同跨越中外古今,在形式上也開始呈現出漫畫式筆法等多種藝術風格,所有這些都對提高讀者閱讀快感大有幫助。可以說,《故事會》在新時期對插畫的重視,是追求閱讀快感這一宗旨下的必然選擇,也塑造了《故事會》圖文并茂、豐富多彩的雜志面貌。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追求接受快感”這一旨歸能夠提出與達成,一個重要前提是《故事會》開始作為紙媒“實體”直接面向廣大讀者群體。如前文所述,前兩個時期《故事會》的主要擬想讀者是“故事員”這一群體,由故事員將故事腳本轉換為聽眾所能接受的故事,實現的是由“書面文字”向“聲音語言”的轉換,故事員是其中的關鍵中介。這一模式的產生既根植于當時民眾識字率低下,也受當時經濟環境下雜志發行量少與流通不暢所限。進入1980年代之后,情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據1984年國民受教育情況的統計顯示,本年普通高等學校招收本科生47.5萬人,高中在校生689.8萬人,初中在校生達3864.3萬人,相比1980年代之前有了極大的發展。①參見國家統計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于198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統計》,1985年第4期。從當時國民經濟發展水平來看,1985年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398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39元,②參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年,第303頁。而這一時期《故事會》每期售價僅為0.2元(1985年第7期后改為0.3元)。
民眾受教育水平與購買力的提高為《故事會》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而國家對于期刊出版業逐步推行的“自負盈虧”政策也對《故事會》形成倒逼之勢,迫使其轉換雜志在前兩個時期的傳播模式,原本“故事員”向一部分聽眾講演的“一本對多人”的故事傳播模式逐漸消隱,代之以每位讀者直面每本雜志的“一本對一人”閱讀。如此一來,紙媒載體直接呈現在讀者面前,成為形塑故事的重要物質因素,《故事會》上的故事不必每則都保持“易講、易傳、易記”的特點,從而允許某些故事兼容復雜的結構與書面的語言;私人閱讀方式的成立,也使得一些故事出現一定程度上的向內轉趨勢,不同于傳統民間故事的心理描寫、人物描寫開始增多。
“紙媒的再發現”對于《故事會》故事創作不僅體現在情節結構技巧方面,還體現在故事長度的標準重塑。對比1960年代《故事會》(以1963年第一輯《故事會》為例)相關情況(見表二),可以看到以下變化:

表 二
在開本不變的情況下,1985年《故事會》的頁數相比1963年《故事會》縮減了近三分之一,但故事數量卻擴大了四倍以上。這樣的調整便導致了一個明顯的雜志內容變化:故事長度大大縮短,占據一個版面的短故事、只有寥寥幾行的笑話屢見不鮮。在1960年代《故事會》每則故事的附記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故事都標注了本故事所需要的“講演時間”,一般在二十分鐘左右,講演的需要使得故事本身不可過短,教育宣傳的目的也很難以短篇故事的形式得到落實。但在追求快感的宗旨下,短篇故事便成為適合當下生活節奏、利于形成閱讀快感的形式,紙媒的形式更讓故事的縮短成為可能,數量增多,長度縮短,無疑更利于對讀者形成接連不斷的豐富刺激。
同樣,所刊故事類別在在1980年代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不同于前兩個時期專注于刊登宣揚社會主義教育與革命教育的“新故事”,1980年代《故事會》開始在刊登故事之類別上呈現出極大豐富性,以1985年全年《故事會》的278個故事(除笑話外)為例,如圖所示:

這一故事分類涵蓋了古今中外四大維度,而在每期雜志目錄的欄目分類中,則呈現出更加具體細微的分別,這一點尤為突出地表現在1985年第9期之后,傳統的“新故事”欄目在這一期徹底解體,被劃分為“新傳奇故事”“法制故事”“愛情故事”等擁有具體主題指向的欄目,這種調整既意味著新故事創作的進一步細分與深化,也有利于讀者根據不同類型故事偏好進行選擇性閱讀。可以說,紙媒這一載體的凸顯,使得更好的“接受快感”效果得以實現,反過來也促生了故事創作的豐富性、多樣性。
閱讀快感的旨歸與紙媒載體的“再發現”,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故事會》在編輯理念上發生的巨大的變化,它形塑了1980年代《故事會》與故事的樣態,是1980年代《故事會》與前兩個時期最顯著的差異。
結語:兼顧上下、雅俗并存
1980年代《故事會》既有對前兩個時期編輯理念的承接深化,又有面對時代新變做出的變革調整,故能最終在眾多純文學與通俗文學刊物中脫穎而出,成為極為獨特的“這一個”。正如許多讀者與學者覺察到的那樣,《故事會》這本雜志存在著一種復雜的矛盾性或模糊性:它既不屬于“精英知識分子”所占據的“純文學”刊物,也不等同于一昧追求低俗趣味的通俗文學刊物,所謂“雅”與“俗”的交織,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故事會》辦刊方針的一個重要特點。
在追求故事的傳奇性與閱讀快感的同時,《故事會》編者總不忘為故事注入一些道德與道理,令故事充滿現實意義,對于故事中一些純粹吸引讀者眼球的低俗要素,《故事會》編者的態度則十分警惕與慎重,如1984年新故事《彩蝶》一則,原稿中作者花費了相當多的筆墨渲染主角與新歡“鬼混”的場景,編輯在審稿時便認為這很可能沖淡中心情節、轉移讀者的注意力,于是將這一部分用寥寥數語一筆帶過。①參見沈國凡:《解讀〈故事會〉》,第75頁。同樣,對于過分強調宣傳教育的理念,《故事會》編者也予以反對:
在實施道德教育這個問題上,新故事走過不少彎路……簡單化的說教,“盡管作者的意圖是好的,但給讀者的印象卻比一位卡普勒教士的說教還要滑稽可笑(恩格斯《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完全喪失了故事的娛樂性、生動性和形象性的特點。②何承偉主編:《故事基本理論及其寫作技巧》,第137頁。
可以說,《故事會》編者最終追尋的理想目標,是在閱讀快感與道德教育之間取得一個動態的平衡。這一平衡的取得,既有前文所述對市場因素的順應,也有對彼時監管政策的體認。相比于對“純文學”的管控更多采取隱形干預的方式,有關部門對通俗文學的監管更為嚴厲。1983年10月,《人民日報》發出清除“精神污染”的號召,刊登通俗文學的報刊成為主要對象,經過審查,包括《廣州衛生》《南華》《故事報》等刊物都被勒令停刊或檢查整頓,與之相反,1980年代之后的《故事會》不僅在銷量上始終保持較高水平(1985年第2期《故事會》銷售量達到了760萬冊,創世界期刊單語種發行的最高數),在國家話語層面也一直享有較好口碑,并在1990年代被中央電視臺評為“讀者最喜愛的全國十大雜志之一”。
同樣是在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洪流中,同樣是在政策的監管壓力下,為何《故事會》能夠對二者皆有更敏感的體認、進而取得更成功的平衡?答案或許需要從《故事會》曾經所擁有的屬性與“身份”中尋找。相比于位置顯赫的各大純文學期刊和1980年代新涌現的諸多通俗文學期刊③1978年之后,國家一度將創辦期刊的審批權限下放,致使期刊種數激增,大量通俗文學期刊出現,如創辦于1980年的《啄木鳥》,創辦于1981年的《小說林》,創辦于1982年的《故事報》等等。,1963年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創刊的《故事會》無疑具有更“兼顧上下”的編輯理念與編輯隊伍的傳承。《故事會》在創刊之初便背負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賦予它的任務,從而確定了其聯結政治話語與民間話語的特性。換言之,兼顧對上層政策的呼應與對基層讀者需求的滿足,既是《故事會》在創刊之初便堅守的理念,又是經過長時間經營獲得的經驗與能力。面臨新時期的變化,這種“兼顧上下”的特性讓《故事會》做出了迅速而恰當的反應,在各種復雜因素的張力下獲得了上下之間的平衡。
在1980年代之前,依照毛澤東“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定義④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國農業科學》,1966年第8期。,《故事會》所面向的受眾(即擬想概念中的“人民”)主要為工農兵,表現題材多集中在后兩者;而1980年代,社會主流話語的調整,讓“人民”概念發生改變,指稱的是“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最廣泛聯盟”。①鞏建青、喬耀章:《歷史時空視域下的“人民”概念理論探微》,《理論與改革》,2017年第6期。換言之,“人民”這一概念階級斗爭的屬性得到弱化,建設者屬性則顯著加強。《故事會》編者無疑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并給予了其更直接淺顯的解釋:“只要能夠參加到推動社會發展的進步事業中來的人,都可劃入人民的范疇”②何承偉主編:《故事基本理論及其寫作技巧》,第66頁。。當純文學刊物沉醉于精英文學浪潮之時,《故事會》適應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起到了填補了群眾“精神食糧缺口”的作用。③1980年代《故事會》中的故事開始反映各階層人民的生產與生活,以1985年為例,經筆者統計,在12期《故事會》所刊登的106個新故事中,涉及到農民形象的故事有35個,涉及到工廠職工的故事有26個(兩組數字存在交互),除此之外民警、醫生、商販、司機、學生等形象皆紛紛出現在雜志中,這表明《故事會》在題材上已然突破了以往的范疇。同樣,當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消費者”又成為了人民身份上的另一重屬性,由此《故事會》又實現了“人民”政治含義變化與“雜志銷量”之間的聯結——這便是《故事會》能夠迅速順應市場機制,實現“紙媒再發現”,展開相應市場運作、品牌建設的理論前提之一。
與之同理,《故事會》對于道德教育的執著,既是源于對國家層面的相關倡議與監管的呼應,又是源于其對社會民眾需求的體察。20世紀80年代前的某些政治運動對社會風氣、民眾思想都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1980年開始引起重視的“青少年犯罪”問題便是其中突出代表,④參見徐建、夏吉先:《當前青少年犯罪新形態與預防研究》,《法學》,1981年第1期。此時重建社會道德倫理、重視教育成為時代民眾的普遍心聲。《故事會》編者同樣覺察到了這一點:“‘十年內亂’期間,我們黨的光榮傳統遭到破壞,社會風氣出現了倒退,生活中所產生的許多現象,與廣大人民群眾的世界觀發生了矛盾”,于是故事創作就需要“熱情歌頌人民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善意批評那種不良的思想和行為,幫助大家識別好壞善惡,分清美丑賢愚,澄清是非界線,以樹立起正確的道德觀念,繼續發揮著故事這種文學形式在人民生活中的教科書的作用”⑤何承偉主編:《故事基本理論及其寫作技巧》,第31頁。。這是《故事會》曾經背負的教育使命與責任在新時代的體現,通過故事對社會產生實際而有益的影響,始終是《故事會》編者的信念與追求。在1985年第10期《故事會》的“讀者來信”一欄里,我們可以看到有軍隊人員來信,稱《故事會》讓干部與戰士“活躍了生活、豐富了知識”,并將《故事會》稱為“軍營的‘編外指導員’”;還有一位青年鄉村教師來信,稱自己為一則新故事所啟迪,認識到“我們女青年不能只向錢看,要把人與人的感情放在第一位”,因而不顧家庭阻撓,“毅然與家境貧困的男朋友結婚了”;甚至有學生來信,稱自己“自從訂了貴刊后,我的智力有了明顯的長進,學習成績也有了顯著提高”。⑥參見《故事會》編輯部:《來信摘登》,《故事會》,1985年第10期。無論這些來信是否能夠代表絕大部分讀者的閱讀情況與感受,編者對這些來信的選登,本身便是對故事“教育效果”的強調與宣揚,體現了《故事會》辦刊的教化屬性。
1980年代《故事會》與前兩個時期《故事會》的關系并非是相割裂、相否定的關系,更多意義上是相繼承、相發展的關系。《故事會》在新時期發生的若干變化,都與其前期屬性具有承接性、順應性。用一句形象的話來總結,《故事會》能夠在1980年代各種因素的張力下取得平衡并繁榮生長,關鍵在于其有兩雙“眼睛”:一雙向上,緊盯國家話語與政策的走向;一雙向下,密切觀察讀者的情況變化。這兩雙眼睛形塑了《故事會》,呈現出一種在張力下保持平衡的復雜樣態,這是《故事會》之所以能夠成為《故事會》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