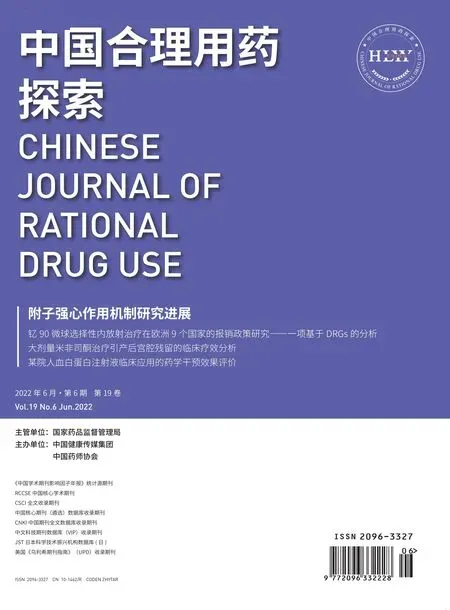413 例藥品不良反應報告的Pareto法分析
何冠蘭,李娜,梁小鳳,廖莎莎,唐秀能
廣西壯族自治區婦幼保健院,南寧 530000
藥品不良反應(adverse drug reaction,ADR)是指合格藥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現的與用藥目的無關的有害反應[1]。ADR 影響患者的用藥安全,定期監測和總結ADR 可有效減少藥源性疾病的發生,對保障疾病治療的順利進行具有重要的意義[2]。同時,ADR 監測也是新藥上市后安全監督與管理的重要手段,是促進藥事管理、促進臨床合理用藥及保障藥物安全的重要途徑。近年來,經過各方的不斷努力,ADR 上報的積極性已經逐漸提高,我國ADR 報告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3]。鑒于此,本研究采用Pareto 法對本院2017 年1 月~2020 年12 月收集上報的413 例ADR 報告進行回顧性分析,以期初步了解本院ADR 發生的特征及一般規律,為臨床合理用藥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收集本院2017 年1 月~2020 年12 月上報至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的413 份ADR 報告患者的病歷,分析患者的用藥情況。
1.2 研究方法
Pareto 法也稱為二八定律或80/20 法則,是指在眾多的現象中,80%的結果往往取決于20%的原因[4]。采用Pareto 法進行分析,將影響因素分為3種類型:①A 類:主要因素,累計構成比在0~80%。②B類:一般因素,累計構成比在81%~90%。③C類:次要因素,累計構成比在91%~100%。其中B 類和C 類在整個分析調查中構成了次要的絕大多數。
1.3 數據的收集分析
應用Excel 軟件,統計患者的性別、年齡、藥物種類、給藥途徑、ADR 的主要臨床表現等并進行Pareto 法分析。根據《藥品不良反應報告和監測管理辦法》[1]的標準,對ADR 的嚴重程度進行分級和因果關系評價,記錄ADR 累及系統/器官及其主要臨床表現,并按照WHO 藥品ADR 術語集進行分類[5]。
2 結果
2.1 ADR 患者性別和年齡分布情況
上報的413 例ADR 報告中,女性患者292 例(70.70%),男性患者121 例(29.30%),男女比例為0.41∶1。將患者按年齡分段,統計各年齡段的例數、構成比以及累計構成比。A 類因素為年齡在0~9 歲(50.12%)和30~39 歲(18.64%),0~9 歲的患者共207 例為ADR 發生的主要群體。見表1。

表1 413 例ADR 報告患者的性別、年齡分布情況(按因素分類排序)
2.2 ADR 報告的基線資料情況
上報的413 例ADR 報告中,既往無過敏史358 例(86.68%),有過敏史49 例(11.86%),過敏史不詳6 例(1.45%);ADR 上報人員類別中,醫師上報277 例(67.07%),護士上報101 例(24.46%),藥師上報35 例(8.47%)。
2.3 ADR 報告主要涉及的藥物種類
根據上報的413 例ADR 報告,采用《新編藥物學》[6](第18 版)中藥物的分類方法,對引起ADR 的藥物進行分類,并統計各種類藥物的病例數、構成比以及累計構成比。其中,引發ADR的A 類因素為抗感染藥物(55.21%)和抗腫瘤藥物(14.29%);B 類因素為生殖系統藥物(11.86%)、營養類藥物(3.87%)和維生素類及礦物質缺乏癥藥物(2.91%);其余9 類藥物為C 類因素。見表2。

表2 ADR 報告藥物種類分布情況(按因素分類排序)
2.4 ADR 抗感染藥物品種分布
抗感染藥物中共發生228 例次ADR。其中,A類因素為β內酰胺酶抑制劑(34.65%)和頭孢菌素類(25.00%);B 類因素為大環內酯類(20.61%)和青霉素類(5.70%);其余7 類為C 類因素。見表 3。

表3 ADR 報告抗感染藥物品種分布(按因素分類排序)
2.5 發生ADR 的給藥途徑
413 例ADR 報告中,共涉及7 種給藥途徑。其中,A 類因素為靜脈給藥(82.81%);C 類因素為口服、肌內注射、灌腸、皮下注射、滴耳及宮底注射6 種給藥途徑。見表4。

表4 ADR 報告給藥途徑分布情況(按因素分類排序)
2.6 引發ADR 的藥物劑型分布
413 例ADR 報告中,共涉及8 種藥物劑型。其中,A 類因素為粉針劑(62.71%);B 類因素為注射液(26.63%);其余6 種藥物劑型為C 類因素。見表5。

表5 ADR 報告藥物劑型分布(按因素分類排序)
2.7 ADR 累及器官/系統及主要臨床表現
上報的413 例ADR 報告中,按照WHO 藥品ADR 術語集分類[5],累及器官/系統的病例數共有688 個;A 類因素為皮膚及皮膚附件疾病(48.55%)、血液系統疾病(15.26%)及消化系統疾病(11.63%);B 類因素為精神與神經系統疾病(8.14%);其余累及系統/器官的臨床表現為C 類因素。見表6。

表6 ADR 報告累及器官/系統及臨床表現(按因素分類排序)
2.8 ADR 的級別和關聯性評價
413 例ADR 報告中,說明書中記載的一般ADR 有364 例(88.14%);新的一般的ADR 有19例(4.60%);嚴重的ADR 有29 例(7.02%);新的嚴重的ADR 有1 例(0.24%)。其中嚴重的ADR有50%由抗腫瘤藥引起。按照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制定的ADR 關聯性評價標準對上報的413例ADR 因果關系進行評價,結果判定為肯定1 例,很可能256 例,可能156 例。
2.9 ADR 對原患疾病的影響及轉歸情況
413 例ADR 報告中,ADR 的發生對原患疾病病程影響不明顯的有391 例(94.67%),導致患者病程延長的有17 例(4.12%),致使患者病情加重的有5 例(1.21%)。經過停藥、對癥治療后,痊愈的有47 例(11.38%),好轉的有362 例(87.65%),4 例(0.94%)不詳。
3 討論
Pareto 法是一種系統量化的分析方法,可以從許多影響因素中找到問題的關鍵,目前已廣泛應用于醫院的各項管理工作中。藥物不良反應監測與評價通過 Pareto 法分析可發現其主要影響因素,便于針對性地進行處理,利于提高工作效率[7-8],同時也為本院的合理用藥提供參考。
3.1 患兒ADR
《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年度報告》[3](2020 年)中顯示兒童ADR 發生率為7.7% 。本研究通過統計分析發現,0~9 歲的患兒ADR 報告比例最高[207例(50.12%)],與婦幼保健院的主要就診人群特點基本符合。其中,男性患兒的發生率略高于女性患兒,這與邢亞兵等[9]的研究基本一致。兒童正處于生長發育的階段,其各組織、器官系統發育不成熟,機體對藥物的敏感性高、耐受性低以及對藥物的代謝、排泄等因素有關,不僅與成人有很大區別,不同年齡段的兒童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10]。另外,由于藥物研發過程中缺乏來自這一年齡組的研究數據,目前來說臨床治療中兒童用藥的劑量很多都是根據其年齡、體表面積或者體重,由成人推薦劑量換算而來的,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相關臨床數據仍較少。且因兒童存在廣泛的超說明書用藥和未獲許可用藥的使用,尤其容易受到ADR 的影響[11]。因此,在臨床工作中,醫務人員在用藥前應詳細詢問患者的用藥史及過敏史,了解藥物的注意事項,預估可能發生的風險并盡量避免;同時用藥期間密切觀察ADR 的發生。
3.2 ADR 的藥物分布特點
發生ADR 的14 類藥物中,引發ADR 的A類因素分別為抗感染藥物、抗腫瘤藥物和生殖系統藥物。抗感染藥物所致ADR 的發生率最高,為55.21%。抗感染藥物包含11 類,其中構成A 類因素的為β內酰胺酶抑制劑和頭孢菌素類,均屬于β內酰胺類。β內酰胺類藥物引起不良反應的原因較多,主要是因為β內酰胺類抗菌藥物及其降解產物、中間產物、聚合物含有抗原決定簇,在體內形成抗原從而誘發變態或超敏反應[12],以及藥物影響腸道菌群平衡,易產生ADR。應在用藥時密切觀察,相關醫療機構應對抗菌藥物的使用加強管理,積極做好相關的預防救治措施,保障臨床用藥安全。
抗腫瘤藥物所致ADR 的發生率為14.29%,《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報告》[3](2020 年)顯示腫瘤用藥ADR/ADE 報告數量呈上升趨勢,且其引起嚴重ADR報告的比率位居首位。抗腫瘤藥物特異性低,在攻擊腫瘤細胞的同時,對人體正常的細胞、組織、器官等也有攻擊作用[13]。且腫瘤疾病復雜,化療周期長,常需要使用多種藥物聯合化療,同時腫瘤患者自身免疫功能也較差,發生 ADR 的風險較高。絕大多數抗腫瘤藥物都會引起不同程度的血液系統毒性,主要表現為中性粒細胞和血小板減少、貧血等骨髓抑制反應。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可根據腫瘤類型和化療方案的不同,以及患者自身條件的差異,進行分層管理,以實現個體化預防與治療化療相關骨髓抑制的目的[14]。在抗腫瘤藥物的用藥過程中,應注意個體化給藥,也應關注抗腫瘤藥物的預處理、溶媒配置、保存條件、給藥方式、給藥速度、給藥時間及滲液外漏處理等各個環節,注意用藥前ADR的預防,用藥期間及用藥后的 ADR 監測,并積極做好相關的預防救治措施。
生殖系統藥物所致ADR 的發生率為11.86%(49 例),其中構成A 類因素的是米索前列醇(17例)和卡前列素氨丁三醇(15 例)。米索前列醇為前列腺素E 類似物,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是合成的前列腺素F2α的15-甲基類似物,二者均為前列腺素類似物,可誘導平滑肌收縮并引起前列腺素樣并發癥,包括惡心、嘔吐、腹瀉、頭痛、發熱以及皮疹等。其所致ADR 一般程度較輕,絕大多數患者可耐受,且在停藥并做對癥處理后都能好轉。本研究中,上報的17 例米索前列醇ADR 中有1 例為過敏性休克,經對癥處理患者好轉。過敏性休克為前列腺素類似物最嚴重的過敏反應[15-16],且米索前列醇和卡前列素氨丁三醇在婦產科使用頻率均較高,在妊娠生理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用藥前需仔細詢問患者病史,避免嚴重ADR 的出現,一旦患者出現過敏性休克,必須及時救治,確保患者的用藥安全。
3.3 ADR 的主要臨床表現
本研究上報的ADR 報告所累及的系統/器官中,構成主要因素的有皮膚及皮膚附件疾病、血液系統疾病及消化系統疾病。其中,皮膚及皮膚附件疾病以皮疹、瘙癢、皮膚紅腫為主;血液系統疾病以白細胞、中性粒細胞或者血小板減少等骨髓抑制表現為主;消化系統疾病以惡心、嘔吐、腹痛、腹瀉為主,這與王丹等[17]的研究基本一致。抗感染藥物和抗腫瘤藥物在各類ADR 和嚴重ADR 中占比最高,其導致的嚴重ADR 表現有剝脫性皮炎、肝損害、休克、骨髓抑制等。臨床使用這些藥物時應嚴格把握用藥指征,對有基礎疾病者、孕產婦、兒童及老年患者等高危人群應加強用藥監護[18]。
3.4 ADR 與給藥途徑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給藥途徑ADR 的發生率差異較大,其中靜脈給藥是引發ADR 的主要原因,其構成比遠遠高于其他給藥途徑,這與黃銀妹等[19]的研究結果相符。主要原因是由于靜脈給藥后藥物直接進入血液,未經肝臟首過消除,血藥濃度瞬間升高,療效發揮迅速;靜脈給藥的pH、微粒、內毒素、濃度及配伍等均是引起ADR 的重要因素[20]。建議臨床科室在用藥時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輸液”的原則,盡量減少靜脈給藥,規范用藥細節,盡量降低 ADR的發生風險。
3.5 ADR 與轉歸
在構成方面,413 例ADR 報告中新的和嚴重的ADR 占比不高,分別為20 例(4.84%)和30例(7.26%)。目前,ADR 的上報原則提倡可疑即報,上報新的和嚴重的ADR 更有意義。在轉歸方面,除有4 例轉歸結果不詳外,其余預后均較好。這與醫務人員對 ADR“早發現、早處理、早報告”有相關性。同時,對于發生ADR 未好轉后出院或轉院的患者,需要做好回訪追蹤工作,盡量完善ADR 的上報信息,將 ADR 可能帶來的影響降至最低。
綜上所述,通過Pareto 法系統地分析本院ADR 發生的A 類因素、B 類因素和C 類因素,發現兒童患者、抗感染藥物及抗腫瘤藥物、粉針劑及靜脈給藥等因素為引發ADR 的A 類因素。提示本院可針對主要因素進行重點突破,有效干預,加強監控,促進臨床合理用藥,保障患者用藥安全。同時,藥師在日常工作中也應該加強干預,積極開展ADR的相關知識培訓,醫生、護士和藥師共同協作,加強ADR報告和信息反饋,提供和完善藥品安全數據,以期減少 ADR 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