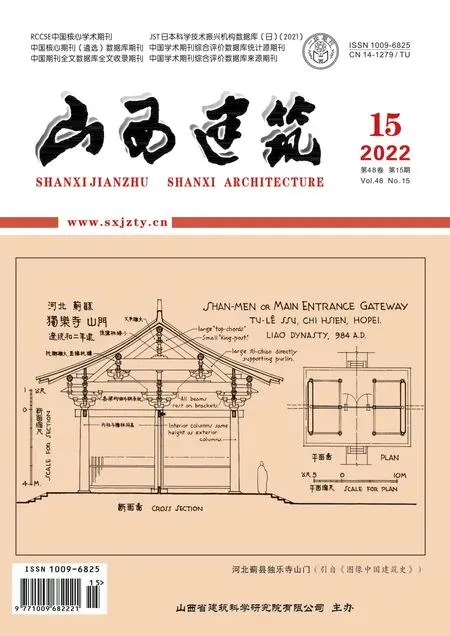利益博弈視角下的漢長安城遺址閑置用地研究
左文妍,陳穩亮
(長安大學建筑學院,陜西 西安 710000)
1 概述
作為西安市乃至中國的漢代文化大遺址代表,漢長安城遺址歷史悠久、文化價值高、涉及社會問題復雜,研究成果豐碩。劉科偉最早于1999年提出保護管理體制的不健全和居民的抵觸情緒阻礙遺址保護與利用[1]。陳穩亮等關注遺址區居民行為對遺址的影響,分析遺址區聚落的時空演變關系,并對漢長安城遺址保護規劃中涉及的協同問題進行分析[2-3]。余潔分析遺址區土地流轉制度,從土地角度考慮民生問題[4]。目前研究集中在鄉村發展、民生問題領域,缺乏對閑置問題的研究。
城鎮化快速發展帶來的土地資源緊缺問題,城市進入存量化發展階段,低效、閑置用地盤活利用勢在必行。劉霖認為閑置空間的合理利用可以消除社會隱患、重現歷史,彰顯空間的社會功能,是將閑置空間轉換為空間資源的有效途徑[5]。劉文輝對漢長安城遺址閑置土地進行識別、特征歸納及分類,提出活化策略及再利用途徑[6]。閑置用地利用是漢長安城遺址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為解決遺址保護與聚落發展長期存在的矛盾提供重要方向。
在大遺址保護過程中,隨著文物保護法律的完善和民眾自我意識的發展,公權與私權的沖突引發廣泛關注。張舜璽認為《文物保護法》在價值取向上過于側重公共利益,而忽視了對個人利益的保護,從而出現了一系列不利于文物保護的狀況[7]。李和平認為城市遺產的財產價值與遺產價值共生,是私權受到公權力強制疊加的表現[8]。張京祥認為在城市規劃建設中公權應合法干預私權,維護公共利益。現有研究主要涉及分析遺址保護中公權私權沖突的影響及應對措施等,較少從利益博弈的視角分析成因[9]。
總體而言,目前針對閑置用地的研究集中在土地識別認定、盤活利用方面,較少涉及對產生機制的探討,并未意識到政策、歷史等因素是導致漢長安城閑置用地難以利用的重要原因。在研究對象上,目前缺乏對大遺址閑置用地利用的研究;在研究視角上,目前文獻采用了土地流轉視角、脆弱性視角以及景觀感知視角等對大遺址保護進行分析,缺乏基于公權與私權博弈視角對大遺址聚落空間發展進行研究。
2 漢長安城遺址概況
2.1 地理區位
漢長安城遺址位于陜西省西安市西北側,北至西安繞城高速,南接大興西路、北二環路,西達西三環,東臨朱宏路,交通條件優越。遺址內主要道路含豐產路、石化大道、豐景路、鄧六路、羅高路等,現狀多為城中村、景區等,地理區位資源明顯領先于當前區域發展。
2.2 空間層次與聯系
2.2.1 漢長安城與西安市
漢長安城遺址位于西安市九宮格局中的漢城遺址保護區,在城市整體空間格局中的文化、生態地位突出。事實上,漢長安城城中村群整體搬遷難度大、用地效率低下,與秦阿房宮遺址城中村群形成西郊城中村帶,阻礙西安城市空間格局向西北發展,與周邊空間產生割裂。
2.2.2 漢長安城與閑置用地
閑置用地隨漢長安城遺址區內聚落空間的演變而產生,即聚落對遺址區空間的生產轉譯斷層時,土地利用陷入停滯[10]。閑置用地作為漢長安城遺址區的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影響聚落空間完整,阻礙漢長安城發展。
總之,漢長安城作為西安市典型的漢文化大遺址,應積極打開閑置空間死角,形成西安市生態緩沖區,充分挖掘其生態和文化價值。
3 漢長安城遺址閑置用地定義、特征及成因
3.1 閑置用地定義
根據《閑置土地處置辦法》,閑置土地是指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人超過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有償使用合同或者劃撥決定書約定、規定的動工開發日期滿一年未動工開發的國有建設用地[11]。由于漢長安城遺址區土地的開發使用受保護政策限制明顯,上述定義難以界定內部的閑置用地。結合現狀將漢長安城遺址閑置用地定義為:因耕地轉租、撂荒、人為破壞或政府征用等非農業技術原因棄耕的農業用地;持續開發使用時間不超過一年、無法產生穩定經濟價值的建設用地;缺乏治理、服務功能低下的生態用地。
3.2 閑置用地特征
3.2.1 空間特征
漢長安城遺址區閑置用地空間分布廣泛且分散,多在聚落外緣、少量點綴于聚落內部或獨立于聚落單獨存在。外部特征不盡相同,但可識別性強,具體表現為:垃圾傾覆、雜草叢生、房屋無人居住或破敗、宅基地空置、廢品堆放等(見圖1~圖3)。


3.2.2 時間特征
隨土地供求關系的變化,漢長安城遺址區閑置用地具有周期性和暫時性。周期性是指用地高峰期內土地被充分利用,其余時間大都處于閑置狀態。暫時性是指土地上進行非建設性開發活動,例如設置停車場、非固定游樂設施、地攤、駕校練車場和拖掛式集裝箱建筑等,隨經濟效益下降可能被閑置。
3.3 閑置用地成因
3.3.1 農業閑置用地
棄耕行為導致農業閑置用地產生。棄耕是農戶在生存、發展過程中,應對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對土地利用采取的一種反應或決策,有主動棄耕和被動棄耕兩種表現[12]。主動棄耕具體表現為:農戶通過轉包、出租等方式將耕地流轉給用地企業(如物流公司)的土地利用決策;因種地收益低下,撂荒土地,選擇收益較高的外出打零工形式。被動棄耕具體表現為:受西安市城市擴張影響,建筑垃圾偷倒、亂倒現象層出不窮,耕地被垃圾填埋,條件不達標,導致農戶棄耕。
3.3.2 建設閑置用地
土地使用權流轉失敗是建設閑置用地產生的主要原因。漢長安城土地歸村集體所有,農戶擁有使用權。受政策限制,土地經營權無法合法轉移給用地企業,或用地企業因經營不善、政策收緊等因素放棄土地經營權。且基礎耕地在產權流轉過程中受到污染,無法回歸農業用途,雙向受阻,導致建設停滯。
3.3.3 生態閑置用地
土地規劃欠佳導致生態閑置用地產生。在《漢長安城遺址保護總體規劃(2009—2025年)》中規劃大面積綠化用地以實現遺址保護、遺址景觀協調功能,但綠化用地往往缺乏設計、可達性差、無妥善維護管理,長此以往雜草叢生、景觀生態價值低下。
4 漢長安城遺址閑置用地產生機制
漢長安城遺址區社會經濟發展的約束政策和條件多,在遺址保護與發展的博弈中,區域中的經濟個體(農戶、用地企業、地方政府)在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間存在矛盾[13]。在利益相關者博弈過程中,土地產權界定不清,集體并沒有完整的土地產權[14],各方利益無法協調,產生以閑置用地為代表的“灰色地帶”,又可作利益博弈的“緩沖區”。診斷漢長安城遺址閑置用地產生機制的重要前提是分析利益相關者訴求及博弈所產生的影響[15]。
4.1 利益相關者
漢長安城中利益相關者為地方政府、用地企業、村集體、農戶,還包括游客、外來租戶等,選取主要利益相關者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利益相關者分析
4.2 利益博弈
4.2.1 公權
公權,是以政府為代表所使用的權力,是用于執行平均分配的權力。漢長安城遺址區公權分散,缺乏統一部門行使權力。各部門間存在對內、對外兩種博弈行為,權限、利益關系錯綜復雜,不利于高效決策。
1)內部博弈。
漢長安城土地資源受文物、國土等多個部門管理,同一土地實體受到不同平級政府部門的處置。資源處置權(即處置、安排某種資源的利用形式和開發方式)的“非排他性”導致政府部門在實際利用這些資源的過程中相互競爭,出現問題又相互推諉[16]。例如在漢長安城宣平里景區的建設初期,未央區農村工作局、未央區文物局、西安市國土局未央分局均同意了該項目審核方案,但西安市國土資源局認定其非法占用農地。用地企業未取得正式批準的用地手續,無視行政處罰決定仍建設并開放營業,對耕地造成嚴重損壞,公權內部博弈的危害可見一斑。
2)與私權博弈。
起初地方政府為獲得快速可視化的經濟利益,支持村內企業開發建設。隨著遺址保護相關法規政策的完善,地方政府依照傳統的遺址保護理念收緊政策,逐步清除遺址區內建設項目,導致原先開發投入中斷、遷出,大面積土地陷入閑置狀態。在2020年9月未央區人民政府最新頒布的《漢長安城遺址區違法建設清查整治工作實施方案》中,要求,“消滅存量、嚴控增量”,實現違建“清零”。
4.2.2 私權
私權是公民、企業以及社會組織甚至國家擁有的財產權和人身權。漢長安城遺址區私權主體主要為村集體、農戶,存在對內、對外兩種博弈行為,在博弈中處于劣勢地位。
1)內部博弈。
由于思想觀念、家庭情況等存在個體差異,村集體中農戶對遺產保護態度不盡相同,對土地是否應流轉進行博弈。部分農戶在“自身遵守文物保護規定,他人不遵守出租土地,自身利益可能受損”的想法驅使下同意土地流轉,與其他農戶由原有競爭關系轉變為合作關系,不利于文物保護觀念深入人心,土地非法流轉形式嚴峻。
2)與公權博弈。
私權與公權發生沖突,公權的強勢迫使私權讓步。集體所有土地處于漢長安城遺址保護范圍內,集體所有補償、居民搬遷等問題隨之產生。由于缺乏明確補償措施,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的個人利益無法真正得到保護[17],導致農戶利益受損或無法達到預期,對遺址保護抵觸、厭惡,不利于維持公權權威性。
5 結論及治理措施
5.1 監督公權
公權的行使應受到制約。由于專業知識及上訪渠道有限,普通公眾無法有效監督政府的行為,公權至上導致私權失語。應盡快建立漢長安城遺址保護特區監督制度,積極發揮非政府組織作用,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保證公權合法行使。
5.2 補償私權
私權對公權讓步應得到補償。地方政府應基于《物權法》對補償項目的規定及實際情況(如地方財政情況、土地質量及保護難度等)明確集體所有土地補償標準。同時,法律應該明確政府在土地使用中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及個人權利被侵犯的救濟制度[18],切實保障私權。
5.3 明確邊界
維護公共利益是公權干預私權的合法界限,公共利益是公權的核心。要充分發揮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優勢,針對公權力的具體行使問題(例如征收土地用于建設村莊文化博物館等)召開村民會議,少數服從多數,聽取群眾意見。
總之,漢長安城遺址保護的核心是解決利益博弈問題,政府應統籌協調利益相關者訴求,完善法律保障體系,實現閑置用地活化利用。同時,應認識到漢長安城閑置用地問題的解決是各方利益主體建立合作、和諧的關系,而非某一方利益受損、向其他權力讓步妥協。最后,我們應以漢長安城閑置用地問題為切入點,探討漢長安城遺址整體與城市的利益博弈關系,充分發揮城鄉規劃學科平衡公權、私權的杠桿作用,為城鄉遺產保護規劃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