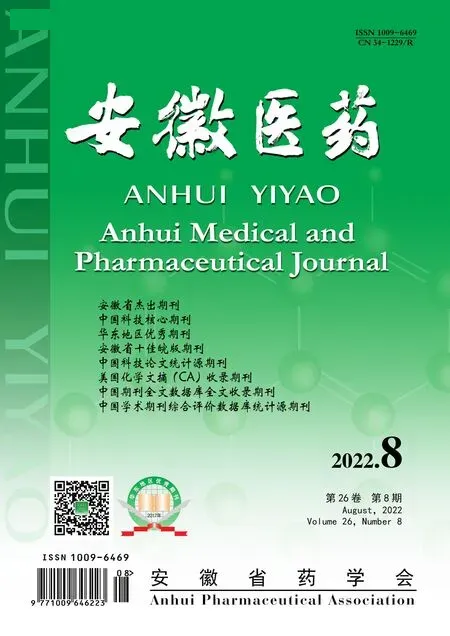急性腦梗死阿替普酶溶栓后早期神經功能惡化預測模型的構建與驗證
李彬
作者單位:安徽理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淮南市第一人民醫院)神經內科,安徽 淮南 232000
腦梗死是指腦供血血管突然中斷引起相應部位腦組織缺血、缺氧、軟化甚至壞死,可損傷腦神經功能[1-3],重組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劑(rtPA)阿替普酶是治療發病在4.5 h 以內腦梗死病人的首選方法[4-6],使中斷的血管再通從而恢復腦部血供[7],但是仍會有部分腦梗死病人接受阿替普酶治療后病情加重,發生早期神經功能惡化(early neurological deterioration,END)[8],這給病人及其家庭帶來不利影響,也給醫護人員帶來了困擾。本研究回顧性分析經阿替普酶治療的急性腦梗死病人,采用logistic 回歸分析,篩選出引起END 的危險因素,通過危險因素構建聯合預測因子,并把聯合預測因子應用到臨床,驗證其預測的效能,為臨床早發現、早干預、早治療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7 年1 月至2020 年5 月淮南市第一人民醫院采用阿替普酶溶栓治療急性腦梗死208例病人的臨床資料(建模組)。納入標準、排除標準參考《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2018》[9]。所有病人在入院時、溶栓后2 h、24 h、病情變化時、出院前進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評分。所有病人或近親屬均對治療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參與NIHSS 評分的醫生均經過統一培訓,合格后方可進行評估。本研究符合《世界醫學協會赫爾辛基宣言》相關要求。
1.2 分組標準 END 是指腦梗死發病后72 h 內神經功能缺損癥狀進行性加重[10-11]。根據阿替普酶治療后72 h 內是否發生END 把病人分為惡化組和未惡化組。惡化組54 例,男36 例,女18 例,年齡范圍為40~83 歲,年齡(66.3±10.5)歲;未惡化組154 例,男98 例,女56 例,年齡范圍為20~87 歲,年齡(65.6±12.8)歲。
1.3 溶栓治療方法 阿替普酶(勃林格殷格翰制藥有限公司,批號S20110051)靜脈注射0.9 mg/kg,總劑量不超過90 mg,總劑量的10%在1 min 內靜脈注射完成,剩余劑量在1 h內持續靜脈滴注。
1.4 人口學和基線資料采集 采集所有病人的年齡、性別、血糖、收縮壓、舒張壓、體質量指數(BMI)、吸煙、飲酒、心房纖顫、冠心病、NIHSS 評分、實驗室檢查[包括血小板計數、白細胞計數、血紅蛋白、中性粒細胞百分比、脂蛋白(a)、國際標準化比值(INR)、肌酐、尿素氮、總膽固醇,責任大血管狹窄程度(正常、狹窄、閉塞)、責任大血管分布位置(頸內動脈、大腦中動脈、基底動脈)、心源性腦栓塞。TOAST 分型可分為動脈粥樣硬化性、心源性、腔隙性或小動脈閉塞性、其他罕見原因和不明原因[12]。
1.5 聯合預測因子的構建 在單因素的基礎上利用logistic 回歸分析篩選出急性腦梗死病人阿替普酶治療后發生END 的獨立危險因素,把獨立危險因素的回歸系數重新賦值,構建聯合預測因子,并計算截斷點。
1.6 臨床評估預測效能 收集2020 年6 月至2020年8 月淮南市第一人民醫院50 例急性腦梗死阿替普酶治療的病人(驗證組),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同前,驗證聯合預測因子預測的效能。
1.7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 中文版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數據采用±s 表示,比較采用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第25,75 百分位數)[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非參數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或百分比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 確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 回歸分析,檢驗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等;對聯合預測因子進行Hosmer-Lemeshow 擬合優度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入院NIHSS評分及惡化組發生END 時間比較 建模組兩組入院NIHSS 評分>7 分和≤7 分的比例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7.48,P<0.05),見表1。惡化組病人發生END 在24 h 以內36 例(17.3%,36/208),24~48 h 內13 例(6.3%,13/208),48~72 h內5例(2.4%,5/208)。
2.2 兩組基線資料單因素分析 惡化組血糖、收縮壓、BMI、白細胞計數、脂蛋白(a)、肌酐水平、責任大血管閉塞占比、入院NIHSS 評分、心源性腦梗死占比等指標均高于未惡化組(P<0.05)。見表2。
2.3 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及繪制ROC 曲線 把是否發生END作為因變量,單因素中P<0.05的因素做為自變量,納入logistic 回歸中進行多因素分析,責任大血管閉塞賦值為1,TOAST 分型兩兩組分別進行比較,心源性腦栓塞與其他原因分別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所以把心源性腦栓塞賦值為1,分析發現高血糖、高BMI、高白細胞計數、高脂蛋白(a)、高肌酐、責任大血管閉塞、入院時NIHSS 評分高是影響病人溶栓后發生END 的獨立危險因素,對上述各獨立危險因素繪制ROC曲線,計算AUC,見表3,4。

表3 logistic回歸分析急性腦梗死發生END的危險因素
2.4 聯合預測因子的構建與驗證 根據各獨立危險因素的回歸系數構建聯合預測因子,聯合預測因子L=1×血糖+0.327×BMI+0.742×白細胞計數+0.026×脂蛋白(a)+0.143×肌酐-2.104×責任大血管閉塞+0.225×入院時NIHSS 評分,截斷點為38.984 6。對上述模型行Hosmer-Lemeshow 擬合優度檢驗,χ2=11.60,DF=8,P=0.170。將聯合預測因子及截斷點應用于臨床,驗證聯合預測因子的準確率。2020 年6月至2020 年8 月我院經阿替普酶溶栓治療急性腦梗死驗證組病人時均按照本研究的聯合預測因子的公式進行計算,根據聯合預測因子的結果與截斷點進行比較,L≥38.984 6 預測為會發生END,L<38.984 6 預測為不會發生END,以阿替普酶溶栓治療后72 h 內是否發生END 為金標準,如果預測為會發生END,72 h 內也發生END,記為真陽性,否則記為假陽性,如果預測為不會發生END,72 h內也未發生END,記為真陰性,否則記為假陰性。共收集50例病人資料,其中發生END12例,未發生END38例。預測真陽性9例,真陰性31例,假陽性7例,假陰性3例,預測正確率為78.0%,靈敏度75.0%,特異度81.6%,約登指數0.566,陽性預測值56.3%,陰性預測值91.2%,陽性似然比4.076,陰性似然比0.306。利用ROC 曲線AUC 評估預測效能,結果AUC=0.92,說明聯合預測因子臨床預測效果很好,見圖1。

圖1 聯合預測因子預測阿替普酶溶栓治療急性腦梗死發生END的ROC曲線
3 討論
急性腦梗死是最常見的卒中[13-14],根據發病機制不同可以分為腦血栓形成、腦栓塞和腔隙性腦梗死等類型。病人發病1 個月后死亡率約2.3%~3.2%[15],3 個月后死亡率約9.0%~9.6%[16],1 年后死亡率約11.4%~15.4%[17]。阿替普酶是世界上公認的治療急性腦梗死的一線藥物,但是仍會有10.0%~30.0%病人溶栓治療后發生END[17],病情進一步加重,對病人近遠期預后產生不良影響,也給臨床醫生的治療方案提出了挑戰。本研究中208例病人中有54 例發生了END,發生率為26.0%,與文獻報道[18]基本相符。Hacke等[19]研究發現24 h內END的發生率約為8.1%~28.1%,本研究中24 h 內END 的發生率為17.3%(36/208),24~48 h 內END 的發生率為6.3%(13/208),48~72 h 內END 的發生率為2.4%(5/208),說明24 h 內END 的發生率最高,與Seners等[20]研究結果一致。
本研究中通過對臨床各項資料的分析對比后發現病人的血糖、收縮壓、BMI、白細胞計數、脂蛋白(a)、肌酐水平、責任大血管閉塞占比、入院NIHSS評分、心源性腦梗死占比與腦梗死病人溶栓后END 的發生有相關性。通過多因素分析進一步發現高血糖、高BMI、高白細胞計數、高脂蛋白(a)、高肌酐、責任大血管閉塞、入院時NIHSS 評分高是發生END 的獨立危險因素。

表4 急性腦梗死不同預測變量下的AUC面積
血糖水平升高會加重無氧糖酵解的過程,導致腦組織發生細胞內酸中毒,從而使低灌注的腦組織發生新的梗死,高血糖還會破壞血腦屏障、產生凝血素效應,加重腦梗死部位缺血程度,加重腦水腫和腦組織損害[21]。此外,血糖水平長期處于升高狀態,多伴有血管不同程度的損傷,血管的波動調節能力和耐受性較差,不利于梗死部位建立有效的側支循環。Miedema 等[22]對1 012 例急性腦梗死病人進行分組研究發現高血糖對162例腔隙性腦梗死病人并無預后不良提示,而國內鮮有相關的報告,本研究中也未對腦梗死類型進行細分,所以未進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中惡化組血糖平均水平為(7.5±1.4)mmol/L,明顯高于未惡化組(5.9±1.0)mmol/L,提示為溶栓后發生END 的獨立危險因素,這與以往學者研究結果一致[17]。
脂肪組織可分泌炎癥因子,后者可促進白細胞附壁,直接損害血管,導致動脈粥樣硬化,Debette等[23]對1 352 名中年人進行研究,發現肥胖可加快他們10 年后大腦血管損傷。本研究中惡化組的BMI 平均值為(23.5±3.1),高于未惡化組的(22.1±2.9)。本研究中發現惡化組病人白細胞計數明顯高于未惡化組,多因素分析顯示白細胞計數是影響溶栓病人END 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崔穎[24]也發現白細胞計數在END 的發生、發展過程中有重要的角色。白細胞可釋放多種炎性物質,增加血管的通透性,促進血管收縮,白細胞聚集過多會阻礙腦組織局部循環的通暢性,即使血管溶栓后再通,也會阻礙腦血流量的恢復,使梗死范圍擴大,導致END 的發生[25]。白細胞的聚集和黏附也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梗死部位側支循環的建立。
脂蛋白(a)可影響體內纖溶酶原,幫助低密度脂蛋白分子黏附在動脈壁上,促進血塊、斑塊的形成,導致動脈粥樣硬化和狹窄[26]。Fan 等[27]通過轉基因兔研究發現脂蛋白(a)可促進動脈硬化。Carey等[28]研究也發現脂蛋白(a)可通過促進動脈粥樣硬化和血栓的形成導致腦梗死的發生。本研究中發現惡化組病人的脂蛋白(a)(297.5±83.8)mg/L 明顯高于未惡化組的(176.1±97.2)mg/L,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與文獻報道結果一致[29]。
王曉勤等[30]發現體內肌酐濃度升高增加了發生腦梗死的危險性,與腦梗死發病成正相關。本研究中惡化組病人的肌酐(79.4±10.1)μmol/L 高于未惡化組的(70.6±11.1)μmol/L,是引起病人溶栓發生END 的獨立危險因素,可能是血栓的形成導致腦組織損傷,從而釋放出更多的血肌酐伴隨尿液排出。
責任大血管是指頸內動脈Willis 環以及腦表面長徑超過0.1 mm 的血管[31],大血管內形成動脈粥樣硬化可導致血管閉塞,28%~46%的急性腦卒中病人可出現大血管閉塞[32],大血管血栓體積較大,溶栓難度明顯增大,遠端血管灌注不足,血流減少可導致腦組織大面積缺血缺氧,這些因素不利于溶栓后血管再通,導致END 的發生。本研究中惡化組中責任大血管閉塞的發生率為72.2%,明顯高于為未惡化組的36.4%,也是溶栓后發生END 的獨立危險因素。
NIHSS評分用于評估腦卒中病人神經功能缺損的程度[5,24,29],評分越高病情越嚴重。張幼林等[33]研究發現預后不良病人NIHSS>7 分的比例高達84.6%,本研究中惡化組中NIHSS>7 分的比例為79.6%(43/54),惡化組中NIHSS>7 分的比例明顯高于未惡化組(P<0.05),惡化組入院時NIHSS 評分為12.0(8.0~16.0),高于未惡化組的8.0(5.0~11.0);以上兩種比較方法的結果均說明了入院NIHSS 評分更高的病人發生END的可能性更大。
經阿替普酶溶栓治療急性腦梗死病人發生END 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發生機制較為復雜,臨床工作中也會用某些因素來預測溶栓后發生END 的風險,但是任何單一的因素預測是否發生END 的效果有限,準確性和可靠性較低,存在不夠完善的缺點,需要找到更為科學、有效的方法來提高預測能力,本研究在多因素logistic 回歸的基礎上利用回歸系數構建了聯合預測因子來預測END 的發生,臨床病史采集時可以根據上述各單一因素進行收集,不會存在采集遺漏的問題,把各單一的因素轉為數字化,納入公式計算,有效提高了預測的全面性和準確性,經過50例臨床病人的驗證發現預測正確率為78.0%,敏感性75.0%,特異性81.6%,利用ROC 曲線AUC 評估預測效能,結果AUC=0.921,對聯合預測因子行Hosmer-Lemeshow 擬合優度檢驗,P>0.05,說明該模型擬合優度及預測效果很好,在預測腦梗死發生END方面有顯著的意義。
綜上所述,入院時NIHSS 評分越高溶栓后發生END 的風險越大,且24 h 以內是高發期。影響阿替普酶溶栓治療急性腦梗死病人發生END 的危險因素較多,聯合預測因子有較好的評估效能,可為臨床早發現、早干預、早治療提供幫助,值得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