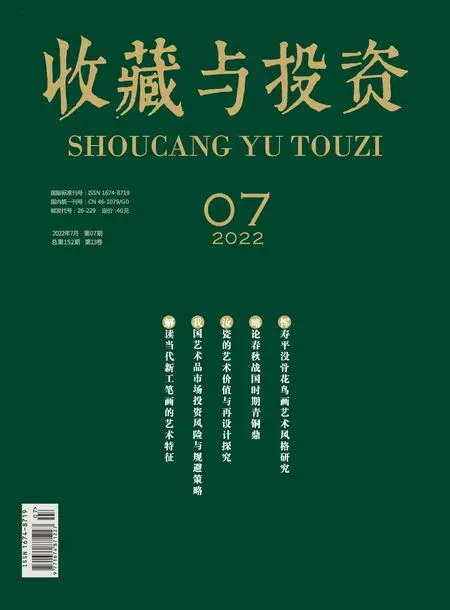論喬托·迪邦多內畫面中的“藝術性”
蘇 暢( 福建師范大學,福建 福州 350108)
喬托出生于1266年,一個拜占庭藝術與哥特藝術盛行的時代。喬托成為美術史的轉折,開啟了下一個時代。拜占庭風格的圣像主要作為宗教禮拜的對象,體現了一種神圣性,所以要求畫家嚴格遵循一些規范,不停地重復一些固定樣式,而不需要有任何藝術的獨創性。在喬托之前的中世紀,是沒有藝術和藝術家概念的,作品的作者只是沒有感情的工匠,重復著記憶中的范式。喬托認為宗教中的人物形象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應該在畫中表現圣人人性的一面,將畫家自己個人的感受融入畫面。在藝術手法上,喬托主張由古代藝術家所創造的但在中世紀被大多數藝術家所拋棄的自然主義創作方法,這為后來文藝復興藝術的現實主義奠定了基礎。他被譽為西方藝術史上第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和西方繪畫藝術之父。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理論家瓦薩里在《著名畫家、雕塑家、建筑家傳》中評價喬托道:“成為一位師法自然的優秀畫家,他完全拋棄了粗陋的希臘風格,使得按實際生活描繪人物的現代風格得以復活,已經有兩百多年沒有人做這樣的事了。”
一、喬托畫面中的形體歸納
面對繁雜無序的現實世界,藝術家需要對自然進行主觀的歸納與總結,使畫面來源于自然又符合繪畫法度的審美。這既是對畫家專業素養的要求,也是檢驗一幅作品是否經得起推敲的關鍵。

圖1 喬托·迪邦多內《猶大之吻》濕壁畫 帕多瓦斯克羅威尼禮拜堂 185 cm×200 cm,1305年
在喬托的作品《猶大之吻》(圖1)中,雖然畫面中的人物眾多,但不會讓人感覺擁擠和雜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喬托對人物進行了梳理和歸納。位于視覺中心的耶穌和猶大通過金色的袍子在畫面中形成了一個堅固的幾何形,并以此為中心區分了左右兩組的人物,而兩組人物也分別形成兩個矩形。遠景的人群也被歸納為兩個概念的團塊,官兵手中的火把和武器看似無序,其實也已被歸納為兩個扇形,兩個扇形的中心分別指向耶穌和右側粉色衣服的人物,而粉衣人物的手又指向了耶穌,不僅暗示了畫面的主次,還引導著觀眾的視覺中心。整個畫面被人物頭頂和腳底的兩條平行線分割歸納成了三部分:遠景的天空、中景的人物和近景的土地,橫向的形體和縱向的人物相輔相成,火把和武器消解了畫面的平行感,使畫面平衡且生動。
《猶大之吻》描繪的是一個充滿背叛和斗爭的激烈場面,讓混亂的場景表現得有序且整體才能成為一幅成熟且完整的藝術品。喬托在極簡的畫面區分中表現了故事最具戲劇性的一幕:在騷動與混亂、充滿動勢、群情激憤的時刻,只有畫面中心的耶穌和猶大處于靜止的狀態,以動襯靜,使觀眾的目光聚焦于畫中的主要人物。無論表現什么樣的主題,也不管畫面中場面有多么喧鬧,喬托都有一種驚人的協調、組織并使畫面重心突出的能力。
二、喬托畫面中的構圖經營
“經營位置”是中國古人在對畫面事物布局方面提出的方法,是對每一個形體的大小甚至每一條線位置的分析、考究、推敲等嚴謹的思維活動。從喬托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對畫面構圖的思考。因為喬托開始運用自然景物代替傳統拜占庭繪畫中單一的顏色作為背景,將繪畫引導到現實生活中。與之前的繪畫相比,他的繪畫不僅擴展了作品表達故事情節的可能性,同時也多了可以增加畫面構成的自然因素。
以作品《給小鳥布道》(圖2)為例,測量圣方濟各頭部光環圓心的位置發現,無論是畫面的高還是畫面的寬,此點都正好處在黃金分割比的位置上,筆者相信這一定是喬托設計的結果。由此可判斷喬托對畫面構圖是極為考究的。土地、背景中的山石和天空三個色塊組成了畫面,不過有意思的是,在畫面最上方,喬托用深色畫了一條抽象的色塊。在對現實的表達上,我們說不出這是什么物象,但是在畫面構成上,這塊細窄的色塊卻起到了平衡畫面的重要作用,其在色彩上與下方的山自然相連,使畫面渾然一體,同時增加了畫面的形式感,使畫面更加完整、美觀。三塊深淺不一的藍色塊僅以輪廓線相區分,并未進行細節刻畫和明暗區分,而是以平面化的形式表達,體現了喬托超前的抽象視角與表達。和背景橫向矩形相配合的是縱向的人物和樹干,畫中依次出現的圓形樹冠以及左側的三叢樹葉、空中的鴿子和圣方濟各光環所形成的潛在弧形,使畫面平面又抽象,穩定平衡的同時又具有豐富的視覺因素。

圖2 喬托·迪邦多內《給小鳥布道》 濕壁畫 阿西西圣方濟各教堂上院 270 cm×200 cm,1299年
在《給小鳥布道》中,喬托對每個對象位置和形體的計劃安排都能顯示出喬托在繪畫時對畫面構圖和構成的重視,這也成為他的作品有別于當時其他畫家作品的獨特因素,顯現出喬托繪畫“藝術性”的重要原因。
三、喬托畫面中的主次邏輯
無論是描繪故事情節的人物繪畫還是描繪自然風貌的風景畫,藝術家都需要為觀眾安排好觀看的線索,這不僅是畫面層次的體現,也是藝術家創作時理性思維的體現。喬托為了使畫面主次分明、中心明確,在畫面中作了很多藝術創新。
作品《哀悼基督》(圖3)中,喬托把觀賞者的視線從天上拉到人間,把這個世人熟知的神圣事件改造成了一出令人信服的世俗生活中的戲劇。畫面中主要體現了近處的人物,圣母瑪利亞把耶穌摟在胸前;女信徒虔誠地托著基督的雙腳,凝視著耶穌被釘子穿透雙腳的傷口;約翰則戲劇性地向后展開雙臂,以非常粗放的方式來表達內心的絕望與悲痛,俯身面對這一可怕的現實。畫面右側的兩個人形成一組,默然地哀悼,畫面左側一組婦女在痛哭和祈禱。所有人包括空中的天使都將目光投向基督,使觀眾也不自覺地將視線落在了基督身上。喬托通過這種方式突出了基督和圣母的中心地位。除此之外,背景傾斜的巖石形成了非常明顯的對角線,也把觀眾的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的頭部。在拜占庭風格中,人物往往為正面形象,而在喬托的作品中,人物刻畫是通過不同效果的側面和豐富多變的造型使畫面更真實,而且喬托在前景中安排了兩個背對著觀眾的人物,不僅是對拜占庭藝術的革新,而且為觀眾提供了一個站在她們身后的觀賞視角,加強了觀眾參與畫面故事的感情共鳴,并且也增強了畫面的戲劇性效果。

圖3 喬托·迪邦多內《哀悼基督》 濕壁畫 帕多瓦斯克羅威尼禮拜堂 185 cm×200 cm,1305年
畫面很清晰地將人物分為了三組,中心人物形成一個三角形,并依靠夸張的動作和多樣的姿態成為畫面的視覺中心。左右兩側的人物在感情上依次按照不同的節奏對人物的情感進行令人信服的表達。他的風格完全摒棄了拜占庭以及哥特式情節和人物孤立的風格,把所有局部融合為一個整體,又通過各種手段建立了畫面的秩序。
四、總結
喬托是一位開先河的畫家,在他之前沒有人這么作畫,他完全沒有可以參照和借鑒的藍本,全憑自己的勤奮和天才的想象力摸索著前進。喬托畫面中的美感延續至今,因為他找到了繪畫的共性,將現實的世界歸納組合形成單位的整體,對每一局部設計經營達成意念的和諧,運用繪畫的方法引導觀眾的視線并突出重點,這些因素合力創造了喬托畫面中的“藝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