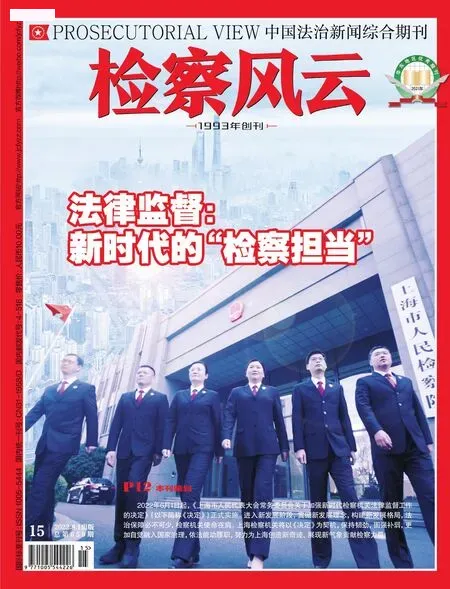耶林: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文/馬嵐熙

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德國中部,有這樣一座建城已超過1000年的城市:它是德國四所大學城之一,誕生了超過4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數學王子高斯曾在此任教直至去世,格林兄弟也曾在此任教。我國學者季羨林曾在此“留德十年”。它就是哥廷根。法學家魯道夫·馮·耶林就住在該市市民大街12—14號。耶林的家是一座兩層半的小樓。斜頂鋪棕瓦,墻面則是舒緩的鵝黃色。一層的窗戶是羅馬式的拱形,二層則是利落的方形窗欞。樹蔭環繞,偶爾也有游客前來探訪。
并不是“板起面孔”的舊式學者
耶林1818年8月22日生于德國北部東弗里西亞的奧里希。他的父親格奧爾格·阿爾布萊希特·耶林就是律師,其家族則有大約300年的法學傳統。1836年,耶林進入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隨后又先后在柏林、哥廷根、慕尼黑等大學學習。這種游學的方式在當時的德國比較流行,因為既可以聽風格各異的教授講課,也可以結交形形色色的同窗好友,并且建立起有益于未來法律職業的人脈網絡。1840年,耶林在柏林大學開始他法學博士階段的學習。他的導師霍邁爾是薩維尼的學生,因此后來有人戲稱耶林為薩維尼的再傳弟子。1842年,耶林在柏林以關于遺產占有人的“論遺產占有”為題獲得博士學位。次年,他開始擔任柏林大學法律系的編外講師。1844年他的首部專著以《羅馬法論文》為題出版。1845年,耶林就已經開始擔任巴塞爾大學的法學教授,此后的時間里,他先后接受了羅斯托克大學、基爾大學、吉森大學、維也納大學的任命,最后于1872年接受了哥廷根大學的任命,在那里生活、任教,直至1892年8月6日去世。
和大眾心目中的法學教授不同,耶林并不是一個枯燥的舊式學者。他喜愛音樂,他最喜歡的作曲家是貝多芬和舒伯特。演奏鋼琴的水平甚至可稱得上專業。在吉森大學任教的16年間,耶林甚至擔任當地音樂協會的理事。在米歇爾·昆澈著的《至愛吉森:耶林在吉森的時光》一書中,還記載了他的音樂軼事:“耶林戲稱自己家有音樂方面的‘義務兵役’,他本人就是一位優秀的鋼琴演奏者。每周日下午,他都要彈鋼琴,晚上和親朋一起演奏或欣賞音樂。耶林家也會定期舉行音樂社交晚會。有時,他會和同事及學生一起組成室內樂樂團。那些會拉大提琴或者小提琴的未來法官,得到了他的器重。耶林還加入了吉森音樂協會。當時樂團的指揮懶散無能,耶林率領大家推動了指揮的更換,并請來了幫手。最終他成了音樂協會的理事。他還組織音樂會。在酒店住宿困難時,那些旅行來的獨奏者們干脆下榻在他家。30年后,音樂愛好者們仍然贊嘆:多虧了耶林,吉森當時的音樂水準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耶林還對園藝頗有興趣——他種過草莓和蘆筍。此外,紅酒和美食也是不能少的。他曾這樣寫道:“沒有色彩就沒有生活——當然葡萄酒、熏制的鰻鱺、山鶉、野雞、惠斯特牌鋼琴、老婆、情人也都屬于其中。”據說曾有人交給過他一個1330升容積的酒桶,里面存滿了好酒。耶林滿口答應,說這些酒可以傳到下一代。然而,5年之后他就把里面的酒全都喝光了。他在法學院課堂上舉的案例也時常離不開“吃”。例如著名的菜單案:“一個法律系學生在一家飯館偷取了制作精美的菜單。10年后他成了檢察官,這時對此前的行為頗感良心不安,于是暗自將菜單又放了回去。這時一個客人拿著這張菜單點菜,對于低廉的價格與豐盛的菜肴頗為高興。直到結賬時才發現,菜價比他按照舊菜單所點菜的兩倍還高。客人與店家爭執起來,問法庭應當如何作判?”
此案并無結論,而是作為課堂案例,并于1846年收入耶林所著的《不附解答的民法案例》一書,供后來者討論。恐怕耶林自己也不會想到,此案在百余年之后被搬上德國最高法院的模擬法庭,成為歐洲法律學生聯合會模擬法庭大賽的決賽審理案件。
名震天下的《為權利而斗爭》
耶林是個非常勤奮的學者,其著作極其豐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為權利而斗爭》,是迄今為止流傳最廣的法學著作之一。此書系耶林根據其在離開維也納大學之前在法學會發表的告別演講擴充而成。這篇演講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兩年內即印到了十二版,此后又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耶林非常具有演講才能,他演講時不喜歡打草稿,而是喜歡即興發揮。另外兩篇重要的演講是《論法感的形成》和《法學是門科學嗎》。他還喜歡撰寫一些法律雜文,既起到普法的作用,又向同行們傳遞最新的研究思路。其中最值得一讀的,莫過于1884年的《法學的戲謔與認真——獻給法律讀者的一份圣誕禮物》。
在維也納大學的四年間,耶林的講課堂堂爆滿。聽眾還包括許多慕名而來的各界人士甚至政府上層官員。加上耶林熱愛藝術、音樂,他很快成了當地法律界、政界以及藝術界、社交界極受歡迎的人士。由于耶林對奧匈帝國法律教育的貢獻,奧匈帝國遂授予耶林一個世襲的貴族爵位,這是過去在德、奧學術界極少數非因政治或軍事貢獻,而僅因學術成就被授予爵位的例子。1872年,耶林打算離開維也納,返回德國任教。作為道別,耶林于1872年3月11日在維也納法學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講。這就是后來名震天下的《為權利而斗爭》。
耶林提醒聽眾們,沒有什么權利是與生俱來的。只有靠斗爭去爭取權利,去呼喚法律,才能真正實現權利。他說:“我的先生們,在當代,我們需要哪怕瞥一眼我們生活的世界,以便看到法是如何進行一場不停歇的斗爭 的。”他認為,權利是人之為人的一部分。權利受害而不作抗爭,幾乎相當于喪失了人格。
與此同時,耶林強調,一個社會應當允許人們“為權利而斗爭”。令人驚訝的是,他舉了《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例子。夏洛克堅持,“權利就是權利”。然而因鮑西婭的詭辯,夏洛克的權利主張落了空。耶林后來在演講擴充成的書稿中對此進行了嚴厲指責,認為這是一種“卑劣的機智”。對于夏洛克的失敗,耶林給予了深深的同情。他說:“狼狽地敗下陣來的,不是猶太人夏洛克,而是無望謀求法律庇護的、處于最下層的中世紀的猶太人的典型形象”。速記員記錄下了當時人們的反應:“暴風雨般的、持續數分鐘的喝彩和鼓掌。”
離開維也納時,耶林拒絕了萊比錫、海德堡等大學的邀請,選擇了小城哥廷根。一方面與他個人生活陷入的困境有關。他的妻子于幾年前去世,使他遭受了巨大痛苦。而他的健康狀況在這一時期也第一次出現了問題,情緒極度消沉。他渴望前往一個安寧靜謐的環境獲得心靈的平復;另一方面,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耶林經歷了學術思想上的低谷。1861年開始,他持續在《普魯士法院報》發表匿名文章“無名氏的親密來信”,長達五年之久。信件批評自己和德奧法律界迄今仍然運用的法學范式,語調尖刻,充滿嘲諷和愚弄。同時,他表明自己對于這一現象也一籌莫展。直到1872年遷居哥廷根,耶林才成功地克服了個人的困難,在學術上開始煥發新生。
在哥廷根,耶林獲得足夠安靜的環境和充裕的時間從事學術研究(這也是耶林受聘哥廷根提出的條件)。在哥廷根市民大街12—14號的兩層小樓內,耶林度過了二十年的時光。而在哥廷根大學這個由約翰·斯特凡·皮特和古斯塔夫·胡果等法學家耕耘了一個多世紀的地方,耶林找到了他的學術之根和最終歸屬。他也幫助哥廷根大學走出1837年“七君子事件”的陰影,再次登上歐洲法學的學術高峰。哥廷根人將一條街道以“魯道夫·馮·耶林”的名字命名(耶林是少數獲此殊榮的法學家,哥廷根大部分街道以自然科學界的泰斗冠名),以此來紀念他為哥廷根所作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