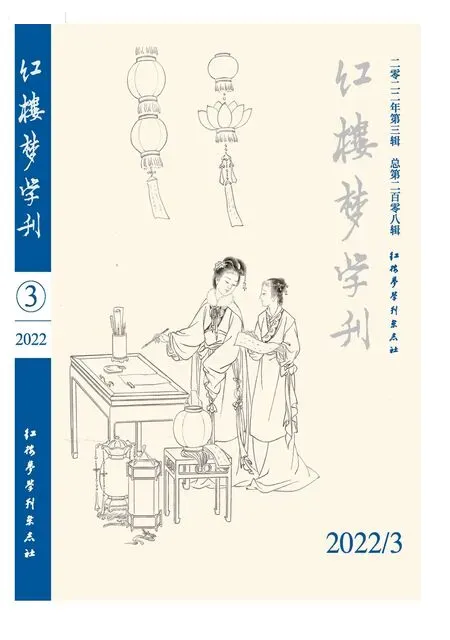經典《紅樓夢》的同人新創與當代書寫*
張春梅 王 寧
內容提要:網文中大量出現的傳統文化表述,裹挾著文學傳統和對傳統意義上文學的利用、改造與重組,從而建立起時代性鮮明的歷史敘述并進行文化再生產。一定意義上,這些趣味感十足的書寫促發了“傳統”的復歸,關乎“傳統的當下性”就成為一個必須直面的問題。關于《紅樓夢》的同人創作是這所謂“傳統熱”中最有吸引力的部分,作為經典的《紅樓夢》被以何種方式表述進而獲得其當代“活法”,被不斷“書寫”的經典攜帶著怎樣的“理想文本”特質,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有望打開傳統與當代之間互為反哺和沖突復雜關聯的諸種面相。
網文中大量出現的傳統文化表述,裹挾著文學傳統和對傳統意義上文學的利用、改造和重組,從而建立起時代性鮮明的歷史敘述并進行文化再生產。一定意義上,這些趣味感十足的書寫促發了“傳統”的復歸,關乎“傳統的當下性”就成為一個必須直面的問題。一則,所敘述的傳統以怎樣的形式存在于敘述之中并發揮何種功能,其代表癥候是什么?二則,這些關于傳統的敘述是在何種想象和實踐空間中進行,在多媒介的融合中如何選取并使其合法化。關于《紅樓夢》的同人創作是這所謂“傳統熱”中最有吸引力的部分,作為經典的《紅樓夢》被以何種方式表述進而獲得其當代“活法”,能夠打開傳統與當代之間互為反哺和沖突復雜關聯的諸種面相。
學界對紅樓同人文的關注時間較早,大概2007年左右就有學者對其概念進行梳理和分類,其后零星的幾篇文章將重點放在紅樓傳統在當代書寫中的延伸,指認其功利性寫作者多。直到2017年《紅樓夢學刊》發表許苗苗《從同人小說看〈紅樓夢〉的網絡接受》一文,正視紅樓同人圈層文化,使研究直面今天的大眾接受,從媒介和受眾角度開啟紅樓同人研究之新局。隨后2020年同樣發表于《紅樓夢學刊》的《〈紅樓夢〉網絡同人小說述論——以晉江文學城為中心》,則將其重點落腳于紅樓同人自身存在的理由,通過表格羅列與文本分析,提出紅樓同人小說之實質和“續書”類似,是讀者與經典文本、作者之間互動交流的有形介質。這些重要的紅樓同人研究成果看到了網絡寫作的媒介規定性以及今天大眾接受已遠非20年前可比的文化現實。在這一脈絡的研究中,留下了重要的問題線,媒介確為促發文化轉型的關鍵,但連接不同媒介的《紅樓夢》卻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學經典,那么今時之改寫者或借題發揮者是出于怎樣的敘事考慮、以何種方式繼續《紅樓夢》經典的影響力?是抹黑,顛覆,還是有一種當下審美理想潛含其中?這是本文在已有成果基礎上欲繼續推進的地方。
客觀說來,紅樓同人文粗看有點“四不像”,既不隸屬《紅樓夢》一脈的正統文學,又與具有媒介規定性的網文存在差異,但這些寫作天然帶有貫通經典之傳統脈絡的功能,連接著此時和彼時兩種文化情境,其間則夾雜著不同歷史節點的各色聲音,寫者也身份各異,有性別之分、文人寫作和坊間戲仿、不同民族的轉寫……這些共同匯成《紅樓夢》經典之路上的光點。如今的網絡同人寫作,則是這光點中極為耀眼的一群。“在網的生活”養成數字驚人的“數字原住民”,他們以趣緣共同體的部落形式,以某一文本或文化現象為底本和軸心,樂此不疲地開展多方位地探秘、改寫和重構,建構起網絡時代堅實的圈內鐵桿粉絲群體。亨利·詹金斯曾對此定義,“粉絲寫作的同人故事建立在粉絲的元文本假設基礎之上,回應粉絲團體內部的常見需求,但是早已超出簡單的批評和解讀;他們是令人滿意的文本,是被粉絲閱讀群體熱情接受的版本,契合這個群體心目中早已設定的理想文本。”從近二十年網文集束式發展趨勢和多版權產業鏈條的聯動局面看,傳統文學尤其當代文學(多稱之為純文學寫作或體制內寫作)的生存空間遭到擠壓,二者之間連綿不斷的口誅筆伐和官司加劇了這種焦灼的現實窘境,為何群體會選擇如是“理想文本”也就成為重要的文化現實問題。
一、經典《紅樓夢》的“同人”之旅
自《紅樓夢》面世以來,續作始終不絕,尤其學界關于后四十回是高鄂續寫的說法生發無數補寫可能性。有同人小說研究者如是說,“從同人小說創作角度來看,這‘后四十回’屬于典型的同人創作,甚至可以稱為《金瓶梅》之外最成功的同人小說,只不過二者走的是相反的路數,《紅樓夢》的‘后四十回’向著原作無限接近”,這種說法是將“后四十回”作為紅樓同人寫作的發端,其特點在于力求做到與原作在故事脈絡、語體風格、主旨把握等方面契合無間。
此后明確為“續寫”的本子層出不窮。既有對一百二十回結局的續寫,如《后紅樓夢》(又名《石頭記后編》,逍遙子作,1796)、《綺樓重夢》(又名《蜃樓青夢》《新紅樓夢》《紅樓續夢錄》,王蘭沚,初刊本1796)、《紅樓復夢》(陳少海,初刊本1796)、《續紅樓夢》(俗稱“鬼紅樓”,秦子忱,1799)、《紅樓圓夢》(夢夢先生,1814)、《紅樓夢影》(云槎外史,1877)等。亦有截取文章中部某一回目進行續作,如《紅樓夢補》(歸鋤子,1819)、《紅樓幻夢》(又名《幻夢奇緣》,97回續,花月癡人,1843)等。這兩種同人創作對故事原有結局“翻案”,即便截中間而續,也往往是接續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斷癡情,薛寶釵出閨成大禮”,林黛玉或投胎或未死,采用寶黛前情再續,以賈府由衰復榮大團圓結尾,表現個人對《紅樓夢》的理解和感悟,在復古與反古的糾纏中,對《紅樓夢》結局的改寫是以文本再建表達求新變意識。其中的“還魂故事在民間流傳廣泛,基本是用來肯定那些克服社會異己力量實現美好夢想的”,顯然同人文作者是借由一個美好的故事表達自身的生活理想和審美旨趣,寶黛情緣恰為實踐這一理想的美的符號。這種理解與關于《紅樓夢》的經典傳播基本吻合,也暗接不同時代更替中思想文化和文人心態的變化。
到了清末,“從中國文化的發展的歷史來看,它是自明中葉至清初思想文化領域活躍、有生氣、有創造性的局面的逆轉”,同時又面臨著尖銳的古今之變、守舊與創新之辯,西學東漸,內憂外患,自然而生變法圖強的新時代氣象。對《紅樓夢》的續寫有《新石頭記》(吳沃堯,1905)、《新石頭記》(南武野蠻,1909)、《林黛玉日記》(喻血輪,1918)《真假寶玉》(張恨水,1919)、《想入非非》(朱湘,1934)。《新石頭記》(吳沃堯,1905)中賈寶玉在1901年復活,在各地游歷,見識到大量新事物,故對未來充滿信心,認為中國有朝一日也將擁有西方科技的能力,提倡只有立憲才能救中國。這一寫法帶有鮮明改良者氣派,不同于對紛亂現實感到悲切、轉而沉溺聲色的絕大部分《紅樓夢》同人續作,對中國的未來抱有積極的心態,是當時眾多續作中飽含啟蒙意識的獨特寫作。1912年辛亥革命勝利,清王朝走向終結,向來習慣于以科舉入世的文人們失去了征伐的領地,報刊業的盛行和坊間通俗文學的傳播,給他們提供了另一方揮墨寶地。鴛鴦蝴蝶派的盛行,是上世紀初世俗文壇的主要風景。其內容不外乎才子佳人情愛故事,言辭在曖昧與人生無常的悲情之中流轉。但要說其只一味談情也不準確,人生所以無常,離不開彼時代關于人與人關系的認知,尤其何為平等的愛情一問成為討論的重點。張恨水的《真假寶玉》(1919)是其中的典范之作。該作講述賈寶玉陷身于精心構造的搞笑環境,夢中見由當時提倡救國的著名戲劇人扮演的充滿喜劇色彩的假寶玉和假黛玉上演幽默的滑稽劇,作者游戲文字,借助“歐風美雨銷專制”“妙舞清歌祝共和”“平權世界”的牌匾戲謔當時的社會情狀,提供消遣的樂趣,卻也在風云變幻的歷史進程中透露出對現實的不滿,既娛樂大眾,亦寄寓政治理想。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走向變革、探索和反思的繁榮階段,作為重要的中華文化代表,紅學成為一門顯學,研究成果堪稱豐碩。有意思的是,因21世紀網絡文學介入而被劃分到“傳統文學”行列的當代書寫者,也并未停止續寫《紅樓夢》的心思,《紅樓夢新補》(張之)、《紅樓夢新續》(周玉清,1984)、《紅樓夢遺事》(都鐘秀,1990)、《夢續紅樓》(胡楠,1994)也是對《紅樓夢》前八十回后的續寫,在主題上表現對《紅樓夢》主題的遵從。這種類型的續作一直延續至今天,由對《紅樓夢》相關考證索隱研究而誕生的紅學,仍舊給予《紅樓夢》無限的創造與可能,《劉心武續紅樓夢》(劉心武,2011)、《黛玉傳》(西嶺雪)、《紅樓夢續》(溫皓然,2011)都是在對《紅樓夢》的鉆研中,作者憑靠自身的調查與理解,進行八十回后的續作,延展自清末“后四十回”創寫的風潮。劉心武不僅續寫紅樓,還演說紅樓,在原作的折疊之處挖掘出各種不曾引人注意的隱秘來。而像王蒙這樣的著名作家,也傾情于紅樓,寫出帶有王氏特色的《雙飛翼》。在當代女作家中,計文君對《紅樓夢》的青睞尤為突出,她不僅研究《紅樓夢》與中國古代小說的關系,而且將其放在不同文化形態的沖突、選擇與守成之間進行自己的文學創作。可以說,經典《紅樓夢》是刻入中國文人骨髓中的文化烙印,這已不是一部簡單的文學作品可以概括。經由這樣一條漫長的續寫之路,借由網絡媒介在不同網站群聚的紅樓同人部落的出現,就有了精神的來處,或許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焦慮在。
早在1993年,網絡文學在國內還沒有什么生成土壤的時候,中國文化界已經有了正統與媚俗的討論,其中殷國明等人“關于正統文學的消解”討論可謂跨越世紀與網文展開對話,指出“以其情節性兼時髦性做成的可讀性、高效率的實現閱讀消遣的滿足,既省心又過癮、從頌圣轉而頌物,這是我們時代轉型的一個既表面又實在的特征”。同一時期的“美女寫作”(林白、陳染等)、“私人化寫作”(衛慧、棉棉、九丹等)等文學口號掀起了小小的關注熱,但與網文書寫相比,這些作家的寫作還有章可循。網文確乎迎來嶄新的網絡時代,“在線的生活”以難以想象的速度建構起當代人的生活日常。寫作這一行為,則從寫者、讀者到傳播途徑整體實現了大反轉,身份的限制被取消,在這樣全新的文化語境下,經典《紅樓夢》一定意義上充當了網絡游戲者“信馬由韁”的中介,這意味著,前此數百年的“續寫”不再是“熱愛紅樓”的一枝獨秀,真正意義上的“紅樓同人文”寫作就此開始。
大量《紅樓夢》同人文幾乎是與網文同步而生,就像網絡改變了人們對“虛擬生活”的認知,同人文寫作幾乎等同于網絡的狂歡。看來自由而無所禁忌的網絡給人們帶來放飛自我的絕佳機會。“經典+無限可能”的組合鑄就了紅樓同人的恣肆想象。作為古典名著的《紅樓夢》不再在情節結構上限制改寫的格局,帶有典型游戲性質的穿越、重生、靈異、異形、玄幻呼嘯而來,原著人物的身份也開始了巨變,各種各樣的改寫給了紅樓眾生粉墨登場的機會。這些具有表演性質的“書寫”在不同網站開花,如瀟湘書院有《紅樓夢外夢》(依稀如夢,2018)、《有鳳難儀瀟湘妃》(依稀如夢,2018)、《重生之林妹妹的幸福生活》(我是一只貓貓,2019)等;17k小說網有《折騰紅樓》(長短三點,2008)、《青黛》(醉琵琶,2010)、《紅樓貴女》(紅迷,2016)等;云起書院有《奮斗在紅樓》(九悟,2016)、《紅樓之庶子風流》(屋外風吹涼,2017)、《紅樓之尷尬夫妻》(林月初,2018)等;起點中文網有《紅樓攻略》(聽風掃雪,2012)、《穿入紅樓》(施家傳人,2013)、《紅樓沉浮》(我是小軒呀,2020)等;飛盧小說網有《紅樓之庶子鬧紅樓》(釘耙豬,2020)、《紅樓王爺不好當》(耶律基德,2020)、《紅樓:命運篡改者》(基本是骨頭,2021)等;晉江文學城有《紅樓之林家皇后》(睡醒就餓,2015)、《[紅樓]板兒的科舉之路》(庭外紅梅,2017)、《[紅樓]公子林硯》(時槐序,2017)、《[紅樓]權臣之妻》(故箏,2017)、《[紅樓]大圣娶親》(一窈風,2019)《[紅樓]大丫鬟奮斗日常》(太極魚,2019)、《[綜名著]帶著大平層我穿越了》(靈默笙,2020)等。從數量、題目到寫者的網名,可謂千奇百怪,無所不有。那么是否這些寫作與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已經南轅北轍,我們又怎樣從這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寫作中去追蹤經典的影響之途,這是接下來要試圖回答的問題。
二、“古為今用”的敘事策略
如果說互聯網時代是什么都有可能的時代,是生活充滿極大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時代,那么互聯網經濟就是促生這些“可能”的新型生產環境。滿足受眾所想、引導受眾需求成為互聯網孜孜之所求。具有當代意義的趣味性是這一生產機制的美學品格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為主要的美學特征,這決定了網文的可變性和不斷翻新的類型制造。經典《紅樓夢》是以什么樣的方式進入到屏幕兩端的寫手與大眾眼中?
我曾在論述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關系時談到,寫手在互聯網擬就的公共空間中借助受眾參與等方式進行相關文學創作,以《紅樓夢》為基礎命題產生傳統與現實文化場域的連接,對文學經典的改編、改寫或者解構是傳統文學直接進入網文的明顯表征。梳理發表于晉江文學城古典衍生下屬的完結紅樓同人作品,1000有余,時間跨度從2003年有相關記錄起始,至2021年4月12日截止,依照表1數據統計,《紅樓夢》同人創作量在2017年至創作頂峰,與同類網絡作品比較,數量規模占比較大。

表1 《紅樓夢》同人小說多維比較
從這些數量龐大的網文和第一部分列出的諸樣題目,我們幾乎富有質感地觸摸到寫手和粉絲雙方構建起的“古為今用”的趣味敘述大廈,然其看似無厘頭的同人背后,卻無一不在提醒著經典《紅樓夢》的在場,從而不斷書寫著繼承與翻新的雙重敘事任務。
(一)敘事結構的承繼與創新
蔣和森曾論說,“《紅樓夢》在藝術上是采取的多線結構。它以賈寶玉作為全書的主人公,并以主人公的愛情婚姻悲劇作為貫穿全書的主要情節故事。當然,整個小說并不是僅僅沿著這條線索發展,還描寫了以賈府為代表的封建四大家族的衰亡過程,其中又集中描寫榮國府。不妨說,這也是貫穿全書的一條‘線索’。它與前一條線索互相穿插地交織在《紅樓夢》里。”主線貫通,多條支線并舉的榕樹狀脈絡,在紅樓同人作品中隨處可見。如《[紅樓]公子林硯》以林硯步步策劃的一生為主要線索,而蘇瑾和皇子的糾葛、林家與甄家的敵對等則作為旁支存留。與此同時,同人作品創作者也對紅樓中已有敘事結構進行重構,植根原作基礎衍生獨特文本結構。常見的是文中留存原著中主角,安排其穿越異世重生至紅樓人物身上(此所謂魂穿),如《[綜名著]帶著大平層我穿越了》,“看到紫鵑離開,小小的船艙里就剩她自己一個人,林黛玉,或者說是喬喬松了一口氣。不再端著千金大小姐的范兒,整個人倒在軟榻上。自己穿成了大名鼎鼎的林妹妹,紅樓的女主角之一林黛玉林姑娘。”林黛玉在成為孤女前期被喬喬占據軀體,因得知未來發展向,遂決定改頭換面,這是典型的借原著之形獲取聯通現實之新時空的生存可能,也是賦予林黛玉生存技能以實現新生存機遇的粉絲想象。
或將原作中支線配角改換靈魂,如《紅樓第一狗仔》將敘事重點放在賈赦這個原著中并不討喜的角色身上,“賈赦從床上醒來時,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張古床上,還想著是他跟拍的明星好心,看他睡在車里可憐,給他挪到影視城內的房間里休息,忽然間頭劇痛起來,許多陌生畫面在他腦海里奔涌,原來還是穿書,《紅樓夢》里和自己同名姓的賈赦”。這種情形在網文中預示著現實版的賈赦已被一本書“奪舍”,經典《紅樓夢》成為引力場般的存在。或主角為作者直接安插的虛構人物,憑借個人運籌帷幄之力改寫《紅樓夢》“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結局。如《紅樓之林家皇后》中林婉玉是原著中并不存在的人物,文中林婉玉是賈敏和林如海的大女兒,《紅樓夢》中林黛玉并無姊姊,由此可知林婉玉乃新設人物。作為虛擬主角,她擁有原作中人物身世記憶,“婉玉一直有點小期盼和回避的事實終于擺到了眼前,表弟表妹都有了,這還淚之說早晚得提上日程,還有等著她們的喪弟喪母喪父,背負著巨大的財產被送進賈家,之后孤苦無依,死于風刀霜劍嚴相逼之下。”這基本就定下了改寫的格調,“假如書本歷史可以重來”,虛設的林婉玉將不再容忍“風刀霜劍”境遇中泣血而亡的悲慘,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個女性人物一反原著女子行事邏輯,步步驚心,卻計劃周詳,終登頂國母的顯赫位置,林黛玉等紅樓眾人之命運就此顛覆。
敘事結構是文章的骨骼,紅樓同人作品通過對結構的選擇性接受與拓展,形成獨具特色的敘事結構體,既區別原作,也做出迎合時代的改造。《紅樓夢》的敘述是超敘述的“木石前盟”說在前,后有警幻仙子演說“紅樓”,然后經由層層敘述者引出人物故事。紅樓同人文則并不拘于原著的天人對應格局,這些網文不滿足于虛構人物,還營建出迥乎現實的異次元世界。打著《紅樓夢》旗號的網文把不同于《紅樓夢》的他者世界與其聯動,架構起獨具特色的新文本世界,既有趣又令人大開眼界。其中經典文本疊加是搭建起傳統與當代橋梁的形態之一。這一架構常常將不同文本世界觀彼此串聯,形成人物共通,情節融合的模式。如《[紅樓]大圣娶親》把《西游記》與《紅樓夢》鏈接一處,孫悟空在西天取經后為絳珠仙草而下凡,奪神瑛仙子的凡胎,贈與賈元春月老紅線,助其一臂之力,獲取凡間皇帝青睞,從而護林黛玉平安,保賈家一世榮華。此外,也有與現實的多空間重疊。《[紅樓]權臣之妻》把清代官員和珅所在現實與紅樓相連,“縱使凌空再不通歷史,也該知道乾隆年間,和琳乃是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巨貪和珅的親弟弟。也就是說——他穿成了和珅”。顯然,此和珅已非彼和珅,住在其間的“另一人”扮演和珅角色,擁有了權力、財力,欲拯救林黛玉于悲慘命途的意圖也就有了可能。如文中述:“‘賈寶玉雖說本性不壞,但以他的性子,若是和黛玉在一處,黛玉便會吃盡虧,受盡苦,說不得又要走上原著的那條死路。那怎么成!這一往下想,就有些收不住了’。即刻派遣劉管家認親雪雁,為知曉林黛玉入賈府后生活境況安置眼線。”這樣搭建起的文本間、文本與現實共存世界圖譜,原著敘事結構雖被改造,但顯然,正是對原著的“不盡意”才有了新安排的嘗試。此亦為“趣文”的一大特點。
(二)敘事內容的承繼與創新
紅樓同人創作雖在關于愛情態度上有不同,但書寫上依然承襲中國古代小說愛情基本模式,大略為“相遇為起、考驗為承、誤會為轉、團圓為合這四個樂章的變奏”,與傳統愛情傳奇有異曲同工之處。如《[紅樓]公子林硯》中林硯與沈沅的愛情之發生依舊是傳統套路:先有兩府意圖聯姻而相遇,接著三皇子假意設計玷污沈沅名節,從而完成對二人情感的考驗;后有沈沅誤會林硯喜愛蘇瑾產生誤會,最終解除誤解終成幸福美滿的婚姻。這種敘事套路在這些同人文中為數不少,顯出傳統價值觀在當下依然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力。
除延續《紅樓夢》的情愛模式,也存在有別于原著以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的三角戀情串聯故事全局的創作線索。最大的不同當屬對原著人物性別的改變,進而依托同性戀情改變其情愛觀。經統計,晉江文學城古典衍生類型已完結紅樓同人文中,這類作品占比26%,其背后的女性粉絲顯然數量不少,直截的情愛表達方式彰顯出當下對愛情已不滿足“小女兒情態”的曖昧表達,而第三者的沖突環節并不討喜。如《紅樓第一狗仔》中賈赦與宋奚,《黛玉是個小哥哥[紅樓]》中黛玉和寶釵的性別反轉,《紅樓之賈赦教渣渣》中對賈赦人設的重新架構。這種同人作品多將視線放在原著中的反面人物,比如賈赦,原本是“色”的代言人,卻轉寫為有話題效應的搞怪黨,這從前列幾個作品標題便可見出。漫長的紅樓同人之路上發生的觀念之變由此可見一斑。
敘事內容的重構還表現在現代元素的運用。這主要體現在有穿越梗的作品中。如《〈紅樓〉公子林硯》就是個古代身體現代靈魂,有點像人機合一的賽博格,總是有超越時空限定的裝備的。林硯自帶隨身空間、有系統任務不斷添加,能制作伽利略結構的軍用三腳立式望遠鏡,現代生活經驗如“會員制”的經營策略也幫助他在異世大放異彩。再如《[綜名著]帶著大平層我穿越了》中有言,“‘唯一安慰的是我的大平層跟著來了’,喬喬看著晃蕩的天花板喃喃低語”,“大平層”一詞攜帶著鮮活的現實生活氣息撲面而來。再如《[紅樓]大丫鬟奮斗日常》《璉二爺的科舉之路》,走的是系統修仙文一脈,這種帶有鮮明互聯網印記的寫作是近幾年較受歡迎的新類型。這類文是把“系統”作為一個游戲系統帶入文本世界,或者說系統就是文本世界規則的制定者和考察者,“原來跟了朱繡兩輩子的‘本領’竟然異化了:‘檢測到靈氣,系統異化升級’‘升級完成,獲得翠華囊’‘開啟強化功能’‘開啟鑒別功能’……朱繡這才確定自己真的有個系統,只是原來的系統只有‘收集熟練度’的功能。”這類文反映出大眾日常生活深受網絡影響的堅實現實,游戲思維也深嵌其中。
(三)敘事視角的承繼與創新
前面提到,《紅樓夢》的敘事視角層層落地,這種寫作方法給后來的小說創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紅樓同人文借鑒了這種多視角綜合運用的書寫方式,如《[紅樓]大丫鬟奮斗日常》立于朱繡視野,由于她為外來者,故獲得洞悉她人生命歷程的洞察力,文內有言,“要不然朱繡做什么巴結王熙鳳呢,還不是怕王熙鳳也像書里那樣,收了人家好處,像把彩霞配給容貌丑陋、酗酒賭博的旺兒之子那樣,胡亂把青錦也配了人。”有意思的是,這個天外來客的丫鬟又將有怎樣的命運呢?這就將其視角從超敘事變成了限制性視角,增添了文本的可讀性和吸引力。
類似的綜合運用全知視角和限制性視角寫作的文本還有很多,但由于紅樓同人文在人設、時空、人物關系上采取多重疊加的方式,這就使得以往必須幾人才能完成的敘事任務,往往一個穿越者就能勝任,從而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如《彼岸繁花[綜紅樓]》中林夕穿越至《紅樓夢》內王熙鳳,作為現實世界有豐厚閱讀經驗的現代人,對書本人物王熙鳳的生命歷程很清楚,也有自己的評價,“《紅樓夢》這書,就找不出比王熙鳳還能干的傻女人了。她拼著自己身子不要,也要爭強去當那個管家婆,累死累活地也沒討到個好。最終是機關算盡,害人也終害了己,填上了自己的性命。”但在拯救“自身”同時,作為穿越者的價值觀會參與到此世社會關系的判定,“林夕皺眉,她估計著,應該是王熙鳳弄權,拆人姻緣逼死人的那件事了。她心下想著,自己來這的時機倒是巧啊,那王熙鳳還沒來得及、弄出傷了人命的事兒呢。要是從今往后,得頂著王熙鳳活著的話,怎么也得扭轉了這事兒,起碼不沾邊才好。”此時,作為旁觀者的林夕變作戲劇化的角色視角,自此進入敘事序列的文本《紅樓夢》便展開一出以外來者林夕(實際是讀者,但同時也是文本的創作者)為軸心的新世界圖景。而經典《紅樓夢》與正在進行的紅樓眾人的“新歷史”和諸般“可能”就此上演,作為經典《紅樓夢》的讀者自然參與到了這一“新創”工程,在經典/同人、寫者/參與者、讀者/創作者等范疇之間展開趣味盎然的對話。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作為經典的《紅樓夢》跨越千山萬水、在歷史長河之中與今天的讀者大眾建立起了歷史的當代性,這理應是紅樓同人文在不斷演說《紅樓夢》的游戲中對優秀傳統文化厚度的再次加碼。
紅樓同人文還存在視角固定化的寫作,這一方式破除原作長于在相應語境下從不同人物視角表達情感體驗的特點,將視角限于一人,從往往是主角的眼光審視事態發展與人物關聯,如《紅樓之林家皇后》中的林婉玉、《黛玉有了讀心術》里的林黛玉、《權臣之妻》中的和珅等,都在寫作過程內站在主角位置洞悉故事情節的變遷,而較少從作品所涉其余角色的角度面對情節流轉。這樣做的好處是故事情節有統一的觀念和邏輯,往往其判斷行為的根據是主角擁有洞穿人物關系和社會奧秘的“前見”,故事也就有了“窺視”和參與的可能性,對于動輒幾十上百萬字的網文來說,零散的閱讀是需要一個一以貫之的眼光的。假如這一眼光是從林黛玉、賈寶玉的角度展開,會更加有吸引力。畢竟,在經典《紅樓夢》中的寶黛看似不斷出場實則浮沉于既定的社會關系結構,是缺少主動性的一方。紅樓同人文的力量往往在于“假如我是”的顛覆性重寫。當林黛玉有了讀心術能夠看透身邊之人的內心隱秘,足以憑借此項技能拯救自我于水火,一改原著敏感而不失激烈的個性,變成溫和的局勢掌控者,終為自己掙得不同于原書的人生結局(《黛玉有了讀心術》)。類似紅樓同人還有《黛玉是個小哥哥[紅樓]》《黛玉有錦鯉體質[紅樓]》《寶玉奮斗記》《紅樓之仙路》《黛玉有了透劇系統[紅樓]》等。亦有立足原作配角角度進行書寫,如《紅樓第一狗仔》中賈赦原為《紅樓夢》中旁支人物,但在此文章中通過其眼目重看大觀園眾人像,與之相同視角選取方式的有《彼岸繁花(綜紅樓)》《[紅樓]錦鯉賈瑚》《惜春是個佛修[紅樓]》《紅樓之好想哭》《[紅樓]他的嘴巴開過光》等,還有從虛構人物視角來嵌入文本描述中,如《紅樓之林家皇后》《[紅樓]無人知是荔枝來》《[紅樓]大丫鬟奮斗日常》《紅樓之黛玉后媽不好當》《[紅樓]養女送子》。
這些文本看似大開腦洞,游戲味足,但透過重重“假如”,卻能讓人清晰捕捉到今時之讀者對經典《紅樓夢》的酷愛以至種種情感上的“不足”“不甘”,倘沒有文學給養、現代知識的熏染和作為現代人的自覺,很難在細枝末節上生發出如此多的“余地”。
三、重繪“理想文本”
新與舊、傳統與當代的問題似乎一直纏繞在文學演進史中,就像馮驥才所說,“在不同的時代,人們會自然而然地將自己對時代的審美感融進舊形式去。”網絡寫作的“集體性”打破“作者個人化語言”的創作秩序,使對紅樓同人的創作成了“一批人”對生活經驗的共同寫作,在寫手與受眾(粉絲)的共同參與下,以經典為底本的同人小說以典型的媒介文化和消費文化形態進入到21世紀關于《紅樓夢》的創寫之途。在這一過程中,“古為今用”帶有更突出的“新變”特征和新影響力。
(一)情節陌生化的追尋
陌生化基本默認為文學之為文學或說文學性的表征,由于“不按常理出牌”或“讓石頭更像石頭”,在藝術表達和習以為常的事物之間拉開距離,讓人產生一種感受和理解上的陌生感和震動效應。經典《紅樓夢》在文本出場的彼時彼刻,古代的白話日常,大觀園中一眾才學品貌上佳的女子,一個抱持男女清濁之分的通靈寶玉般的男子,就已經是充滿審美觀照可能性的陌生化所在,也就自然帶著那個時代的審美理想,或者“假想”。
打著《紅樓夢》旗號的同人創作基本上是真愛粉,多數作品并沒有扔掉原文另起爐灶,但又常另辟新招。網文的類型化決定其必須不斷“老梗翻新”,閱覽推送首頁簽約成功的網絡作品,無不是在既有綱本上推陳出新,憑借新奇和新鮮因素網羅受眾。但作為經典文本的同人寫作,若完全任之天馬行空,則很可能背離接受者的心理預期。在對紅樓的同人創作中,寫手往往保留部分原著經典片段,對其改寫,如賈寶玉初見林黛玉,就同時存在《黛玉的打臉“系統”》(落鵠九囀作)、《黛玉有了讀心術[紅樓]》(元日作)、《[紅樓]大圣娶親》(一窈風作)、《[紅樓]嬌女迎春》(無法忘記的遺憾作)、《[紅樓]權臣之妻》(故箏作)、《紅樓之林家長女》(莫冉塵作)、《紅樓之黛玉不欠誰》(紫生作)等文內。這些題目本身另據新意,有點標題黨的意味,但又流淌著熟悉的幾分味道,對熟知紅樓的閱讀人來說,是“熟悉的陌生人”,心中有舊,舊中見新,為其披上“意想不到的外衣”,打破原著確定化的結構體系和社會關系,情節的更變,為受眾帶來不一樣的審美體驗。當然,這種“新”也是寫者讀者粉絲雙方默認的當下心思和“自我”的另類表達。經典《紅樓夢》在這個意義上便肩負“圈粉”和建構理想烏托邦的雙重功能。
(二)語言網絡化傾向
《紅樓夢》文白相雜的表述方式直接影響到后來通俗文學的語言走向,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是這一脈的流風余韻,此后經現代文學洗禮,白話文逐漸替代古白話的畫風,成為主要的語言格調。時隔半個多世紀,在21世紀初的網文書寫,我們卻看到這種古白話的敘說風格竟成鐘愛之舉。“紅樓體”孵化了眾多古風文本,民國風的書寫也大都含蘊其中。且不說紅樓同人文,《昭奚舊草》(書海滄生)、《金玉王朝》(風弄)、《九重紫》(吱吱)、《甄嬛傳》(流瀲紫)等偏好“古風”寫作的文本,之所以引來粉絲無數,與這種古代白話的表達斷斷是分不開的。
紅樓同人文寫作以古代文言為主體,但與日常語言并不完全割裂,也可同時兼容于單獨的長短句,如《[紅樓]大丫鬟奮斗日常》,類似“三更半夜的嘰咕甚”,其中“甚”為文言,“嘰咕”是白話,二者并存,不影響交流還能制造出輕幽默效果。這只是與日常語言的拼搭,更多的是網絡語言和表情包堂而皇之進入文學表達,從而打上了鮮明的互聯網時代印記。網絡語言包含兩種類型:一是網絡相關專業術語或特定行業用語,二是網民在社交媒體上的常用詞語、語句和符號。紅樓同人文以狹義上的網絡語言為主,其中既有隨意拼貼,《帥爆全紅樓的族長》里的“狗膽包天”,將“狗”與“膽大包天”相接,保持原成語義,并混搭蔑視之情,加重語氣同時豐富蘊含的情緒。還有概念隱喻,如《黛玉是個小哥哥[紅樓]》中“厲害、社會、了不起”,這里的“社會”不僅指生物和環境形成的關系總和,在這篇文章的情境內則表示經歷過社會,對其有深入了解的人,包含調侃語氣。與之類似的還有《帥爆全紅樓的族長》中的“一碗雞湯”等。劉鋒杰曾在論述20世紀初胡適小說中的“美意識”時指出,文字的變革不能僅是文字形式的置換,它更指被置換的文字應能充分體現新的審美意識,利于文學創作水平的提高。如今網絡用語已不再是新世紀初那般令人側目,微信已經深入到人們的日常行為,評價網絡用語已走向不同人群、性別、領別的差異,而不是“用或不用”的問題。變成“日常”的網絡語,出現在紅樓同人文中,很自然地成為彰顯時代和媒介差異的文化符碼,不同說者攜帶的文化基因實際是顯而易見的,于此也更凸顯出寫者的言說位置和世界想象。
(三)生存空間逼仄下對輕松氛圍的需求
王國維論說《紅樓夢》以生活為爐,以苦痛為炭,而鑄其解脫之鼎。曹雪芹筆下的世界是把生命的詩意盡數毀滅,大觀園盛極而衰則為一代皇朝逐步傾頹的縮影。元春省親,“園內帳舞蟠龍,簾飛繡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悄無一人咳嗽”,然屋中賈妃垂淚,一手挽王夫人,一手挽賈母,只是嗚咽對泣而已。本應慶賀,卻場面哀戚,盡顯《紅樓夢》悲喜交重的人生況味。紅樓同人文中也有部分作品沿襲在宏闊的喜慶中流淌悲哀氣息的審美氛圍,如《[紅樓]板兒的科舉之路》結局板兒從家徒四壁搖身為富貴大家,然榮、寧二府從此衰敗,家破人亡,一派熱烈歡喜中蘊藏哀情,悲喜的二重對立躍然而生。
然紅樓同人創作在無網不歡的WiFi時代,離不了觀者的閑情和對緊張現實的緩沖需求。數據顯示,晉江文學城古典衍生類紅樓同人文中,風格輕松514篇,爆笑11篇,占比43.6%,業已形成以《紅樓第一狗仔》《黛玉的打臉“系統”》為典型,快、爽、輕松或爆笑為特質的審美特征。《紅樓第一狗仔》中賈赦頂撞賈母,搬離馬棚,將賈寶玉吃穿用度與己對照,借此羞辱二房,對人物形象進行顛覆創造的同時,將一個并不討人喜歡的“大爺”硬生生寫出幾分英雄氣概。而帶著“大平層”穿越的“大觀園闖入者”,更將當代人的生存空間緊迫感寫得十分傳神。這樣的寫法看似插科打諢,笑料不斷,但輕松背后也讓讀者產生如臨其間的代入感,充分展現出今時今日大眾“屌絲逆襲”和身份破圈的強烈意識。若將這類書寫打包集中起來看,則今時大眾的文化心態、生存感受、社會倫理是可以清晰捕捉到的。對經典《紅樓夢》的“輕松”重述,實有對《紅樓夢》中生活的向往和對自身生活境況的回視。
(四)現代觀念加持下的“理想生活”
一定程度上紅樓同人文自覺將圍繞經典《紅樓夢》的讀寫作為自己的生活志趣。原作中的人物、生活情境、社會關系成為同人寫作百寫不厭的對象,而關于“未來大觀園”的想象則幾乎貫穿這些同人文的心臟。換句話說,對“理想生活”的構想是紅樓同人文的助推器。經典《紅樓夢》成為紅樓迷妹迷弟抒發情懷和雕琢生活的理想文本。
其中,家世背景/愛情的二元關系裹挾著男/女社會身份成為重構“大觀園”屢試不爽的所在。借用馬克思的話說,“對于封建剝削階級來說,結婚是一種政治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個人的意愿”。“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緣”之間的矛盾,在理想的浪漫愛情和世俗社會秩序之間留下了太多令人唏噓和“不盡意”的空白。如果說,寶黛的時代人們還只能身處樊籠而不得脫,今天的大眾卻已經受了太多現代觀念洗禮,諸如“主體”“自我”“自由”“平等”,包括“逆襲”,這樣一些詞匯背后帶來的是深刻的個體意識覺醒,文學史上的“革命”一脈加強了認識和行為的合法性。隨著時代變遷,尤其信息時代的到來,“新”的審美走向不斷替代“舊”的成為言說主題。
在紅樓同人文中,論說婚姻愛情往往將包辦婚姻和“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婚姻倫理邏輯作為攻擊的靶子,這些被選中的人物或穿越者帶著現代光環似利劍般捅破堡壘似的家族陰霾,以當下人的眼光指出經典《紅樓夢》的諸般可能。如《黛玉是個小哥哥[紅樓]》中林探花和妻子達成共識,“要是我們五十歲還沒有孩子那我們就要么過繼要么收養。”顯然,女性主義的各種理論包括普世性的男女平等觀念已經以各種方式浸入大眾日常生活,再卑微的女子也有可能迎來自己把握的人生,如《紅樓之邢氏威武》,在原作內稟性愚犟,只知奉承賈赦的邢夫人通過接回迎春并扶助為妃、挽救賈璉、借助放利錢威嚇籠絡王熙鳳、促使分宗振興長房等方式,塑造了一個足智多謀的女性形象。這類寫法在網文中并不少見,穿越者、重生者,大多有重整河山的氣魄,不管“穿”的行為被迫與否,想要“好好活一次”的想法是共通的。與之稍有不同,紅樓同人文是帶著對經典名著的喜愛和熟悉開始主觀色彩強的行動,也就是說,穿越者和所穿之世界早已建立起觀審關系,在看者/被看者的關系結構中凝聚著強烈的審美判斷和主體意識。這一結構帶動起對整個社會的重新解讀,權力、身份、主體,一個個帶有鮮明現代意味的話語借由《紅樓夢》串聯起今天的文化心理和社會生態。這無疑是經典《紅樓夢》在今日中國讀者中的深刻影響力,是大眾心目中承載著萬般可能的理想文本。
① 相關研究成果大致如下:秦宇慧《當代“〈紅樓夢〉同人小說”初探》,《沈陽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李榮《網絡“紅樓同人”小說創作與當代青年女性心理狀況——以“晉江原創網”與“瀟湘書院”為中心》,《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張慧禾《互聯網時代言情小說出版熱潮分析——以紅樓同人小說為例》,《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王倩《〈紅樓夢〉對網絡小說的影響》,上海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陳陽雪《〈紅樓夢〉在當代網絡文學中的映射》,《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7第1期。
② 許苗苗《從同人小說看〈紅樓夢〉的網絡接受》,《紅樓夢學刊》2017年第3輯。
③ 陳榮陽《〈紅樓夢〉網絡同人小說述論——以晉江文學城為中心》,《紅樓夢學刊》2020年第3輯。
④ [美]亨利·詹金斯編,鄭熙青譯《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北京大學出版2016年版,第148頁。
⑤ 王喜明《同人小說的前世今生》,《書屋》2017年第10期。
⑥ 張云《作為首部續書的〈紅樓夢〉》,《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4輯。
⑦ 龔書鐸《乾隆年間文化斷想》,《北京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
⑧ 殷國明、陳志紅、陳實、朱子慶、何龍、費勇、文能《話說正統文學的消解》,《上海文學》1993年第11期。
⑨ 張春梅《沖突與反哺: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中國文藝評論》2017年第11輯。
⑩ 劉夢溪《紅樓夢新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頁。
[11][17] 靈默笙《[綜名著]帶著大平層我穿越了》第1章,晉江文學城。http://www. jjwxc. net/onebook. php?novelid =5225996&chapterid=1。
[12] 魚七彩《紅樓第一狗仔》第1章,晉江文學城。http://www. jjwxc. net/onebook. php?novelid =2876769&chapterid=1。
[13] 睡醒就餓《紅樓之林家皇后》第17章,晉江文學城。http://www. jjwxc. net/onebook. php?novelid =2319426&chapterid=17。
[14] 故箏《[紅樓]權臣之妻》第1章,晉江文學城。http://www. jjwxc. net/onebook. php?novelid =3349438&chapterid=1。
[15] 故箏《[紅樓]權臣之妻》第4章,晉江文學城。http://www. jjwxc. net/onebook. php?novelid =3349438&chapterid=4。
[16] 陳惠琴《論〈紅樓夢〉敘事結構的三重奏》,《福建論壇版》1998年第2期。
[18] 太極魚《[紅樓]大丫鬟奮斗日常》第9章,晉江文學城http://my.jjwxc.net/onebook _ vip.php?novelid =2648132&chapterid=9。
[19] 太極魚《[紅樓]大丫鬟奮斗日常》第22章,晉江文學城http://www. jjwxc. net/onebook. php?novelid =2648132&chapterid=22。
[20][21] 李一平《彼岸繁花[綜紅樓]》第1章,晉江文學城http://www. jjwxc. net/onebook. php?novelid =3263375&chapterid=1。
[22] 馮驥才《中國文學需要“現代派”!——馮驥才給李陀的信》,《上海文學》1982年第8期。
[23] 張春梅、郭丹薇《網絡擬古世情小說的歷史脈絡與文化空間》,《中國文藝評論》2021年第2期。
[24] 太極魚《[紅樓]大丫鬟奮斗日常》第4章,晉江文學城http://www. jjwxc. net/onebook. php?novelid =2648132&chapterid=4。
[25] 王秋艷《網絡語言成因的傳播學及心理學探析》,《傳媒》2019年第1期。
[26] 劉鋒杰《胡適小說研究中的“美意識”》,《江淮論壇》1997年第3期。
[27]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10頁。
[28] 曹雪芹原著,高鶚整理《紅樓夢》,中華書局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頁。
[29]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委員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頁。
[30] 霜雪明《黛玉是個小哥哥[紅樓]》第1章,晉江文學城http://www. jjwxc. net/onebook. php?novelid =2932100&chapter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