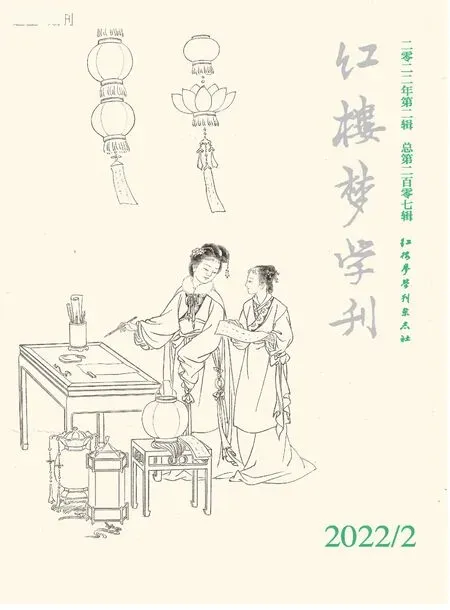“雨夜瀟湘”曲藝音樂改編對《紅樓夢》的傳播
呂 笙
內(nèi)容提要:《紅樓夢》第四十五回展現(xiàn)了一幅雨夜寶玉探瀟湘的溫情畫面,又有《秋窗風(fēng)雨夕》一首,備受讀者喜愛。曲藝音樂對此回情節(jié)進行精心改編與傳唱,進一步擴大了這部經(jīng)典名著的影響。本文以梅花大鼓、岔曲、蘇州評彈等曲藝唱段對小說第四十五回的改編為切入點,探討俗文學(xué)視域下《紅樓夢》的傳播問題。
“曲藝音樂又稱說唱音樂,是以說、唱為手段來狀物寫景、傾訴感情、表達故事、刻畫人物的一種獨特的藝術(shù)形式。它同民歌、戲曲音樂、民間器樂曲一樣,是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說”與“唱”是曲藝音樂的重要特征,鄭振鐸先生曾說:“由于民眾未必都讀小說,未必時時得見戲曲的演唱,這時講唱文學(xué)就成為了他們精神上的主要食糧。”《紅樓夢》第四十五回為“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fēng)雨夕悶制風(fēng)雨詞”,此回塑造了善解人意、通情達理的林黛玉,描繪了一幅沒有口角風(fēng)光旖旎的寶黛溫情畫面,亦是寶黛愛情的一個重要轉(zhuǎn)折點。滿懷愁緒的《秋窗風(fēng)雨夕》長詩透露出女主人公林黛玉悲慘的命運。書中描繪了林黛玉病臥瀟湘館的凄涼畫面:秋夜聽雨聲淅瀝,燈下翻看《樂府雜稿》,見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詩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fā)于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fēng)雨夕》”。初唐詩人張若虛所作《春江花月夜》,是一首“孤篇蓋全唐”的寫離愁別恨的歌行,林黛玉所作之詩在格調(diào)和句法上都有意對其進行模仿。《秋窗風(fēng)雨夕》既可有節(jié)奏地念誦,又可有律動地吟誦,這使其具備了曲藝音樂中“說”與“唱”相結(jié)合的特點,再加上第四十五回所傾訴的情感、刻畫的人物、描述的故事均適宜似說似唱的藝術(shù)表演形式,才有了不同曲藝曲種對這一回目的精心改編。本文擬從梅花大鼓、岔曲、蘇州評彈三類曲種對《紅樓夢》第四十五回的改編切入,從曲種來源、曲本唱詞結(jié)構(gòu)、演出形式等方面考察,探討俗文學(xué)視域下《紅樓夢》的傳播問題。
一、《寶玉探病》——單弦岔曲口口相傳
岔曲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北京城區(qū)及郊區(qū),盛行于乾隆年間。乾隆六十年(1795)在北京出版的《霓裳續(xù)譜》就收錄了北京、天津流行的岔曲一百四十八首之多,包括小岔曲、數(shù)子岔曲、大岔曲、群唱等,可見岔曲在當時已經(jīng)是一個成熟的曲種。在“岔曲”流傳的過程中,雖然特殊時期曾被清代貴族所控制,但在此后發(fā)展進程中為了招徠更多的聽眾,岔曲在內(nèi)容上也進行了一些變化,作品的生活氣息更加濃厚,曲調(diào)及風(fēng)格也變得更加群眾化。在清代貴族掌握岔曲的時期,演唱者一般為“八旗兵弁”和“富豪大員子弟”,當時也只有一種伴奏樂器——八角鼓。當岔曲與牌子曲結(jié)合之后,除了清代貴族演唱,雜耍館子中也出現(xiàn)了岔曲的表演,伴奏樂器在八角鼓的基礎(chǔ)上又多了三弦,在演唱牌子曲之前單獨地演唱一段岔曲,使得這一曲藝形式漸漸地走入了社會的各個角落。岔曲《寶玉探病》的唱詞取材自《紅樓夢》原著第四十五回,言前轍。唱詞的曲頭以寫景始筆,細膩地描寫了瀟湘館內(nèi)外之景、黛玉的神態(tài)及心理變化,曲中大量的對話內(nèi)容描繪了一幅寶玉探黛玉溫情的畫面,曲尾又用簡短的語言敘述寶玉離開后黛玉暗自傷懷的情愫。唱詞詞句清新自然,情感烘托與溫馨對話銜接流暢,用自然又不失雅致的語言道出了一段美好靜謐的感情。
岔曲唱詞的基本結(jié)構(gòu)分為“大岔曲”和“小岔曲”兩種。“小岔曲”唱詞每段共為8個長短句式,前四句為“曲頭”,中間兩句為“過板”,最后兩句為“臥牛”,過板與臥牛合起來可算作“曲尾”,其基本格式為:
(曲頭)四、四、七、七;
(過板)七、五;
(臥牛)三、三、七。
在“小岔曲”的格式中,插入若干“數(shù)字句”(由若干五字句或七字句組成),形成一種大型結(jié)構(gòu)的岔曲叫作“大岔曲”,如《寶玉探病》:
(曲頭)夜雨秋深|(四)
勾惹起林黛玉對景含怨悲懨懨(數(shù)字句)
閑覽詩文|(四)
灑紗窗滴滴點點|(七)

從以上格式來看,“大岔曲”《寶玉探病》是在原基本格式中第4句唱詞之前和第6句之后,加上了大段的“數(shù)字句”。因此,在唱腔基本格式自“滴滴點點”至“凄涼風(fēng)雨”中間,加上了若干緊密的、短小的起著強烈對比作用的樂句,使小岔曲形成了大規(guī)模的擴展。這樣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使每個音樂片段之間形成互相依賴的局面,給聽眾造成不穩(wěn)定的感覺,所以每段音樂之間用過門來增加穩(wěn)定感,“數(shù)字句”的曲調(diào)又可依據(jù)唱詞不斷變化,為我國民間音樂發(fā)展手法提供了美妙的范例。岔曲《寶玉探病》的詞作者不詳,流傳過程中馬增蕙演唱的版本獨具特色,其演出形式為手持八角鼓站唱,并有琴師以三弦為其伴奏。馬增慧自幼隨父親馬連登學(xué)習(xí)演唱西河大鼓,并與姐姐馬增芬一同登臺演出,在咬字發(fā)聲上打下基礎(chǔ)。1952年參加中國曲藝團,1953年調(diào)入中央廣播說唱團,經(jīng)曲藝名家白鳳鳴、白鳳巖指導(dǎo)后,演唱藝術(shù)逐步成熟,嗓音高亢、氣足聲宏、唱腔嘹亮動聽,獨具個人特色。在唱腔設(shè)計方面馬增蕙博采戲曲演唱之長,善于描摹各類人物,傳情演唱,一曲《寶玉探病》將瀟湘雨夜故事進行了完整的表達,用強烈的情感塑造出不同的音樂形象,表演風(fēng)格活潑灑脫,久經(jīng)傳唱。
二、《瀟湘夜雨》——蘇州評彈娓娓道來
蘇州評彈是敘事體和代言體相結(jié)合的表現(xiàn)形式,演唱者除了以第三人稱表述故事發(fā)展過程及進行人物介紹以外,有時還要以第一人稱擔(dān)任故事中的角色。演出形式一般分為一人演唱、雙檔演唱、三合檔演唱、多數(shù)人聯(lián)合演唱四種。評彈的唱詞和唱腔大都上下兩句為一組,唱詞上句末尾字用仄聲,下句末尾字用平聲,上句末尾字可以無韻,下句末尾字要押韻,用吳語音系的蘇州話來說唱。蘇州評彈《瀟湘夜雨》以朱雪琴和薛慧君的合作版本最為經(jīng)典,是有代表的雙檔表演。兩個人各兼一種樂器,主唱者朱雪琴(俗稱:女上手)彈奏三弦,以第三人稱身份表述為主,副唱者薛慧君(俗稱:女下手)彈奏琵琶,穿插演唱。這樣配合默契的雙檔表演,演唱者不會感覺疲乏,還會在演唱水平和舞臺表現(xiàn)力上面?zhèn)涫芎迷u。《瀟湘夜雨》唱詞內(nèi)容以描述黛玉雨夜傷感悲慘命運、燈下創(chuàng)作《秋窗風(fēng)雨夕》、寶玉冒雨探病等場面為主,唱詞篇幅很小,演唱時間適宜,通常被稱為“彈詞開篇”。《瀟湘夜雨》是純韻文體的曲本,韻轍方面采用韻散交替方式,唱詞大都為七字句式,超過七字的句子都是在七字句式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變化句式”。大篇幅使用七字句,使得內(nèi)容描寫細膩、語言押韻合轍、對仗整齊,可以更好地與唱腔、伴奏結(jié)合,且嚴格遵循了蘇州評彈上下句的平仄要求,如:
陰霾霾一座瀟湘館(仄聲),
寒凄凄幾扇碧紗窗(平聲)。
病懨懨一位多愁女(仄聲),
冷清清兩個小梅香(平聲)。
靜悄悄靜坐湘妃塌(仄聲),
軟綿綿軟靠象牙床(平聲)。
在整首唱詞的最后三句,用到了兩個上句一個下句的三句結(jié)構(gòu),這種格式是曲藝唱詞中通用的格式之一,多出的那句為“附句”,彈詞界俗稱這一格式為“鳳點頭”:
那妃子是冷嗖嗖冷風(fēng)禁不起(仄聲),
夜漫漫夜雨愁斷腸(仄聲),
從此后病汪汪魔入膏肓(平聲)。
在音樂方面,蘇州評彈《瀟湘夜雨》是一首獨曲體作品,全篇只用一種曲調(diào),以重復(fù)或變化重復(fù)的方式構(gòu)成大段的音樂織體。曲調(diào)的基本結(jié)構(gòu)與唱詞格式一致,也由上下對稱的兩句組成。朱雪琴與薛慧君的合作演唱,不僅將小說故事直觀傳達給觀眾,也充分展現(xiàn)了彈詞的吟誦體特色。高低急緩、抑揚頓挫、變化多端的曲調(diào)與詩性唱詞完美融合,眾多疊句一氣呵成,在傳播曲藝音樂的同時,也最大程度地還原了《紅樓夢》原著。
三、《秋窗風(fēng)雨夕》——梅花大鼓典雅之作
20世紀80年代,國內(nèi)外紅學(xué)研究空前熱烈。由于“雙百”方針的深入貫徹,曲藝舞臺上的《紅樓夢》題材也重新活躍繁榮。周汝昌先生在第一時間重返紅學(xué)研究的第一線,翻閱查找出當年在周恩來總理號召下欣然創(chuàng)作的鼓詞《秋窗風(fēng)雨夕》交付發(fā)表,并推薦給天津市曲藝團編曲公開演出。周汝昌先生對《秋窗風(fēng)雨夕》詩詞十分喜愛,他認為這首詩包含曹雪芹的詩情詩意,改編成鼓詞之后更可直觀地領(lǐng)略第四十五回的意境和韻味。
梅花大鼓是我國北方曲種之一,又叫“梅花調(diào)”“清口大鼓”。其伴奏樂器有三弦、四胡、琵琶、揚琴、鼓板五種,因五方人坐在舞臺上,形狀有如梅花瓣,故而得名“梅花調(diào)”,后又改稱“梅花大鼓”。這一曲種源于北京,前身是清代中葉的“清口大鼓”。這一曲種唱腔具有文雅抒情的特色,備受文人熱愛,由一些八旗子弟在不掙錢的“清客串”情況下演唱,故被稱為“清口”。至清末,經(jīng)職業(yè)梅花大鼓藝人金萬昌改革創(chuàng)新,又得到劉寶全等名家指點,通過《黛玉葬花》《黛玉思親》《寶玉探病》等紅樓曲目的演唱實踐,逐漸形成了以梅花調(diào)為基礎(chǔ)又富有新意的腔調(diào)。金萬昌以其寬厚洪亮的嗓音、深沉婉轉(zhuǎn)的行腔,自成“金派”,也成為北京“四海升平”書館梅花大鼓表演的創(chuàng)始人,其《紅樓夢》唱段更是受人追捧,被譽為“梅花大王”。梅花大鼓的藝人有男有女,男藝人的發(fā)聲與京劇生角有些類似,女藝人則是用本聲且大都使用較低的音域和寬大的音量。演唱時一邊唱一邊敲拍板和書鼓,伴奏樂器包含:三弦、四胡、琵琶、揚琴、竹笛、簫等等,如此豪華的伴奏,使得音樂織體極為厚重,令人如享聽覺盛宴。
梅花大鼓《秋窗風(fēng)雨夕》是史文秀參加天津曲藝團后,革新創(chuàng)作的一首優(yōu)秀作品。史文秀又名花小寶,20世紀40年代就已享譽京津曲壇,因其音色甜美,低音運用自如,鼓板技藝超群,演唱緩急分明、抑揚頓挫,動作身段以及表情較為文雅細膩,所以演唱內(nèi)容多是以愛情、女子、閨怨等為主題的作品。從唱詞來看,《秋窗風(fēng)雨夕》是一首中東轍的長篇鼓詞,句式規(guī)整,詞句雅馴,使用了大量精美的“垛句”“垛字”寫人達意。如:
黛玉倚雕欄、擁翠髻、鎖春山、撥熏籠、如雕如塑、如癡如夢自把珠淚兒零。
此即使用“三字垛句”描寫黛玉動作神態(tài),生動展現(xiàn)了其嬌弱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描寫黛玉燈下創(chuàng)作《秋窗風(fēng)雨夕》時亦用此類“垛句”:
摯花箋、拈象管、濡彩毫、寫心聲——這不云煙落紙珠玉傾。她道是——慘淡秋花秋葉明,耿耿秋燈秋夜清,已覺秋窗秋不盡,哪堪秋雨助秋情。助秋風(fēng)雨來何驟,驚破秋窗秋夢空,抱得秋懷哪忍睡,自向秋屏挑蠟燈。蠟燭搖搖滴紅淚,淚滴秋心雨又風(fēng),誰家秋院無風(fēng)入?何處秋窗不雨聲?聲聲淚灑窗紗濕——濕透了霞影疏欞一角紅!
周汝昌先生以《秋窗風(fēng)雨夕》的詩句為原型,以凝練詞句描繪出更具悲情、更讓人憐惜的黛玉形象。“垛字”在曲尾的使用也極為傳神:
你看他、頂竹笠、顫紅纓、脫蓑衣、落銀星、羅巾綠、綾襖紅,掐金滿繡輕紗襪,有一雙,雙飛對舞,蝴蝶落花的新鞋就在那足下登!
周汝昌先生將寶玉冒雨來到瀟湘館這一場景描摹得細致、唯美,卻又不失一份俏皮活潑,使得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一下子就映入了人們的腦海,“落銀星”仿佛將那一瞬間定格為慢鏡頭,意味深長。“垛字”的使用,在音樂上一般呈現(xiàn)字少腔多、節(jié)奏緊湊的特點,在演唱中可以烘托氣氛,與過門更好地呼應(yīng)。周汝昌先生的妙筆與史文秀磅礴大氣的唱腔相融合,共同塑造了高雅唯美的《秋窗風(fēng)雨夕》。隨著時代的飛速發(fā)展,人們對于長篇唱段的欣賞越來越少,所以《秋窗風(fēng)雨夕》的演唱機會并不多,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小巧精悍、簡潔明快的短篇唱詞。但其深厚的俗文學(xué)價值不容忽視,正是由于紅學(xué)大家與曲藝名家的創(chuàng)新與改革,才使得《紅樓夢》的曲藝唱段深受社會各界的喜愛。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zé)o論詩詞吟誦、聲樂與器樂曲改編,抑或是曲藝音樂改編都成果豐碩。王立平先生創(chuàng)作的影視歌曲《秋窗風(fēng)雨夕》一經(jīng)播出即為大眾認可,動聽的旋律與演唱者精湛的技藝完美地演繹了“秋風(fēng)煞人、悲涼惆悵”的情緒,人們在歌聲中可以直觀地感受到小說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器樂曲的改編有簫、二胡、吉他等不同樂器的版本,雖沒有語言的潤色,但每一種樂器都有其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旋律一響便可將聽眾的情緒代入其中。相較而言,曲藝音樂的改編是最為獨特的,它可以在一段曲目中包含人物對話、情節(jié)發(fā)展、背景概述、總結(jié)與升華等內(nèi)容,張弛有度,跌宕起伏。單從小說文本來講,第四十五回中寶黛愛情的溫情場面是其他回目較難見到,人們在感慨寶黛愛情悲劇的同時,也渴望聆聽這樣令人動容的曲藝唱段。總體來看,《紅樓夢》本身的音樂性和豐富性也是其能夠廣為各種音樂形式接納的根本原因。但曲藝音樂唱段的演唱時間較其他藝術(shù)形式更長、更為復(fù)雜,需要人們耐心、用心地感受,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受眾的群體與規(guī)模。從曲藝唱段傳播來看,近些年來由于國家對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視,以《紅樓夢》為主題的曲藝演出越來越多,欣賞的人群也逐漸年輕化,《紅樓夢》曲藝傳播受到了更多人的關(guān)注。《紅樓夢》曲藝唱段的內(nèi)容也更加豐富,創(chuàng)作者們在普及小說的同時,加入了不同的思想情感與人生價值觀,使同一題材不同唱段所傳達的內(nèi)容不盡相同,不同受眾的審美感覺亦趨多元,這就是《紅樓夢》曲藝作為俗文學(xué)的獨特魅力。無論哪一方面,《紅樓夢》給予曲藝音樂的滋養(yǎng)已有目共睹,它也是后人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取之不盡的靈感源泉。
①⑧ 《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北京卷》編輯會員會編著《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北京卷上》,中國ISBN中心2009年版,第2、639頁。
②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xué)史》,商務(wù)印書館2009年版,第7頁。
③ 曹雪芹《紅樓夢》,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第529頁。
④ 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全解》,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152頁。
⑤ 《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曲藝志·北京卷》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曲藝志·北京卷》,中國ISBN中心1999年版,第63頁。
⑥ 李嘯倉《曲藝談》,通俗出版社1951年版,第60—61頁。
⑦⑩[11] 胡文彬編著《紅樓夢說唱集》,春風(fēng)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320、54、55頁。
⑨ 沈彭年編著《鼓曲研究》,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0—33頁。
[12] 馮光鈺《曲藝音樂傳播》,華夏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頁。
[13]《中國曲藝志》全國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曲藝志·天津卷》,中國ISBN中心2009年版,第103頁。
[14][15][16] 天津市曲藝團編著《紅樓夢曲藝集》,春風(fēng)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57、58—59、59頁。
[17] 孟凡玉《音樂家眼中的〈紅樓夢〉》,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