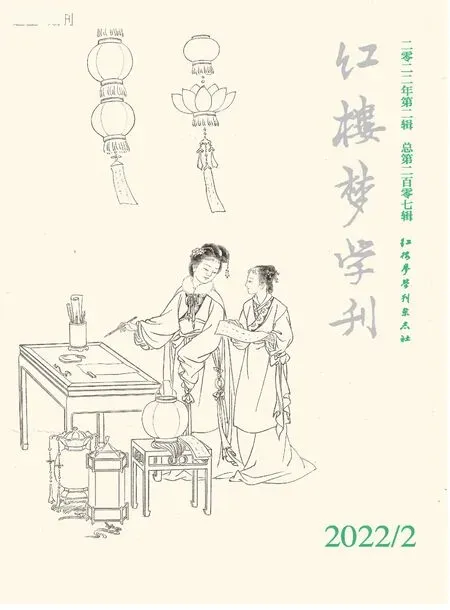《紅樓夢(mèng)》在意大利的譯介和影響研究簡(jiǎn)述*
李 晶
內(nèi)容提要: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意大利語(yǔ)譯介的專門研究不多。本文從譯介和影響兩個(gè)角度簡(jiǎn)要介紹《紅樓夢(mèng)》在意大利的翻譯研究情況。不僅關(guān)注兩個(gè)意大利語(yǔ)《紅樓夢(mèng)》譯本的譯者、人名、地名翻譯,譯本的優(yōu)缺點(diǎn),還關(guān)注《紅樓夢(mèng)》在意大利漢學(xué)界的影響,介紹并評(píng)述意大利漢學(xué)家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的研究。
《紅樓夢(mèng)》是中國(guó)四大名著之一,對(duì)于《紅樓夢(mèng)》的研究與探索,自清中期以來(lái)就已經(jīng)蓬勃發(fā)展,甚至獨(dú)立成為一門學(xué)問(wèn),形成了所謂的“紅學(xué)”。不僅中國(guó)人關(guān)注和研究《紅樓夢(mèng)》,自從18世紀(jì)末期《紅樓夢(mèng)》公開(kāi)印行之后,《紅樓夢(mèng)》很快就被翻譯成了各種語(yǔ)言文字,以翻譯版的形式流布在世界上,也引發(fā)了世界人民對(duì)這部經(jīng)典著作的關(guān)注和研究。針對(duì)這些不同語(yǔ)言、不同版本的《紅樓夢(mèng)》翻譯研究誕生了《紅樓夢(mèng)》譯學(xué)研究。“截止到2017年,《紅樓夢(mèng)》在全世界已被譯成34種語(yǔ)言,其中6種是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文字;有155個(gè)譯本,其中英語(yǔ)譯本最多,有29個(gè),日語(yǔ)譯本其次,有28個(gè)。”英譯版毫無(wú)疑問(wèn)是所有研究的中心,研究成果也最多。而本研究的對(duì)象國(guó)意大利,雖然有兩個(gè)版本的譯本以及一些零星的節(jié)譯,截至目前尚未有完整的一百二十回版翻譯。關(guān)于意大利的兩個(gè)版本的《紅樓夢(mèng)》譯本,眾多紅學(xué)研究者也都曾在論文中提及,但也都是蜻蜓點(diǎn)水,并未有系統(tǒng)和細(xì)致的分析和研究,而且有些研究者因不懂意大利語(yǔ),對(duì)于《紅樓夢(mèng)》的意文譯本也有一定的誤讀。除了翻譯《紅樓夢(mèng)》,意大利漢學(xué)界也不停地在研究《紅樓夢(mèng)》所傳遞的思想、文化價(jià)值,為海外紅學(xué)研究發(fā)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xiàn)。
一、《紅樓夢(mèng)》在意大利的翻譯版本
意大利的《紅樓夢(mèng)》譯本主要誕生在20世紀(jì)50和60年代,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有過(guò)把《紅樓夢(mèng)》某個(gè)章節(jié)當(dāng)作科幻小說(shuō)進(jìn)行節(jié)譯的版本,但是篇幅都很簡(jiǎn)短,所以本文就不再贅述。以下僅按照時(shí)間順序來(lái)簡(jiǎn)要介紹兩個(gè)主要譯本。
(一)1958年的六十回節(jié)譯本
這是意大利的第一個(gè)《紅樓夢(mèng)》譯本,但卻不是由中文直接翻譯而成,譯者克拉拉·博維羅(Clara Bovero)和卡拉·畢羅內(nèi)·里奇奧(Carla Pirrone Riccio)根據(jù)1932年弗朗茨·庫(kù)恩(Franz Kuhn)《紅樓夢(mèng)》德文譯本翻譯而來(lái)。這一版的意大利語(yǔ)譯本由都靈Einaudi出版社出版,書名為《紅樓夢(mèng)》的意大利語(yǔ)翻譯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副標(biāo)題為Romanzo Cinese del Secolo XVIII(18世紀(jì)的中國(guó)小說(shuō))。意大利漢學(xué)家馬丁·貝內(nèi)迪克特(Martin Benedikter)為該書做序,該序言的原文也曾經(jīng)發(fā)表在1959年出版的第五期《中國(guó)》(Cina)雜志上,并附上了《紅樓夢(mèng)》意大利語(yǔ)譯本的第一章。這導(dǎo)致一些不太了解意大利語(yǔ)的研究者誤認(rèn)為馬丁·貝內(nèi)迪克特也翻譯了《紅樓夢(mèng)》的第一章。其實(shí),馬丁·貝內(nèi)迪克特在節(jié)選的第一章節(jié)譯文之后非常清楚地表達(dá)了對(duì)出版社的感謝,允許他將克拉拉·博維羅和卡拉·畢羅內(nèi)·里奇奧翻譯的《紅樓夢(mèng)》第一章節(jié)的意大利語(yǔ)譯文刊登在這期雜志上。
將庫(kù)恩德文版《紅樓夢(mèng)》轉(zhuǎn)譯的兩位意大利譯者擅長(zhǎng)德語(yǔ),但卻對(duì)漢語(yǔ)和中國(guó)文化基本沒(méi)有什么了解,特別是克拉拉·博維羅一直從事的是政治領(lǐng)域的翻譯,因此,1958年誕生的《紅樓夢(mèng)》意大利語(yǔ)版譯文相對(duì)簡(jiǎn)單,而且明顯帶有“異域風(fēng)情”的翻譯特點(diǎn)。
首先是《紅樓夢(mèng)》人物名字的翻譯,譯者采用的是意譯和威妥瑪注音法混合的方式,例如:

中文名 意文譯名 中文含義寶玉 Pao-yü 威妥瑪注音“寶玉”的音譯。黛玉 Gioiazzurra 這個(gè)詞在意大利語(yǔ)原本是不存在的,是兩個(gè)詞的合成詞:gioia意為喜悅、歡樂(lè);azzurro意為藍(lán)色的。寶釵 Pao-Ch’ai 威妥瑪注音“寶釵”的音譯。迎春 Saluto di Primavera saluto意為招呼、致意;primavera意為春天。探春 Profumo di Primavera profumo意為香氣、氣息。惜春 Affanno di Primavera affanno意為嘆惜、煩惱。賈母 Ava avo意為祖先,曾祖,ava指女性的祖先。王夫人 Donna Chêng donna意為女人;Chêng是賈政的威妥瑪注音名。湘云 Nuvoletta nuvoletta是nuvola(云)一詞的縮小化形式,含有親昵和喜愛(ài)之意。
從上表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紅樓夢(mèng)》原文中那些具有豐富含義、詩(shī)意的名字在意大利語(yǔ)譯文中變得有點(diǎn)“奇怪”。曹雪芹在《紅樓夢(mèng)》中大量使用隱喻和象征的表現(xiàn)手法,人名是其中最具代表之一,比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連在一起隱喻“原應(yīng)嘆息”。在這一版的《紅樓夢(mèng)》意大利語(yǔ)翻譯中,按照以上例舉的人名翻譯形式,基本很難表達(dá)出作者的意圖。再加上中意文化本來(lái)就有很大的差異,如果不進(jìn)行必要的注解,意大利讀者對(duì)人名尚且難以接受,更不用說(shuō)去理解名字背后所隱含的意義。
其次是地名的翻譯,意大利語(yǔ)版譯文基本都采用了意譯的方式:

中文名 意文譯名 中文含義十里街 La Strada delle DieciMiglia Strada意為街道;dieci為數(shù)詞十;miglia意為英里。葫蘆廟 Il Tempio del Cetriolo Tempio意為廟宇;cetriolo意為黃瓜。怡紅院 Cortile delle Begonie(Cortile del Rosso Armonioso)Cortile意為庭院;begonie意為海棠;rosso意為紅色;armonioso意為和諧的。瀟湘館 Chiostro dei Bambu chiostro意為亭子;bambu意為竹子蘅蕪苑 La Giungla giungla意為長(zhǎng)滿各種植物、荒草的地方;也有叢林之意。綴錦閣 Chiosco Damascato chiosco意為庭、閣;damascato意為大馬士革錦緞的。秋爽齋 Chiosco del Limpido Autunno limpido意為清晰、透明;autunno意思是秋天。櫳翠庵 Gabbia dell’Alcione gabbia原指鳥(niǎo)籠,也可指類似鳥(niǎo)籠的建筑;alcione指海鷗。
我們知道,《紅樓夢(mèng)》的每一個(gè)地名大多具有特殊含義的,比如“十里街”諧音“勢(shì)利街”,“葫蘆廟”諧音“糊涂廟”。而主人公在大觀園中各個(gè)住處的名稱,也都和居住在此處的主人命運(yùn)或者性格有緊密的聯(lián)系。這些對(duì)于每一個(gè)語(yǔ)種的譯者來(lái)說(shuō)都是很難處理的問(wèn)題。兩位意大利譯者都對(duì)中國(guó)文化不甚了解,其難度更是可想而知。
跨文化翻譯研究學(xué)者王寧認(rèn)為:“翻譯行為亦應(yīng)當(dāng)被看作是一種跨文化闡釋的行為。對(duì)原文本(圖像)的知識(shí)越是豐富和全面,理解越是透徹,所能闡發(fā)出的內(nèi)容就越是豐富。反之,闡釋就會(huì)顯得蒼白無(wú)力,不僅不能準(zhǔn)確地再現(xiàn)原文的基本意義,甚至連這些基本的意義都可能把握不住而在譯文中被遺漏。”因此這一版由德語(yǔ)轉(zhuǎn)譯而來(lái)的《紅樓夢(mèng)》意文譯本,忠實(shí)于原著《紅樓夢(mèng)》的程度必然大打折扣。根據(jù)眾多學(xué)者的研究,庫(kù)恩的德文版《紅樓夢(mèng)》翻譯雖有誤譯,但也是瑕不掩瑜。在翻譯過(guò)程中庫(kù)恩采用了摘譯、編譯、闡譯、增譯等變譯方法,其譯文相對(duì)于原文必然有所增添或者減少。兩位意大利譯者克拉拉·博維羅和卡拉·畢羅內(nèi)·里奇奧既不了解中國(guó)文化,也未親見(jiàn)原文,在翻譯的過(guò)程中也只能忠實(shí)德語(yǔ)“源文”,因此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duì)《紅樓夢(mèng)》原文的忠實(shí)度。
(二)1964年的一百二十回《紅樓夢(mèng)》譯本
1964年意大利漢學(xué)家馬熹(Edoarda Masi)從中文直接翻譯了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mèng)》,該譯本在1964年由意大利UTET出版社出版,這是意大利第一個(gè)從中文直接翻譯到意大利語(yǔ)的版本。1981年、2008年該譯本再版兩次,算是《紅樓夢(mèng)》在意大利相對(duì)完整的譯本。之所以說(shuō)是相對(duì)完整,是因?yàn)樵摪婧笏氖厥且愿攀龅姆绞竭M(jìn)行翻譯的,在前八十回中也有部分章節(jié)進(jìn)行了節(jié)譯和概述,因此這一版也不能算得上是真真正正的完整版譯文。
在譯文的前言部分,馬熹首先介紹了《紅樓夢(mèng)》誕生的時(shí)代背景以及一些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文化,諸如:科舉考試、“無(wú)為”思想以及佛家、道家思想中的“空”;其次馬熹簡(jiǎn)要介紹了《紅樓夢(mèng)》作者曹雪芹的生平;最后評(píng)述了《紅樓夢(mèng)》在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以及《紅樓夢(mèng)》研究的學(xué)科——“紅學(xué)”,并簡(jiǎn)要講述了《紅樓夢(mèng)》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之間的關(guān)系,她還特別提示西方讀者不能按照西方浪漫主義小說(shuō)模式來(lái)閱讀和理解《紅樓夢(mèng)》。書中亦介紹了當(dāng)時(shí)歐洲幾種主要的《紅樓夢(mèng)》譯本以及《紅樓夢(mèng)》研究論文;書后附有中國(guó)的長(zhǎng)度、面積、體積和重量單位的注釋表,時(shí)間歷法,賈府人物關(guān)系圖,以及近400人的《紅樓夢(mèng)》人物注釋表。
馬熹1927年生于羅馬,1948年獲得法律本科學(xué)位,1956年在那不勒斯中東遠(yuǎn)東高等學(xué)院獲得漢語(yǔ)和俄語(yǔ)翻譯碩士學(xué)位,1957年她和比素(Renata Pisu)、科恰(Filippo Coccia)一同前往中國(guó),在北京大學(xué)學(xué)習(xí)中文。馬熹不僅懂漢語(yǔ),而且熟悉和了解中國(guó)文化,在這一層面上,她的《紅樓夢(mèng)》譯本能夠更好地傳遞中文原文想要表達(dá)的意義和思想。
1965年,也即馬熹翻譯的《紅樓夢(mèng)》在意大利出版一年之后,意大利漢學(xué)家藍(lán)喬蒂(Lionello Lanciotti)在當(dāng)年的第15期《中國(guó)》雜志上專門介紹了馬熹所翻譯的《紅樓夢(mèng)》,對(duì)于馬熹的翻譯充滿了贊美之詞:“她完成了一項(xiàng)偉大的翻譯巨作,這也充分展示了她作為漢學(xué)家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熱愛(ài)和激情。”
漢學(xué)家的背景以及在中國(guó)生活學(xué)習(xí)的經(jīng)歷使得馬熹在翻譯《紅樓夢(mèng)》時(shí)能夠比較準(zhǔn)確地詮釋中文文本的含義,特別是《紅樓夢(mèng)》中人名、地名、詩(shī)詞等特有的隱喻特色,馬熹都通過(guò)腳注的方式進(jìn)行了深入解讀,這能夠幫助意大利讀者更好地了解《紅樓夢(mèng)》,從而對(duì)中國(guó)古典文化有進(jìn)一步的認(rèn)識(shí)。
有一點(diǎn)值得注意的是,從章節(jié)回目翻譯上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馬熹所采用的翻譯底本應(yīng)該是《紅樓夢(mèng)》程乙本,而不是1955年已由北京文學(xué)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庚辰本。
例如:第三回回目
庚辰本:賈雨村夤緣復(fù)舊職 林黛玉拋父進(jìn)京都
程乙本:托內(nèi)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馬熹譯文:Con l’aiuto di suo cognato,Ju-hai fa reintegrare il precettore nell’ufficio.La madre Chia accoglie per compassione la nipotina rimasta orfana.
Con l’aiuto表示在……的幫助下,cognato是意大利語(yǔ)中指代配偶兄弟的親屬名詞,我們都知道賈政是賈敏的哥哥,也就是林如海的妻兄,所以這里的cognato指賈政;fa reintegrare是一個(gè)使動(dòng)用法,表示讓某人做某事;percettore意為私人教師,我們都知道賈雨村是林如海給黛玉找的老師,所以這里指代賈雨村;uffico指辦公室;所以該回目的上半句意思是:在賈敏哥哥賈政的幫助下,林如海讓賈雨村官?gòu)?fù)原職。該回目下半句中l(wèi)amadre Chia指賈母;accoglie表示迎接、歡迎;per compassione表示出于疼惜、憐惜;nipotina是意大利語(yǔ)中指孫女或外孫女的親屬名詞nipote的縮小化形式,縮小化通常含有親昵和喜愛(ài)的意思;orfana指失去父母一方或雙方的孩子;所以整句的意思是:賈母出于疼惜之情,接回了失去了母親的外孫女。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馬熹完全是按照程乙本的回目來(lái)進(jìn)行翻譯的。
又如第八回回目:
庚辰本:比通靈金鶯微露意 探寶釵黛玉半寒酸
程乙本:賈寶玉奇緣識(shí)金鎖 薛寶釵巧合識(shí)通靈
馬熹譯文:Per un singolare caso Chia Pao-yüconosce il fermaglio d’oro.Hsüeh Pao-ch’ai per caso viene a conoscere ilmagico potere.
Per un singolare caso指偶然的一次機(jī)會(huì);conosce表示認(rèn)識(shí)、了解、知道;fermaglio意大利語(yǔ)指用來(lái)連接和固定的物體,嚴(yán)格來(lái)講不是回目中所提到的鎖這個(gè)詞,但是由于在意大利語(yǔ)中并沒(méi)有刻意用來(lái)指代中國(guó)人所佩戴的這種金鎖的名詞,馬熹在這里采用了翻譯中的歸化法,用fermaglio指代鎖這個(gè)詞;per caso也是偶然之意;viene a conoscere也表示認(rèn)識(shí)和了解;ilmagico potere字面意思是“神奇的力量”,指通靈寶玉的神力。整個(gè)回目的意思就是:偶然的機(jī)會(huì)寶玉認(rèn)識(shí)了寶釵的金鎖,寶釵也是無(wú)意間了解到了通靈寶玉的神力。綜上,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馬熹翻譯《紅樓夢(mèng)》的底本應(yīng)該是程乙本。
但是馬熹所翻譯的《紅樓夢(mèng)》也有一個(gè)很大的缺憾,那就是關(guān)于人名和地名的翻譯,馬熹全部采用了音譯加腳注注釋的方式。雖然1958年中國(guó)開(kāi)始推廣漢語(yǔ)拼音,但她所采用的注音方式仍然是威妥瑪式注音法,這一注音法具有時(shí)代特征,可以說(shuō)20世紀(jì)的《紅樓夢(mèng)》外語(yǔ)譯本基本都采用了這樣的注音方法。但是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對(duì)于當(dāng)代學(xué)習(xí)漢語(yǔ)或者對(duì)于中國(guó)文化感興趣的意大利人來(lái)說(shuō),他們所學(xué)習(xí)的都是漢語(yǔ)拼音,因此威妥瑪式注音法所翻譯的人名和地名對(duì)閱讀《紅樓夢(mèng)》意大利語(yǔ)譯本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在意大利亞馬遜平臺(tái)上,為數(shù)不多的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譯本的評(píng)價(jià)留言都是關(guān)于注音的問(wèn)題,當(dāng)代讀者們都反映人物名威妥瑪式注音法給他們閱讀《紅樓夢(mèng)》造成了巨大的困擾。這不得不說(shuō)是馬熹《紅樓夢(mèng)》譯本的一大缺憾。
鑒于本文的主題并不是《紅樓夢(mèng)》意大利語(yǔ)兩個(gè)譯本的翻譯策略研究,所以在這里我們就不再展開(kāi)評(píng)述了。
二、意大利學(xué)界對(duì)《紅樓夢(mèng)》的研究
意大利學(xué)界,主要是意大利漢學(xué)界為《紅樓夢(mèng)》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xiàn)。他們不僅研究《紅樓夢(mèng)》所傳遞的思想、文化價(jià)值,并將《紅樓夢(mèng)》放在整個(gè)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體系中研究中國(guó)古代文論。其中的代表人為馬熹、坷拉蒂尼(Piero Corradini)、史華羅(Paolo Santangelo)和柏雷麗(Beatrice Borelli)。選取這四位意大利漢學(xué)家的原因主要在于:馬熹作為《紅樓夢(mèng)》1964年全譯本的譯者,對(duì)于《紅樓夢(mèng)》在意大利的研究與傳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坷拉蒂尼在20世紀(jì)70年代對(duì)于《紅樓夢(mèng)》研究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代表了從政治層面向文化層面的轉(zhuǎn)向;史華羅20世紀(jì)80年代將《紅樓夢(mèng)》研究融入整個(gè)明清小說(shuō)研究,開(kāi)啟了對(duì)于中國(guó)文學(xué)研究由點(diǎn)及面的新階段;柏雷麗雖不如前三位漢學(xué)家富有盛名,但也是進(jìn)入21世紀(jì)之后為數(shù)不多的《紅樓夢(mèng)》研究者。
(一)馬熹:《有關(guān)〈紅樓夢(mèng)〉新的闡釋》
馬熹翻譯的《紅樓夢(mèng)》于1964年出版,但一年之前她就發(fā)表了與《紅樓夢(mèng)》相關(guān)的論文:《有關(guān)〈紅樓夢(mèng)〉新的闡釋》,該文章刊登在1963年第7期的《中國(guó)》雜志上。這篇論文誕生的背景即“1954年,一場(chǎng)由毛澤東親自領(lǐng)導(dǎo)的大批判運(yùn)動(dòng)掀起了,批判的對(duì)象是俞平伯”。由此,1954-1955年間,中國(guó)大陸開(kāi)始了轟轟烈烈的《紅樓夢(mèng)》大討論。馬熹首先簡(jiǎn)要介紹了此次大討論針對(duì)的主要問(wèn)題: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以及以胡適為代表的封建資產(chǎn)階級(jí)思想的討論。“最初看來(lái),這次的討論大家一致批判俞平伯的封建資產(chǎn)階級(jí)思想,俞平伯作為當(dāng)代最主要的《紅樓夢(mèng)》研究者,在這次討論中沒(méi)有一個(gè)支持者,甚至連他自己都不是。”這是因?yàn)橛崞讲缙诘摹都t樓夢(mèng)》研究主要采納了胡適主張的自傳說(shuō),但隨著學(xué)習(xí)和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理論之后,他主張采用現(xiàn)實(shí)主義理論去重新解讀和詮釋《紅樓夢(mèng)》,前后有些矛盾的說(shuō)辭和研究方法使得俞平伯“陷入了所謂的‘模棱兩可’之中”。馬熹還簡(jiǎn)要介紹了俞平伯早期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版本以及對(duì)后四十回作者高鶚的看法,在俞平伯看來(lái)高鶚的續(xù)書并不盡合曹雪芹的原意。接下來(lái)馬熹列舉了俞平伯從1923年開(kāi)始發(fā)表的《紅樓夢(mèng)》研究成果,著重介紹了《〈紅樓夢(mèng)〉簡(jiǎn)論》的內(nèi)容,并高度贊揚(yáng)了俞平伯和胡適在《紅樓夢(mèng)》研究領(lǐng)域所作出的貢獻(xiàn):“他們從哲學(xué)的、歷史的、傳記式的角度給了我們一把解讀《紅樓夢(mèng)》的鑰匙。”緊接著文章談到了李希凡、藍(lán)翎對(duì)俞平伯的批判,在馬熹看來(lái)“完全是將《紅樓夢(mèng)》上升到現(xiàn)實(shí)主義、國(guó)家和人民的層面,對(duì)俞平伯毀滅式的批判”。當(dāng)然馬熹也認(rèn)識(shí)到了,這樣的批判是誕生在特殊歷史時(shí)期和背景之下的,她也發(fā)現(xiàn)所謂對(duì)于俞平伯的批判早已超越了俞平伯和其研究作品本身。
另一位意大利漢學(xué)家李蕊(Laviana Benedetti)在其《意大利漢學(xué)界的中國(guó)文論研究》一文中對(duì)馬熹的這篇文章評(píng)論到:“馬熹的文章并沒(méi)有給意大利讀者解釋‘新紅學(xué)派’如何為‘新’的原因,沒(méi)有談到‘五四運(yùn)動(dòng)’以后的知識(shí)分子批判所謂‘舊紅學(xué)派’的理由。”但在我們看來(lái)馬熹這篇文章的主旨并不是要介紹何為“新”和“舊”的紅學(xué)派,而是主要闡述俞平伯《紅樓夢(mèng)》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和思想以及在特殊時(shí)代背景下一批新人對(duì)于以胡適、俞平伯為代表的“紅學(xué)”研究者的否定和批判。通過(guò)整篇文章,我們也可以清楚發(fā)現(xiàn),馬熹對(duì)于俞平伯的研究觀點(diǎn)是贊同的,甚至影響了她對(duì)于《紅樓夢(mèng)》的翻譯創(chuàng)作。在1964年出版的《紅樓夢(mèng)》意大利語(yǔ)譯本前言中,馬熹清楚地寫到:“根據(jù)脂硯齋的書評(píng),可以發(fā)現(xiàn)《紅樓夢(mèng)》所描述的故事和作者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緊密相連,帶有很明顯的自傳風(fēng)格。”
馬熹的功績(jī)不僅在于翻譯了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mèng)》,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的《紅樓夢(mèng)》研究心得觀點(diǎn),并將同時(shí)期中國(guó)的《紅樓夢(mèng)》研究思想傳遞到了意大利。
(二)坷拉蒂尼:《〈紅樓夢(mèng)〉和西方的關(guān)系》
1976年,另一位意大利漢學(xué)家坷拉蒂尼在當(dāng)年的《中國(guó)》雜志第13期發(fā)表題為《〈紅樓夢(mèng)〉和西方的關(guān)系》論文。文章開(kāi)篇就簡(jiǎn)要回顧了馬熹在《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新的闡釋》一文中提到的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運(yùn)動(dòng),并指出時(shí)隔二十年之后,1974-1975年之間,中國(guó)又掀起了新一輪的評(píng)紅熱潮。對(duì)于這一運(yùn)動(dòng)做了簡(jiǎn)要述評(píng)之后,坷拉蒂尼轉(zhuǎn)入另外一個(gè)主題,即在《紅樓夢(mèng)》文本中出現(xiàn)的與西方世界、西方社會(huì)相關(guān)的物品和事件。
此領(lǐng)域的學(xué)者吳世昌專門就《紅樓夢(mèng)》中提到的西方世界物品列了一個(gè)詳細(xì)清單:擺鐘、懷表、繪畫、紡織品、藥品、剪刀,甚至還有一個(gè)畫著金發(fā)裸女的鼻煙壺。坷拉蒂尼認(rèn)為這些恰恰證明了西方物品在當(dāng)時(shí)被看作是一種奢侈品,廣泛地在貴族家庭中流行。有趣的是,與此同時(shí)的西方社會(huì)也流行所謂“中國(guó)風(fēng)”(chinoiserie)的物品和家居裝飾風(fēng)格。
坷拉蒂尼詳細(xì)介紹了《紅樓夢(mèng)》第五十二回的內(nèi)容,在這一回中,來(lái)京城完婚的薛寶琴暫住在賈府,大觀園的姑娘們邀請(qǐng)她參加詩(shī)社,她講述了自己從小跟隨父親在海外經(jīng)商游歷的經(jīng)歷:“我八歲時(shí)節(jié),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shuí)知有個(gè)真真國(guó)的女孩子,才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發(fā),打著聯(lián)垂,滿頭帶的都是珊瑚、貓兒眼、祖母綠這些寶石……有人說(shuō)他通中國(guó)的詩(shī)書,會(huì)講五經(jīng),能作詩(shī)填詞……”坷拉蒂尼翻譯了寶琴所說(shuō)那位真真國(guó)的姑娘所做的詩(shī),并在注釋里解釋,關(guān)于這首詩(shī)詞,弗朗茨·庫(kù)恩的《紅樓夢(mèng)》翻譯版本中和原文有些出入,而馬熹所翻譯的意大利語(yǔ)版中對(duì)這一章節(jié)內(nèi)容采用了概述的方式,也并未提及這首詩(shī)詞。在坷拉蒂尼看來(lái),寶琴是個(gè)非常有趣的姑娘,而更為難得的是寶琴的父親在那個(gè)時(shí)代竟然可以不顧封建禮教的要求,帶著女兒去海外經(jīng)商游歷,他的行為和賈敬、賈政形成了鮮明的對(duì)比。但是寶琴的父親也有其統(tǒng)治階級(jí)在那個(gè)時(shí)代的局限性,雖然帶著女兒走南闖北,最終還是要將女兒送往京城,依照媒妁之約、父母之命完成自己的婚事。文章最后,坷拉蒂尼還提到賈母賞了寶玉一件來(lái)自俄羅斯國(guó)的雀金呢外套,這也是那個(gè)時(shí)代西方物品在中國(guó)統(tǒng)治階級(jí)中流行的明證之一。
如果說(shuō)馬熹對(duì)《紅樓夢(mèng)》研究的關(guān)注點(diǎn)在于特殊政治背景下中國(guó)不同學(xué)派對(duì)《紅樓夢(mèng)》的理解和詮釋,進(jìn)入70年代,以坷拉蒂尼為代表的意大利漢學(xué)界對(duì)于《紅樓夢(mèng)》的研究有了新的動(dòng)向,即思想文化研究的轉(zhuǎn)向。
(三)史華羅:“情感論”
史華羅在意大利乃至國(guó)際漢學(xué)界都享有盛名。他提出的“情感論”在學(xué)界得到廣泛的認(rèn)同,“因?yàn)樗难芯克褂玫姆椒ㄒ呀?jīng)超出一般的純文學(xué)和史學(xué)的領(lǐng)域,將文本材料的分析與心理學(xué)、文學(xué)批評(píng)學(xué)、歷史學(xué)等方法結(jié)合在一起,采用多學(xué)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對(duì)中國(guó)文明某一歷史時(shí)期的文學(xué)和非文學(xué)性資料進(jìn)行綜合研究,提供了多焦點(diǎn)跨科際解讀和分析的路徑”。
史華羅對(duì)于《紅樓夢(mèng)》的研究和之前的馬熹、坷拉蒂尼不同,他不只針對(duì)《紅樓夢(mèng)》本身,而是把《紅樓夢(mèng)》放在明清小說(shuō)乃至整個(gè)中國(guó)古典文化的大背景之下來(lái)研究,以“情感”為關(guān)鍵詞,探討在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作品中所體現(xiàn)的“妒”“激情”“欲望”“愛(ài)”“誘”等與“情感”緊密聯(lián)系的主題。
在《中國(guó)之愛(ài)情:對(duì)中華帝國(guó)數(shù)百年來(lái)文學(xué)作品中愛(ài)情問(wèn)題的研究》一書中,史華羅詳細(xì)地分析了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的“愛(ài)”與“情”。他認(rèn)為“情”在《紅樓夢(mèng)》中被頻繁使用:“有時(shí)作為單字,有時(shí)組合成其他詞語(yǔ)。當(dāng)作單字使用的時(shí)候,它經(jīng)常超越感情和親情的含義,具有愛(ài)情的意思,有時(shí)還有情愛(ài)的意思;在不同情況下它的詞義差別很大;人們可以用它表示一般的同情、愛(ài)情和男女之間的相互吸引,也可以用它表示好色,甚至表示‘淫’;有時(shí)它主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愛(ài)情的瘋狂,與‘癡’的含義很近,有時(shí)它有強(qiáng)調(diào)的是感情的幻覺(jué)和虛無(wú),與‘空’的含義相似。”情是《紅樓夢(mèng)》的一個(gè)主要線索,甚至該書也曾名為《情僧錄》,在書中秦可卿、秦鐘都諧音“情”,青埂峰也指“情根峰”等等。
在介紹不同愛(ài)情的時(shí)候,史華羅提到了《紅樓夢(mèng)》中所講的“意淫”,并專門分析和介紹了寶玉的“崇高之淫”。“意淫”一詞來(lái)源于寶玉神游太虛幻境時(shí)警幻仙姑對(duì)寶玉的訓(xùn)誡,對(duì)于這個(gè)詞大家基本都持負(fù)面的態(tài)度,“甚至對(duì)‘意淫’的譴責(zé)更加嚴(yán)厲……在《紅樓夢(mèng)》中,‘意淫’與男主人公的形象結(jié)合在一起,具有了新的含義:盡管它仍然表現(xiàn)為‘過(guò)分的情欲’,但與庸俗的淫蕩已毫無(wú)關(guān)系,而只是賈寶玉等人物的情感展現(xiàn)”。
如果說(shuō)“愛(ài)”有低俗的肉欲肌膚之愛(ài),也有上升至精神層面崇高的“愛(ài)”,那么,后者在《紅樓夢(mèng)》中體現(xiàn)為黛玉對(duì)寶玉的愛(ài)。史華羅評(píng)價(jià)這是一種“柏拉圖”主義的愛(ài)情。《紅樓夢(mèng)》是一部青春小說(shuō),是一部女性小說(shuō),史華羅認(rèn)為在這部小說(shuō)中“女性具有純潔的美。因此,盡管對(duì)女性身體美的描寫依然存在,但人們經(jīng)常超越它,通過(guò)間接的影射、傳統(tǒng)的俗套、神話中的人物形象和隱喻等手段,達(dá)到對(duì)女性描寫更加精細(xì)的目的,從而也使描寫更抽象,更具有詩(shī)意”。
最后史華羅評(píng)價(jià)《紅樓夢(mèng)》“開(kāi)創(chuàng)了一種新的愛(ài)情文學(xué)的表現(xiàn)形式。這部小說(shuō)中的人物主要是婦女和青年,他們?cè)趥鹘y(tǒng)社會(huì)中扮演的是次要角色;由于在美學(xué)上的成功,作品不僅引起了人們與書中主人公感情上的共鳴,而且還創(chuàng)造了一種表現(xiàn)感情的精美的新語(yǔ)言。正是由于此類文學(xué)方面的貢獻(xiàn),經(jīng)過(guò)數(shù)世紀(jì)的發(fā)展,愛(ài)的情感也逐步在中國(guó)豐富起來(lái)”。
(四)柏雷麗:《〈紅樓夢(mèng)〉中的戲曲與戲曲演員》
2019年漢學(xué)家柏雷麗以《紅樓夢(mèng)》中的戲曲以及賈家的十二個(gè)小戲子為研究對(duì)象,探討她們?cè)凇都t樓夢(mèng)》中的象征意義,以及她們所代表社會(huì)底層人物在《紅樓夢(mèng)》中體現(xiàn)出的反抗思想與意識(shí)。
柏雷麗首先介紹戲曲在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是貴族階級(jí)的娛樂(lè)方式:戲曲演員在舞臺(tái)上精美的扮相、精致的服裝及其身段、唱腔都使觀眾沉迷和陶醉。但是戲曲演員一旦走下舞臺(tái),便容易生活在世人的偏見(jiàn)里,甚至于被看作是一種不入流的人。同樣的矛盾情形也反映在大觀園的生活里,為元妃省親而買的十二個(gè)小戲子在舞臺(tái)上的表演深受老爺夫人小姐的贊賞,賈府逢年過(guò)節(jié)也少不了要唱戲,戲曲受到眾人的追捧,但是這些唱戲的小姑娘在生活中卻過(guò)得甚至不如賈府的仆人。在《紅樓夢(mèng)》第三十六回中,齡官哭訴自己的命運(yùn)就像籠中鳥(niǎo),是賈府貴族取樂(lè)的工具而已。第五十八回,因?yàn)閷m里的老太妃薨了,賈府家的戲班也被遣散了,十二個(gè)小姑娘被分配到大觀園做丫鬟,就此引發(fā)了一系列的沖突:芳官、齡官、蕊官、葵官、豆官、藕官和趙姨娘的打斗將這一沖突推向了高潮,柏雷麗認(rèn)為這一幕也充分體現(xiàn)了“這些唱戲的姑娘們雖然處在社會(huì)階級(jí)的底層,但是卻無(wú)所畏懼,勇于反抗的精神”。
結(jié)語(yǔ)
《紅樓夢(mèng)》在中國(guó)文學(xué)史,乃至世界文學(xué)史上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國(guó)內(nèi)紅學(xué)研究《紅樓夢(mèng)》的作者、版本、思想文化性,海外紅學(xué)則注重《紅樓夢(mèng)》的翻譯以及跨文化比較研究。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的翻譯研究衍生了紅樓譯學(xué)。研究者針對(duì)不同國(guó)家、不同語(yǔ)種的《紅樓夢(mèng)》進(jìn)行研究,分析其翻譯策略以及作品所要表達(dá)的思想文化。英語(yǔ)譯介研究毫無(wú)疑問(wèn)是該領(lǐng)域的集大成者,但近年來(lái)小語(yǔ)種、非通用語(yǔ)種的《紅樓夢(mèng)》譯介研究也越來(lái)越多。
意大利語(yǔ)作為非通用語(yǔ)種之一,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譯介的專門研究還不多,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的意大利語(yǔ)譯本介紹雖有,但也比較簡(jiǎn)短,不同文章之間也是互相引用,其實(shí)并沒(méi)有太多新的內(nèi)容。本文較詳細(xì)地介紹了意大利的兩個(gè)《紅樓夢(mèng)》譯本的譯者、人名、地名翻譯,簡(jiǎn)要評(píng)述了兩個(gè)翻譯版本的優(yōu)缺點(diǎn)。除了對(duì)翻譯版本的介紹,本文還梳理了意大利漢學(xué)家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的研究,選取了筆者目前所能查考到的文獻(xiàn)資料中意大利漢學(xué)界四位漢學(xué)家為代表,評(píng)述了他們關(guān)于《紅樓夢(mèng)》的研究。我們發(fā)現(xiàn)意大利漢學(xué)家對(duì)于《紅樓夢(mèng)》的研究具有時(shí)代性,而且具有宏觀性。
“與其他中國(guó)古典小說(shuō)相比,《紅樓夢(mèng)》最為豐富地包含著中國(guó)文化的精髓,不管是物質(zhì)形態(tài)、制度形態(tài)的文化,還是精神形態(tài)的文化,《紅樓夢(mèng)》都當(dāng)?shù)闷稹袊?guó)文化的百科全書’這一稱號(hào)。”但也正是因此,文化差異成為跨文化翻譯最大的障礙。而每一個(gè)翻譯者的翻譯對(duì)于原文來(lái)說(shuō)都是一個(gè)新的創(chuàng)作,是其對(duì)原文理解的新闡釋,在這一意義上,《紅樓夢(mèng)》意大利語(yǔ)譯本如何處理由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難題,將是我們一下步研究的主要目標(biāo)。
① 歐麗娟《大觀紅樓1:歐麗娟講紅樓夢(mèng)》,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版,第i頁(yè)。
② 邱華棟《〈紅樓夢(mèng)〉的翻譯本》,《青年作家》2020年第2期。
③ 王寧《翻譯與跨文化闡釋》,《中國(guó)翻譯》2014年第2期。
④ Lanciotti Lionello.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 by Ts’ao Hsuehch’in and Edoarda Masi.Cina 1965(15).
⑤⑦⑨⑩ Masi Edoarda Nuove Interpretazioni dello“Hung Lou Meng”.“Cina”1963(7).
⑥⑧ 陳維昭《紅學(xué)通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7頁(yè)。
[11][15] 李蕊《意大利漢學(xué)界的中國(guó)文論研究》,《文學(xué)理論前沿》2017年第1期。
[12] Ts’ao Hsueh-ch’.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A cura di Edoarda Masi.BUR2018.p.9.
[13] Corradini Piero.I contatti con l’occidentene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Cina.1976(13).
[14] 曹雪芹著,無(wú)名氏續(xù)《紅樓夢(mèng)》,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頁(yè)。
[16][17][18][19] 史華羅《中國(guó)之愛(ài)情:對(duì)中華帝國(guó)數(shù)百年來(lái)文學(xué)作品中愛(ài)情問(wèn)題的研究》,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8、180、248、279頁(yè)。
[20] Borelli Beatrice Teatro,attori e subalternitàne 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Antropologia e Teatro:2019(10).
[21] 陳維昭《紅學(xué)通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