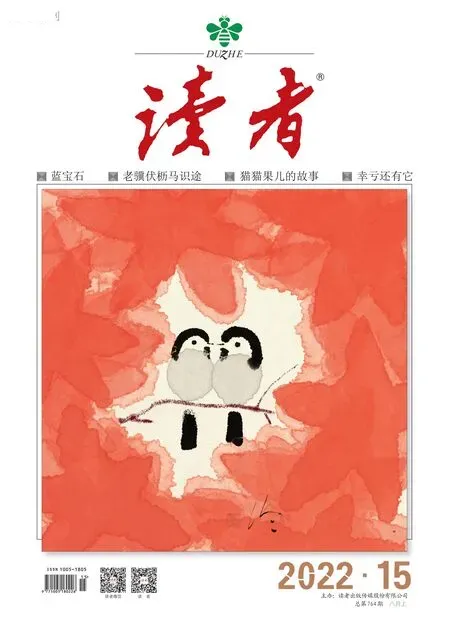粗瓷碗
☉呂 峰
碗是盛放食品的器具。吃飯時我們經常用碗,可是,很少有人留意到它們。其實,碗里大有乾坤,它可盛歲月,可盛歷史,可盛生活。碗里有情、有世界。我家廚柜里有四個外形粗獷的粗瓷碗,是當年爺爺因為家里添丁而購置的。如今它們盛著滿滿的光陰,無語也無聲,固守著家的溫度。
粗瓷碗是那種最普通的白瓷碗,碗邊有兩圈藍色的釉紋,口大肚淺,一副大腹便便的樣子。自從我有記憶開始,飯桌上就有它們的身影。每到吃飯時,我就喜歡幫忙擺放碗筷,一邊擺著,一邊念叨著:“這是爺爺的,這是奶奶的,這是我的……”眼前的碗,對應著一個個正急著往家走的親人。有時,遇到我喜歡吃的東西,奶奶會捏起一塊,放進我的嘴里,母親則佯裝慍怒,瞪我一眼,那種感覺溫暖、祥和。
家里有一條規矩,飯做好后,第一碗要盛給爺爺。奶奶給爺爺盛飯時總是說:“你爺爺是家里的大勞力,家里的活兒全指望他干呢,飯做好啊就得先給他吃。”奶奶去世時,面對鬼子的刺刀也面不改色,號稱“鐵打漢子”的爺爺痛哭流涕,一個勁兒地用手拍打著奶奶的棺木念叨:“你走了,誰給我盛第一碗飯啊!”那副悲慟欲絕的神情,讓前來吊唁的人無不動容。
粗瓷碗也見證了父母親幾十年的相濡以沫。他們之間沒有浪漫的事,有的只是每日三餐、添飯夾菜,雖樸實平淡,卻無限溫暖。每天早晨,母親會雷打不動地給父親沖雞蛋茶。在粗瓷碗里,打上兩枚雞蛋,滴上幾滴香油,再加一勺白砂糖,用筷子攪和均勻,將剛燒開的水慢慢地沖到碗里,邊沖邊用筷子攪動,那碗里就慢慢形成了一梭又一梭的雞蛋穗,略微沉淀后,上面變成稀清的蛋湯,下面是稠狀的蛋花。這是母親最熟練也最拿手的活兒,原因很簡單:父親最好這一口!

當時,我對母親的這種做法很不以為然。后來看到作家張曉風寫道:“看見有人當街親熱,竟也熟視無睹,但每看到一對人手牽手提著一把青菜、一條魚從菜場走出來,一顆心就忍不住惻惻地痛了起來,一蔬一飯里的天長地久原是如此味永難言啊!”原來,碗可盛愛啊!所謂的白頭到老的愛情,所謂的天長地久,就蘊藏在尋常的一日三餐中,蘊藏在精心盛好的一碗飯里。那一刻,我才明白,粗瓷碗中的愛情,因為有日日的惦念,才有天長地久的豐盈。
粗瓷碗里除了有愛情,還有滿滿的親情。有一次,我生病了,一直高燒不退。母親覺得服用湯劑比打針副作用小,就開了一大包中草藥回家煎。她守在廚房的煤爐前,嚴格按照老中醫的要求去煎藥,先用大火煮沸,然后用文火細細地熬。隨著母親的辛勞,那帶點兒苦澀味兒的藥香彌漫了整個房間。
近兩個小時的工夫,那碗黑褐色泛著泡沫的湯藥被端到了床前,我只呷了一口,便受不了那份沁入心脾的苦,不由得嘔吐起來。母親慌忙為我捶背,清掃穢物,焦急萬分。望著她忙碌而辛勞的身影,我內疚極了,真白費了她煎中草藥的苦心。
粗瓷碗原本有十個,后來只剩下了四個。再后來這四個碗也很少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又一套精美的細瓷碗。有一次,朋友來家里做客,碰巧前段時間碗被女兒打碎了幾個,我一直沒去購買。這時,我突然想起了廚柜里的粗瓷碗,便把它們拿出來用以解燃眉之急。端著那早已退出了生活圈子的粗瓷碗,朋友頓時樂了。那天晚上我和朋友之間的話題沒有離開過粗瓷碗。再后來,朋友去了日本留學,每次回國,捎來的禮物都是圖案各異的碗碟。看著那飽含心意的禮物,我知道碗里還藏著友情。
粗瓷碗里有美好的回憶,那是逝去的懵懂歲月,那是千金不換的溫情與美好。因為它,家的概念更加清晰,家也在無情的光陰里側影翩躚。每逢節假日,我便拖家帶口去田間鄉野,過幾天農家生活,用粗瓷大碗吃飯、喝粥。夜晚坐在農家小院里,天上一輪明月,碗中似乎有月光在蕩漾,讓人心醉。
人生很復雜,又何其簡單,簡單到只是由兩個動作組成的一條線。一個動作是捧起碗,另一個動作是放下碗。在捧起與放下的過程中,生命一點一點變得絢爛,又一點一點走向枯萎、終結,直到那個碗最后一次被放下,永不被捧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