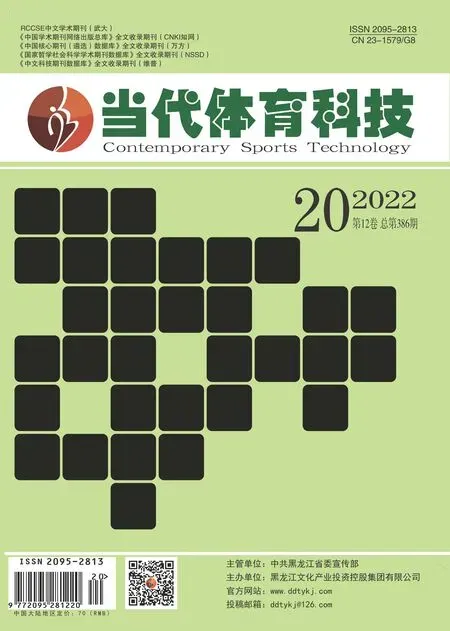我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現狀、熱點和趨勢
——基于CiteSpace(2000—2020)知識圖譜分析
潘嘉峪
(廣州體育學院 廣東廣州 510500)
20世紀90年代,歐美國家確立了體育人類學獨立的學科地位,傳統的體育人類學被視為是對原始的體育活動或體育文化以及異體育文化的研究。直到21世紀,后現代思潮對工業社會的反思日益深刻,人們開始重視身體本身長期受到忽視的事實,體質與文化的融合研究,使體育人類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逐漸豐富。
中國體育人類學學科的建構過程是東西方文化接觸、傳播及變遷的過程。一方面,受早期文化人類學的影響,中國的民族體育研究者開展了大量田野調查,積累了許多研究素材和資料。另一方面,日本學者寒川恒夫一行于1990年前往上海體育學院講學,并在其學報上刊發了《體育人類學》一文。與此同時,胡小明教授在與日本學者交流中發現,中國已有多年積累的民族傳統體育學研究,在國外屬于體育人類學的研究范疇。體育人類學由此開始進入我國體育界學者的研究視野。
21世紀以來,中國的體育人類學逐漸拓引、吸收人類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結合本土化實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面對新的社會問題和現象,體育人類學研究者能夠運用人類學的知識對其進行專業性解讀,對體育領域的相關問題進行綜合性審視,顯示了體育界學者對世界變遷和時代更迭的洞察力和反思力。
1 研究設計
21 世紀是體育人類學學科構建和探索的重要時期,該文通過對20年來在體育類核心期刊中發表的有關體育人類學的論文進行可視化分析,以期得到體育人類學研究領域的統計數據和共現圖譜,分析其研究現狀、熱點和前沿主題等內容。
1.1 數據來源與分析
以“主題=體育人類學或含體育+人類學”為檢索條件,檢索時間限定為2000 年1 月1 日至2020 年6 月30日,期刊范圍為11 種體育類核心期刊(北京體育大學學報+成都體育學院學報+上海體育學院學報+首都體育學院學報+體育科學+體育學刊+體育與科學+天津體育學院學報+武漢體育學院學報+西安體育學院學報+中國體育科技),經過檢索并篩選后,得到141篇有效文獻(見圖1)。

圖1 文獻出版來源分布圖(2000年—2020年)
1.2 研究方法與工具
利用CNKI 的計量可視化分析功能對所得的141條文獻數據進行初步的年度、文獻主題類別分析,形成體育人類學研究領域的初步認知。
借助CiteSpace 分析工具,以141 條數據源為研究對象,分別選擇Author(作者)、Institution(機構)、Keyword(關鍵詞)等為節點類型進行圖譜分析,對其研究熱點、知識基礎和前沿主題進行分析。
2 結果分析
2.1 年段分析
從圖2中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來,我國體育人類學領域的發文數量呈現出突變式的發展特征。

圖2 我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發文數量年度分布(2000年—2020年)
2009年7月,第16屆IUAES大會在中國昆明召開,其中“中國體育人類學的發展”和“體育人類學的國際視野”兩專題由我國體育界學者承辦,這標志著中國體育人類學研究開始進入世界最高學術殿堂,這也是2009年—2010年發文數量上急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2010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的指導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對運動員文化教育和運動員安保工作指導的通知》。對核心期刊中2011年所發布的所有文獻進行了文獻主題類別分析,論文主題主要與競技體育及運動員、學校體育及體育產業相關賽事等相關(見圖3)。由于政策導向作用,研究熱點發生變化,2011年體育人類學主題文章數量下降。

圖3 2011年CSSCI發文主題統計
2010 年,華南師范大學的“體育人類學”課程被評為廣東省研究生示范課程標志著“體育人類學”在高等教育課程中開始占有一席之地。上海體育學院也通過了以“體育人類學”為內容的多篇博士論文答辯,因此2012年以后,學界對體育人類學領域的關注逐漸增加。
2.2 作者分析
對作者合作網絡的分析,如圖4 所示。在共現頻次上,論文數最多的研究者是胡小明,發文量達24篇,其次是譚廣鑫和楊海晨,排名前4位、前16位的作者發文量分別占所有作者發文量的39.00%和82.27%。可見,我國體育人類學研究領域作者發文集中度比較高。
在研究者合作網絡共現圖(見圖4)中,字符最大的胡小明(1952 年—2014 年)是中國體育人類學的探路者,于1999年編寫了國內首部《體育人類學》著作,對中國體育人類學的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胡小明認為,我國的體育人類學應當結合體育學自身既涉及自然科學,又涉及人文社科的特性,成為二者之間的橋梁。其帶領的研究團隊選取了東巴文、古彝文及巴蜀圖文等文字中的動詞與原始宗教、祭祀中的身體動作相聯系進行思考,展開了一系列的雙向實證研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育人類學研究路徑。

圖4 我國體育人類學研究者合作網絡圖譜(2000年—2020年)
目前,相對活躍的研究者分別是楊海晨、譚廣鑫、倪依克、楊世如等人。
2.3 研究熱點分析
突現性較高的主題詞是某個時期內頻次變化率高的詞,能夠挖掘研究熱點,反映研究趨勢。圖5中列出了2000 年—2020 年我國體育人類學領域研究主題詞突現的術語TOP6。在21世紀初,體育人類學領域的研究熱點主題仍是偏向傳統意義的體育研究,并未細分。此時的體育人類學主要以嫁接西方人類學理論來關照中國體育實踐的方式進行。

圖5 體育人類學研究熱點突現詞Top6分布圖(2000年—2022年)
在2008年—2010年間,主要研究熱點集中在文化人類學領域,這個階段發文數量也呈現出第一個小高峰,我國體育人類學的研究重心由體質人類學向文化人類學轉變,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村落集群文化生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保護成為主要的研究內容。在2010 年—2013 年間,研究主要關注民俗體育領域,研究者主要從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入手,進行體育人類學研究。在2013年—2015年間,哲學人類學是研究熱點。在2014年—2015年間,由于學界在構建體育人類學學科的過程中不斷探索,逐漸明晰主要研究方向應當是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因此一些研究者又回歸到民族體育的研究上。從2017年至今,關鍵詞開始出現體育人類學,由此可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并逐漸認可這一學科。
從我國體育人類學研究的關鍵詞熱點變化可以看出我國體育人類學學科的發展趨勢,人類學對體育呈階梯式影響,早期的體質人類學對人體測量方法有所影響,在學科正式建立以后,多以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指導學科的構建,當前則進入了體育人類學自身的體系建設階段。
2.4 研究主題的分布及演化分析
研究主題的分布、演變可以直觀地反映出不同時區熱點、分析視角和研究方法的區別和變化。關鍵詞的相關性是對學術論文研究主題的精細化表達,在一定限度上可以揭示學科領域內知識的內在關系。研究人員利用CiteSpace 繪制2000 年—2020 年體育人類學研究熱點的時區分布圖(見圖6)。2000年,人類學、社會學與體育相關聯,說明這個時期體育人類學研究的主要視角是從人類學、社會學角度研究體育領域的問題,這些熱點詞匯與后來的東巴文化、體質與健康、體育哲學、儀式體育等都有關聯,說明我國的體育人類學研究主線是將體育置于人類學、社會學等人文領域的視野中進行研究。

圖6 體育人類學基于關鍵詞的熱點時區分布圖(2000年—2020年)
2.5 研究趨勢分析
2.5.1 預測趨勢一:體育人類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
2020年9月20日,教育部等多部門共同發布文件,要求加快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明確提出了促進跨學科發展的要求。體育人類學研究本身就是多學科融會貫通的研究,在研究中率先倡導文化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的有機結合,利用中國特色的民族文化資源,在學科探索階段充分運用自身的學科優勢進行研究。
2.5.2 預測趨勢二:“一帶一路”倡議下的體育文化傳播與交流
“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重大戰略,始于經貿,綿延于文化。在這一區域中國家和地區星羅棋布,跨度廣闊,具有多民族、多文化的特點。體育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借此機遇可以延展和傳播,隨著“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交流合作的深化,體育人類學可借此機會實現體育文化的國際化傳播。
2.5.3 預測趨勢三:體育人類學的產學研集合發展研究
在國際社會中,體育人類學家并不僅限于傳統體育人類學研究,也傾向于體育賽事、社會異化、大數據等方面的研究。相對而言,我國的體育人類學研究仍然較為傳統,但也應關注社會的發展動態。與研究者的自我專長相結合,以人類學的角度拓展關注的深度和廣度,保持敏銳的思考力,積極參與體育領域的社會治理。
3 結語
研究表明,我國的體育人類學學科并不成熟,仍在探索中前進。學科基礎薄弱和人才匱乏,致使我國體育人類學發展一直處于邊緣地帶,無法在短時間內產生成果,也就導致論文成果較少。
體育人類學研究的是整個體育領域及其文化的表現,在學科建立初期,體育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體育社會學、民族傳統體育學等學科的關系模糊不清,導致這一學科難被認可。多年來,體育界理論研究的短期功利主義色彩過重,忽視了基礎理論的夯實,加之研究隊伍薄弱,使學科難以得到蓬勃發展。今后體育人類學研究應當將理論與實際及未來發展趨勢相結合,充分發揮體育人類學的學科優勢。